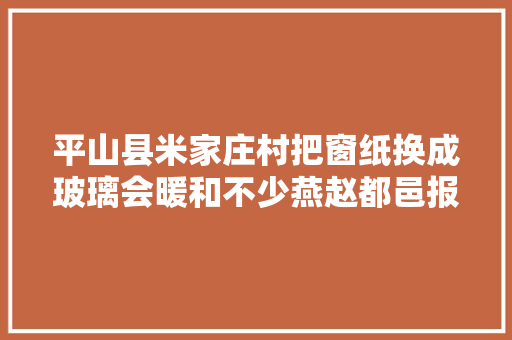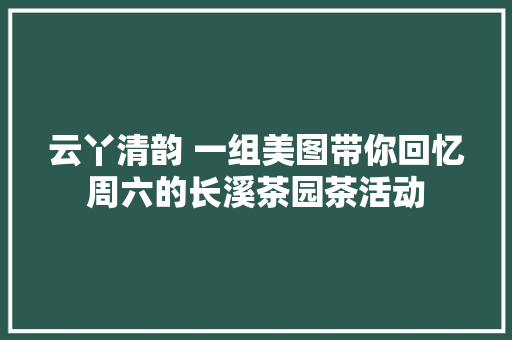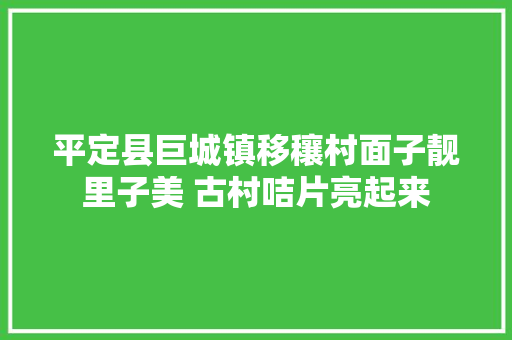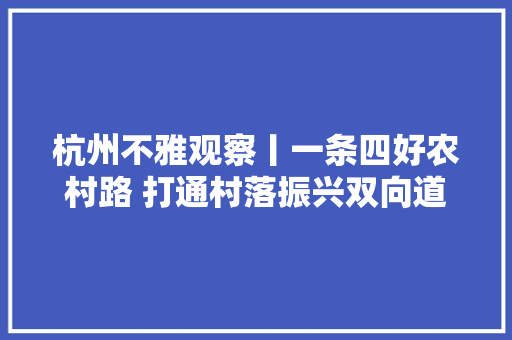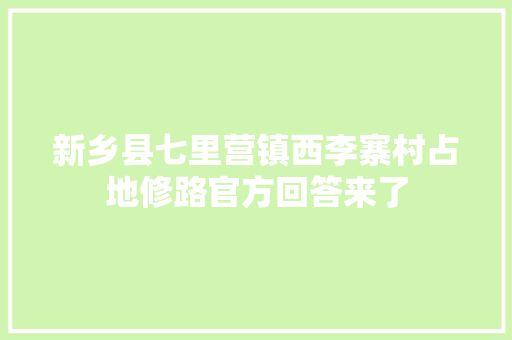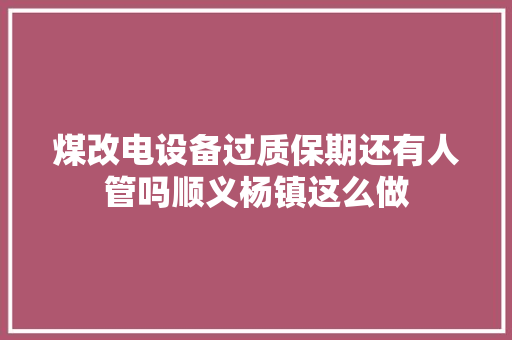此刻,我又一次拿起手机,端详着这张黑白老照片。画面中,一位民国装扮的娇小女子正仰面与一尊俯首低眉的大佛相视。她在想什么呢?佛又在想什么呢?
实在我“认识”这位女子,她叫林徽因。我还“认识”拍下这张照片的人,他叫梁思成。并且不久前,我才从这对夫妻取景留影的地方回来,那里叫小相村落,就在山西汾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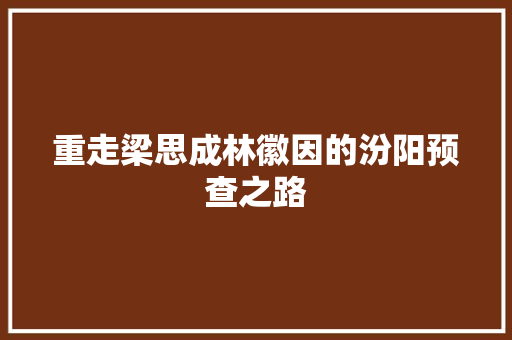
曾是避暑胜地的峪道河
1934年暑假,继上一年稽核大同古建、云冈石窟和应县木塔,梁思成、林徽因再度踏足山西。这一次,他俩应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约请,来到汾阳峪道河。费慰梅在《林徽因与梁思成》一书中说,这是“一个能够让徽因暂时摆脱日常家务的机会”。不过,梁、林出于建筑学家的职业习气,依然带上了心爱的“宝贝”:相机、三脚架、皮尺、历史地理书……结果,说好的避暑度假,变成了以峪道河为根据,四个人或徒步或骑毛驴或租传教士汽车向临近诸县“多次的旅行”。费氏夫妇卖力丈量等较大略的活儿,“思成拍照和做记录,徽因则从寺庙的石刻上抄录主要的碑文”。
那年9月,林徽因以这场“旅行”为写作背景的散文《窗子以外》揭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次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刊登了林徽因执笔,梁、林署名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纪略择要记述了在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和赵城(今属洪洞)八地调查的部分古构。取名预查,是由于梁、林已萌生重返复查之意。但直到1936年10月,营造学社“三进山西”才得以实现。可惜的是,成果还未及整理,七七事变爆发,营造学社匆匆南渡,托管于天津英资银行地下室的大批资料后遭水患毁灭。因此,《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弥足宝贵。尤其汾阳,成为梁、林稽核的绝响。
1934年夏,梁思成、林徽因在晋汾预查路上。 (庞勉供图/图)
时隔八十六年,我也来到了峪道河,背包里就揣着那份《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峪道河的班车时有时无,谁都说不准。汾阳朋友冯师长西席也由于临时有事,耽搁在市里,不能立时驾车赶来会合。没办法,我只好一个人走上被日头晒得发亮的村落庄公路。
身旁,与公路平行的,是一条蒿草、荆棘与石头“打底”的河床,没有一滴水,远近只有横卧的几座水泥桥,连接着两岸平淡无奇的街道。当地人见告我,这便是峪道河,河水在源头就被泵站抽走,供应了汾阳市民。面前的景象,很难让我相信,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还是与北戴河、庐山、莫干山齐名的避暑胜地,“是山右(指山西)绝好的消夏去处”。梁、林到来时,费氏夫妇正住在恒慕义(即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阿瑟·汉默)留下的别墅里。说是别墅,实在是一座因电气磨机问世而“下岗”的磨坊,当地称为“水打磨”。“坊内均铺光润的地板”,“舒适风凉”又“富有雅趣”。那个时候,峪道河沿岸,像这样被洋人买来避暑的磨坊多达数十处,水泉和赵庄两村落最为集中。
连问了数人之后,我才在赵庄以南、公路东侧一片稀疏的白杨林里,找到了仅存的一处磨坊遗址。与许多年往后费慰梅回顾中的描述极其相似,这也是一座大略的平屋小院。然而,已是断壁残垣、房倒屋塌的废墟,根本无从辨认是不是梁、林曾经的住处。一轮半截埋进砖土堆的石磨盘或许知道,可它不会说话。
峪道河仅存的一处“水打磨”。 (庞勉/图)
赵庄坐落在一片山崖上,准确地说,是高踞在一片土塬上。梁、林在峪道河稽核的三处古建:东岩上的实际寺、西岩上南头的关帝庙和北头的龙天庙全都位于赵庄的附近。然而,我转悠了老半天,只在赵庄小学内找到了关帝庙。这间“几经建筑模样形状殽杂别有意见意义”的小庙,门窗紧闭,廊下还堆放着沙石和水泥。通过一块碑,我理解到最近一次的翻修是在2013年。“以风景幽胜著名”的实际寺和“山西南部小寺院代表作品”的龙天庙再也找不到了。那抹“在日光里与山冈原野同醉,冶艳夺人,尤其是在夕阳西下时,砖石如染,远近殷红映照,绮丽特甚”的美妙景致,已如梦幻散去,只有翻开《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的书页,才能逐一浮现。
不过,一位牧羊人见告我,二三公里外的柏草坡还有一座龙天庙。其时靠近中午,栽种着玉米和高粱的塬上空旷沉静,偶有几辆电动车停靠路边,那是村落民下地务农的交通工具。路遇的一位老汉,听说我要去看龙天庙,几次再三叮嘱我进村落后找一个叫武晋明的人。
武晋明是个木匠。在他家的院子里,我见到他时,他正拿着墨斗在给几块大木料弹线。很快,他带我来到村落庄中心的一幢“会堂”样子容貌的建筑前,取出钥匙打开了门锁。在幽暗的楼梯里上高下下之后,一座红墙灰瓦的古庙赫然涌现。此情此景,陡然让我想起梁、林稽核赵庄龙天庙时,也是向村落民索取钥匙才得以入内参不雅观。
这座龙天庙的全称是龙寰宇盘庙,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中轴线上由南至北排列的乐楼(即戏台)、献食棚和正殿还算完全,牌楼、钟楼、鼓楼、东窑均已不存,西窑的瓦顶上有几棵潦倒的草茎……整座寺院的形制与赵庄的完备同等。
顺着武晋明的手势,在正殿的梁架上,我依稀辨认出“大金承安五年……大元国至元二十七年……”的字样。承安五年是公元1200年,至元二十七年是公元1290年。如此看来,这座寺院比赵庄龙天庙(1347)还要悠远了上百年的光阴。
临去时,我拍下了一张武晋明和寺院的合影。镜头里的他,合法心翼翼地锁好正殿的大门。
木匠武晋明,是柏草坡龙天庙的“国宝守护人”。 (庞勉/图)
杏花村落里的寺庙和古塔
我正打算离开峪道河,朋友冯师长西席开车从汾阳市区赶了过来。听说我要去杏花村落转转,他很高兴,由于那里是他的老家。
杏花村落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小村落,它和紧邻的峪道河一样,已升格成统领着十几个自然村落的大镇。《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提到的大相村落崇胜寺紧挨着杏花村落镇,杏花村落国宁寺和小相村落灵岩寺如今则属于杏花村落镇的地界。杏花村落最出名的,当然是酒。从峪道河出来左转东行,沿途招牌中频现的便是“酒”字,乃至车轮下的这段G307国道也更名汾酒大道。当年,梁、林就在这条路上,远远地看见了崇胜寺的翘角飞檐。
“由大殿之东,进村落之北门,沿寺东墙外南行颇远,始到寺门。”那时的崇胜寺殿宇弘大“规模宏敞”,共有六进庭院,山门、天王门、钟鼓楼、天王殿、前殿、正殿(毗卢殿)和后殿(七佛殿),“明初至清末各种的模样形状都有代表列席”。正殿前廊西端还立有一方“任敬志造像碑”,是北齐天保三年(552)的遗物,“劲古可爱”,被梁、林视为极品。清代顾炎武、朱彝尊以及民国王堉昌等名人都曾慕名拜访。
朋友把车停进大相村落文化活动中央的广场,见告我这里便是崇胜寺旧址,中央大楼就建在原来山门的位置。我下车,环绕着充满孩子嬉闹声的广场走了一圈,没有创造一丝可以称得上是古迹的印记。除了“任敬志造像碑”我知道着落(此碑现存杏花村落镇上庙村落的太符不雅观),那些耸立在梁师长西席镜头里的内额、斗栱、格扇、脊饰……都去哪儿了?无人知晓,回答我的是黄土高原上瞬间刮起的风。
崇胜寺如今是大相村落委会所在地。 (庞勉/图)
比起梁、林感叹“雨后泥泞波折,难同入蜀,愈行愈疲,愈觉灵岩寺之远”,我切实其实快捷如风。风还未停,我已经从大相村落抵达一起之隔的小相村落,在为灵岩寺砖塔拍照了。《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说灵岩寺“远在村落后”,“寺址之大,一望而知”。但眼下,砖塔被一道矮墙箍在巴掌大的地块里,与村落路搭界、与民房为伍,塔后是一座看上去崭新的寺院。砖塔官名“药师七佛多宝塔”,建于明嘉靖年间。塔基为石砌须弥座式,塔身为砖砌八角。我数了数,共13层,约30米高。朋友说他小时候常来爬塔,能爬四五层。现在铁将军把住塔门,进不去。
在梁、林的眼里,这座“秀挺”的砖塔“可作晋冀两省一种晚明砖塔代表”。只是他们预查的时候,灵岩寺已被清光绪年间的村落民因械斗拆毁,“十室九空”。一片瓦砾之上共趺坐着五尊明正德年间铸造的铁佛,“铸工极精”。个中“东首一尊且低头前伛,现悯恻垂注之情”。“此时远山晚晴,天空如宇”,梁师长西席抓拍下林师长西席仰面与铁佛相视的一刻,也便是本文开篇提及的那张照片。这大概也是五尊铁佛留给人间的唯一影像了,四年往后,它们被化为铁水,制成了射向日本侵略者的子弹。
和崇胜寺一样,梁、林也是从公路上觑见了国宁寺。“了望似唐代刻画中所见双层额枋的建筑,故引起我们绝大的兴趣及希望”。之以是说“绝大的兴趣及希望”,是由于梁师长西席一贯有一个梦想,要“创造一座一贯保存到20世纪的唐代木构造寺庙”来解开《营造法度模范》之谜。虽然这个梦想延至1937年创造五台山佛光寺才得以实现,但在1934年,杏花村落国宁寺,这座“敕赐于唐贞不雅观,重修于宋,历修于明代”的、业已残破的寺院,的确让梁、林怦然心动过一回。只管接下来的预查弄明白,心动不过是“奢侈的误会”。但梁、林还是忍不住在“做汾酒的古村落”奢侈“血拼”了一回。以至于稽核晋祠前,不得不精减行李,捡出“粗重细软——由杏花村落的酒坛子到峪道河边的兰芝种子——累累赘赘的,背着掮着”,寄存在车站。
汾阳文峰塔落日 (IC Photo/图)
站在汾酒大道旁,看着面前的车水马龙和鳞次栉比的建筑物,朋友也分辨不出昔日国宁寺的准确位置了,一说是杏花高中,一说是东堡小学……但毫无疑问的是,很多年前,有两位年轻的中国学者的身影走过这片地皮,留下了足以让这些寺庙、古塔得到永生的笔墨。
庞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