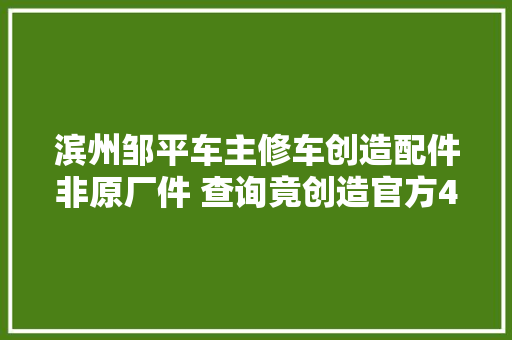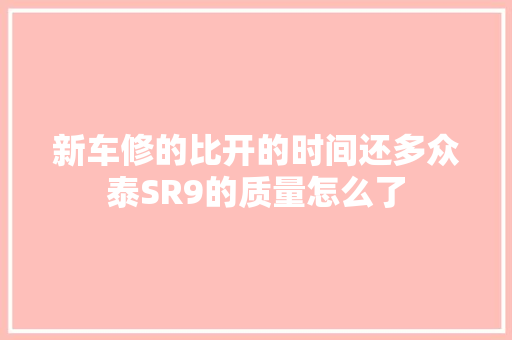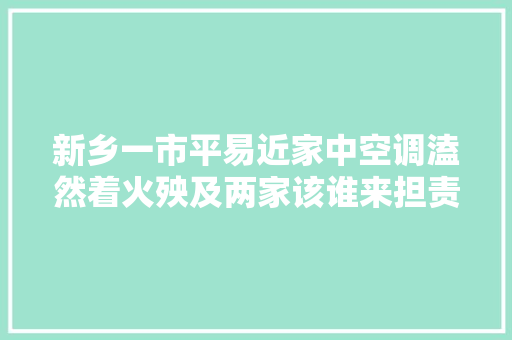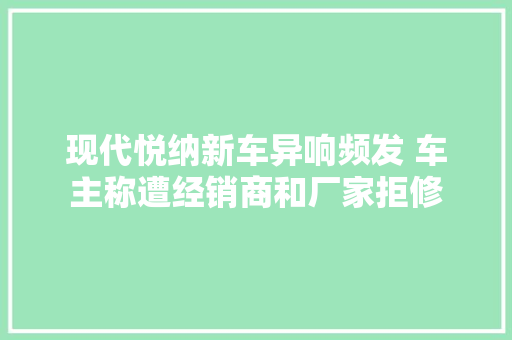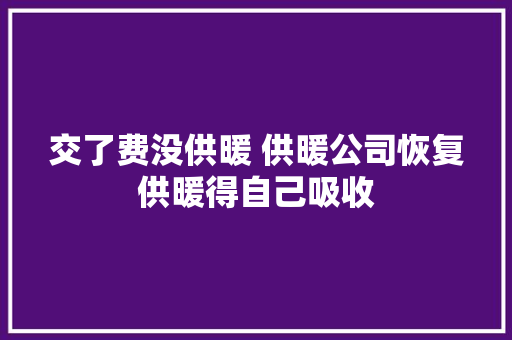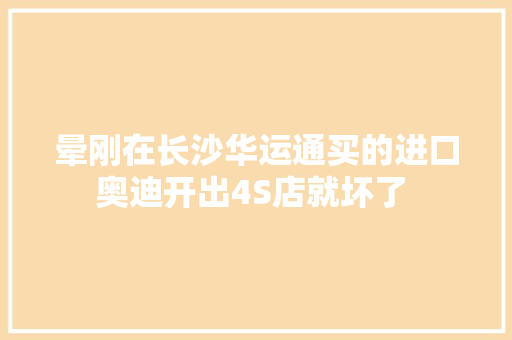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在北京形成了冯玉祥和奉系、皖系的联合政权,保举段祺瑞为临时总执政。

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京召开政变成功后的第一次政治军事会议,决定约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11月10日,孙中山揭橥《北上宣言》。
11月13日下午,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后改为中山舰)从广州出发,明天将来诰日晨抵喷鼻香港,改搭日本“春洋丸”邮船,于17日上午12时许抵达上海,停泊于法租界外滩码头。
11月20日,冯玉祥致电马伯援,请匆匆孙中山火速北上。马伯援当即持电面陈。孙中山告之已决定绕道日本赴天津。
11月22日,乘日轮“上海丸”绕道日本去天津;23日过长崎,24日下午5时许到达神户,下榻于东方旅社。11月30日,从神户乘日轮“北岭丸”赴天津;4日中午安然到达天津,船泊于法租界美昌码头。
11月的天津景象非常寒冷,但孙中山却把帽子摘掉,与两万多欢迎群众相见,接着驱车前往河北曹氏花园访晤张作霖,发言达两小时之久。回到行辕张园(原张勋府第)后,身体即感不适,寒热交作,肝胃作痛,急请德国年夜夫史密特诊视,认为是重感冒兼胃病,嘱停息统统演议和应酬,安心静养几天即可。
12月5日下午,肝痛暴发,不可忍。
12月6日,孙中山热度增高,身边的人都忧形于色。恐德国年夜夫用药未妥,又延请日本年夜夫长田村落会同德医诊治。两位年夜夫见地不一,德国年夜夫说孙中山患的是肝脓肿,日本年夜夫说是胆汁缺少。不过两位年夜夫的治疗方案尚无大异,乃决定仍用德国年夜夫开的药,并贴止痛膏。孙中山觉得似有些效果。
12月8日,孙中山精神稍有好转。
12月10日,病情更有转机,铁狮子胡同行辕门前旁边之人稍觉安慰。
12月25日,请日本年夜夫小菅勇来给孙中山看病。据他说,病情甚沉重。而德国年夜夫史密特则较乐不雅观,说是病情稍有好转,不敷为虑。
12月31日,孙中山致电各报馆,告之即日抱病入都,选择医疗。上午10时,在夫人宋庆龄及汪精卫等随行职员陪同下,赴天津老车站,乘火车前往北京,德国年夜夫史密特随行,下午4时旁边抵达,下榻于北京饭店506房间,别的同行之人则寓居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今张自忠路23号)。入京当晚,即请北京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诊视病状。
1925年1月1日,孙中山揭橥《入京缘由》,感谢各界各团体盛意欢迎:“这次扶病入京,遵医者之戒,暂行疗怅。抵站之时,荷各团体诸君及代表盛意欢迎,深为惭感。俟疾少瘳,再当约谈。”
1月2日,延请协和医院年夜夫狄博尔、克礼,美国年夜夫施美路德士及俄国年夜夫等七人与德医施密特共同会诊,同等认为“患有肝部慢性发炎及肝部肿胀之急性病”。协和医院美国年夜夫建议立时施行外科手术探查,否则不但不能探明病源,还可能贻误病情。孙氏旁边不敢做主,复商于孙夫人宋庆龄,孙夫人亦以孙中山年事已高,恐不禁开割手术。
1月3日,协和医院与孙中山本人发言。孙中山认为自己“曾习医,深知此症难治,然予料予病不深,尚无须开割”,决定用内科治疗,并请德国克礼任主治年夜夫,逐日临诊。
1月4日,克礼和各国年夜夫为孙中山再次会诊,“断其症为肝脏脓疡”。
1月5日,经七年夜夫(德四美三)之会议后,遂共推克礼为主任。初拟施行割治,众颇难之,旋用X光探照,知肝内并未有脓,故决用药针注射,以减其痛,惟戒以勿阅报,勿应接来宾,勿贪硬性食品,藉图静养而免劳累,如是者殆两旬”,而病情毫无转机。
1月21日,孙中山的病情日益恶化,“体温升降忽失落常度,脉搏亦陡异”。
1月23日,克礼创造孙中山的眼球有黄晕,认为是胆汁将侵入其他部分,非施行手术不可。1月24日,孙中山与中医大夫葛廉夫发言,并请其诊病开药方,发言内容如下:
孙:久仰清名,今幸相见。余平生有癖,不服中药,常喜聆中医妙论。昔年有乡亲返粤者,常以师长西席医案示余,明理卓识,不愧名医。余请君以中理测我病机。
孙:夜不成寐,每晚则面热耳鸣,心悸头眩,喧华躁急或胸中作痛,干呕,甚则上气面浮,有时而消。此何故?
葛:此水不涵木,气火上升。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厥阴之为病,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呕吐。若下之,则利不止。所见诸证,全是肝郁日久,气火化风,上干肺胃。以师长西席之遭际,惊险忧疑,心肝俱瘁,又不能孤眠,气血焉不得伤?真水焉得不耗?
孙:此时补救,尚有法乎?
葛:何尝无法,要戒之在怒,不再耗精,不过作劳,破除烦恼。孙:此皆有所不能,将奈何?葛:节之可也。再用药食,以为滋助,已耗者虽未必能复,未耗者尚可保存。
孙:以君之高论,如饮上池。可能为我拟一中药方乎?
葛:可。(乃为拟复脉汤,去姜,桂枝改用真安边肉桂,麻仁改用炒酸枣仁,加生龟板、生石决明、龙齿、犀角片、羚羊片、鲜知母、黄柏。)
孙:君所拟方,以何者为紧张?
葛:张仲景谓厥阳独行,犹夫无妻则荡也。今用三甲复脉汤,加知柏、枣仁,以滋水养肝,安其家室,潜其阳用,引荡子以归家。以是去姜之辛,用肉桂而引火归元,犀角、羚羊、石斛清肃心肺,俾君火以宁,而精灵之气得令,则烦悸不眠者皆蠲矣。
孙:我平生未服过中药,恐不能受。欲以君之药方,转示西医,使师君之法,改用西药,以为何如?
葛:鄙人不知西医,西药能代与否,不敢妄答。(据《医药精华集》葛廉夫《孙中山师长西席病状及治法记》。)
孙中山师长西席
1月26日上午,经年夜夫、家属协商,复要求得孙中山的许可,便于这天下午3时搬到协和医院的特等病房。一到医院之后,或者是由于沿途振动的关系,体温更是加高,面貌与眼珠时时刻刻改变,越变越黄。各年夜夫断定病症到了很紧急的时候,非即刻施行手术不可。下午4时由医士部邵乐尔施行解剖手术,助之者为院长刘瑞恒,始见其肝部坚硬如木,生有恶瘤,遂妥为洗涤,并割取其外皮,以显微镜详加试验,乃断定其症名曰肝癌,允为不治之症。手术25分钟,其后即移入三百零一号病室。7时许即已醒觉,并不觉痛。据主治医云:割治后所经48小时不发热,病状亦无变革,当无危险。惟当时实为最危险之期间,故绝对禁止师长西席旁边入室探视。其吸出之脓,经剖析、化验之结果,断其病已起在十年以前。忆民国五年间,师长西席即患胃病,殆即此肝部之癌作祟欤!
惟时有由本党特聘之俄国医士某君亦亲视其状,既还,乃密语同道谓:师长西席是病远在十年以前,大抵为至微之寄生虫由肠胃而传播肺部以及于肝,遂成为癌,癌则不治。要之,其病由久居热带,于饮食、呼吸之际而生,殆无疑也。
1月27日,协和医院发布关于孙中山肝病治疗经由的第一次报告称孙中山肝部生有恶瘤,病状颇为危险。这天午后,觉得神态渐爽,思进食,乃进燕窝汤。既食,复以蜜柑取汁,热而进之。至五时许安眠至夜,为状均佳
1月28日,孙中山神昏至夜半乃略清,但腹部不痛,因得静睡。
1月29日,孙中山起坐发言如常,因进鸡汤及麦麸粥;手术割口已交合,已撤去所有缝线、绷布。
1月30日,孙中山割治伤口已愈,就寝亦甚安稳。并安慰夫人宋庆龄说:“余诚病,医者亦诚无如余此病何!
但余所恃以支持此身者,夙昔即不完备恃医,而侍余自身之勇气。余今信余之勇气必终降服此病,决无危险。”
2月2日,孙科、李烈钧、张人杰等二十余人抵京侍疾,下午2时赴协和医院探视孙中山,师长西席精神清爽,与孙科、张人杰等发言约二十多分钟。时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均在。李石曾言:“师长西席之病,西医虽绝望,尚有中医可治。石曾即言先延萧医(北京名医萧龙友),萧谓:如能度过立春,当再拟方。又延陆仲安(亦名医之一),彼诊察病症,言尚三成希望。惟师长西席不愿服中药难堪耳!
其意待西医无办法后,再服中医药可耳”。经多人多次劝告,孙中山终不允服,而脉象逐渐衰弱。同陆仲安商量,言或先试服人参汤数日再进药。故劝中山师长西席服人参代茶,并非服药。中山师长西席谓:曾服高丽参精,竟至心脏停滞。因此坚执不允。四日,。五日、六日,均以人参二钱饮之,脉象转佳。
2月3日,德医克礼、美医泰尔和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等将病症真情见告孙中山。“孙师长西席听之甚为安静,而精神倍增年夜胆”。
2月4日,孙中山在病房与协和医院主治年夜夫泰尔发言,泰尔亦劝其改用中医。但孙中山曰:余笃信余之病可望治愈,不必改用中医,且尚有以镭的母(Radium)照治之法,尚未实施,如医院有此种设备,予极愿就此法医治。泰尔以院中有此种设备,可以一试,即允照办。因无法劝服中药,改用参一钱加麦冬煎汤,和于食品饮之,病情较为好转。
2月6日,协和医院开始用镭射治疗,以减轻孙中山的病痛。
2月7日,张人杰奉告孙中山用参和入食品令其服用事宜,中山师长西席言:既如是,勿再和入食品,待予自饮可耳。参汤我人本代茶饮,非中药治病也。后进以三钱,如是连进三日。请陆仲安前来诊治,陆仲安云:舌苔较润,脉反转弱,非服黄芪、党参大补剂不可,仅用人参不敷以治病。中山师长西席抱定非出院不服中药之旨,无法,竟至乃劝饮黄芪羊肉汤,是食品,非药也。以是允之。后更进以黄芪冰糖汤。
2月8日,停滞进参。
2月10日,孙中山身体日益衰弱,脉搏为120次,体温为37.4℃。用镭锭治疗,效果甚微。又据该院院长声称,病者精神目前虽好,但内部实剧损甚重(据云师长西席除肝病外,亦有脑炎病状),现在,稚虫已由血管流传遍体,日内当有变象,恐病者无中兴之望。连续服用黄芪冰糖汤。
2月11日,脉象大佳,每九十六至。又服黄芪冰糖汤(以黄芪二两、冰糖少许)。
2月12日,西医宣言脉象渐弱,并创造代脉。服黄芪四两(冰糖煎服),脚肿略消。陆仲安诊疗,并无代脉,惟脉象转弱,舌苔较佳而不退化,然亦无进步。
2月13日,孙中山病情不佳,双脚又肿。停服中药
2月14日,西医宣告孙中山病危,其生命至多不过七日。以劝进参、芪,师长西席大怒,脉搏至二百四十余至。孙夫人乃抚慰不可发怒,自此再不劝服先方,怒方息。而脉仍百四十余至并气匆匆。以是无法,孙夫人奉告,即以参汤递与师长西席,师长西席亦不详询,即一饮而尽。倾顷,脉搏复旧百至至百十余至。
2月15日,孙中山身体日益衰弱,但并不感痛楚。又进黄芪(四两)冰糖汤。是晨,西医在师长西席前表示绝望。师长西席怒,欲立时出院。告以风大,待越日迁移。商之西医,言此时迁移,在恐至中途必生危险。又决之陆医,彼病之如何不敢断言,至即日移动,必无危险,敢负全责。以师长西席决意欲迁,遂决是议。当知协和,即告年夜夫。年夜夫立出署名通知布告二纸:一、道中发生危险,彼不卖力。二、师长西席生命无生存希望。
2月17日,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致一英文函于孔庸之
孔庸之师长西席转孙师长西席家族暨国民党党员诸君鉴:孙师长西席入本院即发觉所患为肝癌最末期间,为不治之症。经于剖割及将癌之外皮用显微镜稽核,证明诊断为确。病自不好而至极不好,余等以孙中山师长西席之生存为无希望矣。缘故原由是“镭锭本系末了治疗,而其用以四十八小时为限。今用镭锭已四十余小时仍无效果,故断为绝望也”。
2月18日十二时,由医士克礼、刘瑞恒等诊治后,乘协和医院特备汽车,移住铁狮子胡同行馆,并令秘书处发出专心养病、暂时停滞接见和发言之缘由:
奉孙师长西席面谕:
这次搬入行辕,专为疗病,统统来宾,概未接见。凡到访者,派员招待,惟以讯问病情为限。关于军国之事,暂时停滞发言。特此通知布告,诸希谅察。汪精卫将出院倩形,随即电告广州胡汉民:总理受镭锭母治疗,已历四十余小时。协和年夜夫谓此病用镭锭母亦未必有效,且用四十八小时,即当停滞。而连日总理体气日弱,年夜夫屡告绝望,故总理决意出院,迁入行馆调理。家属及同道皆赞许,即于今午迁入,沿途安然。
即日,延请京、沪等处名中医为孙中山诊病,改服中药,延请京、沪、粤三处名中医为师长西席治病(粤医未到京)。移居铁狮子胡同之第一日,京、沪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为师长西席诊病后,所断脉象及所开药方不同。经家属及党人议定,并征得师长西席赞许,决定先由陆大夫诊治。陆出谓:脉象较昨日更差,今幸出院,并无危险,然现状而论,一成希望,尚属勉强,颇抱悲观。今日不必书方,先以黄芪六两、党参二两服之,如毫无转机,则无办法矣。若得半之进步,可另进药。同人以药量过重为疑,商陆略减。彼谓非此不可,时不待人,稍纵即逝也。同人因无他法,随决与师长西席家属同煎服。下午服半剂。晚熟睡五小时。
2月19日,孙中山身体舒适,体温如常。上午又服半剂。晨,大便颇畅,小便亦利,肿消大半,体温、脉搏、呼吸等皆有进步。九时,陆医来诊。诊后,面有喜色,言药已有效,可即书方进药,方如下:黄芪八钱、黄芍、党参五两、麦冬、沙苑子。十一时,德医亦来诊,谓:师长西席今日较佳,或系樟脑注射之效。嘱樟脑吗啡连续注射。上午服别的半剂,下午服新煎药半剂,黄芪加至10两(这天服陆医十六日余下之半,又新煎半剂),晚熟睡八点钟。
2月20日,孙中山病状转佳,肿水全消,精神亦旺,十一时,德医诊后,言:虽病状转佳,然勿以小愈遽抱乐不雅观,肝部渐大,终成绝望。
2月21日,德医克礼发出第三次孙中山病情报告:“现服中药亦不过能令病人减少痛楚,于癌病本根治疗仍未敢望,因癌之进行并不因而停滞也。”认为中药只可有益就寝,减轻痛楚。肝肿日大,家属等勿存奢望。
2月22日,孙中山新患腹泻,身体更弱。
2月23日,腹泻已止,陆仲安为孙中山复诊。据其所开脉案及药方如次:惊悸忿怒,都伤肝经,血沸气滞,瘀浊闭阻,转为肝硬,由硬而疽,日久成浓,升降之机失落度,气血因之大耗。因此神倦食少,足肿瘦削,舌干苔脱,脉象洪数,按之无根。《内经》以肝为将军之官,相火内寄,得真水以涵濡,真气以制伏,庶可见效。谨拟方于后,候酌:耳环石斛三钱 野山参三钱 山萸三钱 寸冬四钱 鲜生地四钱 沙苑子三钱 沙参三钱 甘草二钱。
2月24日,服陆仲安中药无大效后,又请上海名中医唐尧钦、周树芬为孙中山会诊,断为肝血大亏,阳盛阴衰,并施以养血补肝,佐以行气疗法,开出‘三物汤’方,中药有:秦当归身一两,生白芍药五钱、川芎一钱、缕砂仁钱半。服用后未能止泻,反致小便短赤,渗出困难,殊觉苦闷,饮食
2月25日,孙中山益趋衰弱,眠食俱减。
2月26日,孙中山脑腹俱肿,又大腹泻,病体益虚,停服中药,仍由克礼年夜夫用西药止泻利尿。各地名医所寄赠验方均不用。
2月27日,葛辛慈医士自上海来京为孙中山进行精神治疗。
2月28日,孙中山体力日弱,胃不消化,小便减少。
3月1日,孙中山精神略好,所进滋养品略增。
3月2日,脉搏、体温未有变革,惟体力渐弱。
3月3日至4日,病情无大变革。
3月5日,“腹部水分渐增,四肢日呈浮肿之状”。葛辛慈年夜夫于这天停滞推拿。山东年夜夫王纶为孙中山注射日本新发明之驱癌药液——卡尔门
3月8日,孙中山腹部水肿日甚,动作困难。
3月9日,孙中山腹水增加,病势更衰。
3月10日,停滞注射卡尔门,王纶年夜夫推却去。
3月11日,病势垂危,已近病笃之境。
3月12日,上午1:30分,转侧甚盛,厥状极呈不安,喉中哼哼作声,通知进麦秕汤少许,已不能纳,多流出牙床之外。3:10分,喘愈甚,以手抚胸不止,入气甚微。8:35分,通知再进牛乳,已不能启齿。9:10分,两目向上直视,渐不见瞳子,于此病状万分沉重之中,口里仍呼‘和平……奋斗……救中国’‘同道奋斗’等数语,声至朦胧,几不可辨。须臾,又呼汪精卫,张口欲有所言,不能出声,喉中痰益上涌,面益转灰白色,伯仲渐冷,不能动弹。9:30分忽然逝世。享年59岁。
孙中山师长西席遗容
孙中山病逝后,尸体被运回协和医院,由协和医院做尸体的防腐处理,由当时协和医院的病理系主任詹姆斯·卡什卖力进行尸体解剖。对孙中山尸体解剖仅限于胸腔和腹腔,由于孙中山罹病紧张就在肝部、胃部。尸检报告出来往后,得出一个与前面完备不同的诊断结果——胆囊腺癌。年夜夫这时才创造,孙中山的病是癌细胞侵入肝体往后,壅塞胆管,并向肺、腹膜及肠广泛性转移所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