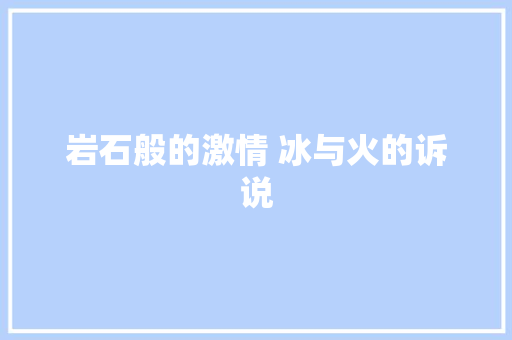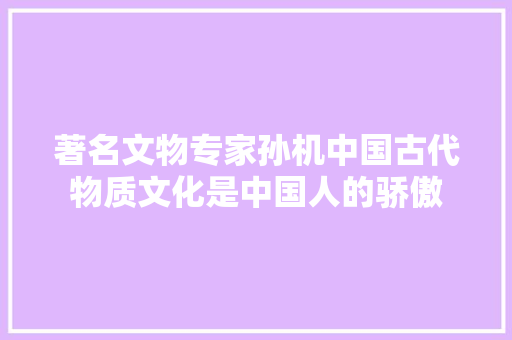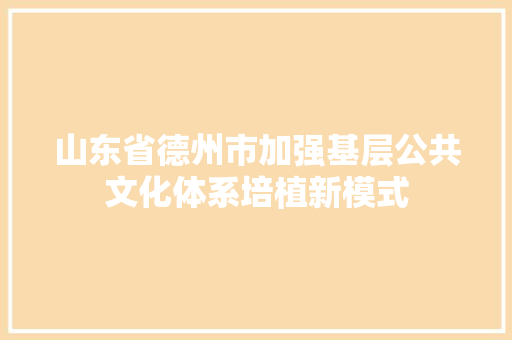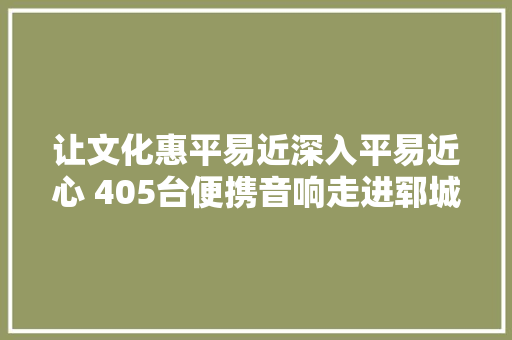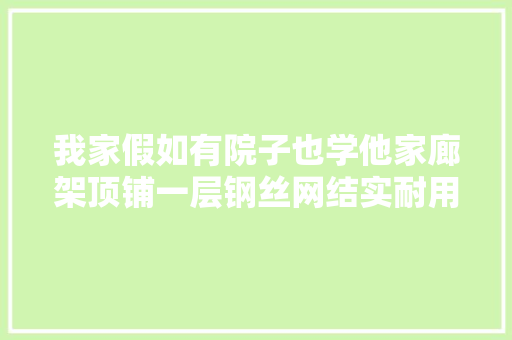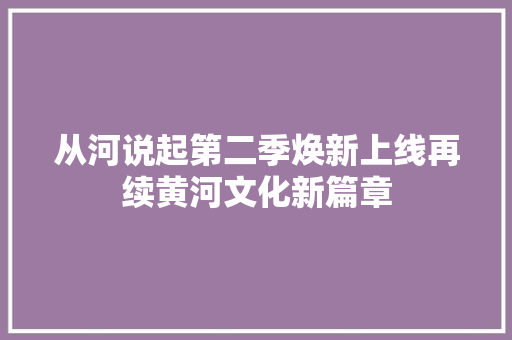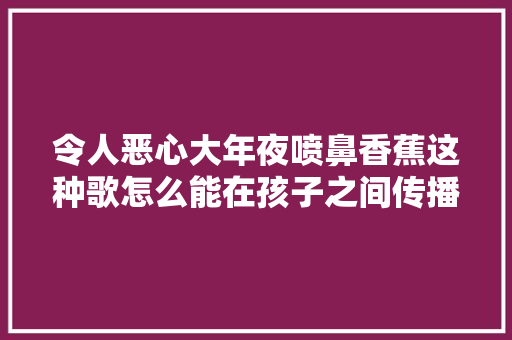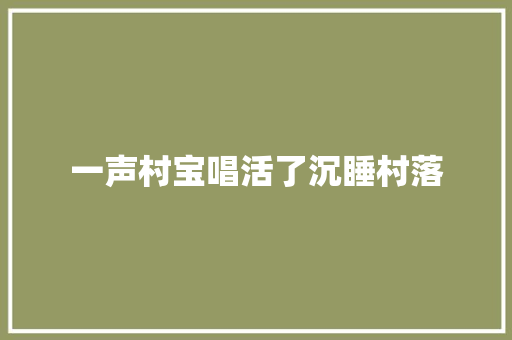作者简介:姜宗福,男,祖籍湖南岳阳,1969年9月出生于湖北石首。曾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主管旅游,因炮轰张艺谋、批评高房价和表露官场潜规则而走红。2010年5月6日调离行政岗位,任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院长助理至今。出版有长篇小说《官路》、学术随笔集《中华汉字随笔》、散文集《瓷禅一味》。
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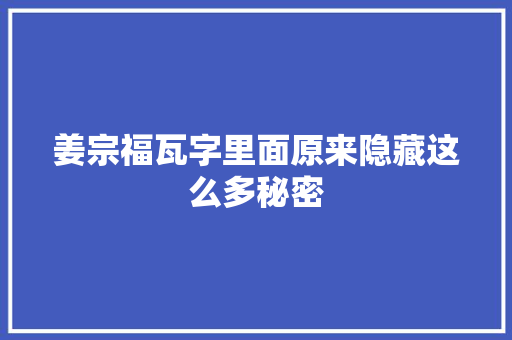
——“颠覆说文解字”系列散文之三
姜宗福
在许多大众的眼里,文化始终是一种很博识的物质,贴在脸上,便是一种光彩。
实在并没有那么神秘。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历经韶光的熏烤,为文所化,便是文化。如瓦片。明朝时候的官员张谷英在渭洞山区造祖屋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用来盖房屋的青瓦有朝一日竟会成为一种文化,还会被当做国宝给保护起来。著名学者江堤师长西席曾经不幸被这样的瓦片击中额头,他不仅不恼,反倒认为是一件幸事。他说,文化是人与韶光拉锯的产物,寄托于某一载体而存在。被明朝、或者年代更为久远的瓦片击中,那血的痕迹,是生命与文化碰撞之后流出的血。他乃至疑惑,生命的每一次痛每一次失落血是否都是文化引起的。我也想探个究竟,便把目光投向那些瓦片,溘然间以为它有了生命,湿湿的,长满了传说,像明朝的眼泪。
我明白,那眼泪是属于明朝的,不属于瓦片。明朝前前后后统共才支撑了多少年呀?不像瓦片,它的文化生命比明朝其实要倔强得多。《说文解字》阐明说,所有的用土烧制的东西都叫瓦。清代乾嘉学派的中坚段玉裁师长西席则认为,土器在没有烧制前叫坯,烧完之后就叫瓦。按照他们的理解,“瓦”字的形状该当是一座窑,那中间的一点则表示在窑里煅烧的坯。也便是说,先有窑后有瓦,瓦的历史在窑之后。我却认为,瓦的生命该当更漫长。古代的“瓦”字,活像屋脊下的一片树叶,中间的“\”代表树叶的叶脉。我们的先人发明房屋的时候还不会烧窑,用来覆盖屋顶遮风挡雨的建筑材料只可能是就地取材。那时森林茂密,树叶自然是最佳选择。这便是最原始的瓦片。后来人们发明了窑,创造用黏土做成坯往后烧成块状,用来覆盖屋面远比树叶稳定、结实,于是便有了瓦。隶书的“瓦”字非常靠近现在的小青瓦的形状,上面的一横代表屋脊,中间的一横表示雨水,右边拖出的一笔,就像瓦背向上的滴水瓦的瓦头(滴水瓦头高下垂的边儿),别号瓦当(呈圆形或半圆形,上有图案或笔墨),全体形状呈现屋瓦俯仰相承的样子。在我看来,房屋是空气中游动的鱼,瓦片是鱼儿身上的鳞,贴上韶光的代码,便是拍卖锤下的文化。可惜的是,人们看重的是鱼肉、鱼油、鱼漂、鱼籽乃至鱼目(可以混珠),对鱼鳞却总是视而不见。秦砖汉瓦,当鱼鳞的瓦和鱼肉的砖取得同等文化地位的时候,已经晚了整整一个朝代。
我们暂且把朝代抛在一边,登上渭溪河边的龙形山上去俯瞰张谷英村落。面前是一片巨大的鱼鳞,鱼鳞上长了许多瓦松(多年生草本植物,叶肉汁多浆,厚而苗条,茎的上部着花,总状花序,花白色。多生在房屋的瓦垄上或山地岩石间),恢弘,但悲情。只管张谷英曾经是朝廷命官,但毕竟成了草民。草民有草民的颜色,以是砖瓦一律是草木灰的颜色,而不是黄地皮的颜色。天子是黄土,百姓是淤泥。皇天后土,黄土的颜色属于天子。以是宫廷的瓦上了金黄色的釉,内层依然是土,代表大地,表面却镀了一层琉璃,金碧辉煌,显示皇族的崇高血统。天子崇拜孔子,迷信佛教,孔庙和寺庙的屋顶覆盖金黄色的琉璃瓦,那是皇上的恩赐,皇恩浩荡,昭示天下。草民是不可能享受这种恩赐的。他们的房舍只能盖草灰色的蝴蝶瓦,也便是中国民居用得最遍及的小青瓦。由于草民的瓦是泥土烧制的,泥土是廉价之物,以是瓦器就有了卑下的含义。连屈原都瞧不起它们。屈大墨客在他的《卜居》一诗里说:“黄钟毁弃,小人得志。”他把“黄钟”比做贤良之人,把“瓦釜”比做平庸之辈。意思是说,贤良的人不被重用,而平庸之辈却窃居高位,得意一时。瞧不起瓦的还有壮士。有气节的人嘴上常常挂着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表达了一种宁死不屈也不做下贱的没有气节的瓦片之英气。壮士轻看瓦片也就算了,连草民都轻贱瓦片,的确令人憋屈。在民间,每逢生男生女,乡民们都免不了指鸡骂犬地把瓦片阴损一番。生男孩叫“弄璋之喜”,“璋”是古代贵族所用的一种玉器,是崇高的象征。生女孩叫“弄瓦之喜”。古时候妇女纺织用的纺砖(纺锤)是用黏土烧制的称“瓦”,表明这个孩子将来终年夜只能从事纺织一类的事情,含有卑下的意思。清朝期间,无锡名流邹光大接连生了好几个女儿,每次都给好友翟有龄发喜帖。翟红包掏了又掏,烦他,便赋诗一首作贺礼,讽刺他的妻子是生产瓦片的土窑。诗云:“去岁相招云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寄诗上覆邹光大,令正(您的妻子之意)原来是瓦窑。”诗很诙谐,亦引人发笑,但笑过之后呢?
笑过之后是悲哀。
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情由轻贱瓦器。它就像一件廉价而实用的蓑衣,为我们遮挡风雨,听凭肃杀的寒流凌迟,不攀比不寄托不屈就;如佩戴在白墙上的头钗,侵润在小桥流水的水墨画里,在欸乃声中呼吸,一点暴躁也没有;又像匍匐在男人怀中的新娘,日日更新阳光和风雨的姿势;更像一枝幽兰,在灵魂里盛开,弥漫一种永恒的圣洁。瓦器是文化的喷鼻香火,听凭历史的风吹雨打,历史毁灭了,可瓦砾(破碎的砖头瓦片,形容建筑物被毁坏后的景象)还在,它们倔强地堆成废墟,扒开岁月的土层,透过碎片就可以找到文化的蛛丝马迹。文化是靠废墟来延续的,瓦器是文化断层的焊点。精心地焊接,耐心地修复,可以填补历史的漏洞。
这让我怀念宋朝。
宋朝和元朝,是草根文化最为繁荣的期间。那时,都邑中的游乐和贸易场所称为“瓦子”、“瓦舍”、“瓦肆”或“瓦市”,演出杂居、曲艺、杂技的,买药、卖布、打铁的,饼铺、酒店、茶楼林立,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沿清明河一起繁华。为什么这些热闹的场所无一例外的都带了“瓦”字呢?由于这些店铺皆系草民所开,屋顶面的都是草灰色的小青瓦子,称“瓦舍”,瓦舍相连便成“瓦肆”,“瓦肆”相连便成“瓦市”了。还有一种说法:“瓦舍者,谓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吴自牧在《梦粱录》中阐明说,游乐贸易的人互不相识,就像一堆散土临时捏合在一起,完事后就像碎瓦一样各自分散,以是称“瓦”。这种说法我认为是很牵强的。“瓦解”并不是指瓦易碎,而是指瓦呈弧形,一片一片叠放在一起,用绳捆之不宜散开,既省空间,又便于搬运,谓之瓦合。如将绳解开,瓦片会散落一地,谓之瓦解(比喻崩溃或分裂/使对方的力量崩溃。如~仇敌)。过去瓦片烧好之后,层层瓦合,放置于土台之上,土台垮塌,瓦片散落谓之“土崩瓦解”。这个词具有光鲜的无产阶级革命色彩。如果封建统治者不施仁政,荒淫无度,就会失落去老百姓的支持。老百姓是土,土台子垮了,政权也就“土崩瓦解”了。中国历史上最昏庸的帝王当属隋炀帝。翟让在河南滑县的韦城瓦岗寨起兵,调集天下的瓦民,建立起了强大的瓦岗军,颠覆了天子头上的那片琉璃瓦。那些小青瓦们,经由了历史和文化气流的熏烤,已不仅仅只是普通的瓦块。透过这些青瓦,我们看到的不纯挚只是小雨缠绵,还有民生,还有国命。它如同一个气场,气场散了,繁华不再。如今,用宋词堆砌而成的宋朝早已气数已尽,消逝在了历史的风中,它的繁华被张择端画进了《清明上河图》,原件进了博物馆,复制品被挂进茶楼酒肆,成了一道搔首弄姿附庸风雅招徕客人的伪文化招牌……
张谷英无需这样的招牌。它的每一片青瓦都被精神打磨过,建筑与风水被艺术粘合,十全十美,通过无数个天井吸纳润湿的地气,获取了一种文化的真气,因而得到了生命。夕阳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封建王朝,化成一缕缕淡蓝淡蓝、淡得靠近于草灰色的炊烟,还瓦片以生活的本色,阔别了战火,阔别了苍茫,阔别了盛衰。“瓦”从此不再卑下。王朝消逝了,琉璃瓦终于低下崇高的头颅,步入了大众生活。小青瓦亦不再自卑,成为了民俗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就连“瓦”字,其地位也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纪念英国科学家James Watt发明了蒸汽机,1960年,国际计量大会第11次会颠末议定定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国际单位制中功率的单位。中国人在翻译他名字的时候,把这一无尚的光彩给了“瓦”字,音译为瓦特。日本人紧随其后,将煤气、沼气等老百姓必不可少的可燃气体由英文gas翻译过来,取了个中文名字叫“瓦斯”。还有,保护汽车发动机曲轴的钢套被称作轴瓦;自行车、三轮车等车轮上安装轮胎的钢圈被唤作瓦圈……瓦特是电的功率单位(电压为一伏特,通过电流为一安培时,功率便是一瓦特,也便是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量的乘积。简称瓦),瓦斯是居家必备,轴瓦、瓦圈乃汽车、单车、三轮车必不可少。这些外来的光彩虽与瓦片无关,但与生活有关。而百姓的生活又与瓦片息息相关,所有的日记都记在上面,每翻一页便是一个日子……
不知道张谷英在明朝的时候是如何过的日子,古村落那连片如鳞的蝴蝶瓦上泛黄的记载已经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天光暗淡下来,万家灯火次第,外出的人陆续回屋,皮影开始活动。我不是瓦匠(即瓦工。指砌砖、盖瓦等事情/做上述事情的建筑工人),亦没有瓦刀(瓦工所用的工具,多用铁嵌钢制成,形状略像菜刀,用来砍断砖瓦,涂抹泥灰),不会煅烧、更不会安装这些民间的瓦片,但我完备可以以一个文化仰望者的姿态倚在这些成堆的烟熏味十分浓郁的瓦片上去读历史,读生活。我亲眼读到那些大日子小日子从张氏子孙的家里顺着古老天井的光柱爬上屋顶,在瓦片上跑来跑去,高枕而卧、欢声笑语,一副乐享明日亲的样子。我举头望天,浩瀚无垠的天幕如一张硕大无比的瓦片将我覆盖,我顿然领悟了苍生的含义:
苍天如瓦,挡住众生,那是国命。屋顶瓦(读wà,动词,盖的意思)瓦,遮风挡雨,那这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