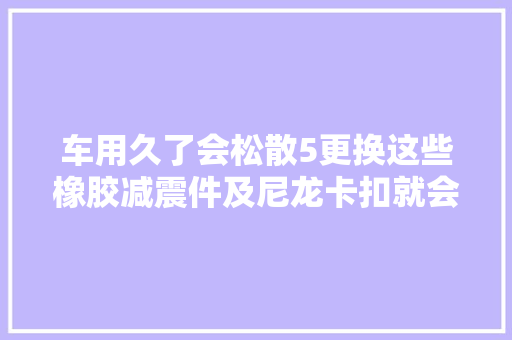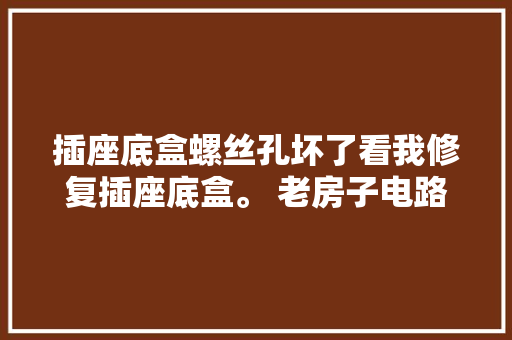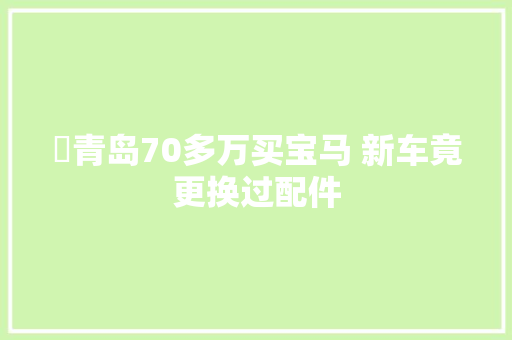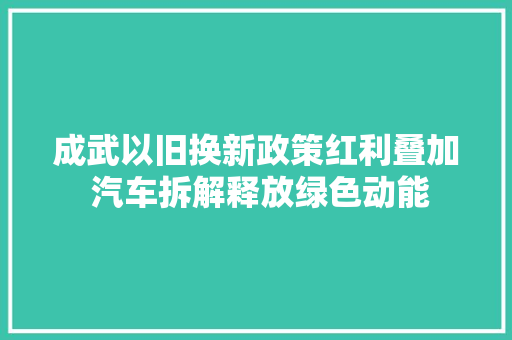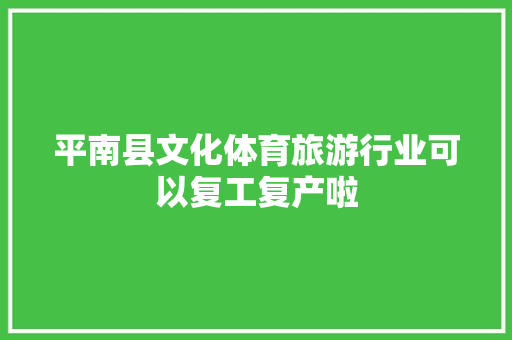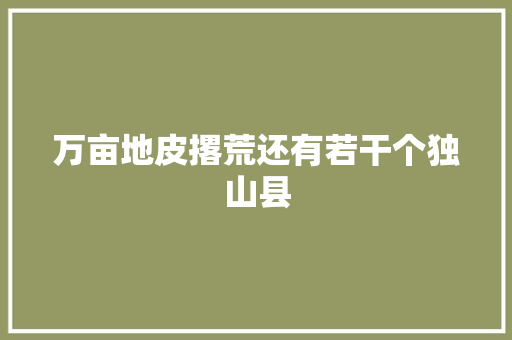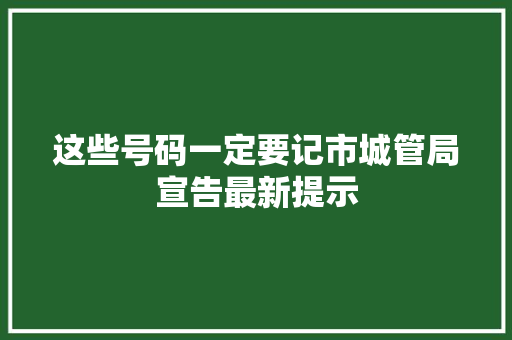加格达奇,鄂伦春语樟子松成长的地方,是大兴安岭特区首府。自一九六四至一九八三年,铁道兵第三、六、九师奉命开往大兴安岭,八万余官兵爬冰卧雪,风餐露宿,逢山开路,遇河架桥,施实了震天动地的铁路培植,为大兴安岭开拓立下了不朽功绩。我有幸成为这支英雄部队中的一员。加格达奇,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加格达奇是大兴安岭地区一座边陲小城。小城后边是连绵起伏的大兴安岭余脉。一条宽约百米清澈见底的甘河,临小城面前滔滔流过,汇入嫩江。加格达奇是前有“照”,后有“靠”,一方窝风旭日风光无限的风水宝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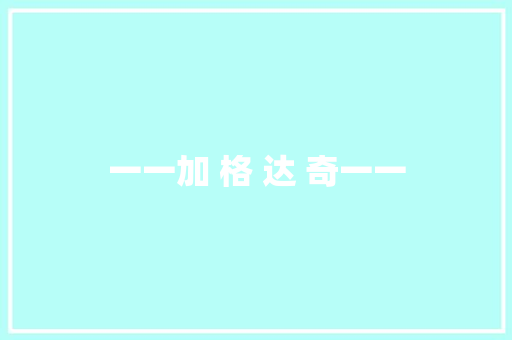
大兴安岭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直至六月中下旬,春天才
一九六六年春,我们新兵营从辽宁大石桥登上了铁皮闷罐专列,一起“咣当当咣当当”向加格达奇进发。闷罐车内铺了谷草,我们吃喝拉撒全在车上。白天,新兵们席地而坐相互拉歌。“背上了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雄壮的那个军队浩浩荡荡”……那首雄壮豪迈的《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军歌声一阵高过一阵。
夜间,车顶上挂一盏阴暗的马灯照亮,随着列车的颠簸和“咣当”声,马灯一直地悠来荡去,愈发显得原始与苍凉。不管这天间黑夜,有谁要大小便,要拉开闷罐车厚重的铁门,或站或蹲在门口边沿,车内有一两个人使劲拽着,以防人掉到车下。不少人对这样拉撒很不习气,或站或蹲在门口边沿,十多分钟完不成任务,把屁股冻得猫咬似的痛。
列车在大兴安岭的夹缝中穿行。车外,除了皑皑白雪和黑白相间的原始大森林,一望无际的枯黄草原,还有大片大片的草滩和湿地,显得原始与荒凉。我们第一次目睹了未开拓的大兴安岭真容,一块为数不多的未开恳的处女地。
列车运行多时,铁道两侧未见有村落落,只见一座连一座白色帐篷打起的军营,时时传来战士们一阵阵“杀!
杀!
杀!
”练拼剌刀的喊“杀”声。大兴安岭,到处都充斥着“苏修亡我之心不去世”战役一触即发的炸药味。一九六九年初春,苏修侵略我珍宝岛,我们打起背包,连续几天拥枪而睡。只待一声令下,随时准备开往前哨。
在一个北风呼啸,晴天雪纷纭扬扬的清晨,在一阵阵“叮叮当当”欢迎新兵的锣鼓声中,我们走进了加格达奇,走进了白色帐篷打起的军营。大兴安岭用“寒冷”这特有的“见面礼”,欢迎我们这队初来乍到的新兵,有点儿不太友好。我们也知道了大兴安岭严明冷漠有余,温顺热烈不敷的粗暴脾气。
战士不言苦。新兵连战士大都写岀了“担保书”或“决心书”,表示要到最艰巨的地方,接管煅炼和磨练。我们对部队“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教诲,很不以为然。新兵营大都是屯子兵,早已练就了一身吃苦刻苦的硬功夫。能吃了屯子的苦,天底下还有什么吃不了的苦?只要不饿肚子,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
“洒尿要用棒子敲”,那是笑谈。吐口唾沫,落地成冰却千真万确。大兴安岭最低气温可达五十七八度。据传,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心曾派员开拓大兴安岭,终因招架不住“生命禁区”的寒冷而三进三出。一九六四年,中共中心,国务院,中心军委一声令下,铁道兵三、六、九师浩浩荡荡开进大兴安岭,并落地生根着花结果。
大兴安岭来了铁道兵,便有了活力。沉寂的大山顿时人声鼎沸,热火朝天。广大官兵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神圣义务,施工、军训、站岗、巡逻……清晨,军营传出了悠扬的起床号声,传岀了“一、二、三、四”洪亮清脆的出操口令声。大山里有了歌声、笑声、欢呼声,还有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声。
大兴安岭没有青菜,部队官兵每天吃萝卜干,茄子干,芸豆干,学名叫“脱水菜”。炊事班费尽心机换着花样做,干菜还是嚼不烂,犹如嚼蜡。屯子兵嘲笑城市兵娇贵,吃干菜怎么了?比榆树皮,榆树叶好吃多了。韶光一长,许多官兵得上了夜盲症。
转过年来,部队官兵业余韶光开荒种菜。大兴安岭,有史以来头一次长出了土豆、黃瓜、茄子,还有青椒,芸豆等等。部队的菜园绿油油的,长势喜人。后来又养了猪,部队生活才有所改进。当地老百姓见部队种菜,深感稀奇,也学着部队种起菜来。敢在大兴安岭种菜,部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漫长的冬天,部队官兵大都吃雪水。后勤部修理营制造连打出了加格达奇第一眼深水井,听说深达七八十米。井壁上结的冰,常年不化。制造连把水井当了冰箱。杀了猪,用绳子将猪肉吊在井内冷藏,效果极佳。
那时,大兴安岭地区被称为反修一线。夜间,各色旗子暗记弹不知从哪个山头或山后,会溘然腾空而起,在夜空划过一道道刺眼的亮光。有时旗子暗记弹竟打进兵营,乃至落在哨兵脚下。部队立即组织兵力,对山头进行拉网式搜索,抓捕特务。但每次都无功而返。久而久之,部队便泰然处之。这点小伎俩,除制造一点点紧张空气外,別无他用。
退休后,我携老伴共去过三趟加格达奇,每次都有一种久违回家的觉得。老伴也曾见过一些世面,到了加格达奇,便大加讴歌,直呼这里是最美的地方。我不知道老伴的话,是不是因我在此当过兵而爱屋及乌,但我相信,老伴的话绝对是发自内心。
我和老伴先去看我当兵时的营房所在地,这里早已高楼林立。昔日部队靶场,也建筑成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公园。几处大熊猫及恐龙等动物雕塑,错落有致装点个中,凭添了几分新意。只是几棵人造椰子树,显得虚假而不谐调,有点不伦不类。
宽约百米清澈见底的甘河,仍旧那样宽容和顺。两岸河堤,也早建筑成柳绿花红的滨河公园,游人如织,热闹非凡。垂柳树下,有几人旁若无人悄悄垂钓,更显诗情画意。
原营房后山,更是要去的地方。沿盘山路往东约二三里路,便是原总字五O五司令部后山。大兴安岭特区政府,在此建筑了高耸的不锈钢材质的铁道兵开拓大兴安岭纪念碑,阳光下熠熠生辉,成为加格达奇标志性景不雅观。
纪念碑上,记载着铁道兵三、六、九师开拓大兴安岭的劳苦功高。自一九六四至一九八三年,共建筑铁路八百四十七点二六公里。桥梁一百二十四座,六点五五二公里。隧道十四座,十点五七三公里。超过三百名官兵殉职。
我在纪念碑下肃然站立,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五味杂陈,说不清是啥滋味。是思念?是追忆?是凭吊?是展望?大概都是。但日月匆匆,统统都成过眼云烟。
我把稳到纪念碑上的几个主要数字,铁路、桥梁、隧道,这些反响功绩的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的三位数。而殉职人数,本是最随意马虎统计和节制的,却说是“超过三百名兵员殉职”。“超过”是一个很模糊的观点,令人费解。我想,这大概是分外年代的分外用词。
翻过山冈,一壁西旭日的山坡上,有一处偌大的义士陵园。长眠在这里的,大都是和我险些同期从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陵园内荒草凄凄,野蒿有一人高。坟茔和墓碑都掩蔽在荒草之中。
我在坟茔中流连许久,梦想数一数有多少位战友长眠在这里。无奈,数了几遍都没有成功。我站在陵园前,脱下帽子,为战友们深深地躬身致哀。
五十多年了。长眠在这里的战友们,可曾想起自己的亲生父母,想起自己的兄弟姐妹,想起身乡的父老乡亲?我知道,你们啥都不想了,你们早已把自己的青春与生命,献给了铁道兵这个光荣称号,献给了高高的延绵一千二百公里的大兴安岭。
长眠在这里的战友们,大概并不孤独和寂寞。有三百多位战友永久留在了大兴安岭,差不多有两个连啊!
你们每天都能看到一列列火车,在你们亲手建筑的铁路上飞驰,每天都能听到火车的一声声气笛的长鸣。这些,都是你们生前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如今,早已变成了现实,你们该含笑地府了,唯愿战友们在天国安息。
我和老伴这天间乘车离开加格达奇的。列车驶出加格达奇,我透过车窗玻璃,贪婪地看连绵的大山,看茂密的森林及统统景致。我溘然创造大片大片的原始大森林,还有大片大片被称为“地球之肾”的草滩和湿地,已被开拓为农田。铁路两侧,时时会涌现一个不知啥时候出身的村落落。
这让我想起加格达奇西侧那一大片长满塔头草的湿地,早已高楼林立。西山坡上一眼望不到边的原始大森林,也早被砍伐殆尽,如今是一个乡政府所在地。听说,那里是“棚户区”改造的重点区域。
对森林资源的如此开拓,好与不好,我不敢妄议。人说历史是公道的,那就留待历史去评说去定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