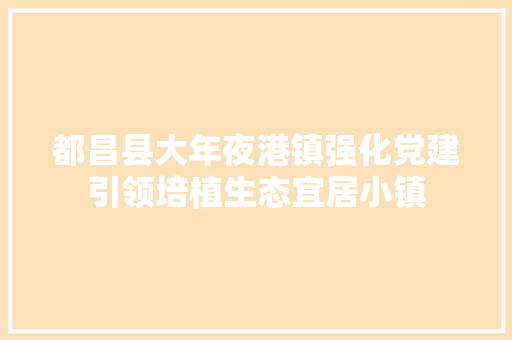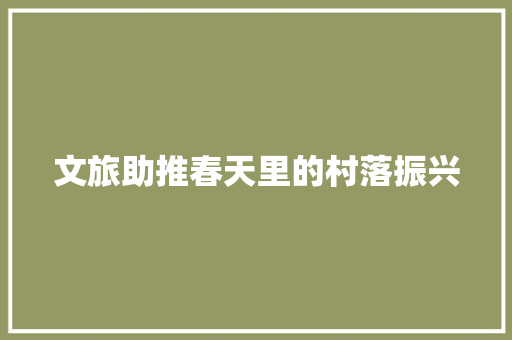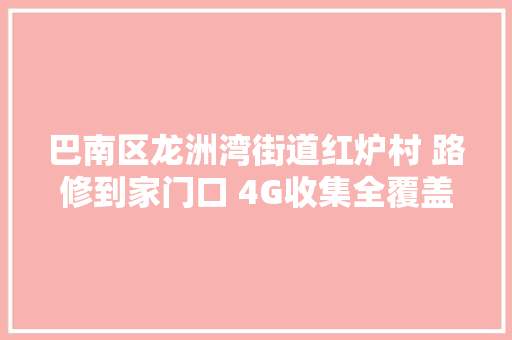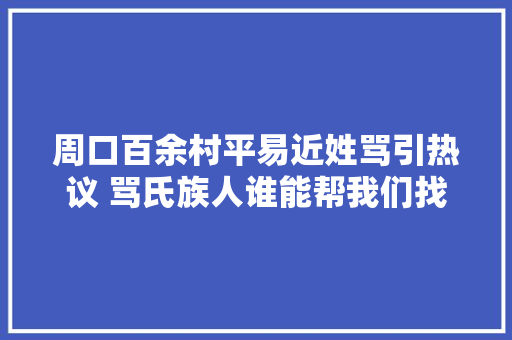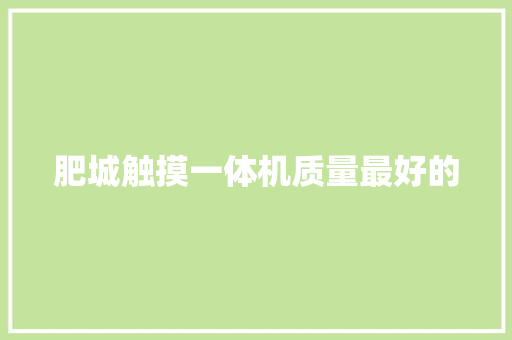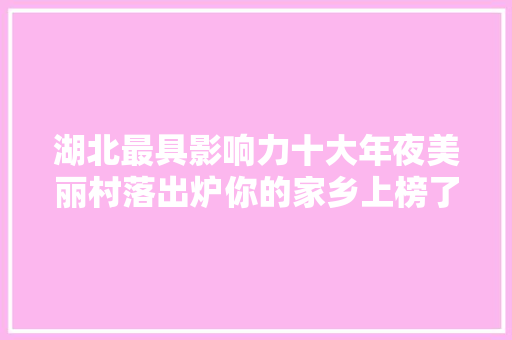站在穿云破雾气势磅礴的龙江大桥边,同样感慨。2007年出差到腾冲,腾冲机场尚未通航,需从保山翻越高黎贡山,走的是老滇缅公路的线路。山高谷深、弯多路窄,初到云南的忍不住拉紧门把手,腿肚子都发软。2011年采访完盈江地震,从腾冲坐大巴车返回昆明,许多路段高速尚未通车,路上竟花了十三四个小时。
与比较,龙陵县邦焕村落的村落民们体会更深。邦焕村落在龙江大桥底下,是个传统农业村落。村落民刘从珍家里开小食馆十多年,她专门手写了大桥通车带来的变革交给:在建筑期间,村落民务工人为由每天三五十元涨到一百多元,农人种的蔬菜和养的猪鸡鸭鹅都脱销,附近群众的钱包鼓起来了;修起大桥后很多游客来看大桥,还有国际拍照师,来我们这里用饭……在村落上干了二十多年的老支书王宝昌如数家珍:桥修睦后进村落道路也硬化了,大卡车开进村落,如今村落里每年出栏生猪两千多头、发卖二百多吨茶叶和三百多吨无筋豆,村落和颜悦色均纯收入早就过了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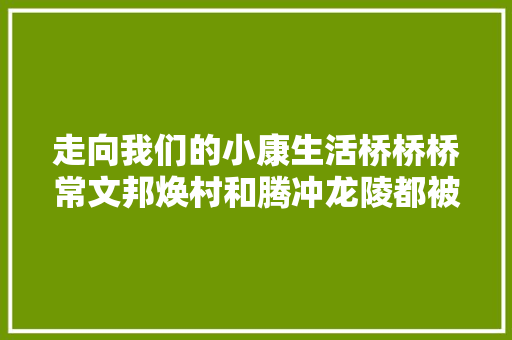
提及这些年云南交通培植的成绩,省交通厅总工程师吴华金也变得抒怀起来。他自满地先容,2018、19两年,云南交通培植投入都超过两千亿元,在全国稳居首位,近四年来的投资额,是十二五期间总和的1.76倍。“过去用15年修了三千公里高速公路,今年一年就要修这些”,他说:“云南村落庄也普遍通硬化路、客车和邮路,农人在家收快递,站在村落口招招手坐客车。”
吴华金还先容,如果说以前修桥是渡过来、跨过来,现在则是高空作业“飘过来”,目标也从通达、通畅到通得绿色便捷。“我们把世代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大山里确当地人送了出去,也把全天下的客人请进云南的大山回物化然”,吴华金说。他以为,修路架桥最主要的变革,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时,从大开大挖毁坏山体植被到“为树让路、为水改道”,在生态环保的理念下“把公路镶嵌进大自然”。
常文在老家门口修桥,还有一段佳话。他的爷爷作为乡绅,抗日战役后曾率领乡亲们修复了被炸毁的桥。那座不通汽车只通人马的老桥犹在,记录一段沧桑岁月。当年修桥用的构件,不得不拆了废弃坦克再到铁匠铺人工打造。而如今,龙江大桥的设备早已基本实现国产化。大桥主缆用钢从入口的六七万一吨,低落到国产的两三万每吨。祖孙修桥,也折射着历史变迁和国力变强大。当地人有新桥落成时“踩桥”的习俗,即将远行的游子,也会到附近的桥边祭拜。常文说,有老乡从四十多公里外专门赶来,就为了看看大桥,如今龙江大桥边,也拴了许多代表美好祝愿的红绳。
今年8月15日,腾冲到陇川的高速顺利通车。这意味着,从腾冲到瑞丽再到芒市全程高速,滇西南“自驾游金三角”形成。对此常文说,边陲的发展和祖国越来越紧密的连在一起了。而吴华金更表示,如果说云南以前姓“边”名“陲”,如今则正在改名换姓,变成姓“前”名“沿”、姓“枢”名“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