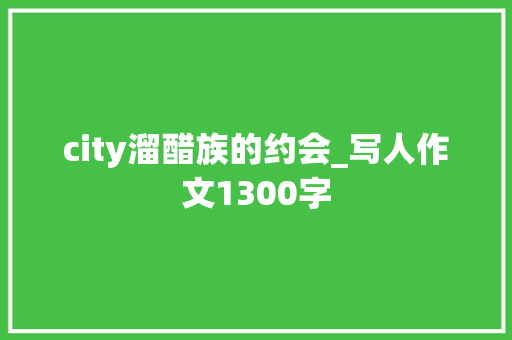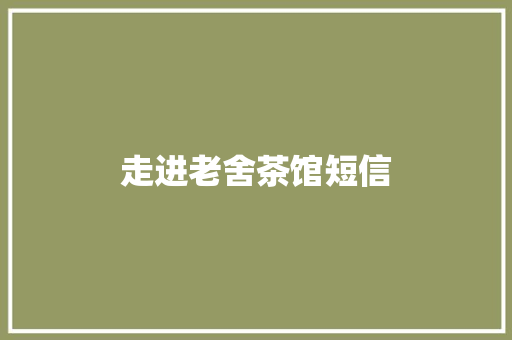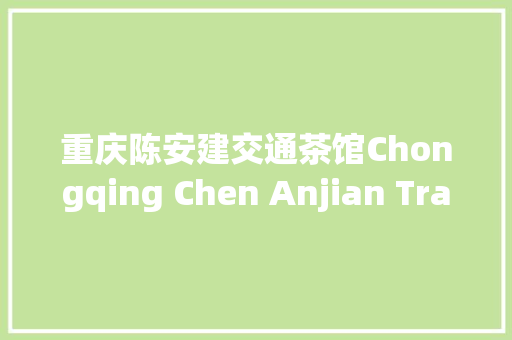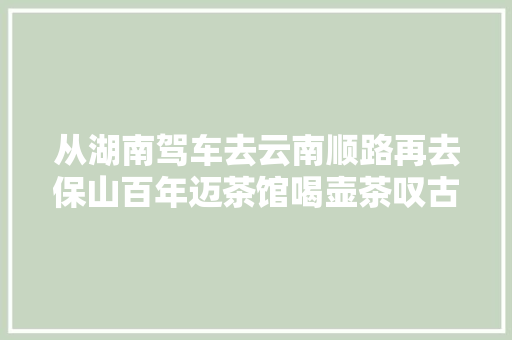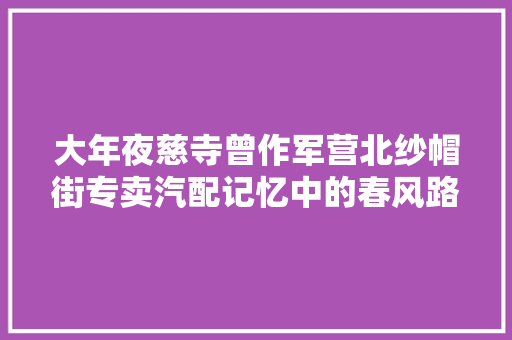2000年7月的一天,我去了大慈寺,在里面的大慈庄和文博大茶园坐了好几个小时。
大慈寺是成都有名的寺庙,建于魏晋期间,在唐宋规模达到极盛。里面有精美的壁画,明末大慈寺毁于战火,清末重修,但是规模大大缩小,室内的壁画也没有规复。在全体清代和民国期间,这里的喷鼻香火十分兴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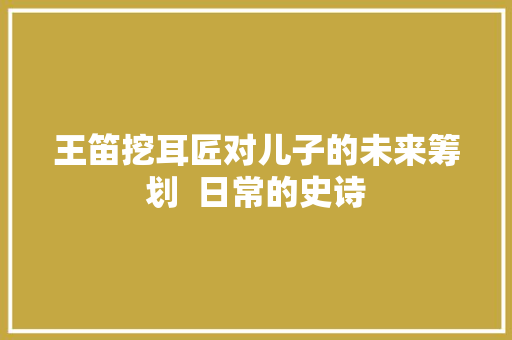
1966年,我家从布后街2号搬到了东风路(本日的大慈寺路),就在大慈寺的对面。东风路是成都新开辟的一条大道,从公民南路(本日的天府广场)开始,过总府街、春熙路、东风大桥、水碾河,一贯到五桂桥,进入到工业区。再连续往前走便是龙泉驿。虽然这条路很长很宽,但是车实在并不多。记得我有一段韶光晚上还常常在大马路的路灯之下打羽毛球。
“文革”期间,大慈寺成为成都防备司令部驻扎地,进进出出都是军人。正是由于军队的长期进驻,大慈寺的建筑没有遭到进一步的毁坏。但和成都的文殊院、昭觉寺不一样的是,大慈寺因此很永劫光没有和尚和喷鼻香火。1982年开始,那里成为成都邑博物馆办公的地方,并在1984年对外开放。 那个时候成都邑博物馆在大慈寺的几个大殿也有一些展览馆,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多少茶馆,特殊是文博大茶园,充分利用了大殿的回廊和院落,还有藤蔓架子、树荫下面,都是品茶的利益所,所以是一个非常有情调的茶馆。那里所用的有扶手的竹椅、木桌,外加三件套的茶具,都是过去成都老茶馆的标配。
四川省文联的一些先生长西席,退休后都喜好在文博大茶园聚会谈天,像流沙河、车辐等著名作家文人,都是那里的常客。我父亲退休往后的许多年里,每周也有一天固定的日子,在茶馆与同事们碰面。
在大慈庄茶园门口地上,立有个牌子:“大慈庄,茶、饭、棋牌,10-15元,耍一天,韶光:8:00-22:00”。其余,后面还有一个固定的大招牌,上写:“大慈庄,亭苑风格,环境优雅,酒菜飘喷鼻香,欢迎惠顾。主营:川菜,棋牌,茶,零餐,包席,丰俭由人。”然后是业务韶光和订餐电话。
这种到茶馆聚会的模式在成都非常盛行,费钱不多而且方便。喝茶、谈天、打麻将都包括在内了,只不过10块钱到20块钱。大家谈天吃午饭,喜好打麻将的,午饭往后还可以打打麻将,这样既联结了感情,也有了娱乐。
这是一个茶饭一体的茶园。走进圆形拱门,里面为一院子,左边有一小池塘,上有一亭,里面有一牌桌,木椅子多少,池内有鱼。
右手是一搭有藤架的回廊,下面有八九张麻将桌。现在正是中午,客人都去里面餐厅用饭了,全体园子无人喝茶打麻将。
迎头见一四十岁旁边穿黑衣的妇女,问用饭吗,还是喝茶?答喝茶,有三元、五元等。各桌都放有麻将。她说大家都在室内用饭。我从玻璃窗可见里面坐满了人,围着五六张八仙桌用饭。我问:10-15元包吃、包喝茶,便宜呀。她说是呀,没有多大赚头,而且从早忙到晚。看来她是老板,呼唤一旁一个屯子样子容貌的年轻女人泡一碗茶。看来老板很忙,说了一声请逐步喝,便忙去了。
据那个女做事员说,每天有人送鱼到此,便放入池里,这样可以担保饭厅每天的鲜鱼。一下子,我便见一个师傅从池里用网捞出两条大鱼提到厨房。
坐了好一下子,用饭的人们陆续从饭厅出来,大多是退了休的老太太。先是一胖一瘦两个老太太在那里为十元钱拉拉扯扯,一个要给,一个不收,“我请你的嘛!
”“弗成,弗成,哪能不给钱!
”于是两人把一张10元的票子在桌子上丢来丢去。那瘦的到底没有收那胖的钱,那胖的笑着说:“我不想在这里跟你争来争去。”便把钱收了起来。
这种争着付账的情形,在过去中国的社会交往中是常见的。过去茶馆也有这种习气,在李劼人的《狂风雨前》和《大波》里边,沙汀的《在其喷鼻香居茶馆里》,都有“喊茶钱”的描述。在餐馆里也可以创造这种环境。这种习气至少在晚清民国期间就能看到,到了本日仍旧存在,是人们社会交往的一个办法。也不仅仅是成都或者四川的习气,全体中首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环境。别人为你付账,你为别人付账,是表现紧密关系的一种润滑剂。当然在现在的中国,特殊是在年轻人中间,开始各付各账的办法。不过,在朋友之间、亲戚之间,这种各自付账的方法并不盛行。不过在退休老人的定期聚会中,各付各的账倒是常见的,由于老人们紧张靠退休金生活,收入有限,当然不得不量入为出,这种付账形式大家都没有包袱。
接着出来更多的老太太,看来是从一个单位退休的,有人说“下星期二来早点占地方”,另一人说“那我们就下星期二在这里碰头”。看来这一拨老太太是定期聚会。
陆续用饭的都出来了,有的嚷着:“好热,出来还凉爽点。”有的便坐在桌子周围,又玩起麻将来,一边还摆着龙门阵。一些人却逐步走出园子,嘴里说“先去摄影”。在亭子里那桌边打麻将,聊得也很热闹,我听她们说某人的女儿学习很努力,考上了一所美国大学的研究生。
这天景象闷热,不过环境不错,但坐着喝茶仍旧以为热。回廊沿墙放着三台电扇,呼呼吹着,但许多人仍扇着扇子。园内地上还放了不少盆景,门口树下还有两桌在喝茶打麻将。
在那里我年夜约坐了一个钟头。从大慈庄茶园出来,接着去同在大慈寺内的文博大茶园。在大慈寺的门口有一个大牌子,写着押韵的顺口溜:
文博大茶苑,
直走后花园,
环境也幽美,
茶好饭菜鲜,
做事也全面。
欢迎:会议、聚友、休闲、包餐,棋牌免费。
但是在茶馆内又挂着“文博大茶园”,看来“茶苑”和“茶园”茶馆自己也是在混用,我在这里还是统一用“茶园”。
这的确是一个大茶园,里外都古色古喷鼻香。高高的石阶上,园内的树下,摆满了竹椅、木桌。
这是一个有三个大厅、三套院的古园。大厅内阴凉,园内也有树荫覆盖。第一个大厅有一半作文物、字画展览和出售,一半用作茶馆。
文博大茶园里边也有不少麻将桌,很多人在打麻将。有些放麻将的桌子空着的,该当是打麻将的人用饭去了。有些茶客就直接在茶馆用饭了,从桌子上的碗碟来看,吃得还蛮丰富的。而且景象热,不少客人干脆把上衣也脱了。茶馆是一个“自由的天下”,此话真的不假。
文博大茶园的露天部分,搭有竹棚,上面有绿色的藤蔓,既美化环境,也可以遮阴;既透气,又不晒太阳,也是茶客们喜好坐的地方。这里有些客人也是赤膊。
文博大茶园的一角,可以看到墙上挂着国画,有一个画商在这里卖画,也给茶客供应了一个欣赏国画的机会。没有人买画的时候,画商就坐在这里喝茶,这个买卖倒是做得很惬意。
第二个厅里不像一样平常茶馆椅子围着桌子,而是竹椅子排成行,一根柱子上挂了一壁红旌旗,上面写有“成都老年体协活动中央”,许多老太太、老头目在那里。还有几个手拿大红、大黄扇子的老太太在切磋舞蹈。
我在园子里寻一空桌坐下,不一会儿,便听见大厅里整洁大声地唱起了“社会主义好……”的盛行革命歌曲,然后是多少年前盛行的“亲爱的朋友们,本日来相会……”随后,录音机里响起了欢畅的舞曲。从我坐的地方,可瞥见十几个老太太,彷佛也有一两个稍年轻的,在那里跳了起来,并舞着红绸,立即招来一些人围不雅观。接着是独唱黄梅戏“牛郎织女”,然后是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各种歌舞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我创造,她们中四五十岁的也有不少。
听着她们唱这些老歌,大都是过去传统的革命歌曲,只管改革开放已经很多年了,新歌也不少,为什么她们还唱这些老歌?我想这些歌曲是和她们的青春联系在一起的,她们年轻的时候就唱的这些歌,跳的这些舞,现在年迈了,这种青春的影象已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其余,新的歌曲对她们来说,可能很难像年轻人那样很快地接管和在她们中间盛行。
还有一个有趣的征象,便是参加这些唱歌舞蹈的都是女性的老年人,而在阁下看的倒是老头目多。为什么老年妇女更生动地参加公共生活?在晚清的时候就有这种征象,去庙中烧喷鼻香的也因此妇女为多,特殊是老年妇女。现在退休后的老年人,男女也可能是不同的爱好,比如说男性老人对社交的渴望不像女人那么强烈,他们也可能去下象棋、打扑克、钓鱼或者参加其他的娱乐活动。女性的选择则小一些,那么在公共场所唱歌舞蹈,可能便是她们不多的可以坚持下来的几项活动之一。
最里面的(即第三个)大院,我见有些人在打麻将,有些在看报纸,有个光膀子的人仰头躺在竹椅上睡觉。一个四五十岁的瘦男人,手里拿着一个金属夹,打得当当响,在桌子间穿梭。他是掏耳朵的师傅,还招揽到一些买卖。看起来他与堂倌也很熟,在给一个顾客掏耳朵后,拿着一张大票子去找掺茶师傅换小钱。没有买卖时,便与堂倌坐在一桌喝茶。
当挖耳师从我阁下走过,我叫住他,问挖耳多少钱?答4元。我说给你4元,不挖耳,我们摆摆龙门阵。这时买卖清淡,他看起来很乐意谈天,说不要钱,他便坐下来,我担心谈天可能要延误他的买卖,以是还是给了他钱。
他说已在此掏耳朵九年了,从开始的1.5元,涨到现在的4元,不过老人一样平常3元。最长掏10分钟,最短只几分钟。干这行不需办业务容许证,但每月要交给茶馆200元。每月5日交,他说从未拖延过。大慈寺内各茶馆都是他的口岸,若其他人来做这个买卖,将被茶馆赶走。
一个月他大约可挣600-700元,扣除交茶馆的200元,每个月可剩500-600元。他妻子在茶馆擦鞋,一元一双,一月也可挣500-600元。
他现年五十多岁,17岁随父亲学这门手艺,先是在理发店谋生。他家在距成都大约二十公里旁边的双流县(目前已经成为成都的一个区了),每天骑摩托来成都。因外县摩托不让进城,先把车放在二环路他姐姐家,然后走到大慈寺。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在茶馆掏耳朵(茶馆业务韶光是8:30-17:30),中饭外出吃稀饭馒头,两人只须要花1.5元,泡菜免费,进大慈寺也不用买门票(门票一元),由于门房认得他夫妻。
他的工具有五种,一只大铁夹是他的“招牌”,招揽买卖时便拨弄它出声;二是刀子,苗条,有柄,他说是耳洞有汗毛挡住视线,须要用刀子先去毛;三是“启子”,为一薄薄的细铜片,用它刮耳壁,可以给人以舒畅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工具;四是小夹子,用它把耳屎夹出;末了一个工具是一小毛刷,用鹅毛做成,末了掏完后,便用其把耳轮里的残渣扫干净。他说备齐这套工具约需40-50元。一些由自己做,一些在铁匠铺订做。
我问他顾客是否讲价,答要讲的,他的底线是3元。问是否有人掏了耳朵不给钱,答也碰着过,但不常常。一次给三个小伙子掏,个中一个说没有掏舒畅,三个人都不给钱,先是吵,后拉扯起来。他气得掀翻了桌子,打烂了三副盖碗茶具。后在茶馆的其他人帮助下,把三人扭送到附近的派出所。派出所令他们付掏耳朵费12元,赔三副茶碗约8元,共约20元。他在府南河边的茶馆也遇过类似事情,也由派出所令付钱了事。
他说有时茶馆老板和堂倌也请他掏耳朵,他只收3元。
下午四五点这里买卖不好后,他便移师府南河边的茶馆。那里的茶馆不用交钱,因此在那里揽买卖的同行比较多。府南河边到了晚上很凉爽,吸引很多的人在河边茶馆坐坐,特殊是那些晚饭往后出来聚会和闲步的人。那么要掏耳朵的客人自然也多一些。
他说1970年代中期之前,喝碗茶仅5分钱,挖耳是1角5。茶馆没有私营的,都属于“单位”经营的,像公园、戏院、电影院、老人协会等,但60岁以下的不让进茶馆。根据我个人的影象,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实在他的年纪也不大,可能这个说法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我小时候,父母带去逛公园的时候,也是常常到茶馆的。
我们谈到那些在大厅里面唱歌舞蹈的老太太,他见告我,她们每周三在此操练,她们喝茶是2.5元一人。打麻将是每人3元的茶钱,一桌4人12元;但麻将的桌面(即四面有口袋的桌布)和租借麻将牌共8元,玩半天四个人花20元;若玩一天,则23元。
我问是否常见人吃茶不给钱,答曰是的。一样平常是泡茶时付钱,但有些人泡茶后对堂倌说过一下子付,打麻将的却称一下子谁输谁付。有些人喝完茶后,便丢几个空烟盒在桌子上,貌似还有东西在桌上,然后一个接一个溜出去小便,就再不回来了。碰着这种情形,茶馆也毫无办法,只好认栽。
也有集体逃茶钱的,那丢失就更大。有一次一个工厂的工人在此聚会,许多是下岗工人。泡茶时说一下子人到齐了一起算茶钱,一共泡了三百多碗茶,但只收到一半的茶钱,半数人喝茶后没付费即开溜了。
挖耳师的两个儿子本日也在茶馆里玩,一个读小学三年级,一个读初中。说是都已经放假,家里没有人照看,故带在身边。我问他是否让儿子继续父业,显然他没有这个打算,以为掏耳朵这个行当并不是很有出息的谋生之道。他操持大儿子再大些便送去学修汽车,他家住的地方口岸很好,开个修车铺买卖一定不错。
这个掏耳朵的师傅头脑非常清楚,对自己的下一代也有明确的操持和安排。他自己的处境不是非常好,并不知足现在的处境,以是对下一代还是有憧憬的。显然他干这一行,也是由于找不到更得当的职业,对他来说,掏耳朵该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两个儿子和他老婆就坐在不远的一个茶桌旁,小儿子过来几次,彷佛对我和他爹的发言很感兴趣,但都被他赶走了。有一次他借口说是有耳屎,请爹帮他掏,但他把工具给儿子,丁宁他去叫他妈帮助掏。 看来这位掏耳朵师傅也很享受和我的谈天,分享他的经历,不想被小儿子来打扰。
我问是否教有徒弟,他说教了他小舅子这门手艺,在府南河一带谋生。按照他的说法,这门手艺大约要一年才能出师。
我们聊到他家里的状况。他家承包了7亩田,都种水稻,田里的活不是太多,纵然是收割忙季,也只用三天。他父母尚在,帮助照管田地及家畜。家里养有鸡二十余,鸭二十余,猪年出栏二十余,另还养有一头牛,常常卖鸡蛋。每年田里的出产加副业,可收入1万,加上夫妻俩挖耳擦鞋,可以挣六七千元。这样,年收入1.6万-1.7万的样子,年支出1万旁边,所剩便存入银行。
我以为他每天从城外到城里来谋生,还是比较辛劳的。但是比起在屯子种田,要轻松得多,而且可以增加不少收入。他的状况比一样平常的农人工要好,由于他和他老婆能够在一起还带着小孩,这样一家人在一起,他的小孩也没有成为留守儿童,这种情形在农人工中间是不多的。而且在农忙的时候,他还可以随时回家帮助务农。父母有了病痛,还可以随时照顾。
当然这样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比如说两个小孩全体夏天放假的时候就待在茶馆里,缺少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实在我们知道,中国的小孩在暑假都须要做不少的作业,有条件的家长还会请辅导老师,或者把小孩送到暑期班。而他们的小孩就在这个喧华的环境里,度过了全体夏天。从小在茶馆这种繁芜的环境、三教九流聚拢的地方永劫光地逗留,过早地打仗社会,理解他们不应该理解的东西,不一定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些担心,实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相反的例子:小孩在一个艰巨的环境下终年夜,看着他们的父母如此辛劳地挣钱,把他们抚养大,可能比那些在优胜的环境中终年夜的小孩更懂事,更有奋斗精神。
王笛
责编 邢人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