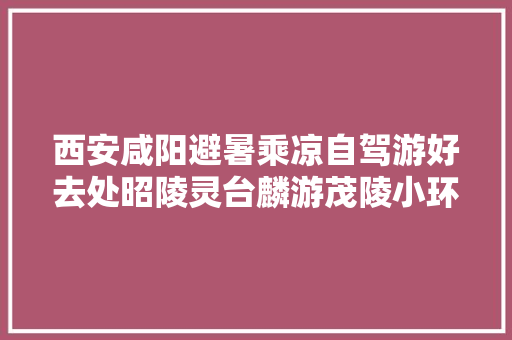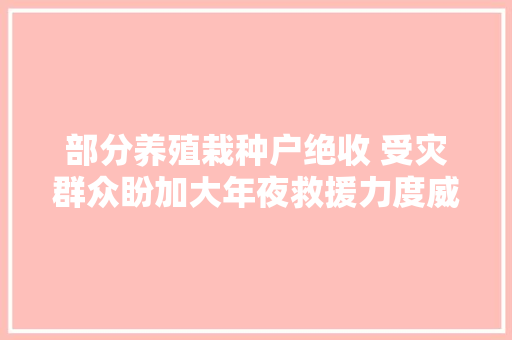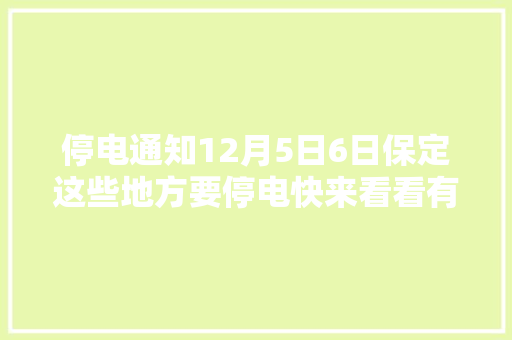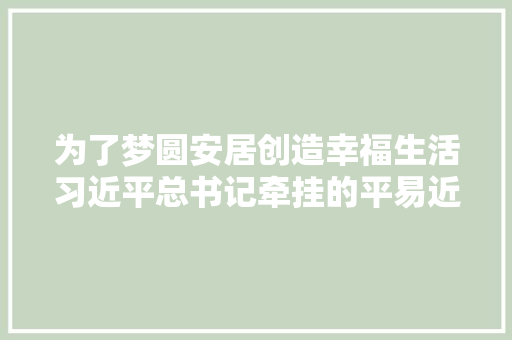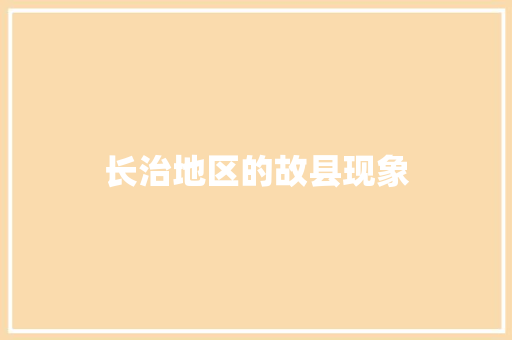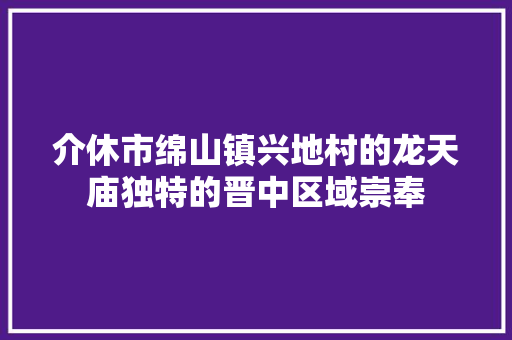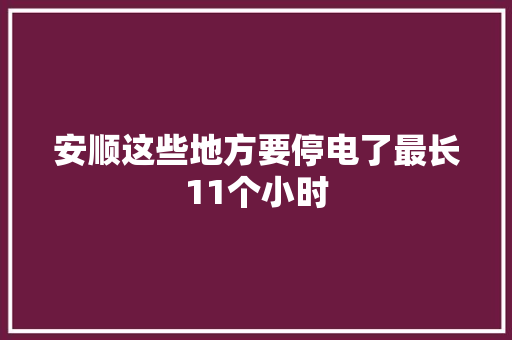6月10日,控拜村落银匠龙太阳在自家事情间里焊接银饰。刘荒摄
在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东北,有3个远近有名的银匠村落——控拜村落、麻料村落和乌高村落,当地苗家人多以银饰加工为生,世代相袭。由于它们在地理位置上呈三角之势,被人形象地称为“银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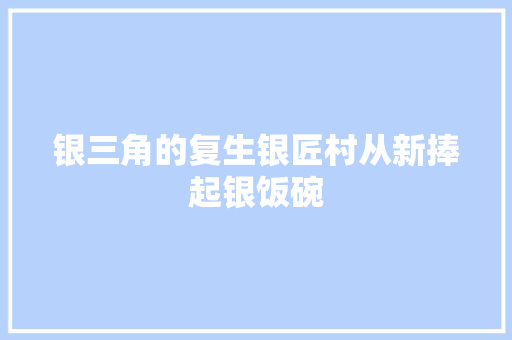
虽说这里的银匠技艺高超,却很难走出封闭而迢遥的大山。捧着“银饭碗”过穷日子,彷佛成了这些手艺人的宿命。
上世纪90年代末期,“银三角”终于通电通车,古老的苗寨开始拥抱当代文明,传统手艺却遭遇前所未有的市场冲击:机制银饰进入人们视野,外出打工成为潮流。银匠们纷纭丢下手艺外出闯荡,银匠村落一度都变成“空心村落”。
如今,“银三角”正在历史的变迁中觉醒。文化旅游开拓为民族特色和自然生态赋能,吸引更多游客走进“银三角”。一些重拾手艺的银匠们,带着痛楚、思虑和希望重回村落寨,使这门古老的手艺谋变求新,重获活气。
银匠们失落落、出走、奋斗、回归的创业故事,真实生动,再现了这些古老苗寨的改变与冲突,令人动容,引人寻思。
大山里拍抖音的网红银匠
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镇麻料村落,肤色黝黑、身材健壮的潘仕学,蓄着刘欢式的长发,身穿一件玄色粗布衫,时时露出实诚的笑颜。只见他左手握着一根银钉,右手拿着一把小锤,敲敲打打中做出一对手镯。
“这对《大话西游》主题的情侣手镯,形似至尊宝所戴紧箍咒,是李师长西席为新婚妻子准备的礼物。由于创业繁忙,他没有办法常常陪在妻子身边,向我定制了这对寓意生平所爱的手镯。”短视频中,37岁的银匠潘仕学讲述着银饰背后的故事。
他从去年5月开始拍抖音做直播,不仅积攒了9万多粉丝,还收成了28万多元订单,从大山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手艺人,变成一个会说故事的网红银匠。
早在2010年,淘宝店铺最火的年代,在湘黔交界景区开银饰店的潘仕学,决定开网店卖银饰。由于自己不太懂,身边也没人会,他花了一年韶光才把淘宝店开起来。
也是这一年,他将景区门店交给妹妹打理,陪有身的妻子回到黔东南州首府凯里市,专注银饰加工和淘宝买卖。电商运营古迹虽有增长,却一贯不温不火。直到有一次,有位客户在他的淘宝店购买一只手镯,还问他是否开团。
“我不懂团购,被他给问懵了,还反问他团购是不是须要装修店铺呢!
”潘仕学笑着回顾道。
没想到,这个客户把银饰图片放到论坛去晒,很多粉丝惊呼“种草、拔草”了,我就给他们团购价优惠,店铺发卖一下火了——订单从中午接到第二天,有100多单,“当时愉快坏了”。
后来,淘宝上的一位北京客户,专程飞到凯里找他谈互助。连同此前在QQ群认识的一位成都客户,仅为这两个大客户代工的发卖额,一年就达到25万元。
如果没有站上电商的风口,潘仕学可能还在景区去世守着门店。“线上发卖稳定了,我才能回村落里发展,不然回来也待不住。”如今,已是麻料银匠协会会长的他坦言。
控拜村落的银匠龙太阳也玩抖音,视频画面里,妻子手握一把喷火枪,专注地焊接银饰;5岁的小女儿拿着小锤子,有模有样地敲敲打打。但比较之下,他的订单更多来自微信。
2013年,龙太阳开始用微信与客户联系,通过朋友圈发图、推举名片等社交功能,迅速打开市场,当年微信收入就有2万元。近几年,他加大微信推广和线下体验力度,深度挖掘用户需求,仅线上收入就已超过20万元。目前,他正准备在手机上开直播,向粉丝们展示银饰的打制过程。
对线上发卖渠道并不感冒的顾永冲,是乌高村落最有名气的银匠之一。年轻时他走村落串寨打银饰,有了积蓄后,在雷山县城开了一家银饰公司。
他也曾考试测验开网店做电商,由于自己不入门,只好委托他人运营掩护,结果白花了10多万元,却未见任何转机,即是打了水漂。
“他们便是骗我父亲这种不懂的人,当时还不如把这事交给我。”提起这件事,25岁的银匠顾仲杰总以为可惜。
到温州做鞋匠断了两根指头
在控拜村落一栋新装修的木楼里,身穿蓝色布衫的银匠龙懂阳,正专注地趴在桌子前干活。他左手食指按着一个五角硬币大小的银花瓣,右手牢牢握住一把镊子,灵巧地调度着银花瓣的形状。
与弟弟龙太阳不同,龙懂阳更像一个敦厚朴实的庄稼人。如果不是他见告,根本想不到这个靠手艺用饭的银匠,右手竟有两根断指。一双机动的双手对付手艺人来说,主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银三角”家家户户叮叮当当响,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随着福建模具商进入银饰行业,大批量、低本钱的机制银饰涌入市场。“手工银饰没有市场了,只有名气大的银匠还有活儿干。年轻人待在村落里赚不到钱,都跑到表面打工去了。”七八岁开始学手艺的龙太阳,眼看着银匠村落走向凋敝。
1996年,他们兄弟俩到温州打工,转业学制鞋手艺。二哥龙懂阳在一次操作冲床时,欠妥心夹断了两个手指。
有一次母亲生病,龙太阳赶回来了。当时,村落里一位孤寡老人欠妥心跌落山下,一个星期后才创造,找到时尸体已经糜烂了。遐想到村落里独居的母亲,在外闯荡4年多的他,动了回家的动机。
“村落里有老人去世,都找不到年轻人抬棺,全是60多岁的老人去抬。”龙太阳回顾道。
2002年,龙家兄弟从温州回到凯里。当时,去温州学做鞋,回来在县城开厂做鞋或开店卖鞋很盛行。“我们与几个朋友合资办起了皮鞋厂,就想把鞋做好,把很多村落里的熟人带回去!
”龙太阳说,投产不到两个月,生产的鞋却卖不动,只得把鞋厂转让出去。
两年后,龙太阳回到控拜村落,买了辆二手面包车,靠拉人赢利,“一边跑车,一边做银饰,当时村落里没有人打银饰,我成了银匠村落末了一个银匠”。
与龙懂阳的断指之痛比较,4年之后,同样在温州,同样做鞋匠,潘仕学经历了打工生活中最难过的一天。
2005年,22岁还在读高三的潘仕学,接到同学从河北保定打来的电话,称有一份月薪四五千元的事情,听起来很诱人。
这个有些音乐天赋的苗族小伙,高中时就开始组乐队、当鼓手。一想到“乐队要买台1000元的琴,就像要了父母的老命”的困窘,他打算先赢利,再追求音乐梦。到保定后,他才创造所谓的“高薪”事情,实在便是做传销。
之后,他又辗转浙江、广东等地,干过短期的餐厅配菜工、琴行西席,给瓷碗贴过印花,在电子厂加工过芯片,没事情就靠打零工养活自己。
潘仕学至今仍记得,在温州一家皮鞋厂给皮鞋刷漆,两个老板就他一个工人,一天12小时干下来,“又累又困又饿”。一天晚上,朋友请他去饮酒,听他聊起事情时说:“你本来是个音乐人,干这个太不适宜了。”
“听到这话,我眼泪一下就出来了,那是在温州最伤心的一晚。”潘仕学回顾说。
2008年初,他准备去上海的家具厂打工,在凯里开银饰店的堂哥,劝他留下来,还给他看了自己接的银饰订单——半个月就赚三四千元,比自己在外打工一个月赚的钱还多。在外四处碰钉子的潘仕学,决定留下来跟堂哥学习打银饰。
人来了财来了,烦恼也来了
沿着蛇形山路驶入控拜村落,一眼就能看见吊脚楼群的最高处,写着“龙太阳银饰”的大幅招牌。
44岁的龙太阳,看上去年轻精干,艺术范儿十足——身穿黑背心黑裤子黑皮鞋,留着小髯毛,头顶两侧理着超短发,中间盘着一个小发髻。
这个“失落传”多年的苗族传统发型,连村落里老太婆都以为不男不女,竟以为他没钱理发呢。特立独行的龙太阳,还冲破了银匠“传男不传女”的传统,给女儿起名“龙传艺”,寓意传承龙家的技艺。
“这次疫情影响大,往年这时候每天有很多游客,这个长桌都没空位。”龙太阳站在自家客厅里,指着面前可容纳10多人的长桌对说。
2012年,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带动,加上龙太阳逐渐有了名气,村落里来的游客多起来。近3年来,他通过打造个人“IP”,挖掘游客体验式的场景消费,每年接待1万多游客,年收入达40多万元。
为打造银匠村落品牌,让村落里人一起受益,龙太阳想动员银匠们签一个诚信协议,确保银就银,铜就铜,手工就手工,机制就机制,是谁打的就打谁的名字,违约造成的所有丢失自行承担。
“就这么大略的协议,很多人都不愿意签。”他觉得紧张是不雅观念改变难。有时,村落里来10多个游客,他宁肯自己家空着,雇主分几个住,西家分几个住。可还是一度引起村落里人的妒忌,乃至有人偷偷给他家掐电断水。
“人家以为是在帮我龙太阳的忙,我还欠一个人情。后来,有客人过来住不下,我就让他们去西江住。这些人又抱怨没人来住。”龙太阳感慨地说。
不过,他认为,被村落里人妒忌反倒是一件好事,“他们从妒忌逐步变崇拜了,村落里已经有几户,开始往这个方向走了。”
重拾手艺回苗寨的“龙太阳”们,不但搅活了村落民们的心思,也吸引着大量游客的涌入,“银三角”涌现前所未有的躁动。
在控拜村落通往麻料村落的岔路口,一边石头上刻着“中国民族银饰艺术之乡控拜”,另一边石墙上写着“中国·银匠村落雷山麻料”,更像是两个银匠在暗中角力。
过去,路口的小广场是“银三角”的公共园地,三个村落的村落民都在这里赶集,彼此友好相处。
当地政府曾故意把这三个银匠村落整合起来,对外打造全国最大银匠村落的品牌。或许是“同行是冤家”的缘故,彷佛很难把它们拧到一股绳上。
3年前,这三个村落有告终合意向,决定联手举办一个节日活动,还约请多家媒体宣布。据当年一位亲历者回顾,由于这次活动麻料村落出人着力较多,风头较盛,有过度“突出自我”之嫌,引起控拜村落民的不满。
从此,三个村落少有往来,热闹的小广场变得生僻起来。
潘仕学认为,紧张缘故原由是竞争,过去控拜走在前面,现在麻料银匠追上来了。已当选控拜村落党支部布告的龙懂阳坦言,人越多工艺越好,找不到对手怎么弄,大家相互学反而快一些。
银饰也要学会讲故事
苗族历史上多次迁徙,生活流落不定,族人习气以钱为饰保值财产。当地一贯有“无银无花不成姑娘”的说法,父辈们即便穷尽家财,也要为女儿置办一套银饰。
古老的习俗催生出“银三角”银匠群体,他们以种地为生,靠走村落串寨打银饰补贴家用。重山阻隔,外出每每要走上几天几夜的路。湖南、广西、重庆的苗族、土家族、侗族穿着的银饰,很多都是这里的银匠打造出来的。
站在银饰展厅里,龙太阳聊起银饰作品的故事,语速飞快、干脆利落。里侧墙吊颈挂一只银质牛角,展柜里摆放着精细的蜻蜓、蝴蝶等银饰。
说话间,窗外下起了暴雨。这个时令的大山里,雨天再平常不过了,古朴的村落寨被雨水一遍遍冲洗着。不由得让人遐想到,“银三角”古老的手艺,也在经受市场的一次次洗礼。
“苗族没有笔墨,很多文化内容在不断丢失。”龙太阳看到银匠村落空心化后的文化传承危急,便凭借银匠这门手艺做起文化保护与传承,还受到省里有关领导的表扬。
“我当时有点飘,文化保护做着做着就没钱了。后来,那位公开表扬我的领导又提醒我,文化要保护,先要养活你的家人。”自那之后,龙太阳的不雅观念发生转变。
“银匠回村落首先要生存,如果我连饭都吃不饱,不可能去传承保护这门手艺。”他说。
如今,苗族人以银饰保值财产的办法,早已被进城置办房产所替代。“原来苗族人结婚,标准的15–20斤银饰。现在年轻人就要一个帽子、两个项圈,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了。”银匠们已把稳到本地苗饰需求萎缩的现实。
银匠回归过程中,也带回了市场思维。他们开始跳出民族银饰的消费圈子,靠手艺打制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
2010年,贵阳一名研究生为写文化保护论文,来控拜村落采访龙太阳。临走时,想买一个银质花朵,龙太阳打算收70元,但对方执意给150元,说“这朵花的本钱是20元,在村落里一天赚130元,你会坚持做下去。如果只赚50元,迟早有一天你会走。”
这段话启示了龙太阳,不能纯挚地卖产品,要探求新的出路。为了追求创新,他打制过蜜蜂、草帽、四叶草等创新银饰,还做过一双纯银“皮鞋”,并没得到过多的市场关注。
真正让他一夜成名的,竟是一副银质文胸。7年前的一天,他要带妻子到县城买衣服,妻子笑问:“你这么穷,恐怕连个文胸都买不起。”他萌发一个动机,为妻子打造一副银质文胸。
后来,一位朋友把这副文胸带去国外参展,好评如潮。在老外眼里,这副银质文胸的故事,凝聚了一个农人匠人的高超手艺和浪漫情怀。
这件传统手艺与时尚饰品相结合的文创产品,关键的硬核是故事。这也让龙太阳得到启示,遐想到苗族故事和文化,都通过衣饰来传承的民族特色。他开始用讲故事的办法,给银饰产品赋能,提高产品附加值。
一次,他无意中抓拍到,女儿被一只蜻蜓吓哭了的场景,决定打一只银蜻蜓,待她终年夜后会想到,自己曾被这只蜻蜓吓哭过。他打造这东西的时候,也会定格于女儿被吓哭的那一霎时。
“将这只俊秀的蜻蜓银饰,融入我们的感情和故事里。”龙太阳补充说,这门手艺是“非遗”,而产品不是。
他勾引前来体验手艺的游客,做有自己故事的饰品,“男女朋友曾经为一个东西动了感情,就用苗族手艺把它做出来,这个故事就跟银饰一起活了”。
“以前打的银饰宁靖易近族化了,不易被表面的人接管。后来看重产品创新和设计,把市场做好了,才能做好文化传承。”潘仕学说。
2017年,潘仕学通过参加手艺人培训班,走上“非遗”传承之路,同时形成了全新的市场思维,“从那之后开窍了,设计理念开始转变。”
“非遗”传人为何让儿子学模具
2014年,19岁的顾仲杰也走出大山。不过,与银匠外出打工不同,他考取重庆机电职业学院,学习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为家里的银饰家当转型做准备。
“做手艺已经养活不了自己,只能以机制养活手工。”身为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的顾永冲,讲出这样一番话,让儿子顾仲杰深有感触。
当年,打银饰还没有喷枪,都要用嘴吹石油灯,顾永冲吹灯功力高,在行业内出了名。
“前些年,我家机制和手工各占一半,这两年很多做手工的师傅,就没什么事做,每天闲着。”顾仲杰说,父亲希望他理解外界的新机器,在机制银饰的市场中,“勉强还可以争一争”。
虽然自己学的是机制工艺,但顾仲杰仍以为“机制是没有灵魂的”,“毕竟很小的时候,父亲每天做银饰,我在阁下读书,在这种环境下终年夜,对机制总有些抗拒的生理”。
顾仲杰记得还在读小学时,有4个外地人登门拜师,还拿出2万元学费,被父亲顾永冲谢绝了。他可能担心教了别人,自己不好找事情做,怕抢买卖。
后来,顾永冲开银饰公司,由于合资人撤资,公司人手不足,有订单也没法完成。
“父亲纠结了一个半月,想通后就要去表面贴广告招人。母亲出主张说,不想教外人,就先问问家里亲戚,从此才开始收徒弟。”放假在家的顾仲杰,目睹了父亲痛楚的转变。
2017年,顾仲杰毕业回到家乡,随着父亲学手艺。当时,父亲每隔一两个月就外出跑发卖,总能从老客户中带回两三百万的订单,按条约哀求加工生产,整年收入1000多万元。
一年前,顾永冲溘然病倒了。“银饰里的很多图案,都在父亲脑筋里,现在没有人辅导,我自己做没有把握,很头疼。”顾仲杰说。
虽然他扛起身业,却不得不做出改变——调度职员,压缩开支,出资支持父亲的4个徒弟外出,到杭州、成都、广州开银饰店拓展销路,家里卖力生产。
“我不怎么和当地人做生意,由于总会有一家价格比你低。”顾仲杰对当地低价竞争显得有些无奈。他透露,去年接的订单中,只有零散几个要手工产品的客户,大多数客户只看性价比,更喜好机制产品。
顾仲杰认为,机制品把银饰价格压得很低,已经形成恶性竞争。“比如1块钱的工费,勉强还能赚一包烟的钱,价格已经叫到生理底线。同行知道后,就算不赢利,倒贴都要跟你拼。”
“有些外洋的老板订做的银饰,一个单价就几十万元,紧张是冲着父亲的手艺。可现在父亲还没康复,一位北京客户都等一年了。”顾仲杰说。
只管家里的银饰机制品已占到九成,但他未来还打算学妙手艺,走父亲那条路,“到那时自己也拿个证”。
只有手艺是靠不住的
2017年,潘仕学的银匠村落复兴梦,刚迈出第一步就险些短命。
他已经深刻意识到,纯挚靠银饰产品走不通了,未来要走“非遗”这条路,把手艺放在文化旅游的新业态里。
潘仕学打算带领银匠回村落,通过博物馆和公司的模式,协力打造银匠村落。但第一次在西江开会动员,20多人里只有两三个举手的。多数人依赖门店发卖,认为回村落无疑是一场冒险。
“他们担心没有游客进来,回村落开再华美的店,也没有用。”潘仕学说。
他想争取更多村落民的支持,却换来不少冷嘲热讽:“在城里都混不出来,到村落里就会有客户?还不是拿大家的钱做形式上的事情。”
这种想法与顾仲杰的顾虑有点契合,他既认同旅游对银饰的带动效应,又以为“光靠银饰吸引人到那里,有点悬。”
“银饰这东西,看一眼就够了,不是每个人都想学,大部分游客是来看风景和当地人的生活。”顾仲杰说。
潘仕学坚持认为,该当先打造好银匠村落,才能吸引到游客。“控拜早有名气,没多少人知道麻料,如果博物馆和名气都没有,游客进来还是个‘空心村落’。”
他四处游说,给村落民讲苗寨的旅游潜力,未来的体验式、场景化消费。村落里才终极达成共识,集资了100多万元,加受骗局支持的58万元,银匠村落复兴梦总算有了启动资金。从2018年开始,村落里逐渐来了游客,银饰和田舍乐有了收入,博物馆银饰年发卖额达到几十万元。
如今,麻料村落的旅游新业态已初具规模,村落口苗寨风格的木质门楼上,写着“西江麻料银匠村落”;阁下公示牌上,有13家银饰工坊、5家堆栈与田舍乐的名字;石板路的岔路口旁,直立有“麻料银饰刺绣传习馆”“东京银饰工坊”“银泉田舍乐”等指示牌。
比较本日的麻料,银匠最早回村落的“前浪”控拜,却像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控拜只回来零散几个银匠,还没达到龙太阳的预期,“我屋子也盖了,钱也赚到了,但一个人好不算好,还要把全体村落带动起来。”
在他的设想中,村落里要建一个博物馆,展示着祖孙三代的银饰作品,全体银匠村落有上千个银匠,上千种不同设计理念和风格的银饰全部展出来,每家发卖自己名号的产品,而不是千篇一律敲上某个大师的名字。
到那时,村落里拿出部分收益分给旅行社,借助他们的渠道吸引更多游客,盘活村落里的旅游资源。而他以前以为,“自己在保护文化,客人都是深度的,不想走传统旅行社。”
顾仲杰却以为,第一批回村落的银匠尝到了甜头,但如果没有更多游客和需求,光靠空谈手艺传承,难以吸引其他银匠回村落。
“靠补贴也弗成,可能一天还给不到300元,在老家坐一天空吃一天。我在县城店里每天也能赚300元,回村落里每天坐着,啥事没有,谁也不愿回去。”顾仲杰说。
无论是银匠丢下手艺走出去,还是重拾手艺回村落寨,究竟是受市场力量的驱动,民族手艺和文化的传承、保护固然主要,但却无法分开市场讲坚守,传统手艺靠去世守是守不住的,这是“银三角”变迁带给人们的启迪。(刘荒、完颜文豪、罗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