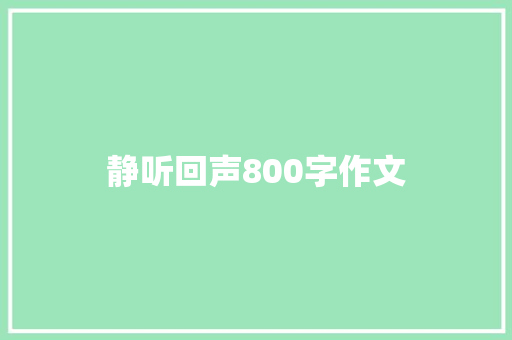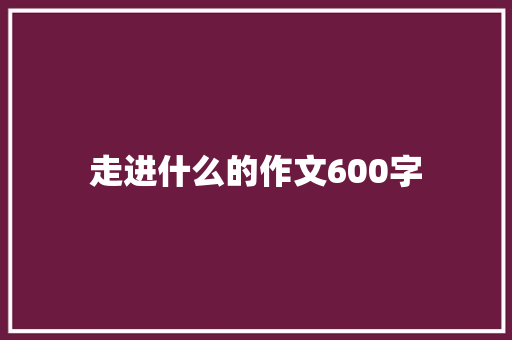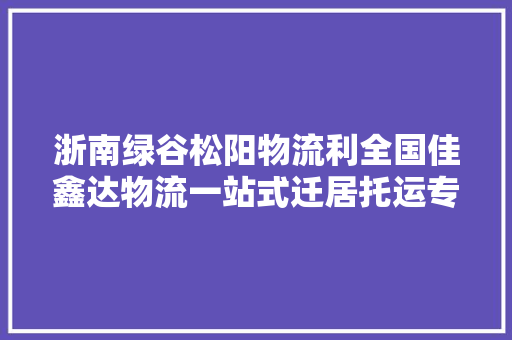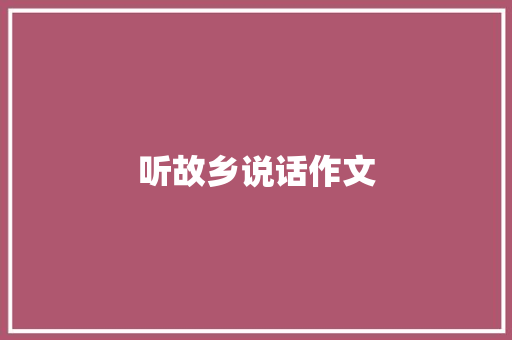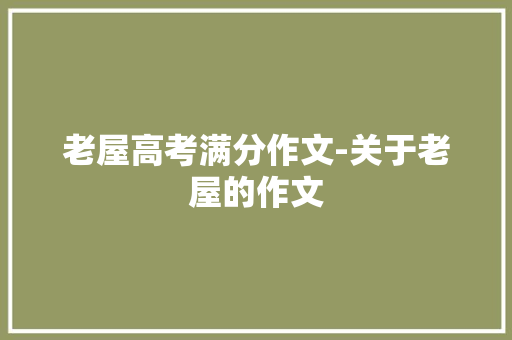然而,这“活着的清明上河图”,一度也面临成片古旧民居成危房的尴尬田地,而一旦这些老屋成为废墟,再美的人文风景也就没了人气与灵气。几年前开始的松阳老屋拯救行动,让老村落活了过来,更关键的是,老手艺人纷纭返乡,给这些村落庄留下了一支穿梭在古建筑间的工匠军队。只要有这支军队,至少今后十几年,“末了的江南秘境”不愁没人守护。
松阳手艺人修老屋现场。受访者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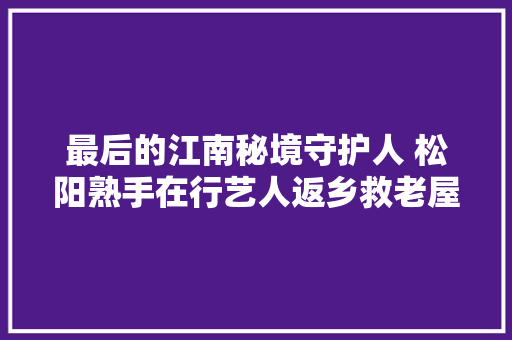
“大木匠”六年救了160座老屋子
“修古建筑比建新居子更难,里边有太多隐蔽构造。”今年26岁的叶彦杰,参军队退役后便接过了父亲叶常贤的手艺,虽然已经从事这行五年多,但叶彦杰碰着问题还会时时时请教 “师父”。面对呆板的学艺,叶彦杰说自己是个倔脾气,“只要能把修古建筑这件事做好了,别的啥也难不住我。”
古建筑修缮工艺有严格的哀求,在没有设计图纸的情形下,要修旧如旧,最大程度还原古建本身。在叶彦杰并不算长的修缮履历中,他修过的古建筑隐蔽构造多、建筑工艺繁芜多样、建筑用材还各有不同。
父亲叶常贤今年57岁,16岁时拜师学艺,有数十年古建筑修缮履历,仅从2016年至今就修了当地160多座古建老屋,是德高望重的“大木匠”。大木匠不同于当代装修中的木工,由于松阳当地的建筑多为木构造,大木匠是起先当地人建屋子离不开的真正老师傅,一个大木匠的手艺决定着全体建筑的好坏。
在叶彦杰的影象中,父亲干这一行从前并不是很吃喷鼻香。在自己还没出生之前,父亲就不得不转业另谋出路,直到2008年,才重新捡起了这门手艺,做起了包括老屋在内的各种古建筑的修缮事情。
松阳修缮老屋现场。受访者供图
最初学手艺的日子,叶彦杰对父亲的各种老木工活儿实在不以为然,他乃至以为,“用铁钉固定一下就行了。”可是,这个想法遭到了父亲的严厉批评,“这你就不懂了,修文物是不能用铁钉的。”由于不雅观念上的差异,父子俩少不了常常辩论,但也正是这种辩论,让叶彦杰对什么是老手艺、什么是修旧如旧有了切身的认识。
在参与拯救老屋行动过程中,叶彦杰和父亲卖力的团队得到了修缮资质,现在父子俩的军队中有38个手艺人,均匀年事超过50岁,像叶彦杰一样的年轻人非常罕见。“现在学这门手艺的同龄人太少了,干这行比较辛劳,须要学徒两年半到三年才能出师,可惜年轻人多数静不下心来学手艺。”
跋涉数十公里探求老瓦片
老屋建筑是传统村落的主要组成部分,庄家对世世代代居住的祖宅是有感情的,6年前开始的拯救老屋行动,更让当地人对老屋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在松阳有一户人家,丈夫生病做手术急需用钱,恰好有商贩要高价买家里老屋子上的木雕,但一家人商量许久后还是坚持没卖。
但普通人家想保存老屋,确实有太多困难。松阳古建大多是始建于明清至民国期间,个中明代古建筑较少,清代与民国期间的建筑居多,老屋大多为夯土墙构造,世代人聚居传承,产权繁芜、居住人口多,这些都增加了老屋的修缮难度。
在叶彦杰参与修缮的老屋中,玉岩村落有栋老屋里有19户人家,常住人口100多人。仅修缮这栋屋子,工匠队就花费了七个月的韶光,“须要和每个村落民进行沟通,理解他们的需求。”
古建筑常日没有设计图纸,上百年的各种改造常常让老屋子面孔全非,仅剩下主体构造。2021年,叶彦杰在修缮七村落一座祠堂的时候,创造一些难以确认的痕迹,为了搞清楚详细构造,多次跟村落里老人沟通后才知道,原来祠堂里曾经有一对旁边对称的仙鹤,如今只有一边留下了些许痕迹,若非老人的口述,没人能理解到祠堂原来的设计。
在松阳,有些老屋屋顶经由风雨冲刷,已经难辨之前的构造样貌,在修缮中一点点找回之前的样子。受访者供图
老屋子大多是村落民就地取材。在松阳,杉木建筑居多,为了确保不改变文物的原状,小到一个窗框尺寸与屋顶瓦片,大到整体风格,工匠们对修缮都有严格的哀求。有时为了找到得当的旧瓦片,父子俩会到几十公里外的村落找上好几天乃至半个月。
能修不换的工匠心
经由松阳拯救老屋行动后,“能修不换”成为当地工匠们的共识,也是严格秉持的原则。
在玉岩镇大岭脚村落叶氏宗祠里,有一根直径75厘米的大梁,表面雕刻十分精美,但中间已经蛀空,霉烂得手指头可以直接戳进去。工匠吴炳松犯了难,建议直接换新,村落民也提出了换新的建议。不过,“老屋办”哀求“既担保构造安全,又保留文物代价”,逼着吴炳松研讨起贴皮拼接技能,终极完成了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吴炳松说,连族人们末了都看不出来大梁是修补过的。
修缮松阳蔡氏宗祠。受访者供图
能修不换,对生活中更方向换新构件的村落民来说,有时候并不完备理解。工匠曾荣华就曾碰着过这样的质疑,“为什么只修不换?你们只修补太不负任务了!
”对工匠来说,实在换新比修复挣钱更多,但修缮军队一贯遵照的原则便是不能单单为了利益而修缮。曾荣华向村落民反复阐明,老屋是文物建筑,只要不影响安全利用,就不能轻易改换构件,才能最大限度保持文物的原状。
在松阳县拯救老屋行动中,对修与换进行了明确划定。比如老屋地面,原来是三合地皮面,住户改为了水泥地面,是保留还是要修复,要根据其位置来判断,公共区域建议修复,附房区域许可保留,三合土表面磨损较小可保持现状。
工匠回流把技能留在当地
明清以来,松阳一贯是出建筑工匠的地方,近些年,当地的派系和技艺相继面临失落传。拯救老屋行动中,这些老手艺人有了一波还乡潮。其间,松阳县造就了2000余传统工匠,30多支军队,累计参与项目的传统工匠有千余人,形成了“松阳工匠”品牌。
在三都乡,有一批被称为“三都帮”的传统工匠,范例的代表便是曾荣华的军队,夯墙、翻瓦、大木等工匠全都来自三都本地,形成了三都工匠修缮三都老屋的景象。工匠曾信亮是三都乡有三十多年木匠履历的老师傅,他原来以为自己的手艺没有用武之地了,后来去了杭州从事装修行业。家乡开始拯救老屋后,他带着儿子回来修老屋,一年多韶光,接了五个老屋项目,原来的军队也增加到20人。
松阳村落民也参与到修老屋行动中,自己挑土修房。受访者供图
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遗产五室主任黄贵强说,“拯救老屋项目不但把老百姓的屋子修睦了,还把本土工匠培养出来了。”2021年,松阳县还推举叶常贤到松阳职业技能学校担当老师,传授修缮古建的手艺,现在叶常贤每周去一次学校,给40多逻辑学生教课。
在松阳,叶彦杰和父亲的手艺已经很有名气,有时候也能接到外地的活儿,但大多韶光父子俩还是在松阳修老屋子。最近,他们正在修缮当地历史上一处大户人家的老屋,房屋上的木雕繁复精美,极具年代感。“比起赢利,我们这些工匠师傅更加在意的是自己的名声。”叶彦杰说,工匠们有时会在建筑上“留痕”,柱子是什么日子做的、什么时候拼的,手艺人会给予标注命名,也正是这种“命名”,让修老屋子这件事对工匠来说,不再仅仅是一份事情,“犹如在参与一段历史,我们事情的痕迹,将与这些老屋一贯延续下去”。
新京报 耿子叶
编辑 张树婧 校正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