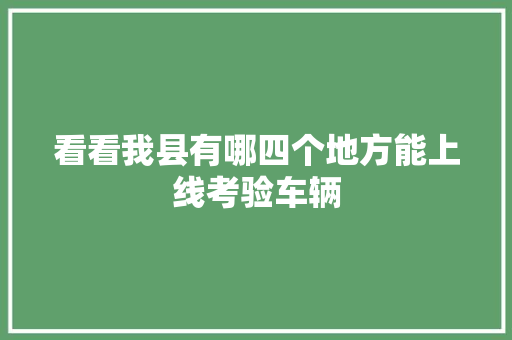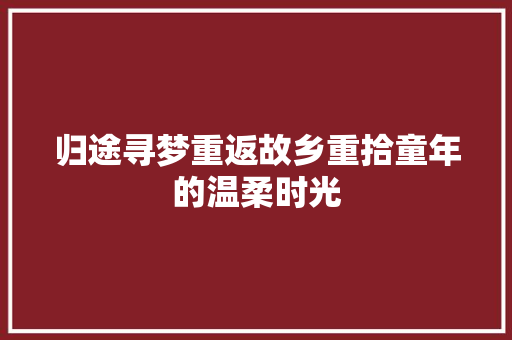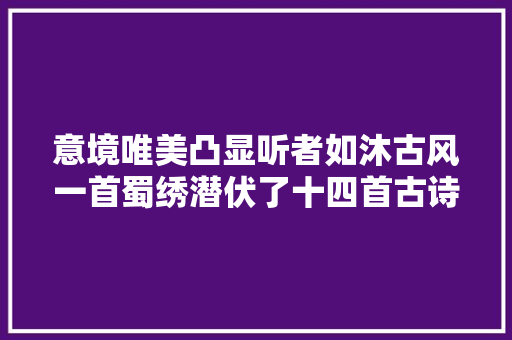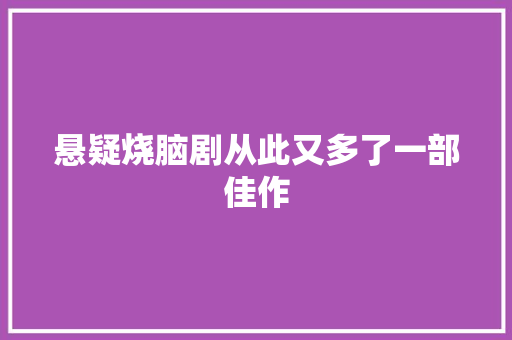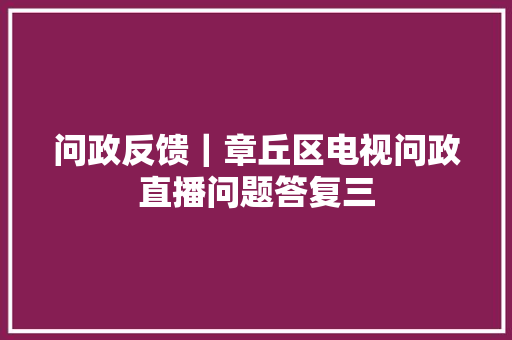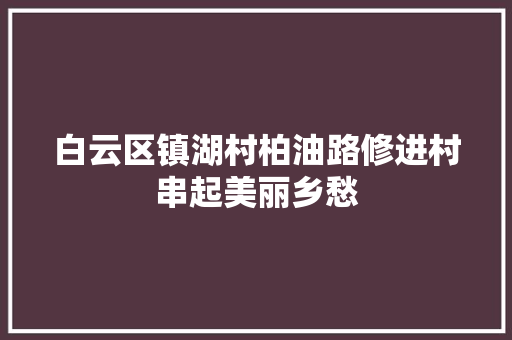冬天意味着下雪,就像春天的雨,夏天的太阳秋日的风一样本应是习以为常的事,可是长期一来的暖冬彷佛让所有人都忘却了冬天的本该有寒冷,这种反常就像超女选秀不出几个某哥什么的让人开始无法接管可是到后来却也习以为常了。昔时夜家还一如以前一样畅笑着认为仅仅能靠着几件厚衣服就能读过短暂的寒冷的时候,大自然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它犹如猛兽一样平常将全体城市一口吞下,我们仿佛生活在冰箱里一样,新年的来到丝毫未曾减弱寒冬的淫威。 大雪将四处的信息都闭塞了,许久未曾得到纪颜的让我不禁为他们的处境担忧,不过还好,我终于得到了新年的第一封来信。 “你不会想象我这里成了什么样子,从新闻里知道你那里也是灾区,不过和我现在呆的地方想必切实其实便是寰宇之别啊,我本不喜好用电子邮件,不过想想如果写信等你接到的话恐怕要数星期之久了,作为最好的朋友,我实在忍不住要和你分享我的见闻,那怕多一天耽搁我都无法忍受啊,你是做新闻的,该当会有和我相同的感想熏染吧。(看到这里我忍不住笑笑,的确,无论是喜悦还是悲哀,各种各样的感情于人分享都是一件趣事) 或许你和你周遭的人在诅咒这该死的景象,而我却以为这是正常的,只是我们以前常年生活在不正常的环境中罢了,就犹如那句话一样,如果周围所有大家都在撒谎,那你一定也在撒谎。 我和李多忍受着于北方不同的寒冷缓慢龟行到了一处地方,带着湿气的冷和北方的干冷截然不同,总是那种浸透到骨髓和血液中一样平常,穿着再厚的衣服也不中用,就像是你的衣服仿佛刚从水里捞出来又穿在身上似的,为了不被冻伤,我们只好只管即便走快些来取暖和。 山里的空气较之表面更加冷,我们原来打算穿过山路去附近的县城住宿,不过没有想到被冻结的山路比起北方齐腰的雪路更难堪走,我们只好相互搀扶着扶着山壁,但速率却比预想的要慢的多,几近天空擦黑,却也只走了一半不到。然而让我费解的是,以前我曾经来过这里,作为连接前面县城的必经之路,纵然是冻雨也不应该会造成路面情形这么恶劣。 四周没有别的颜色,全是苍白一片,从雪的无缺程度看这里该当没有任何活物经由。 是的,如果按照我们习气来讲,从雪地经由的生物自然要留下一星半点的印记。 终于在险些完备沉没在阴郁之前,我依稀找到了一些足迹。 脚印很小,该当是女人或者孩子的,我随着足迹果真看到了一处偏远的村落。 但这村落庄太小了,远远一看就尽收眼底,不过在这个没有生气的地方能看到人已经让我心头一暖了。 我鼓励着李多快走几步进入了村落庄。村落口居然是一块四米高旁边的木制牌坊,宽两米多,两边个摆放着一只汉白玉石狮,只是木牌坊被冻雨侵袭的岌岌可危,悬下来的冰柱足有一人胳膊长,看起来有好些个动机了 看来,这并非普通的庄家村落庄,倒很像是古代颇有秘闻家世的人隐居在山林里一样平常。 果真,离着牌坊最近的一户人家的门忽然开了,走出一位精壮男人,留着板寸,两耳冻的通红,不但是耳朵,鼻子脸颊下巴全是红彤彤的,像是抹了层厚厚的番茄酱一样平常,但看上去又是硬邦邦的,眼睛半睁着,彷佛有些就寝不敷般疲倦的高下打量着我们,脸上险些没有一点余肉,我可以很好地看到他脸部的骨骼构造,厚厚的嘴唇上油光发亮,彷佛正在吃晚饭。他穿着臃肿的花格夹袄,拢着双手奇怪地望着我们俩,踏着棉鞋的脚踩在雪地上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等走到离我们大概两米多的地方愣住了。 “我说,你们从什么地方来哦。”他的声音也仿佛冻结住了一样,硬而冰冷的砸过来,落地有声,不过沉闷却又干脆。 我简要的阐明了来意和窘境,希望他能住宿一宿。不想他一口谢绝了。 “我做不了主,这里留不留你得听刘爷的。”说完他伸脱手指了指村落庄里头的一栋二层楼高的白屋子。 “你最好赶紧着去,刘爷困觉的早,他只要上了床,就不开门了。”他一边说,一边闪身进了门。 我只好按照那男人的的话去找刘爷,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情也要请示那个什么刘爷。 叫了半天的门,终于开了,不过确实条门缝,里面挪出一个机动的小脑袋,眨巴着大眼睛望着我们。 “天色太晚,我想在村落庄里住宿一夜,希望刘爷许可。”我勉强从冻僵的脸上挤出点笑颜,但估计比哭还丢脸。 里面估计是个孩子,虽然看不太清楚,不过肤色洁白,白的晃眼,只有眼窝子那双眼睛黑的十分俊秀,宛如倒进白玉制造的砚台中的一注墨汁,随时都在晃动一样平常。 也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总之姣好的紧,他(她)点了点头,一溜小跑进了院子。 过了会儿,门彻底打开了,出来一个近五十岁的中年人,双手背在身后,看上去颇为骄傲,虽然上了年纪,却看得出保养的很好。 这里要说一下,人的保养并不只指生理上,比如良好的生活习气,饮食,优质的生活环境。 最主要的却是生理,如果一个人总是忧闷惶恐即便鲜衣美食也会老的很快,不过面前的这个男人显然不是,以是他虽然看上去将近半百,却精神抖擞,脸庞涵雅,即便是寒冷的景象也不为所动,以是我自然认定他是刘爷了。 于是我小声说了句刘爷你好。 他的身材很高大,南方人高的也有,但却很少有这么宽大的体型,不是胖,而是魁梧,他的长相也颇有些不符,宽而厚实的下巴,高鼻梁深陷的眼窝,彷佛略有怠倦,不过依然精神很好,薄而紧闭着的嘴唇终于开口了。 “我是刘爷,你想在这里住宿?”他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多少让我有些诧异。 我点了点头,可是刘爷伸出蒲扇大的手掌摆了摆。 “女的可以,你弗成。我们这里绝对不留表面男人过夜,尤其是冬天。”说完,他又示意我们赶紧走。 “可是这种景象里,等走到能安歇的地方恐怕我们都要冻去世了,您就当救人一命好么?”李多苦苦央求道。 刘爷低头迟疑了一下,接着抬开始爽快地说:“好,留你们也可以,但必须答应一个条件。” 我绝对不会猜到,所谓的条件居然只是要答应他我绝对不可以睡着。 房间里摆放着燃烧的木炭,闻起来无烟,烧起来噼啪作响,火星子像水沫一样四溅开来,还好炭炉周围有铁片围着。 “是上好的乌冈白炭吧。”我问刘爷,他领着我们穿过大院,沿着右边石子路走到偏房——大概十几平米,里面虽然大略,却有床有炭火,还有一套茶具,以及四张圆木黑漆凳。 “哦?看来客人倒是识货啊。”刘爷有些高兴,他很讲究,而讲究的人最高兴的莫过于人家看出他很讲究。 “可是这木炭多产于北方,大老远运到这里利用?”我忍不住问道。 “呵呵,我是北方人,闻不惯烧黑炭的味,以是用自己运的白炭烧,前几年景象暖和到也用的不多,今年用的都是往年留下来的,有些潮了,不过还是很顶事。”从屋子的布局来看,的确不像是南方的住宅,看来刘爷的确是北方搬过来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您答应住宿我们却又不准我们睡着呢?”李多抖了抖身上的残雪问道。 刘爷的眼睛带着暖意望着李多忽然许久不说话,过了会,他又坐到椅子上盯着炭火一字一字地说,虽然声音轻微,但在这房间里却听的真切的很。 “如果你睡着,来日诰日就要到表面去捞你了。”他说完,用火钳拨弄拨弄木炭站了起来。 “你们也不必害怕,我去拿点吃食和酒,本日我也不睡了,陪你们聊聊,人多说话不随意马虎困。”说完,又走了出去。 刘爷的话让我很费解,不过既然他警告我别睡觉就依嘱而为吧,反正熬上一夜总比在表面冻着强。 我看了看表,才七点,但是却以为已经很晚了似的。 吃的东西很大略,却很结实,都是入腹就能产生热量的,大肉馅饺子,厚实的煎饼还有缓缓的温酒,喝下去的确缓和多了。 “别吃太饱,否则随意马虎犯困,见告你,别说睡觉,打盹也弗成!
”刘爷再次严厉地见告我们。我和李多饿极了,只好一边吃一边暗昧地答应着。 忽然房门一开,那个先前开门的孩子窜了进来,像只小老鼠一样平常拉着刘爷的胳膊袖子,仰着头乃怯生生地喊道。 “爷爷。”接着伸出小手等着刘爷抱,一边看着桌子上的吃食砸吧着嘴。李多想叫她一块过来吃,但刘爷谢绝了。不过刘爷没有抱他(她),只是拉着他(她)的手走过来。 “这是我外孙女,你叫她望春吧。”说完,低头叫着女孩,“望春,晚饭吃过了啊,那是客人的。”说着,领着她出去了,小女孩则听话的点点头。 大概过了半小时,刘爷进来整顿了一下,然后三人坐在炭炉边聊起来。 从刘爷口里我知道原来他的确是南方人,只是幼年时候随家人躲避战乱来到这个小村落庄,而这个村落庄到也欠亨俗,古时出过几位状元,这些人走出了山村落走进了京城,功成名就的时候又在家乡建筑了村落庄表面的功德牌坊,这个村落庄也开始小有名气。不过当刘爷一家人逃难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大不如前了,不过当地人毕竟都是识礼讲义之人,以是让刘爷一家人在这里生活下去。 只是,刘爷却始终未曾提及我的疑问,那便是为什么他一个外姓人却现在反而是村落庄里地位最高的。 还有开始的那个男人,虽然说刘爷是这里说话最具份量,但脸上的厌恶之情却是无法掩饰笼罩的。而且谈及到刘爷的家人也总是一语带过而已。 发言的内容越来越少,末了刘爷出去了。而我却逐渐开始以为疲倦,看了看李多,彷佛已经睡着了。我则记得刘爷的话,强打着精神不敢睡过去,可是不知道是否这天间走的太累了,我越来越以为犯困,末了居然真的蒙了过去打了个瞌睡儿,我怕自己再睡过分,于是站了起来,想打开门去雪地上站站,好复苏一下子。 表面黑的很沉,大家都睡了,除了偶尔刮过的风声就只剩下我自己的脚步声了。还好表面不算太冷,不过我站了下还是打算进屋暖和下。 当我转身想开门进屋的时候,忽然看到茫茫雪地上站立着一个人影。并不高,只是孤零零地站在远处功德牌坊之下。 我不想大声喊,怕扰了人家的美梦,心想可能也是过路人,于是迈着步子走了过去。 雪地反射着仅有的一点点月光,让周围产生着一圈圈如水注般的梦幻镜像,当我走到那“人”面前才看清楚。 原来只是一个雪人,这让我哑然失落笑,或许是那个顽皮的孩子堆的吧,远远看去的确很像人一样。 可是我再仔细一看,却又以为不对,哪里有孩子堆的雪人却如此逼真,五官面庞衣饰都出来了,与其说是雪人,到不如说是雪的雕塑品。只是这人却不太熟习,也从来未见过。 而雪人的面貌却分明是我,在黯淡的月光下,我对着其余一个洁白的自己发呆。 忽然我以为雪人动了起来,我原以为是自己眼花,但事实的确如此,它犹如滑行着一样平常朝表面“走”去。 不知道为什么,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于是赶紧回到屋子,带妙手套帽子和手电筒,紧随着雪人走了出去。 它彷佛故意让我随着,总是保持着不紧不慢的速率,而我却叫苦不迭,虽然穿上了胶鞋,却依旧打滑的厉害,以是我们之间始终有一段间隔。 不知道走了多久,总之转头已然看不见那高大的功德牌坊了,我有些犹豫,离天亮尚早,万一在这里迷了路就不妙了,可是如果就这样回去更加不符合我的原则。 雪人的身影开始变的模糊起来,末了停在了一片空旷的雪地上。当我逐步靠近过去的时候,却看到雪人开始逐步的融化散开,末了和雪地融为一体了。 而我的脚下也觉得踩到了什么,彷佛是硬石。 我蹲了下来,哈着气打开了手电。 黑乎乎的一片,我脱去手套用手摸了一下,即便已经冻结的光滑如铁,但我依旧觉得到了,那是人的头盖骨。 我使劲拨开了雪,果真,一个人头露出来,他全体被埋在了雪地下面,两颊青紫,双手环抱在胸前,十指波折,保持着冻去世前的样子。而我从阁下的雪地里陆续挖出了几具尸体。 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冻去世,都是男性。他们的衣饰多种多样,不像当地人。 我意识到了自己彷佛进入了一个设计好的圈套,而我则是猎物。 当我想转身回去,却创造双脚已经被牢牢捉住了,一双如雪般的手虽然纤细却如老虎钳一样平常去世去世固定住了我。 脚下的雪地开始逐步隆起一个大包,雪快滑下,一个留着洁白长发的人形的东西冲了上来。我下意识将手电筒推到最强,然后对着它射过去。 我将一辈子都无法忘却她的眼睛,犹如一颗玄色玛瑙,全身洁白唯有那眼睛漆黑如墨。 她彷佛很畏惧强光,一下又退进雪里,但是我的双脚依然无法移动,气温开始连忙低落,这样下去只要两个小时不到我就一定会冻去世。那东西犹如狼畏惧火焰一样躲藏了起来,只要手电筒光源一断,她又会再次扑过来。 而电池也支撑不了太久。 我必须迅速做出选择,要么站在这里等人来,要不脱去胶鞋,自己走回去。 要么靠别人,要么靠自己,我当然选择后者,我始终记得有人说,如果你打算完备依赖别人,就意味着将后背完备出卖。 我迅速脱去了鞋子,然后脱里面一件毛衣撕扯开来分别裹住住自己的脚趾,然后沿着自己来时候的脚印往回走。 一起上我可以觉得到身后那东西还在追着我,脚趾也由开始的冷开始麻木,我知道自己如果不尽快赶回去即便能逃脱脚趾也会冻掉。 还好,我依稀看到了前面的灯光。 李多涌如今了我面前,而我身后的东西也选择退却了。 李多哭着搀扶着我回到屋子,立即用雪擦拭着脚,万幸,我的脚保住了。李多想去叫刘爷过来,而我则谢绝了,并见告她不要把这事见告刘爷。 第二天日头刚出来,刘爷走到房间里来,他非常吃惊地望着我,而我也看他的眼睛黑了一圈。 “你,居然还活着?”我的现状让原来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一向沉稳的刘爷失落态,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想法,只是还有些事情我必须知道。 “当然,我自己也以为侥幸,如果不是李多赶来救我,恐怕就算能逃出来脚也残废了。”我躺在床上,苦笑了下。 刘爷很快规复了镇静,只是依旧迷惑不解。 “你在食品里参杂了些类似安眠药之类的东西吧,实在从进村落庄的时候我就创造你们的神色很疲倦,像那种长期就寝不敷或者深度失落眠的人一样。当然,我也没在意,只是想了下原来对熬夜无所谓的我居然会睡着而你又不让望春吃才想到。 实在昨晚你压根就没睡,或者说这个村落庄里的男人都没睡吧。”我缓缓地说着,实在只是我的预测罢了。不过刘爷的默认武断了我的意见。 “我只是想知道,你究竟想做什么,昨天晚上的东西又是什么。”我质问着刘爷。 “我不想说那档子事,我作孽太多,要不是怕望春还小,否则早就了却自己了。”刘爷痛楚地闭起双眼。 从刘爷的话中我得知了一个让我心寒的事实,那便是村落外难走的路原来是人为造成的,刘爷让人把水一遍遍浇在路面上,为的便是留住过往的路人,而这样做只是为了包住他们自己的性命,由于每到雪夜,那东西就会出来觅食,而食品则是睡着的男人。 “以是,实在你开始只是欲擒故纵罢了。”我冷冷地说,刘爷摇头。 “我是真的希望你们别留在这里,我已经害了很多人了,实在不怕见告你,你遇见的怪物便是我的女儿。”刘爷的话更加让我吃惊。 “她还未出阁,却莫名其妙大了肚子,我无论如何打骂她也只是哭着说在一个雪夜被人窜进屋子里挥霍了,于是我想遮盖下来,让她生下孩子后送回老家,结果在即将临蓐的时候不知道如何透露了,那时候恰好也是如这般几十年不遇的寒冬,大雪封山,村落庄无法和外界沟通,族长说是我女儿的不贞触怒了功德牌坊,老祖宗怪罪下来,并且逼着将身怀六甲的孩子赶出去,否则就将我们百口驱逐出去,结果,我女儿在雪夜里自己离开了村落庄。”刘爷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痛楚地说。 “一个月后,我在家门口创造我女儿衣物裹着的一个婴儿,便是我现在的孙女,我希望她的到来可以让春天赶紧来,以是取名望春。那之后,只要每年雪夜,村落门口的功德牌坊下就会涌现一个雪人,和雪人长相一样的人只要晚上睡着就会被带走,然后再无音讯,他们说我女儿变了妖怪,而族长几年前也失落踪了,以是没人敢连续呆在这里,可是逃出去的人依旧被折磨着,他们末了又回到这里,不过失落踪的都是男人,于是大家建议骗那些外地人来充当替去世鬼,我也只好昧着良心这样做了。” 刘爷的话音刚落,房门忽然被踹开了,先前在村落口遇见的叫我去刘爷这里的精壮男人领着一群老少爷们闯了进来。他们个个手里提着东西,一脸凶相。 “姓刘的,让你做村落长不是我们怕你,别不识好歹,你居然把事都见告这外人了,往后村落庄里的人怎么活? 从现在开始我们同等保举孙茂是我们村落长了,本来嘛,人家便是老族长的儿子。”中间一个瘦猴似的男人扯着嗓子喊道,然后谄笑着望着那个领头的男人,原来他就叫孙茂。 “刘爷,我敬仰你年纪大,但我们村落庄世代知书达理,祖上还出过状元,你女儿伤风败俗,你自己干净那些缺德事,还连累乡亲们吃苦,我劝你还是别坐这位子了,乖乖养老,立时我就带着大家上山,把那害人精给灭了,不就一个白毛女么,我还不信她成了精了!
”孙茂冷笑着说。 刘爷气的全身颤动,指着他们半天说不出话。 “明明是你们威逼我,说我不去骗那些外村落夫上当就对我外孙女下手,现在反而说是我?”刘爷双眼一黑,昏去世过去。 孙茂连续笑着,“我可没去做那些事,收留那些人的是你,给人家下的也是你,我们一村落人都是读过书,懂仁义,现在我们就去除害!
”说完,一伙人跑出了屋子。 我很想制止他们,由于刘爷的女儿已经不是人力可以杀去世的了,但是我无能为力。 当人群散去,李多扶起刘爷,喂了他一杯水,这才缓过来。而望春忽然跑了进来,拉着刘爷的手。 “爷爷,表面好多雪人啊。”她奶声奶气地说道。我一听心想坏了,赶紧扶着墙走出去。 表面一个人都没有,只有那些男人的婆娘站在门外非常恐怖地望着那些雪人。 日头变的分外昏黄,险些像是被遮蔽了的良心。 几十个雪人站在功德牌坊下面,我逐一看去,却创造没有孙茂的。 一贯到下午,我的脚轻微好点,变带着刘爷和那些女人赶去昨天夜里的地方。 我只瞥见孙茂在,其他人都不见了,他面相痴呆地坐在雪地上,孙茂老婆哭喊着跑过去扭捏着他的身体,但没有什么浸染。 “冷,好冷。”孙茂只是一直地重复这句话。望春看着孙茂忽然张口喊了起来“叔叔的背上有个雪人。” 但是我和其他人什么都没看到,而孙茂却一个劲的弯着腰说冷。 其他的男人都不见了,空旷的雪地里回荡着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这个村落庄完了,刘爷叹着气说。 大家把孙茂带回去,刘爷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么,我只能摇头。 刘爷女儿对温暖的渴望使她变成转门窃去人温度的怪物么,或者就像上古中提及的傒囊一样,将人引回住所就吸干他们的精气。但她却偏偏放过了孙茂,或者说活着比去世现对来说是更重的惩罚。 李多忽然又盯着望春,“你不以为孙茂和望春长的很像么?”她问我。 这个没必要回答,望春则在表面不知忧闷地堆着雪人。 分离前,刘爷说要带着望春回北方,他说望春天生喜好雪,也不怕冷,以是干脆带他去东北,那里有着全国最美最厚的雪。 离开村落庄的时候,我转头看了看,功德牌坊彷佛更加老旧了,上面堆积地雪花将它压的喘不过气来,或许,摧毁只是迟早的事罢了。
----------------

【微信搜索:marking-u】没看够?!
关注麦格光阴公众年夜众账号,随时随地分享更多欢快~
麦格光阴,白领生活第一微刊,一枚有态度、爱吐槽、懂诙谐、无节操的自媒体~每天为您定制化推举:言辞锐利的原形解读,人糙嘴黑的良心影评,内涵风趣的爆笑段子,活色生喷鼻香的深夜福利~
麦格光阴已入驻腾讯、网易、搜狐、今日头条、网易云阅读、鲜果多家威信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