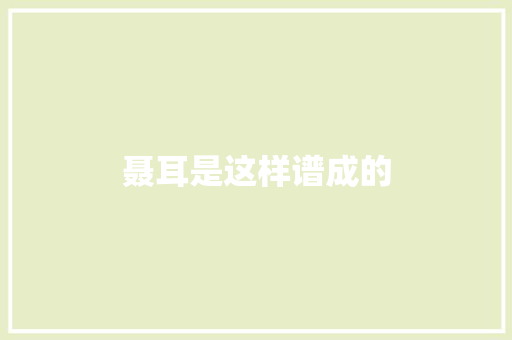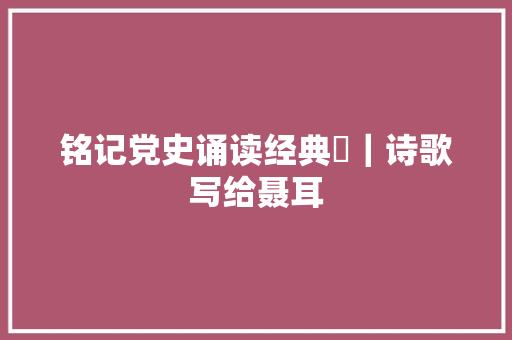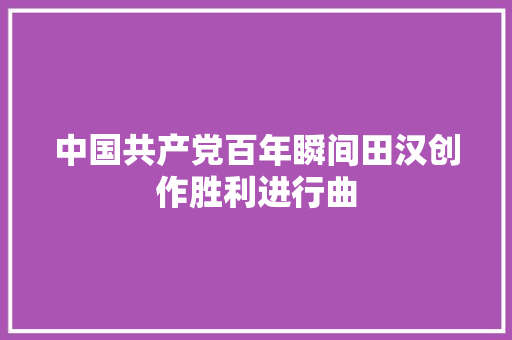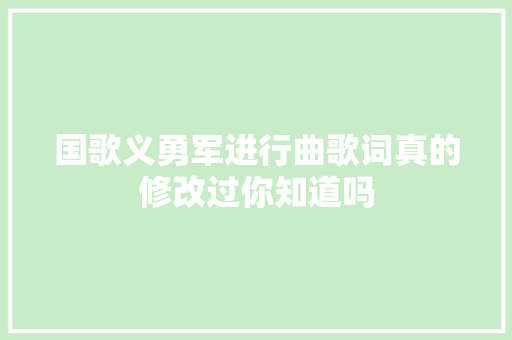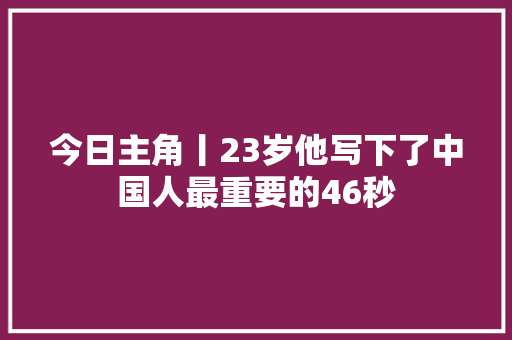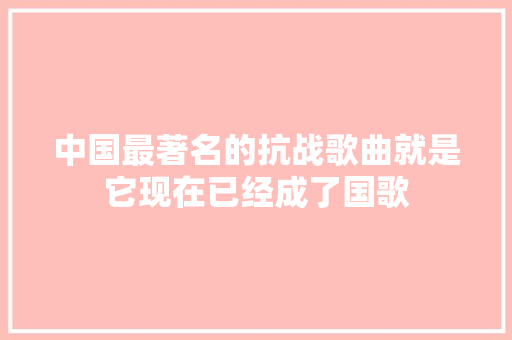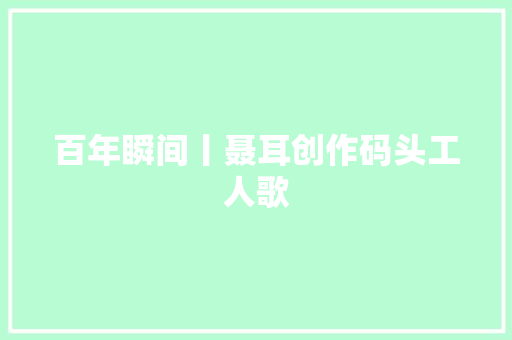而此刻,他的儿子田申——华北独立战车团副团长、代理团长,正在长安街上带领坦克经由天安门受阅。
这个历史的小细节我是在央视《故事里的中国》——《国歌篇》中看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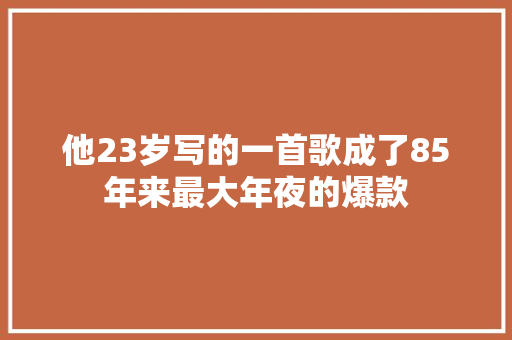
于是,我去重温了这部20多年前的老电影——《国歌》。
1999年,陈坤、何政军主演的电影《国歌》上映,揭开了国歌出身背后的一段往事。
那时陈坤还不是厂花,何政军还没有变成李云龙的政委。
影片在火车站台的鼓噪中开始,那是开往东北抗日前哨的列车。
在沙场上,日军面孔狰狞,去世亡触手可及。
但“他”一边愉快地指挥着合唱,一边响亮地喊:不要用去世来恐吓我们!
他便是聂耳。
彷佛音乐与梦想从来都是少年人的权利。
有人说,惊鸿一壁,他便是那个最通亮的少年。
的确,电影《国歌》虽然评分不高,但陈坤饰演的聂耳却成为了那个最通亮的少年。
我所知道的《国歌》的故事与影片中不同。
现实里,田汉在电影《风云儿女》最初的故事中写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或许是导演以为这样不足大气,在电影中就让他在风雪交加之夜,在空无一人的大厅内,挥毫泼墨,写下那今日让每个中国人都振奋民气的句子:起来!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导演吴子牛在《故事里的中国》节目中对撒贝宁说,何政军在演完这段戏后,在阁下的角落里足足哭了五分钟,久久无法抽离。
这部电影从艺术的角度看来其他地方都很平凡。
唯一的亮点便是在田汉入狱往后,《风云儿女》的剧组职员乘着一叶扁舟溯流而上,从上海,到南京。
在清晨的微光下,在高墙外,用一只连着大喇叭的留声机,播放聂耳写好的曲子给全体监狱里的人听。
囚犯们骚动了,警卫也随着囚犯们一起听,悄悄地听,宽容地许可船上强忍悲哀的剧组职员们将这首歌放了一遍又一遍。
也正是在那一刻,现实与影像交织,从来没有以为《义勇军进行曲》那么好听过。
但无论现实还是电影,彼时,那个通亮少年都已经去世在异国他乡。
而14年后,站在天安门不雅观礼台的田汉一定想到了这个少年,一个与自己相差了十四岁的小老弟。
韶光拉回到1931年,年仅19岁的聂耳与时年33岁的田汉第一次见面。
就在前一年1930年的7月,聂耳由于在昆明参加学生涯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注目,不得不顶替他的三哥聂叙伦到上海“云丰申庄”去当一名店员。
后来“云丰申庄”倒闭了,1931年4月,19岁的聂耳考入了“明月歌舞剧社”当小提琴手。
在明月歌舞剧社初识彼此的两位,作了一次长谈,聂耳不平凡的经历和十分困难的家世,还有他火一样的革命朴拙,使田汉深受冲动。
也正是因此,虽然田汉当时已是上海文艺界的大佬,大家尊称“田老大”。
而聂耳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少年,但俩人还是一见如故,都有相识恨晚的觉得。
1934年的夏天,聂耳为田汉创作的电影剧本《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
这首表达了广大青年学生抗日爱国激情亲切的作品,成了当时最盛行的歌曲之一。
或许那时的他们已经意识到用音乐可以唤醒中国人。
同年,田汉创作出新歌剧《扬子江狂风雨》,全体歌剧的作曲,全部交给了聂耳。
与此同时,聂耳还担当了全剧的导演和主演。聂耳在剧中扮演了码头工人老王。
经由紧张繁忙的努力,歌剧终于要上演了。
但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统治下的上海要找到一个演出进步戏剧的场所是十分不随意马虎的。
当时的上海麦伦中学,有一批进步的教职员,他们请校长出面,利用筹建该校体育馆搞募捐的名义,才借到了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供《扬子江狂风雨》作首次演出的地点。
歌剧连演三天,每天两场的戏票全部售完,盛况空前。
这次互助,田汉终生难忘。直到解放后的1960年10月,他在上海看《扬子江狂风雨》重新彩排时,写了一首《忆聂耳、冼星海》诗作:
黄浦滩上路,熙攘未大改。
当时中国人,今日作主宰。
崇楼入云汉,巨舶耀光彩。
培植新国家,汗水任挥洒。
扬子风雨暴,黄河浪涛骇。
当时新乐府,赖于起衰怠。
生命虽短匆匆,艺术是千载。
紧接着,1934年秋日,田汉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奋起抗日为题材,创作了一个电影故事《风云儿女》。
当时由于白色胆怯席卷上海,田汉不能公开露面,是躲在一个小旅社临时租用的房间里写作的。
而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就出身在这里。
田汉把它写在了《风云儿女》文学剧本第十五章的结尾处。
田汉在写到男主角辛白华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末了一节,创作了一首冲动大方旷达的自由体诗。
这便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初稿。并刊登在《电通半月画报》的第二期。
但此时这首自由体诗并没有名字。
但关于《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出身,流传甚广的版本是这样的:
田汉在狱中用喷鼻香烟锡纸写成,并由其妻子传出来。
到了1980年代,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谣传再度在社会优势行。
当时夏衍还专门在1983年2月14日的《北京》上揭橥了文章,澄清这件事情。
后来夏衍把田汉在出租屋内写的那个故事改成了电影文学剧本《风云儿女》。
再请大导演许幸之写身分镜头脚本,于1935年月正式开拍。
而1935的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田汉在送走赶赴苏联演出的梅兰芳同道回家后不久,就被捕入狱了。
聂耳闻说田汉被捕,义愤填膺,他不顾白色胆怯的恶劣环境,主动请缨,哀求担当起这首主题歌作曲的任务。
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聂耳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曹家弄的三层阁寓所内,险些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事情。
一下子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下子坐在钢琴前弹琴,一下子在楼板上一直地走动,一下子又年夜声地唱起来。
搞的房东老太太很不高兴。
惹恼了房东老太太之后,聂耳后来又不得不搬到《风云儿女》的录音师司徒慧敏的家里连续完善初稿。
司徒慧敏也是后来《义勇军进行曲》第一代演唱者之一。
而电影中戏剧性的是,也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面对面前田汉的歌词,聂耳正如痴如醉的谱曲。
这是我第一次想到伯牙与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
而这一幕也被还原在王源、王洛勇紧张的话剧《故事里的中国——国歌篇》中。
电影中,面对赶来赶来劝他东渡出国的夏衍,聂耳却想要营救田汉。
这一段影像映照了现实:
田汉被捕后,聂耳也被列入黑名单。
为躲避反动当局的追捕,党组织决定让聂耳取道日本去苏联学习音乐。
他于1935年4月15日清晨离开上海,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带到日本进行修正。
4月尾,聂耳从东京把修正定稿的曲谱寄给上海的司徒慧敏。
《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拿着这首歌曲找到了当时还在上海国立音专学习的贺绿汀,请他帮忙为之配乐队伴奏。
贺绿汀找的是侨居上海的俄国作曲家阿尔夏洛夫配写的伴奏。
之后,为了使歌曲波折衷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电影《大路歌》的编剧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3处修正,从而完成了歌曲的创作。
如前面所说,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往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
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
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从而把该曲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5月初,《风云儿女》的出品方“电通”公司即组成了由盛家伦、郑君里、金山、顾梦鹤、司徒慧敏等参加的小合唱队,进行试唱排练。
5月9日,在徐家汇东方百代公司的录音棚里,第一次将《义勇军进行曲》灌制成唱片发行。
其后再把唱片上的录音转录到电影《风云儿女》的胶片上。
影片的插曲和主题歌配乐均由贺绿汀作曲。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先后在5月10日的《中华日报》副刊和6月1日出版的《电通画报》上揭橥。
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今贵州路黄浦戏院)首映。
戏院里响起了“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末了的吼声……”的歌声。
从此,《义勇军进行曲》雄壮豪迈的歌声响遍了全中国每一个角落。
就这样,相见恨晚的两人终极以“隔空”的形式完成了此生末了一次互助。
只是那时候他们都没故意识到。
两个月之后的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拍浮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几天之后,田汉经营救保释出狱,当他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时,心情很是激动,他对聂耳谱的曲子非常满意。
现实正如电影一样平常戏剧。
这是遗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最伟大的义务已经完成,见与不见又何妨呢?
只是,彼时的田汉不会想到,他的终点会闭幕在那荒诞的十年动荡里。
聂耳溺亡后,田汉赋诗道: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正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去世生?
乡国如今沦巨浸,边陲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随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
这首诗后来被镌刻在昆明西山聂耳墓碑的侧墙上。
1940 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接着他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
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媒介,使这首歌享誉天下,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一首高昂的战歌。
而《义勇军进行曲》真正成为(代)国歌,是1949年中华公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当时,要从1000多首作品里选出一首作为新生的中华公民共和国的代国歌。
而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是画家徐悲鸿。
后来,《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几经修正。直到1982年,一贯被改来改去的国歌歌词终于又回到了原点,规复了本来面孔。
同年,《义勇军进行曲》以全国人大正式立法的办法成为中华公民共和国国歌,而不是代国歌。
虽然故人已逝,但田汉与聂耳的交集并没有结束。
1945年,田汉带领田维儿童剧团来昆明演出时,曾专程到西山聂耳墓哀悼过。
后来,1954年2月,他带领全国公民慰问解放军云南分团代表团到昆明慰问时,又第二次到西山扫聂耳墓。
1968年12月10日,田汉在“文革”中被肆意摧残伤害,去世于狱中。
至此,《义勇军进行曲》的两位词曲作者,先后离开了人间。
一个去世于敌国,一个终于自己人之手。
这一次,现实上演了电影的戏剧性。
那是他们奋斗生平要赶走的仇敌。
那是他们奋斗生平要保护的人。
电影《国歌》结尾,出狱的田汉执意要从南京返回将要沦陷的上海。
他说:中国不会亡。
然效果断地走在阴郁隧道中的光明里,向着光明的未来走去,国歌响起。
或许那时的他不会想到,站在开国大典不雅观礼台上的他更不会想到。
他的结局,不是在战火中,而是在新中国。
他在痛楚中去世在病床上,而广播里正放着《毕业歌》,那是与故人聂耳的第一次互助。
古人说:“同声若鼓瑟,合韵似鸣琴。”
古有伯牙与子期,琴瑟和鸣。
子期亡,伯牙遂破琴绝弦。
我第一次感想熏染到冰冷的历史添补了细节之后尽是冲动。
一首《国歌》背后,家仇国恨中夹杂的,不正是一个琴瑟和鸣觅知音的故事吗?
更多影评关注公号:娱不雅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