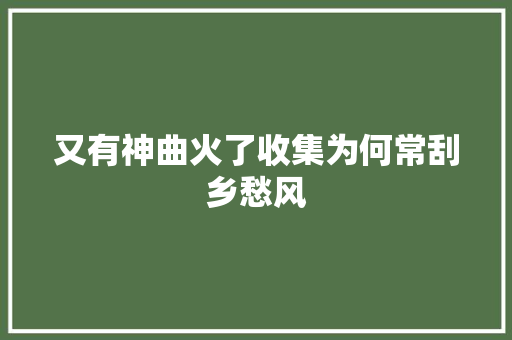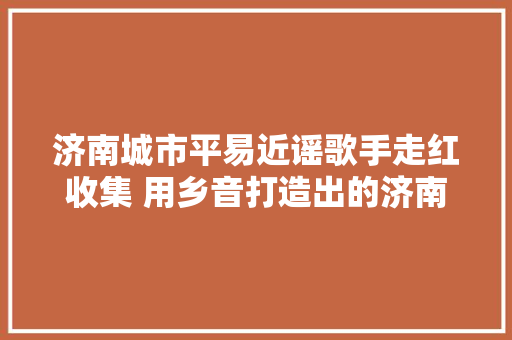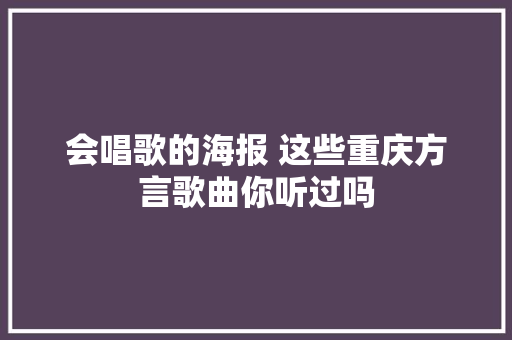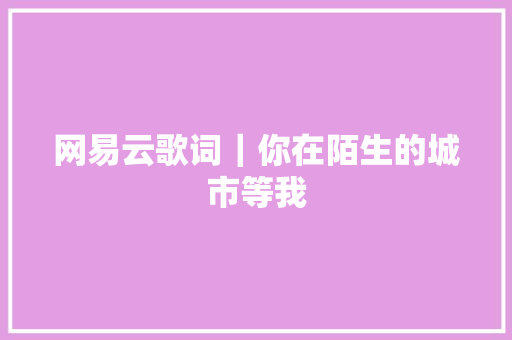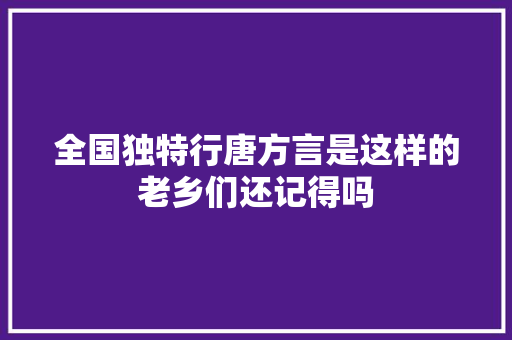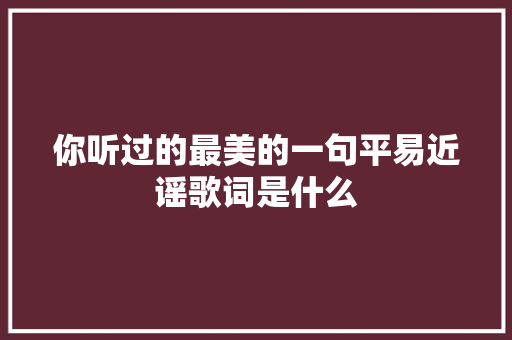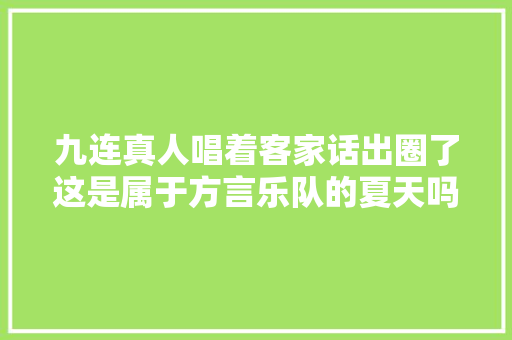编辑 | 黄月
从近期的一档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中,不雅观众们看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音乐演出。新人乐队“九连真人”的《莫欺少年穷》和“斯斯与帆”的《马马嘟嘟骑》尤为引人瞩目,这两首歌曲的共同点在于都以地方方言为演唱措辞——前者以客家话演唱,后者唱的则是常德话。与常德话比较,客家话明显更难堪懂,其发音与普通话差别较大,字词构造也有所不同,比如说字幕表述为“眼高手低、奔波不屈稳”的歌词,其原文是“看唔起/放唔落/毛线毛着落”。节目也呈现了现场听众对方言歌曲的反应,“这是哪里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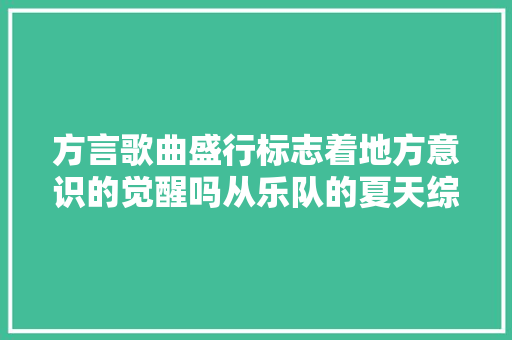
既然听众理解起来难度颇高,为何歌手还要选择以方言演唱呢?苏阳曾在接管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时提到,“为什么音乐的地域痕迹重?由于你就生活在这个地方,就要唱最近的地方和够都着的东西。花儿就唱一个锄头、唱个树枝、唱个鸟,一天到晚便是麦苗长了、麦苗短了、麦苗青了,唱来唱去都是这个题材。”近年来以方言演唱的乐队或音乐人实在不少,比较著名的有用西北口音演唱的苏阳、马飞和低苦艾乐队,还有以上海话演唱的“顶楼的马戏团”(已经终结)、以东北方言为根本的“二手玫瑰”,以及以西南口音(如重庆话、贵州话)的rap形式出名的一批嘻哈歌手。
从中我们可以不雅观察到,对付音乐人来说,方言不仅是创作或演唱的外壳形式,也使他们得以在普通话及北方口音的演唱主流之外开辟另一片天地。乐评人李皖在《向民歌寻源,用方言歌唱》一文中写到,方言歌曲的浸染犹如地方志、山村落大不雅观、县城万象一样平常,呈现了普通话主流音乐之外的天下。
的确如此。在可被视作“地方志”的方言音乐中,我们得以一窥与自己差异巨大的生活履历。比如重庆嘻哈歌手GAI和贝贝的《只手遮天》(重庆城/红岩魂/酆都江边过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好帮你修做坟),唱的是重庆孕育的充满草莽气息的生活;西安歌手马飞的《两个科学家吃面》(本日早上又没洗脸/又是我一个人吃的饭/遇见个熟人/打了个呼唤/我进了家牛肉面/我说老板/来个辣子多的油泼棍棍面)则慢悠悠地讲述了一个西安人从早起、吃面到和老板闲扯的经历……对付这些音乐地方志所反响和代表的生活履历和地方意识,我们或许还应做出更细致的探寻。
以方言唱歌:北方的曲艺风格,南方的地区意识
有关地方饮食的歌曲是方言歌曲中一个不错的范例。天津岩石乐队主唱李亮节的《大饼卷统统》唱的是天津卫的大饼,歌词繁复地铺陈了大饼的内容及其味道,比如“大饼卷鸡蛋好吃又好看/大饼果子配豆浆它味道特殊浓/大饼卷炖牛肉怎么吃都吃不腻”,最富有文学修辞性和想象力的是“大饼卷素丸子它架炮往里轰”,以及将大饼的味道形容为“酸甜苦辣咸/鲜喷鼻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在《乐队的夏天》节目中,熊猫眼乐队的《我爱吃烤鸭》以北京腔咏唱了北京烤鸭的吃法——“一张饼卷一只鸭”“加点葱再加点黄瓜”,比较于《大饼卷统统》而言较为简洁。
这两首歌曲的共同点不仅在于以方言演唱地方特色——不管是烤鸭还是大饼,都已经成为了颇具代表性的城市标志——还在于二者都融入了地方曲艺风味。《大饼卷统统》第一段在铺陈了大饼的各种正经吃法之后,第二段如相声段子一样平常抖出了“大饼卷统统”的包袱:“大饼卷皮皮虾怎么能够不扎嘴/大饼卷炸蚂蚱为民除害虫”。《我爱吃烤鸭》虽然歌曲大略,但也融入了北京曲艺的味道。有评论者认为《我爱吃烤鸭》与大张伟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这实在并不奇怪,大张伟曾说自己的歌曲《穷愉快》结合了太平歌词《十三喷鼻香》的风格。(有趣的是,李亮节还创作过其余一首天津烤鸭主题的歌曲《莎莎烤鸭真好吃》,用七言绝句的形式夸奖天津烤鸭“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景象半明朗/油少皮酥肉质厚/莎莎烤鸭味道纯”。)
比这几首歌更进一步的是西游乐队的系列歌曲,《玲珑塔》《口吐莲花》《同仁堂》和《满汉全席》都改编自相声名段。歌词唱道“先变个珍珠倒卷帘/再变个狮子滚绣球”,“请来马连良/再请谭富英”,无疑是借用了晚清的京津曲艺的套式。来自东北的“二手玫瑰”常常被戏称是“二人转摇滚”,在演唱中,二人转那种戏耍式、拖长式的唱腔,以及“哎呀我说”这类口头禅,与命运、生存、意义等严明拷问奥妙结合——“哎呀我说命运啊”“大哥你玩儿摇滚/摇滚它有啥用啊”——风趣与严明、庸俗与崇高在这里混搭并构成反差,达到了反讽的效果。
在听完受相声、太平歌词、二人转等北方曲艺影响的北方方言音乐之后,走进南方方言音乐,我们可以创造,地方性的认同与守卫意识已经崛起。上海已经终结的“顶楼马戏团”不仅有唱上海申花足球队的歌曲(《申花啊申花》)、唱上海人空想中的隐匿之处崇明岛的歌曲(《崇明岛》),还有一首《南方个南方》,堪称抗议北方小品演员污名化南方人物形象的宣言。
《南方个南方》也如同一场小品,炮火集中于常常在晚会上饰演南方小男人的辽宁籍演员巩汉林。歌曲先是勾勒了巩汉林的生平和专业经历,“师长西席巩汉林/籍贯是辽宁/师傅是唐杰忠/国家一级演员/师长西席巩汉林/专业攻小品/差错是赵丽蓉/特长演南方人,”接着调侃道,“巩汉林师长西席/伊一点勿像南方人。”虽然整首歌彷佛都在说巩汉林不是“真正的南方人”,但他到底是不是南方人、什么才是南方人,实在并非这首歌所要表达与磋商的重点。在这里,“顶楼马戏团”借由上海话来发布某些人不具有代言南方的资格,意图表达的是对由北方方言主导的措辞类诙谐节目中南方声音的长期缺席的不满。
值得一提的是,“顶楼马戏团”武断不移地用上海话歌唱上海故事,在其他不同的歌曲里也触及到了疑惑北方方言一统天下的主题。在另一首《海风》里,他们用上海话问到,“听说天下将要天下大同/但请侬见告我/究竟想要我哪恁做?”纵然不用上海话演唱,演唱者的吐字习气也会暴露他们的地方属性,比如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摇滚乐队“铁玉兰”的摇滚单曲《回家的路》,个中平翘舌音不那么分明,副歌部分“我走在回家的路,记得我们曾存心追逐”的发音明显受吴语入声发音影响,也被认为上海风格显著。
上海话并不孤单,从最近网络热门的一段吴语RAP大凑集中可以看出。在这段视频中,演出者有上海人、杭州人、嘉兴人、宁波人、苏州人和宜兴人。在上海即将拆迁的乔家路上,他们途经拎着菜篮子的姨妈和身穿西装的房产中介,每人一段,协力完成了一首吴语RAP。他们唱出了各自家乡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或是最光鲜的特色——杭州开过G20,嘉兴有五芳斋粽子摊,上海人谈吐有风姿还有嗲囡囡(囡囡指女孩),苏州人听评书爱打牌,宜兴盛产陶器等等——他们意识光鲜地以“江南的兄弟”名义凑集在一起(嘉兴段),唱道“苏州杭州rap paradise”(杭州段)、“苏州杭州宁波上海,吴侬软语听阿拉帮侬盘起来”(上海段)。
有趣的是,“高铁”一词在这段歌曲中涌现了多次,他们唱到城市在高铁穿行中处于哪个位置,以及高铁如何联结了江浙沪三地的朋友。来自嘉兴的歌手唱到,嘉兴的地理位置是上海与杭州高铁之间“拐个弯”;宁波人则唱到,喊上海朋友来吃夜饭,两个钟头动车高铁定时来到南站——在这几个城市之间,高铁的密切往来也进一步巩固了吴语区的联络想象。在发布这首歌曲MV的微博中,制作方表示,发布这段音乐的目标是吴语RAP复兴,“代表吴语文化发声”以及“用自己的母语表达自己的态度”。这大概正与李皖的说法——“选择唱方言,是一种主动选择,显示了对本民族、本族群文化认同的觉醒”——相吻合。
被滥用的地方性:当“南方”“北方”沦为民谣俗套
然而,方言音乐并不即是标榜地方性的音乐。这些根植于中国各地地方履历的歌曲虽然事实上演唱着东南西北各个方位,却与那些常常涌现抽象“南方北方”意象的歌曲有所不同。
在近年来的民谣中,我们可以看到“南方”“北方”的说法频繁涌现,地名乃至也作为抒怀工具而直接入题,比如赵雷的《南方姑娘》以及《成都》。但事实上,这两首歌所描述的“南方”或成都,可以适用于中国险些所有大中城市。《成都》歌词里的成都意象仅有玉林路的小酒馆,而其最动听的副歌部分——“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一直留”——与这座城市的气质以及人们的生活险些没有关系,仿佛是一位游客匆匆途经的写生之作。
这一类以城市命名却与城市关联甚少、犹如游客抒怀之作的歌曲并不少见。高进的《下雪哈尔滨》所唱的哈尔滨,与成都一个东北、一个西南,险些处于对角线上,两地从景象风土到人情方言都差距甚大,然而,除了题中地点标志性的中心大街、索菲亚教堂、道里道外,两首歌曲的歌词意象十分相似。《下雪哈尔滨》的副歌部分唱的是,“在没路灯的大街/我走不才雪的哈尔滨/当风霜撕碎年轻的面庞/在没冬天的南方/你如果遇见下雪的哈尔滨/就抱紧我/就当青春没走远。”对应的画面仍是主角在城市的街道上走来走去,纵使街道上路灯熄灭也不愿意离开,惋惜着已然失落去的恋情与青春。
至于此类歌曲中对南方和北方的描写,诸如“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马頔《南山南》)、“当你整顿行李回抵家乡/我的余生却再也没有北方”(宋冬野《关忆北》)等等,“南方”和“北方”在这些歌词中被抽空内涵,变成了一种寄托失落败恋情、青春走远的软弱的想象。另一方面,也可能正是借由这种失落去了详细性的空荡的抒怀,这些歌曲迅速地打开了介于民谣与盛行之间的音乐市场。
如果将这一种“南方”与“顶楼马戏团”《上海童年》中的南方比较,我们会很随意马虎创造两者之间的不同。它们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前者是普通话、后者是上海话,还在于前者总是忧伤的、湿润的、失落恋的、青春不再的,而后者的故事里有人在大光明吹凉气、去外滩谈朋友、去肯德基小个便。
“顶楼马戏团”的私人回顾当然仅仅是地方方言音乐的一种,低苦艾乐队对付北方城市兰州的歌唱就没有那么详细噜苏,而因此地标和方言汇聚成了边塞诗歌一样平常的、意象恢宏开阔的歌词:“从此寂寞了的白塔后山今夜悄悄落雨/为东去的黄河水打上了霎时的荡漾/千里之外的高楼上你彻夜未眠/兰州总是在清晨出走/兰州夜晚温暖的醉酒/兰州淌不完的黄河水向东流。”与那些用南方北方寄托青春爱情的例子比较,“顶楼马戏团”和“低苦艾”的名贵之处就在于,每个字都落在地面,没有人生活在空中。
如果将南方和北方作为一种创作套路或速成模板,人们完备可以复制出一百个城市的、与《成都》相类似的主题歌,但这些歌曲与地方性之间究竟有多少关系,这一点颇令人疑惑。与之相似,一些民谣中的女性形象(紧张是妈妈、姑娘、妹妹、姐姐)也被滥用到了令人迷惑的程度。而当地方性与女性形象两者结合,险些就构成了表达情欲渴望工具的完美典范,就像赵雷《南方姑娘》所咏叹的——“北方的村落落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好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沉着悠扬/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南方”“姑娘”“悠扬”和“忧伤”这些意象险些可以互换利用。如果我们可以用它的歌词风格来做出评价,我们或容许以说,这是一首沉着悠扬、温暖忧伤的南方之歌。尧十三的《南方的女王》也是关于穿越南方北方来相爱的抽象故事,歌词中我是“悲哀”的、梦是“匆忙”的、爱情是“当仁不让、空空如也”的。事实上,这些词语的混搭配套可以排列组合出许多不同的歌曲,这一点在近年盛行的民谣中不丢脸到。
地方性存有被滥用的可能,方言也会被疑惑被挪用为盛行的工具,就像歌手们会在歌曲中穿插大略的英文、法文、韩文或日文短语以抒发感情一样,一些方言也进入了盛行歌曲。歌手王源在《我是唱作人》舞台上演出的歌曲《吆不到台》中也有一段重庆话RAP演唱,“我都是吆不到台,我都是重庆的崽”,他在歌词中交出了出生在沙南街、上学在南开的个人地方简历——如同一张歌唱地方性的合法性证明。但由于《吆不到台》的featuring显示为GAI,歌词中还涌现了那句标志性的“勒是雾都”,RAP部分与前面的歌唱明显割裂开来,歌曲的原创性也受到了一些网友的质疑。这段RAP是否真情实感我们暂且不论,值得思考的一点是,如果说“勒是雾都”可以从一句地方性的呼号变成可被挪用的盛行语,那么地方性是否也有着分开详细地方语境、成为不雅观光广告的危险呢?
国音之争:什么是标准的,什么是分外的?
宽泛地说,歌词也是文学的一种,而如果将磋商方言歌词等同于谈论方言文学的意义,那么就会牵扯到方言应不应该入文学、该当以若何的形式入文学的问题。
上海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被视为近年来吴语方言写作的代表;以双雪涛、班宇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东北作家也创作出了包含东北方言、颇具东北特色的小说。有趣的是,就在《三联生活周刊》今年一期以“讲述东北”为主题的内容中,学者梁鸿彷佛反对将地方文学的地方性看得太过分外,她说,地方写作既要写出地方性,也要写出普遍性,比如东北作家迟子建写作的主题既是地域生活,也是人类的大历史,真正使一个写作者脱颖而出的还是“根本性的人类存在”。
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理解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真的存在着抽离详细地方的普遍人性吗?将这个问题再向深处推进,我们会创造,实在核心的难题在于谁应该被视为普遍的、标准的,谁又应该被视为分外的、地方的。“顶楼马戏团”唱的上海故事一定是局限于上海的分外体验吗?操着北京口音的乐队所歌唱的内容便是可以推广于全国的普遍履历吗?标准与地方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而确然存在着权力的次序——如果仅从措辞的利用来看,这个问题就转换成了:为什么某些方言能够成为代表全国的措辞,而有的方言却是局限的、分外的(乃至短暂而不可持续的)存在?
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的《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当代中国》一书中,他回顾了20世纪初国语措辞标准运动中北方方言是如何降服南方方言,取得全国性的主导地位的。王东杰揭示道,国音标准的形成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南北双方的拉锯斗争。在国语标准构建之前,明清官话分为两个别系——一个是南音,代表是南京话;另一个是北音,代表是北京话——这两种音都是官话的根本方言。而在近代国语标准构建的过程中,京音派势力逐渐壮大,即便如此,一些南方人仍旧表示不服气,他们认为京音也不过是一种方言土语罢了,并没有代表全国的资格(直到20年代,吴稚晖还在强调京音不过是一种土话)。
南北音的主要差异之一就在于,南音有入声、浊音,北音则没有,这也成为了南音派攻击京音派的主要论据。在1913年开幕的读音统一会上,南北双方据浊音和入声展开了辩论。南音派认为,没有入声和浊音,所有诗词韵文的读法皆一扫而空;京音派则认为,加上浊音的话,“我全国公民世世子孙受其困难”。王东杰剖析道,南方文人对北京话不以为然的态度,表示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雅俗之分和阶级意识,由于近代以来江南文化水准远超北方,“江南人士自视前辈,北方士人则明显底气不敷,”以是,只管京音已占上风,心存雅俗之辨的读书人仍旧崇尚南音。
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际,口语又成为了国音国语的候选代表(虽然那时各地的口语没有统一标准,每每是各写各的、夹杂着土话的口语),主见者仍旧在攻击北京话是土话。1917年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就号召新文化运动者自觉担当制订“标准国语”的任务,否则难道要“专用北京土话做国语吗”?陈独秀回应说,“用国语为文,当然采取各省多数人通用的措辞。北京话也不过是一种特殊方言,哪能算是国语呢?”当20年代旁边注音字母揭橥、《国音字典》刊行,国语标准已经向京派倾斜时,南音派仍有斡旋争取的可能,节制教诲部实权的吴稚晖、钱玄同、周作人等人能够通过“修订”国音的办法来平衡南北方的势力。1919年,注音字母中还添入了一个表入声的字母。
虽说京音派逐渐以“活措辞”(真正有人利用的语音)取得了对“去世措辞”(那种想象中的飘在空中的、无人利用的语音)的胜利,终极节制了国音标准的话语权,成为全国标准音的根本,但总的来说,京音在之后数十年间还是面对着无数的质疑乃至不屑。这种质疑有针对付北京中央地位的,有针对付发音是否与传统接续的,还有针对付文化专制的危险的。而正是这些关于中央与地方、当代与传统、专制与民主的各类谈论让我们看到,标准并非从天而降,而始终处于质疑与辨析之中;更主要的是,国音标准的形成不仅关系到入声、浊音的去留,还关系到如何塑造一个空想的中国。这可能也是我们磋商方言歌词、然而又一直留于方言歌词分外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