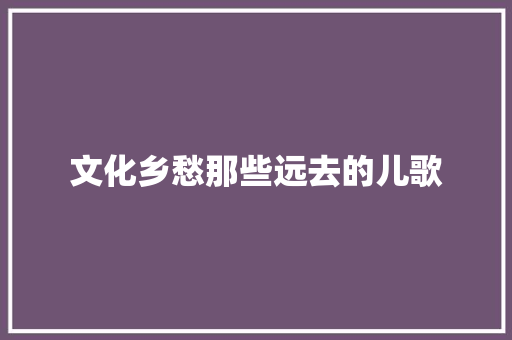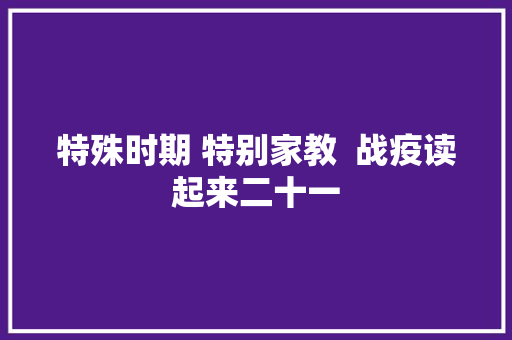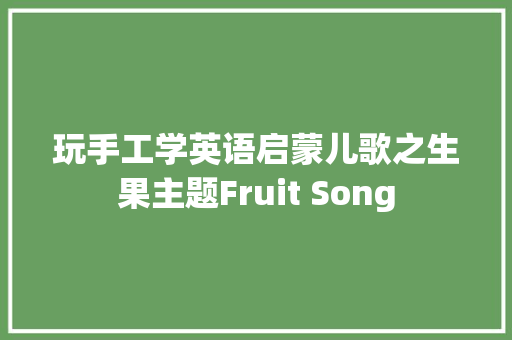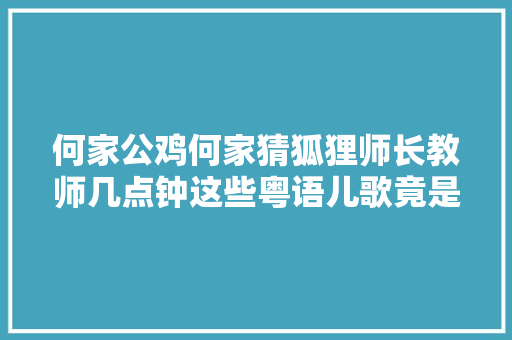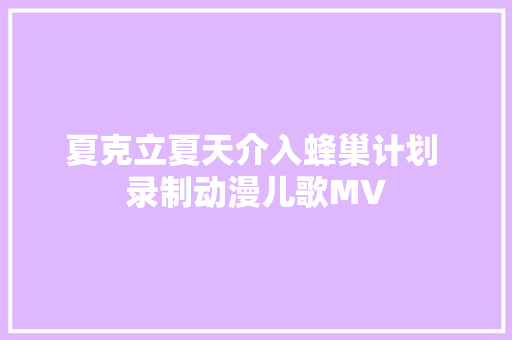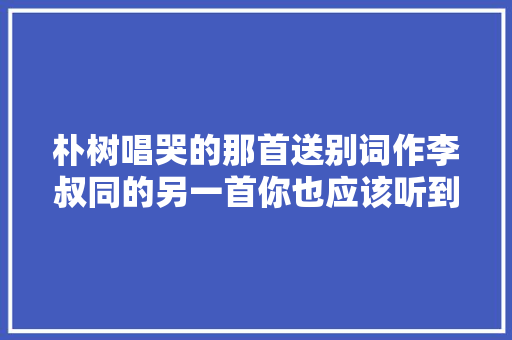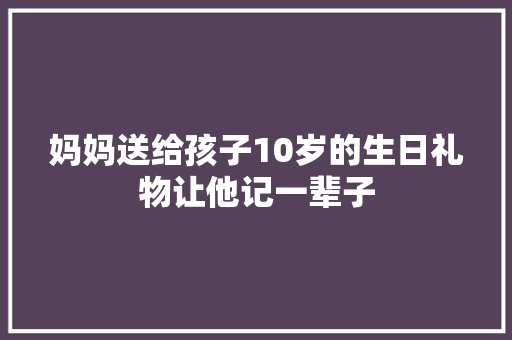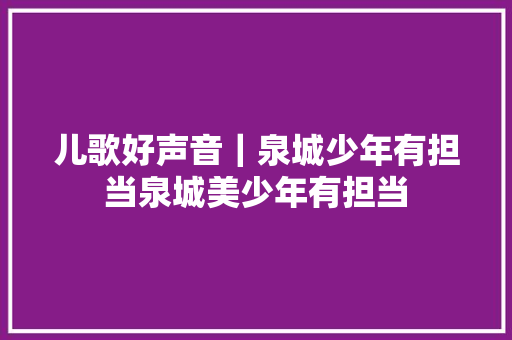腰里别个花手巾。
你丢了,我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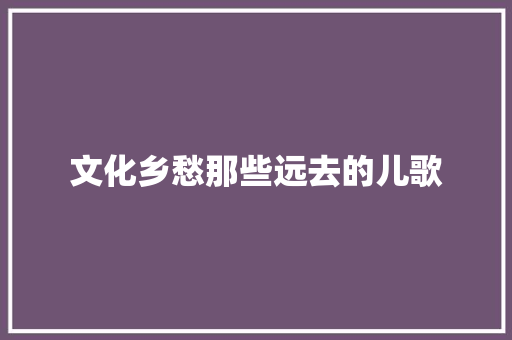
骨碌、骨碌进城了。
你卖啥?我卖烟。
你卖啥?我卖粉。
我也不吸你的烟,
你也不搽我的粉,
咋俩打个琉璃滚。”
小儿子的出生,使我们累并快乐着。来我们家帮忙引孩子的表姐年近70岁,时时地哼唱些老童谣。妻感到有些“土气”,我却不以为然。当年,我们70后不都是听着哼唱着这些终年夜的么?小时候,最怕冬天的早上起床。冷冷的“里梆儿”(里间、寝室) ,黑黑的墙、沉甸甸的被子,总想赖在暖活活的被窝里面不出来。娘做好饭,给我穿衣裳了,我百般抵赖。有时说:“太早了!
”赌气不起床;有时又说:“太晚了!
”还是赌气不起床。娘就会说:“夜黑(夜晚)做个梦,老鼠噙个杏,一走一呱嗒。想给你捎回来吧,怕你咬不动。”我会问:“真的?”娘就说:“真的做了梦。不过杏没有捎回来。你起来吧。今黑再做梦了捎回来。”晚上的童谣最多。有玉轮的晚上,我们会说:“月奶奶,黄巴巴。爹织布,娘纺花。小孩儿哭着要吃妈儿(奶),拿哟蒸馍哄哄他。爹一口,娘一口,咬住小孩的脚趾头。”等我大些的时候,在玉轮地里玩。小伙伴们会一齐喊道:“玉轮走,我也走,我给玉轮牵牲口。一牵牵到玄月九,开开后门摘石榴,石榴树上卧斑鸠。问问斑鸠吃啥饭,臊子面条肉浇蒜。谁烧锅,黑老婆;谁点灯,扑愣愣;谁铺床,小孩他娘。”洗了小脚脚上床睡觉。我与哥哥坐在一起,娘又会一边用手指捣着我们的小脚丫,一边唱起“捣跟脚”:“捣、捣、捣跟脚,亚亚(腰)葫芦扯簸箩。簸箩东,簸箩西,簸箩南,簸箩北。扁担曲儿,吹叫曲儿,小金莲,蜷一只儿。”末了一个字落在那只脚上,那只脚就要蜷缩回去。有时候,哥哥还会用他的手,轻轻地抚摸我的膝盖,口中念念有词:“一抓金,二抓银,三抓不笑是年夜大好人。”有的童谣,大概是咿呀学语时教给小孩子的。如:“俺家近,恁家远,狗咬住,俺不管。”“一二三四五,蛤蟆背着鼓。瞎子来算卦,摸住驴屁股。”有的是学走路时说的:“沿杆儿沿桥,掉河里,冇人捞。”有的是能被大人背了,口中念叨的:“背缸背罈,骑马卖鞋。”玩耍中,有的孩子相互攻讦:“凉荫里,老(‘很’的意思)凉爽。日头地儿里晒鳖盖。”对方回答:“凉荫里,叫(让的意思)狗卧。日头地儿里老(‘很’的意思)暖和。”男孩子喜好去河里、池塘里玩,玩一阵子,站在岸上,双手轻快地拍自己的身体,边拍边喊:“拍、拍,拍麻秆,你哩不干我哩干。”拍着拍着,还会相互追逐。跑在前面的会猛然间“噗通”一声,再次跳进水里。后面的也会随着跳进来,接着再玩。做游戏的时候,也有童谣。流传颇广的“鸡鸡翎,砍大刀”,是男孩子常玩的游戏。两组人分列两旁,中间相隔十几米远,一组向另一组“寻衅”:“鸡鸡翎,砍大刀,恁边儿人,叫俺挑,挑谁哩?挑XX。”然后,XX从自己的一组中冲出,跑向对方,对方则牢牢地手拉手。如果撞开对方的手,则为胜利;如果撞不开,就要留下来归对方所有,对方胜利。这个游戏,近几年编成了歌曲《机器铃 砍菜刀》。大概是方言读音的问题,一些字词涌现不同的版本。但是是一个游戏,流传于中原以及周边一带。难怪歌曲推出后,引起共鸣,听说前半个月点击量就达1800多万。那时候,家家喂养猪、羊、鸡等家畜家禽。草是它们的饲料。薅草是小孩子们能干的劳动了。一群干活的小伙伴像一群麻野雀,叽叽喳喳,嘴中不闲,他们说:“胡撇嘴(音),吃着美,回家恁娘打你的嘴;毛妮菜(音),吃着赖,回家恁娘打你的盖;麦连子(音),吃吃去世。本日吃,来日诰日去世,后天坟上挂白纸。猫猫眼,点三点,嘴上扣个大白碗。” 胡撇嘴、毛妮菜、麦连子(也有称“麦天子”)、猫猫眼均为当地野草,胡撇嘴、毛妮菜是可以吃的。太阳将要落山了,该回家了。又有人说:“日头落,狼下坡。赤肚孩,跑不脱。芝麻茬,绊住脚。”在有说有笑有闹中,大家赶紧往家赶。三、童谣也有时期特色
有的或许流传了数百年、数千年,有的是近当代形成的。“妮、妮,快点长。终年夜嫁给炊事长。穿皮鞋,披大氅,坐个轿车嘀嘀响。”产生于大跃进期间。那时候的“炊事长”是实权派,掌管着食堂的吃喝,难怪群众渴望自家姑娘快点终年夜、嫁给炊事长喽!
刘胡兰是孩子们心中的英雄。这方面的童谣有好几个版本。如:“刘胡兰,十三岁,参加革命游击队。骑白马,挎盒子,打住仇敌的肉脖子。”“纺花车,圆又圆,里边坐着刘胡兰。刘胡兰,拿盒子,打住地主老婆子。”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屯子自行车很少。骑自行车的技能大都不好,一欠妥心就会跌倒,乃至摔骨折。于是有了这样的童谣:“骑洋车,没带铃儿,头上磕个小窟窿儿。买幅药,一块多,看你(往后)烧包不烧包。”洋车即自行车。“烧包”为方言词,指干事不端庄、卤莽。那时的“一块多”看来也是“巨款”了。要不,花“一块多”就心疼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小学校园里还流传着这样的童谣:“一年级,开飞机,二年级,开大炮,打住仇敌的钢壳帽。三年级去世,四年级埋,五年级哭哩站不起来。”大概是六七十年代“备战、备荒、为公民”在孩子们中间的反响吧。有的童谣是谜语。
村落中有的婶子大娘嘴巧、记性好,会用谜语般的童谣逗孩子们玩。
“红门楼,白院墙,里面坐个耍儿郎。”答案是嘴巴。
“兄弟两个一样平常大,隔着毛山不得见面。”答案是耳朵。
“一棵树,八丈高,上边挂满杀人刀。”答案是皂角树。
“南阳诸葛亮,稳坐中军帐。排起八卦阵,单捉飞来将。”答案是蜘蛛。
“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白天看不见,夜黑数不清。”答案是天上星。
上小学时,又有了许多字谜童谣。
“一点一横长,口字当他娘,孩子去斗殴,耳朵拽多长。”答案是“郭”。
“一点一横,两眼一瞪。”答案是“六”。
“一点一横长,一撇撇南阳。南阳有个林,长在石头上。”答案是“磨”。
“王大娘,白大娘,两人坐在石头上。”答案是“碧”。
如今,孩子们进了幼儿园,学的是新童谣,那些传统的童谣,大都阔别了他们的视线。而这些传承的童谣,在我的影象深处,带着乡愁,是挥之不去的。(郭敬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