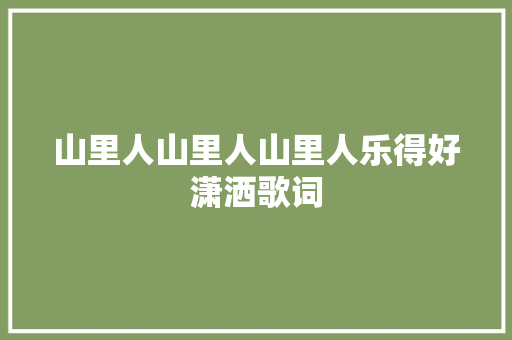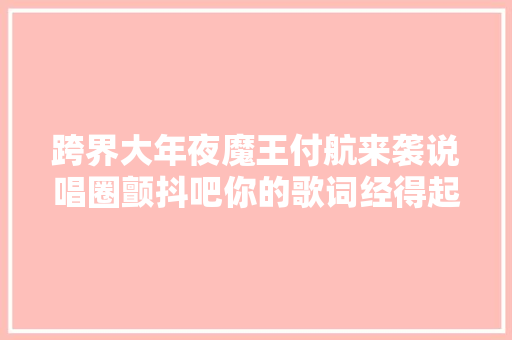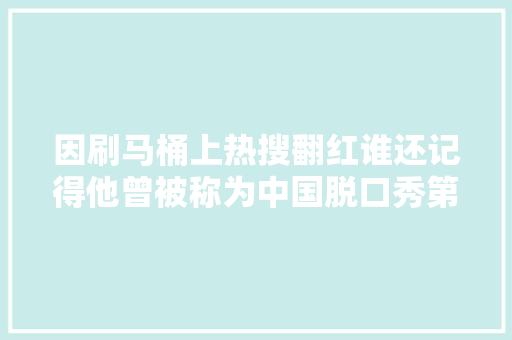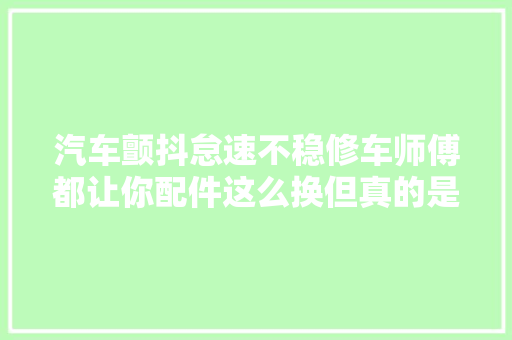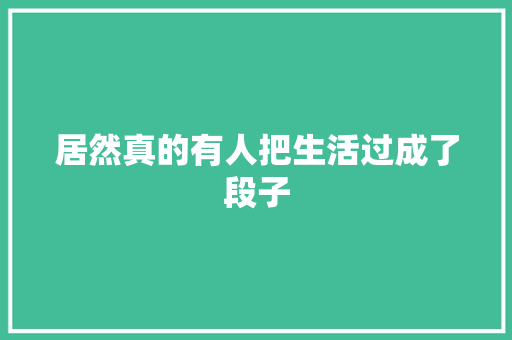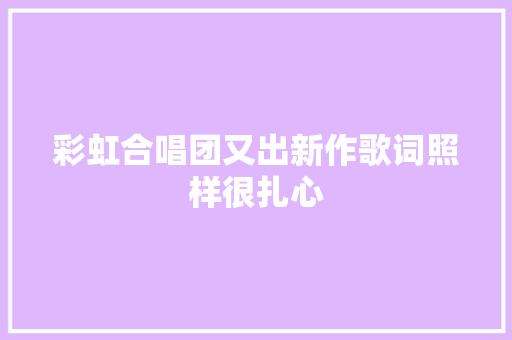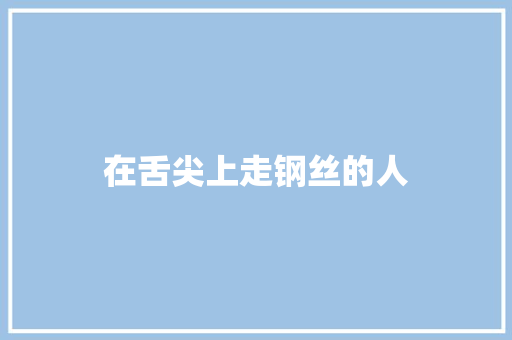我的生活轨道本是一条缺少调味的白水鱼,每天打开电视都只能在虚假的恋爱剧和和拙劣的现实主义之间选择。直到上个月,在我那乏味的生活中,溘然涌现了三位笑剧侠,他们的马不是白的,铠甲也不见踪影,但他们携带着满载的笑料,年夜胆地闯入了我的天下。
这段韶光,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无限期停播,精神食粮断了,觉得生活更无聊了。就在我险些要沦为无聊之神眷顾的捐躯品时,我的朋友,那个勇于冒险的MISS汉谟拉比,向我透露了她的小秘密——平行空间角落里的三位脱口秀巫师——便是传说中的“三个火呛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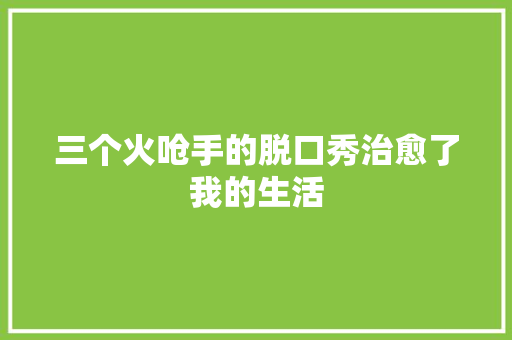
那天下班路上,正遇上他们“七宗罪”系列——暴怒。这三人用密集的段子,将我放工的路程直接听成了笑剧现场。大翟和思宇这两哥们儿,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讲段子,怎么说呢,虽然是音频节目,但总能觉得他两一个嘴角上扬就能让你实行笑的命令。他们便是那些连笑话都能讲得巧嘴如燕的天选之子。
写到这,让我想起一个人--杨超那个怂。
回忆起三年前,“杨超那个怂”还没去杭州搞直播带货,在电台业已然薄暮的日子里,他倒好,自己弄起了一个电台,既当老板又当主播,每晚7点一到,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台脱口秀节目“晚高不要疯”正式开演,他的节目收听率独占鳌头,位列我城市的电台第二(谨遵马老师的教诲,真正牛人从不自称第一)。
至今影象犹新,他每期节目都用大张伟那令人脑洞大开的《人间佳构起来嗨》作为开场曲,洗脑的歌词“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统统二十块,统统二十块,阿哩哩阿哩哩……”,我到现在都清楚的记得这个旋律。
每天的开场白都是“大家周末快乐!”,将听众比作他的“姥姥姥爷”,精力病一样(这是他口头禅)。
他总是带着几分喝多后的戏谑调皮,一边自嘲是“西北边陲九流二把刀主持人”,一边夸年夜地流传宣传自己是“新疆著名酒后演出艺术家”。
某些时候,他前一天真喝多了,第二天就不上节目,也不打呼唤,听他的节目就像赌徒摇骰子,有时你赢得欢快,有时你沉浸失落落。
更多时候,放工高峰期能听到他的节目,总以为自己像是中了大奖,把他的电台脱口秀作为回家路上意想不到的乐趣。
彷佛所有美好的事物总会有闭幕,杨超那个怂的“晚高不要疯”终极也走到了尽头。
电台干黄了,他不再有卖段子的放荡不羁,而变成卖货的网红主播。
每个人总得为生活找条出路,哪怕是在直播的狂潮中随波逐流。而我,除了偶尔听一下早高峰的路况播报,再也没关注别的电台节目,
别急,故事还没完,虽然与电台脱口秀的情绪已分裂,谁知误打误撞听到了“三个火呛手”的段子。他们让我重拾欢畅的步伐,让我在充满戏谑与搪突的故事里笑一场!
永久不要鄙视一阵笑声的力量,它补充了那被失落笑清空的空隙。
末了先容一下这三个火呛手吧:
三个火呛手--雷哥、思宇、大翟,他们仨是同时开始讲脱口秀的笑剧伙伴。
雷哥,因当年在《奇葩说》中降服黄执中而小有名气(现在连奇葩说都没了,还有啥好说的),是杭州某电台正儿八经的主播,浙江嘉兴人。他总能以他独特的不雅观点和诙谐的风格,带领节目走向高潮。
思宇在微博上自称为“不爱表达的思宇”,而他在成为脱口秀演员之前,曾是汽车理赔员,来杭州7年。他的机警和搞笑天赋使他在节目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至于大翟,他和思宇同为东北鞍山老乡,还是中学同学,学习比思宇好,但也没考上啥好大学,对思宇青春期的各种糗事记得清清楚楚;以前是个程序员,这两年被大厂裁员了三次,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反而选择了做自己喜好的事情——讲脱口秀。
“三个火呛手”的组合就像一个笑剧的快乐盒子,他们整天抱团在一起,比比谁的段子更锐利,谁的脑洞更大,谁能让听众先爆笑。每当他们三人同台的时候,雷哥常常以主攻手的姿态带领节目,思宇偶尔抛出一两句冷笑话调节气氛,而大翟则用东北硬汉、钢铁直男的“不服不忿”表示脱口秀的“搪突”。只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性情,但他们的共同点便是,“这帮家伙是不是已经统治了我的笑神经了?”
每天听他们挖掘生活的负面感情,唠一唠社会上的热点话题,骂一骂那些该骂的人或事,每天放工路上轻巧地被他们戳中笑穴,让我在繁忙和怠倦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丝乐趣和轻松。
“三个火呛手”的涌现就像我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他们是我大笑一场的邪术剂。他们的声音照亮了我日常的天空,而我的笑声不便是他们连锁反应中最亮丽的一个烟火吗?
个人不雅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