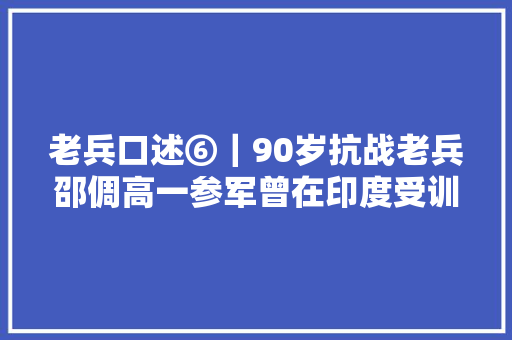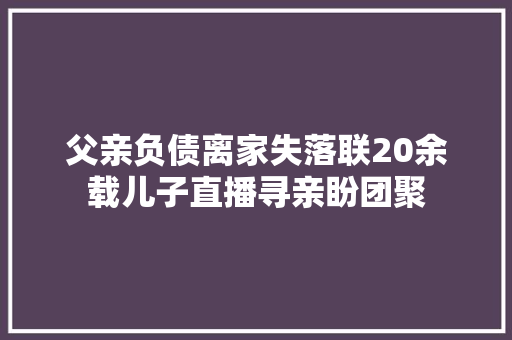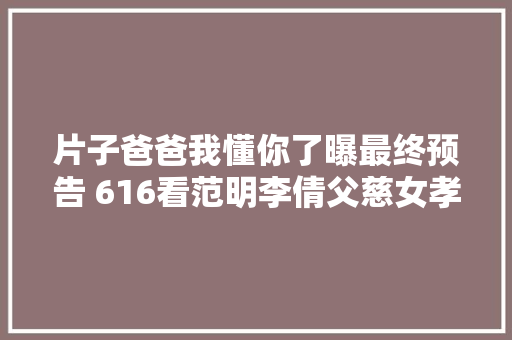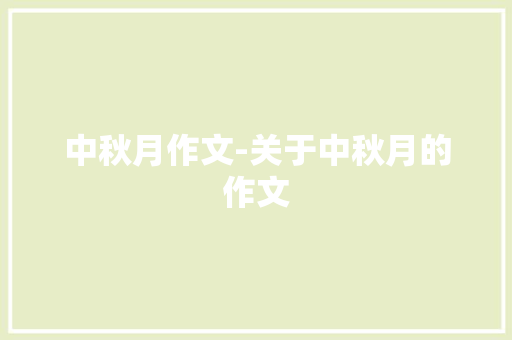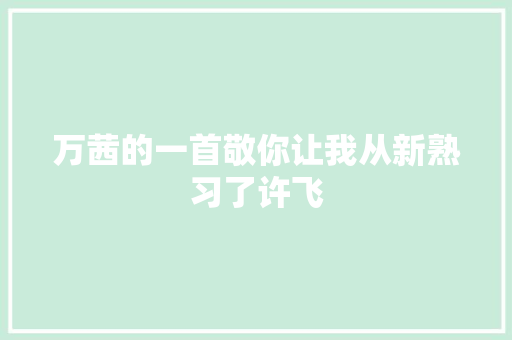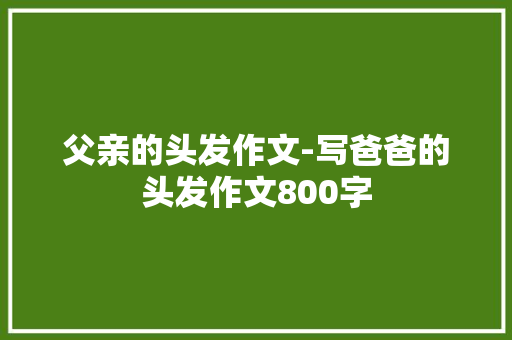然而,在本日物欲横流、尘嚣烦躁的快节奏社会里,有多少人能真正感知这背后的意义? 又有多少人亲自体验过农人的费力与汗水? “干农活”在当今这个时期是否还有代价?
湘西山寨里,刘明与父亲、儿女三代人一起,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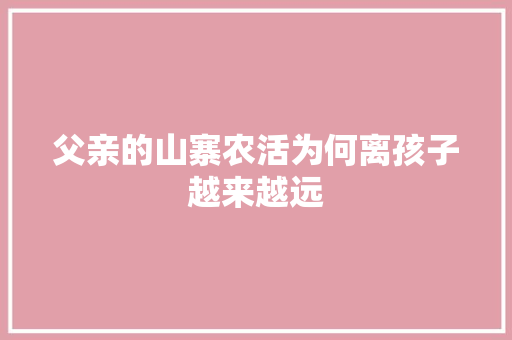
虽已是立秋第十三天,但湘西的景象酷热如故。
尤其是附近中午这段韶光,纵然那只常常陪伴父亲的猎狗,也失落去了昔日活蹦乱跳的激情亲切,躲在油茶树下打起盹来。
它怠倦地眯着眼睛,把舌头伸得老长,任我怎么叫吼,它只是微微睁开眼,委曲地摇了摇尾巴,满脸窘态。
这个暑假,我便是在这种景象里带孩子们干农活的,这活儿,用湘西本地话说,叫“掰苞谷”。
父亲今年种的苞谷地,零零星碎、远远近近地藏在大山深处,大约有七八亩。
我们掰的地方,在木屋后五百多米远的山坡上,是一亩多的平地,东边有块密欠亨风的油茶林,南边有几棵高高的松树直插云天。
我们虽在树荫遮挡之地劳作,可仍感到闷热难耐。
热烘烘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样,不一会儿,燥热的脸上闪烁着豆大的汗水,孩子们皱着眉头盼风来,然而一丝也没有。
毒辣的太阳从蓝蓝的天空火一样平常地炙烤着大地,苞谷的绿叶早已被烤干,扯开灰色的叶片,连金黄色的玉米也有些愁眉苦脸。
不知什么时候,明朗的天空里悄悄飘来几朵稀疏的白云,白中带点黄,犹如晚来的春雪,又宛如彷佛飞扬的风帆,平平的,长长的,傻傻的。
云的边缘仿佛棉花蓬松优柔的花边,每个瞬间都在悄悄地变革着。但它们实在太少了,无法为人搭建一堵遮住太阳的云墙。
忙了一下子,我把孩子们送到树林里躲阴。
一棵刚砍下不久的松树悲惨地躺在地上,压住了一些小草和杂木,树的叶子看起来还是绿色的,可已经蔫了,垂头丧气地耷拉着,一动不动。
知了们不知躲在什么地方,断断续续地唠叨着。一只鹞鹰旁若无人地在木屋上空盘旋,一群麻雀从头顶飞过,猎狗象征性地尖叫起来。
一阵风吹过,四周一下子变得扭捏起来、欢腾起来,小草们优柔的叶稍也在翩翩起舞。
我和弟弟不由自主地大声“哦嗬”起来。
儿子呢,也很高兴,他竟然教妹妹背起唐诗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劳。
童声清澈如山泉,连父亲也笑了。
我一贯迷惑,现在的父亲,却越来越不肯望孩子们一起干农活。
就说这次暑假带孩子们回父亲的山寨,他总不要我们去田地里,说太阳底下热,苞谷叶子痒人。
要不是我坚持,他根本不会带我们去。
这和过去我读书时,完备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记得三十年前,我读初中时,一到农忙时令,父亲总会拉着我去干农活。
用他的话说,这是体验生活,磨练意志。
而那个时候的我,却害怕干农活。
记得天刚麻麻亮,就被父亲喊醒,打着哈欠,揉着眼睛,扛着锄头,迷迷糊糊地来到苞谷地锄草。
父亲给我分了一块,说锄完这些草,就放工逮早饭。
开始,我还激情亲切满满的。不便是除草吗,一块山地,多大略的事。
可父亲说,既要锄掉杂草,更不能伤着苞谷的根,还要把地皮弄松软一些。
父亲的山寨坐东朝西,背后的龙头山犹如巨大樊篱,田地斜斜地躲在山坡丛林之中。
也便是说,附近中午时,太阳才从龙头山翻过来,这一个上午都是干农活的好韶光。
父亲的山寨下,不远处还有一条河,叫两岔河,下贱流淌几公里注入酉水。
酉水,便是沈从文师长西席笔下那条著名的白河。
两岔河是永顺和保靖两县的分界,夹河高山,壁立拔峰,竹木青翠,水深而清,山鸟纷飞,走兽聚群。
夏秋的清晨,两岔河面总能升腾起柔柔的雾气,高达数百米,山谷云遮雾绕的,宛如瑶池。
一阵阵湿润的晓风犹如微波荡漾,吹在脸上,让人有一种不可言说的舒爽。
但对付当时锄草的我来说,却无暇欣赏这些美景,只希望快点搞完。
可越是焦急,心里就越烦躁,尤其那一人多高的苞谷,叶子划在人脸上、手上,夹杂着汗水,湿湿的,麻麻的,痒痒的。
我把锄头丢在一边,坐在石头上罢起工来。
父亲见状,意味深长地说,儿子,读书比干这个要舒畅些吧,你不好好读书,将来还要干一辈子呢!
我溘然顿悟,还真是这样,不管如何,读书总可以安定悄悄地坐在教室里,不会遭受日晒雨淋。
再想想父亲为了养活我们读书,夏天放木排、冬天烧木炭,农忙时从未歇息过,风里去,雨里来,真不随意马虎。
父母从来没有读过书,他们含辛茹苦地劳动,不便是希望我们好好珍惜读书的光阴,跳出农门吗?
我为自己常常打扑克、烧野蜂、掏鸟窝、看录像等不好好读书的行为感到羞愧!
一语点醒梦中人。
父亲的话,犹如翻过龙头山的太阳,一字一句彷佛年夜水般的阳光倾泻而下,让我的心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
是啊,我过去读书成绩差,那是我的心思不在读书上。得过且过,混日子,无所谓过去和现在,更无所谓未来。
三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
但三十年来,无论读书岁月,还是工厂上班,或是从事新闻事情,碰着困难、心情忧郁时,想想父亲的话,统统就都好了。
所有的挫折和痛楚,都是发展的经历。
我再怎么难熬痛苦,总比三十年前跟父亲在苞谷地里除草要好吧?
现在,父亲不肯望我们干农活。无非认为,他儿子已经在城市里立足了,不须要种地了。
至于孙辈们,在他看来,由于在城里终年夜,也不可能再回到乡下干农活了。
他干了一辈子农活,头白了,脸黑了,背驼了,何尝不知道个中的艰辛与劳累呢?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太阳底下的煎熬,与孩子们朗读时的清脆与浪漫相去甚远。
特殊是我们那个靠天用饭的地方。
为了赶田水,我曾打着火把和父亲在深夜犁田;为了好收成,我曾寒冬尾月赤脚陪父亲翻坂田。
为了筹学费,我曾和父亲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到保靖卖木炭......
家里年年喂猪年年卖,我们读书时从来没有杀过一回年猪……
干旱、山洪、猪瘟、鸡疫等等,还有一些无法预测的灾害,很多时候,父辈们一年的劳作常化为泡影。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对付很多农人来说,只不过是俏丽的梦想罢了。
但即便是这样,第二年春天来临,父亲的山寨依然忙劳碌碌,农人们不会由于去年的丢失而永久将劳作束之高阁。
远去的一年,虽然刻骨铭心,但父老乡亲们乐不雅观、豪放、执着和脚踏实地的精神,永久值得我们敬仰。
而现在的孩子,正好就缺一颗年夜胆、坚守的心。
我想父亲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就说这些年吧,读书条件越来越好,考取大学也越来越随意马虎,为何父亲的山寨却几十年没有人再考学出来呢?
说白了,便是现在屯子的孩子,也没有多少人在真正干农活了。
很多父辈们认为,干农活苦,条件越好,越不能让孩子们做这些事情。
实在他们忽略了,这正好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诲。“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再不妨环顾一下我们身边。
无论是城市,还是屯子,我们的下一代,大多数人短缺的正是苦难教诲。说像温水里煮田鸡,一点也不过分。
再苦也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真不能穷教诲。这本身没有错。
错就错在,很多父母经历一些苦才成功,自己却不太会让孩子去历练,也就无法让他们懂得生活的来之不易了。
高枕而卧的生活,色彩斑斓的日子,眼花缭乱的天下,不知不觉间,我们却培养了自己有些失落望的一代。
读去世书、去世读书、轻实践、远自然、无是非、少怜悯、缺辞让、爱撒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心智薄弱,如此下去,何以担当?
我把自己的教诲理念说了,父亲说这样是好,可现在的孩子哪里能和过去比,毕竟对屯子不熟习、没感情。
正由于不知道,以是得体验。我见告父亲,不管孩子们的未来怎么样,但从小多打仗屯子干些农活,并不是坏事。
我希望孩子们不作温室里的花苗,而要像大自然中的农作物那样,接管日晒雨淋和风霜雪雨的洗礼。
当然,对付我这个走出屯子的青年人来说,更要不忘初心,有韶光一定得多干农活。
农活干起来累这不言而喻,但这个过程收成的却是一颗强壮的心。
父亲说不过我,就不再阻挡我们干农活了。掰完苞谷后,我再去背匝笼,他只是说,少背点,逐步走。
我少年时候背过匝笼,知道步伐怎么走,但多年没有背了,刚走两百多米,近百斤的重担,压得我大汗淋漓。
儿子也是,从来没用背篓背过苞谷,而且还走山路,在太阳照射下,全身衣服湿透,肩上还勒出两道血印来。
可忙完之后,我们大口喝水,打着赤膊,让风拭干汗水,从头到脚都爽得让人发颤。
儿子彷佛不以为疲倦,下午还帮爷爷晒起苞谷来。
苞谷,便是儿子书中说的玉米。他看到苞谷掰下来、晒太阳、再粉碎煮熟喂猪,很好奇。
爷爷见告他,自己种苞谷,一年收成七八千斤,紧张便是喂猪喂鸡。
听着爷孙俩互换,我才想到另一件事情。
去年三月,父亲的山寨电力才好,为方便喂猪,我买了台磨碎机给他,只是忘却了,剥苞谷也有专门的机器。
想想过去每年几万个苞谷,都是父亲一个一个用手剥出来的,我感到很自责,于是和弟弟说,赶紧买台机器来。
我们费尽心机给镇上的熟人打了电话,很快,机器就送到了家。
晚上,大家一起上阵,原来父亲至少要花三个月晚上剥完的苞谷,我们差不多三个小时就弄完了。
我对父亲说,这便是“有了电,真方便,电的好处说不完。”
我说,毕竟时期不同了,希望他在享受彩电、冰箱和洗衣机带来舒适的同时,也能感想熏染到农业当代化的便捷。
但问题又来了,我们给他买了些机器,他笑着说,当代化好,明年还要多种些田地,看到好田土都疏弃了,实在可惜。
我说,您都七十一岁了,咱们又不缺吃穿的,干农活权当磨炼身体,何必弄那么多呢?
父亲望了望我,想说什么却又没说。
我理解他们那一代人对地皮的感情,却不理解,父亲为何不睬解恰到好处。
毕竟岁月不饶人啊。
还好,他不再谢绝我和孩子们干农活了。
就在昨晚,他打电话见告我,准备下个星期打谷子了,如有韶光,可以来山寨体验体验。
当然,孩子们要上学,是无法去了。
我想我还是要去的。
打谷子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找寻和陪伴。
陪伴父亲劳作和谈天,找寻那颗曾经的初心。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