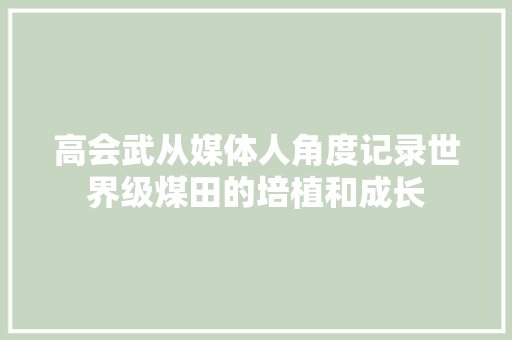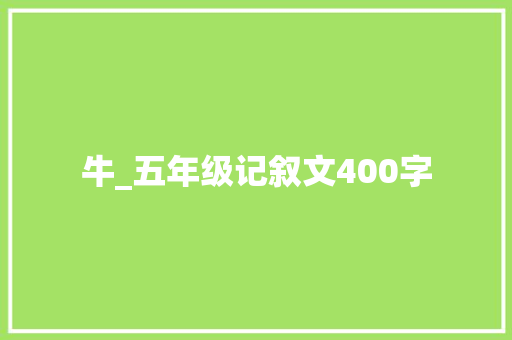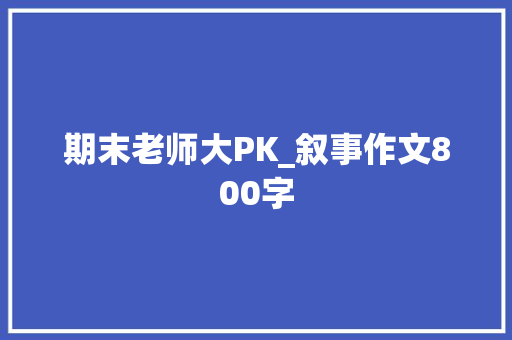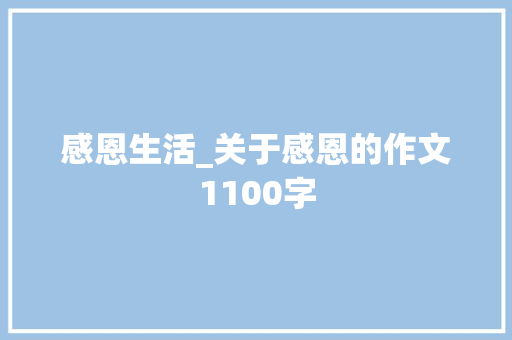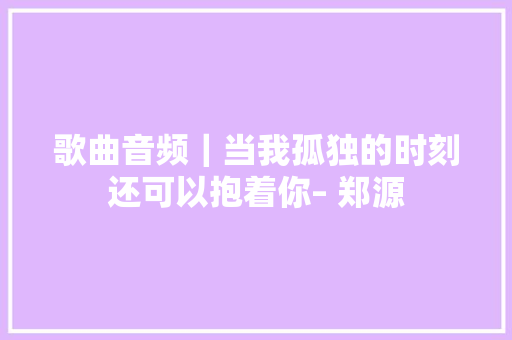散文 / 诗词 / 小说 / 情绪
七九四——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当年拾级而下要小心,很陡,现如今被枯叶覆盖,被覆盖的,还有一段尘封的影象。
多少人离开了七九四,还想着回来啊!
这是唐健、唐江平的父母调回老家后,前两年返回七九四,在子校门口合影留念。如今第三代人已经比第二代当年来七九四季刻还要大了。
这是我在辋川中学没迁来之前拍摄的,当时一把大锁锁着大门,现在胖了已经翻不进去了,当年天蒙蒙亮,学校没开门,我们可以从阁下一下子翻进去。学校大喇叭里播放着“哗啦啦下雨了,看到大家都在跑——”一些喜好运动的同学一早就绕着操场跑步。这个花坛,该当是林喷鼻香阁当校永劫刻垒砌的。子校的校长还记得吗?刘校长,金校长,王忠民,林喷鼻香阁,到后来的英语老师蔡老师老公王建国……。
从左到右,第二排,你还记得这些老师吗?第二排左起第一个和右起第一个不是老师,左边是霞子,右边是张晓红,后来随父亲调到山西太原。解剖兔子的闫老师后来还做过职工医院的院长,我有时想,他给人的开刀会不会想到当年解剖兔子的环境。这个班听说很牛,出了幼儿园院长,妇产科大夫,部劳模,古董贩子,水果西施,音响批发商,纺织专家,英语西席,航天车间主任,饭店老总,消防安装老板,涂料大王,等等。最牛的,是当年的霞子现在已经做奶奶了。
到了高中一下子少了很多人,那时国家政策活了,很多人调回家乡,或者有的参军走了,有的遇上末了一批接班早早事情了。不管咋样,这些老师永久是七九四子弟们的启蒙者,教我们认字,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值得我们尊重。但有时我们也很恨他们,他们喜好和我们的家长在路上碰到了,讲我们的学习成绩。我还记得李怀家的妹妹当年在四年级教我们英语,我是插班生,没有教材,她就下课了把教材借给我用。实在,每一棵幼苗终年夜成树的时候,都会戴德大地对他的滋润津润。
每一个七九四子弟,都是在父辈的教导和熏陶下,茁壮发展,大差不差,在面对社会的时候,都懂得与人为善。不管后来做什么,都会像七九四院子里挺立的树木那样,正派和积极向上。
还记得1979年时候,右边的传授教化楼才盖好,那个时候的七九四无所不能,这个传授教化楼是自己职工在缓建时候自己盖的,那是学校操场堆满了东北运来的坑木,一下课同学们都在这些木堆上玩老鹰捉小鸡。第二节课间操,“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公民体质。第二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大喇叭的声音传遍了全体辋川山谷。
右边是高强的弟弟高勇,左边是胡玉坤的弟弟胡玉成。那时在子弟学校,陵暴人也要看对方家里兄弟姐妹多不多,恶不恶,嘿嘿。谁敢陵暴我,我的大舅哥曹庆宝会武术。学校有个老师,听说很厉害,后来练鹤翔庄,在操场上给我们讲,他可以让玉轮停下来,可以随着手掌起伏,井水也会随着起波浪。
那时受武打片的影响,图书室的《武林》、《中华武术》能翻烂。彭江练武就很厉害,起几个旋子,把人能镇住,后来彭江到了部队,就很有用,做到了徐良连的连长。矿里一个工程师黄建义,每天傍晚都会一手迁徙改变着玉石球,在学校操场边走来走去,那个时候就有养生的意识,以是现在身体还很好。
七九四目之所及,都是山。那时音乐课有一首歌,唱的是“山里的孩子心爱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园”,随着那个音乐老师磨出包浆的脚踏风琴,孩子们扯着嗓子喊,喊到肚子都饿了,就等下课铃响了背着书包回家用饭。三线子弟,没有城里孩子们更多的诱惑和享受,以是要想理解大山表面的天下,只能看书读报听广播看电影电视,反而文化素养要比城里孩子高,大山让孩子们能沉淀下来,形成专注和踏实厚重的品质培养。
这是七九四人最大的体育和娱乐场所,灯光球场从早到晚都有打球的。文革时候也是开大会的地方,工会组织的各种比赛都在这里进行。至今还记得雷鹏的爸爸在球场边做裁判时候跑来跑去洒脱的动作,哨子一吹,手一比划,推人,重新发球——
背对着跳起来抢球的,是魏淑珍老公白忠锋,从更高的班级汪洋、魏元奇到王平,都常常能看到在这里投篮打球的身影。山里阳光少,晒被子和打球两不耽搁。春节时候,爆玉米花,嘭的一声,不用急着去端,你家的盆子还在后面排着队呢,第几响了你再去才轮到你。
工会在办公楼山墙上贴一个海报,今晚放映《流浪者之歌》。迅速传播到百口眷区每一个角落,一下子功夫一块块国土面积就被分割成美国舆图,粉笔画一个方框,里面歪七扭八写着:这是魏红家的地,这是王红家的位置。
大家都很自觉,别人圈定好的位置不要去占,自己去坐没有国界的地儿。到冰棍房拿保健票去买几根冰棍,怕化了,用茶缸就着,一家人或者单身楼几个一起上班的老乡坐在那里,静等新闻简报和矿里宣扬科做的幻灯片放完,看正片。很怪,每次看传片,都会下雨,什么《天云山传奇》、《少林寺》、《武当》,都是打着伞看的。有一次前面没位置了,我到后面那栋楼李长江家,隔着窗子看电影,那天演的《本日我安歇》,第一次看到那个穿着白色警服的警察从右边登上自行车。
多年后变成遗址的七九四,对付七九四人来说每次回来都很失落落,父辈、我们这一代都在这里生活和发展,如今破败不堪,草木疯长,无人整顿。但对付山表面的人来说这里是一个充满神秘和具有艺术觉得的地方,这个画家在我们已经谢幕的舞台上悄悄绘画,独享那份午后的宁静,但他享受不了我们曾经作为生于斯长于斯、每天都经由这里或者在这里欣赏比赛、参与比赛和看露天电影的那份快乐。
记得有一次下大雪,我们放学后,出了校门来到大雪满天飞的操场,操场上空无一人,但承包的电影放映队不管有没人看都要完成他的事情,在放映一部《贝多芬》的电影,由于景象缘故原由和故事情节不吸引人,那天全体操场上白茫茫一片,只有我和玉成还有谁,三个人在那里看完。记得电影里有一个情节,讲贝多芬过生日,一个朋友送来做成小提琴形状的蛋糕,贝多芬尝了一块儿,说:终于尝到了音乐的味道——
工区单身楼前的花坛里的植物在没人收拾的情形下疯长,记得每次七九四,尤其纺织城里的姑娘外嫁,单身矿工们都圪蹴在墙边晒太阳,看到接新娘的婚车远去,就会感慨:唉,又走了一只羊,又多了一匹狼。
一觉醒来,创造鹅毛大雪洋洋洒洒,把全体辋川装扮的银装素裹。七九四的孩子们最愉快的时候到来了,我一说七九四的人都会说出来,滑雪。排成队,蹲在那里,从招待所一气滑到辋川河大桥上。期间滑到,摔疼屁股,都不会喊出来,一贯玩到棉裤湿透回到家被妈妈骂一通才算安生了。记得后来到了美国事情的王伊的弟弟王沛那时就很爱玩滑雪,不知他还记得不记得了。
这是七九四人最喜好去的地方,二楼商店里,李维平、李维利、李维勇的妈妈,李长青、李长江、李长华的妈妈,周静、周健的妈妈,恒子、小惠、张文新的妈妈,这个姨妈,那个姨妈,新惠姐后来也在这里事情,山表面的东西运进来,成为七九四人购置日用品晚高下班最乐意闲逛的地方。
还记不记得大礼堂侧那边有个肉店,肉不多去晚了肉没了,为了给生完我侄子的嫂子补身体,我被我妈妈一早天不亮就叫我去排队买肉,一个人孤零零站在肉店门外,看到咱矿起来最早的人是范卫东、范君的父亲范矿长,搓着玉石球,老红军的淡定,他看到我,还给我说话。那时的矿领导和老人都很和蔼,姜矿长还在我家讲他在八路军时候摸鬼子炮楼的故事,梅子的爸爸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时候他们认为刚发的复员安置费到了朝鲜用不上,边过江边把钱往江里扔的环境。
如果,哪一天
小商店也被拆迁
我们该去哪里,再拾回我们如金不换的青春?
打开水、买馒头的路,去沐浴的路,提个壶,端个盆,碰到了大家都会打个呼唤。原来在这条路上常常碰着二猫拿着扳手管钳,去修那个地方的水泵去了。
我在矿上挺佩服一个人,许慧英,见谁都会笑脸问候,坐在班车上碰着七九四看大门、蓝田县的老毛也会毛师傅毛师傅的嘘寒问暖。
七九四就如一个大家庭,到现在回到蓝田老大院还是新大院,你越来越觉得到七九四人越来越联络了,不管婚丧嫁娶,都会有人来帮忙,谢文杰、钱宝宝、海斌、范卫东、传说中的马大姐刘新惠,都可了不得,煮臊子面的,写对联的,司仪主持的,写礼单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立时给你一摊儿支起来。
我走过那么多城市,没有碰着像七九四人那样的热乎劲儿,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几十年在一起学习事情生活相处才能凝聚成的一种情意,现在通过微信七九四人联系越来越多,园区群、同学群、知青群,相互联结,相互关怀,人以群分,能走到一起一辈子的真不多!
一九七五年唐山大地震后,这些楼房都进行了加固,穿管子加横梁,机电车间一样平常人忙的不亦乐乎,如今人去楼空,踏入这里,仿佛进了考古现场,但对付七九四人来说,昨天的味道依旧弥漫在空气里。
七九四再也喝不到赵大秋养的奶牛挤出来的牛奶,再也喝不到李越翰搭棚子卖的散装啤酒,再也吃不到我老丈人曹师傅蒸的馒头,再也吃不到小妮家加工的猪头肉,再也吃不到王红家的芝麻烤饼,再也吃不到食堂小李在工区楼下晚上的烤串儿,问世间还有什么味道能唤醒你大略、纯挚的味蕾和影象呢?
镜子上工工致整贴的福字依稀可辨,如今这家人过的幸福吗?
这个大树倒了可以再扶起来,但那些歪七扭八、模模糊糊的美好影象和从楼上每天郑老师吹出来的笛子声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缥缈。曾经的芳华,如今被白雪般的银发所覆盖,堆积成声声嗟叹!
赤色的砖墙在岁月催人老的暮色中,随影象一起刷白。曾经稚嫩的脚印在春天来临之前被融化。
曹继哲妈妈小时候的待业证,被一个网名叫“秦岭思思”的游客拍到,放到网上,他拍照技能很棒,斑驳的光影和阁下飘落的黄叶衬托,让这张照片呈现后当代主义的风格。现在你走进七九四,真的就犹如走进了一个后当代主义的博物馆。
待业青年,作为那个时期的标签,在七九四的子弟心灵上都嵌入一个深深的戳儿。
我成熟的诗句哦,竟然从秋日写起。我寂寞的窗棂,在有月色的夜晚,被思绪缠绕、疯长,一页页叶片悄悄地偷看我那一行一行倍受煎熬的诗句。直到清晨,叶面上的泪珠还在朝阳下闪烁……
那一晚景象好闷热,端放在小凳上纳凉夜话,家长里短,喝一口辋川河煮了半天的茶水,让自己进入王维的禅境。
岁月是把杀猪刀,紫了葡萄,黑了木耳,软了喷鼻香蕉。韶光是块磨刀石,平了山峰,蔫了黄瓜,残了菊花。
儿时的小伙伴叫我下楼看《加里森敢去世队》,一遍遍呼叫,我不敢下去,作业还没做完呢。小伙伴的叫喊声爬满了我的窗棂,让我的心随着加里森和酋长一起激荡。
这是我唯一一张在工区上班的照片。这里的人,你们能说全名字吗?
七九四矿始建于1971年,矿部位于辋川乡境内,历经了初建(1971-1979)、缓建(1980-1983)、复建(1984-1993)和正式生产四个阶段,1993年通过国家验收。
这块地,是我们同学昌荣的父亲从官上村落征来的,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父辈们会战三线,艰巨奋斗,打造了我们曾经赖以生存和至今难忘的“单位”。
当时从渭南、陕北和河南等地招工招来100名青壮年,个中就有我哥哥、闫新亮、李来发河南籍的,还有“大闹”、“二闹”,那时的七九四人才济济,英雄辈出,尤其“闹”赵新安他们,捉住到矿上偷东西的,打的没人敢惹七九四,每次看冯小刚拍摄的《老炮儿》,就想起了“闹”哥。虽然我没见过他斗殴的样子,但能想象该当便是老炮儿那样的范儿。
这是去一工区、二工区必经的木板桥,七九四高下班走路来回的都经由这里,河沟里有人浪金,包括“曹县长”,多少个上大小夜班的夜晚我们摸黑走过,到了这里就离家不远了。
一座小桥,承载着七九四人徒步高下班,养活家人的重担。尼勇他父亲尼叔活着的时候老给我讲,当年一个人人为加保健,养活家里六口人,第一代首创者,活在精神天下里,大略而纯粹,为什么那代人很龟龄,跟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所处时期有关,没有啥想法,事情过日子,不像我们活的有点繁芜了。
我还记得,我初中时候,暑假抱着我侄子去变电所,经由这个小桥,到我嫂子上班的地方给刘晓川喂奶,胖乎乎的,背着来回可累人了。
如今辋川河靠近七九四一侧的小道上杂草丛生,之前让七九四人走的光溜溜的。夏天每到傍晚,吃过饭,很多人到河边闲步。记得语文老师胡老师和蒋科长带着他们的孩子到河边玩沙子,说这样最能磨炼孩子的想象和塑造能力了。
夜色掩护之下,单位上谈工具的,也会到河边闲步,就如城里人逛公园一样。那时单位谈工具是这样的:单位很多大妈喜好做媒牵线,约好男方和女方到她家来看电视,放上瓜子糖果,玻璃杯泡上茶叶水,等两人来了往后,姨妈就会推说,有急事到谁家去一趟,让他们看电视,然后就关好门出去了,约摸差不多韶光了才回来。
由于怕谈不成闹的满城风雨,以是先这样秘密谈,谈的差不多了,要么公开一起坐班车去西安,要么就一起傍晚出来到河边闲步,就公开了,也是见告别人,你们别想了,我们是一对。
呀!
谁家的窗子还没关严,上班老忘却关窗子,这下雨了屋里进水可咋办?现在的年轻人就这样粗心,问问她婆婆家或者他妈妈家有没有他们家钥匙,来关下窗子。
那是很倾慕他们住平房,平房的孩子比楼里们的孩子好玩,空间大。那边高勇家,钱晓丽家,周大胡子家,骞江丽家,刘独立家,胡玉成家,王琨家都住平房。自己修的厨房,多出一间寝室,家里夏天很风凉。
平房内的厨房便是一间寝室,可以分开男孩女孩住,当我们搬到西安十里铺去住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记得当年还住过这么小的房间呢?
——老嫂子,你们家本日杀鸡了?炖的肉这么喷鼻香啊!
——叫你们家老李一下子过来和我们家娃他爸喝一壶吧
这帮傻孩子等车下蓝田等了二十几年了,还在这里等,本日矿里放大炮,车都到工区了,没有车下蓝田。
左边这栋楼里的孩子最多,一家老五老六的,以是这里最热闹。七九四的孩子很多从穿开裆裤幼儿园都在一起,右边的幼儿园一度曾经是刘军家的服装厂后来转成矿里的服装厂。
八十年代的时候,刘军他爸开的服装厂,年底给员工发彩电,发上千元的奖金,曾经让在职职工都倾慕。唉,系统编制啊,那个时候能人每每被系统编制压抑着。七九四能人很多,很多可惜了------
七九四之前是没有大门的,后来家属工做了围墙,就有了大门,有了大门,就有看大门的,冬天发个军大衣,夏天一把扇子坐在桥头和过往的人们聊着天值着班,右边那个井口,我曾经每天进出几次,拿个管钳,开水关水,往山上水塔打生活用水。那个时候我权利可大了,老姨妈们碰到我:小刘,本日早点送水吧,我家本日煮饭早------
这个食堂里,七十年代末,一个蒜薹炒肉两毛钱菜金,这里还举办过晚会,我在上学时候还在这里诗歌朗诵过。那时候,许小毛、张宏的哥哥、文四都是文艺骨干,一台晚会不亚于现在的春晚。大礼堂那个时候晚会,约翰和李长青他们还演小品,可故意思了。
一到冬天,汽车队去外省拉大白菜,轮着楼号送白菜。半夜睡的迷迷糊糊,就被大人喊起来下去搬白菜。一个长门板,大台秤过称,大白菜、土豆、胡萝卜、白萝卜、大葱,就被放进各家的菜窖,埋在沙子里。
一个冬天,便是这样炖粉条吃米饭,那时没有暖气,家家户户都是火炉子,既可以烤火烧水,也可以热饭。
中午放学,听着收音机里的长篇评书联播《隋唐演义》,或者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叶秋红》,吃着烩菜米饭,一个冬天就这样过来了。单位福利很好,夏天一洗脸盘的降温糖,过年一个职工十条带鱼。过年拿着肉票到蓝田南街找老魏家的女儿,让给割一点肥肉,肥肉可以回来炼油。
春生、春玲可能不知道,你爸爸妈妈,来发哥便是在这排平房里结的婚,那是很大略,炒几个菜找几个老乡吃一下就算结婚了。这是我到矿上参加的第一个婚礼。送礼,都是枕套,被面,茶具,水壶之类的。我刚到矿上时候,矿优势行做折叠椅,王富强、安子哥都是做折叠椅的老把式。闹哥彷佛打沙发是一把妙手艺。
在七九四,有一批子弟,我们的哥哥姐姐那一批人,很多是相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们多在蓝田马楼乡插队。前两年,安子哥、喷鼻香姐带着我们去马楼吃鱼,讲起他们插队的故事,很是难忘。
从马楼回矿上,找了一个单车,安子哥骑着单车带着喷鼻香姐往矿里赶,我想安子哥吭哧吭哧上坡下坡,当时再累,心里也是甜蜜的。那批知青回矿事情后,成为七九四曾经的骨干力量。他们比我们后面的吃了更多的苦,如今也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了,知青岁月成为他们永久的印记和一段刻骨铭心的影象烙印。值得尊敬的一代人!
对面官上村落的山,很像珠穆拉玛峰。如今,山也还是那座山,河也还是那条河,人去楼空,再也回不到那种王维《山居秋暝》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再也回不到大山里的芳华岁月。
N年前,回七九四的时候,在我曾经常常出墙报的办公楼前拍照留念。那时每天组稿,到广播室送稿件,范卫雇主的嫂子也到了窑村落去了,雪蓉有时休假,我就自己念稿子。有时坏坏的想,既然是直播,那我假如溘然朗诵一首王维的诗歌会是若何的反响呢?当然只是想想,可不敢,政治事情办公室,可不是闹着玩的呢,嘿嘿!
那年我回七九四的时候,把所有的七九四楼宇都拍照存放在盘里,一旦回忆七九四的时候,打开浏览一下。
这两天写稿的时候,上网搜了一下,创造竟然有个七九四吧,里面有一个网名叫做“秦岭思思”的人发了一组七九四照片,还有一组网名794矿的人发了一组冬天的照片,我就加上我拍的,一起组成了这篇回顾录。
很感谢他们在网上发的这些照片,找不到你们的实名,联系不上你们,就借用你们的照片引发我的许多美好回顾和灵感。
在这个百度七九四吧里,“洋洲收拾来一套”说,感谢分享!
能给我一个详细位置吗?我很想再去看看。莼綷,估计是下一代,说:记得之前回去看还有几家买不起下面屋子的老年人在住…。实在下一代虽然在七九四矿上住的韶光不长,但对付七九四还是很有感情的,他们现在终年夜成人了,七九四也是他们美好影象的一部分。
“ZWB阿彬”回顾说,我还记得小时候在䋞川河里溜冰掉到桥下的冰窟窿,还记得救起我的人叫王兵非常感谢。还有个“qw7nv”留言说:怀念794难忘的岁月。还有人进吧吗?月尾去西安出差,很想去794一趟,离开有三十年了!
还有找人的信息:我叫李勇,后来改名叫秦玮有人认识我吗?我的同班同学刘建军,王强,王亚燚,吕红娟,陈小妹,韦宁宁,王凤兵,边旭青。特殊是我的班主任支淑丽老师,很惦记老师和同学们,那时我们还是一群娃娃。
七九四,一个单位的代号,也是我们每一个七九四大家生进程的符号。虽然很多人早已调离,虽然很多人石沉年夜海,虽然很多人已经放手凡间,虽然很多人年过半百,虽然很多人只是童年少年的短暂生活,但凡是跟七九四沾边的人,待过的人,七九四,永久是每一个人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拆与不拆,卖与不卖,回与不回,她都在那里,守望着你,不离不弃……
记于2019年6月1日
作者简介
乡土蓝田平台特邀作者:刘新锋,生于1968年,曾在辋川一军工企业生活和事情,后来南下深圳,从事企业管理事情。在海内各种刊物揭橥学术文章和文学作品百余篇,新浪博客访问量50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