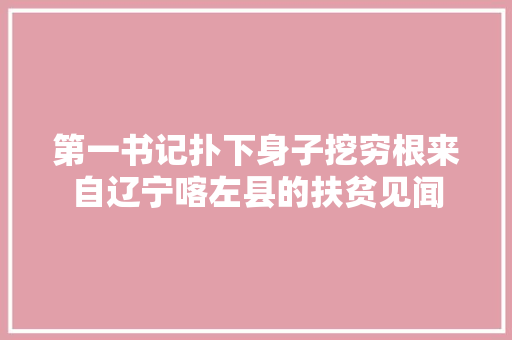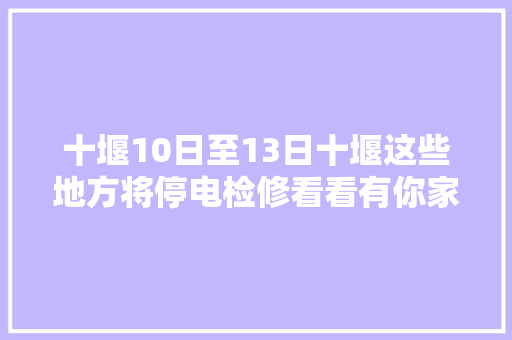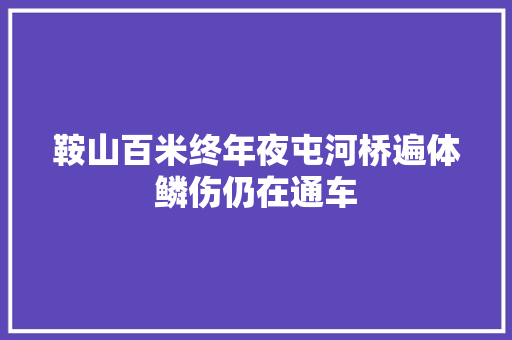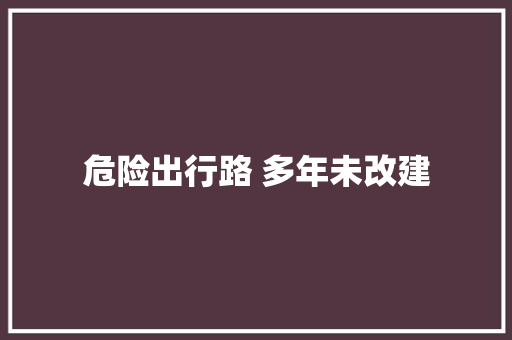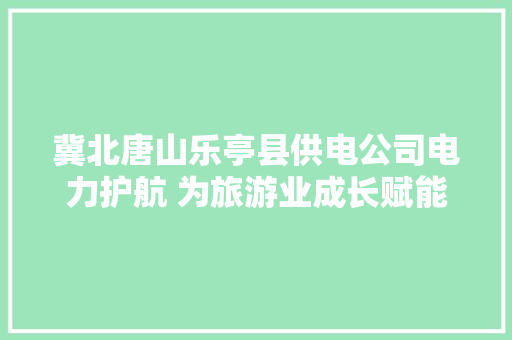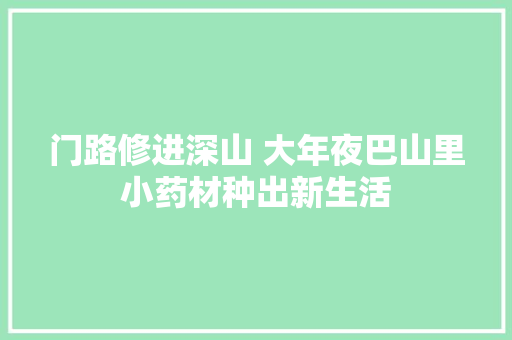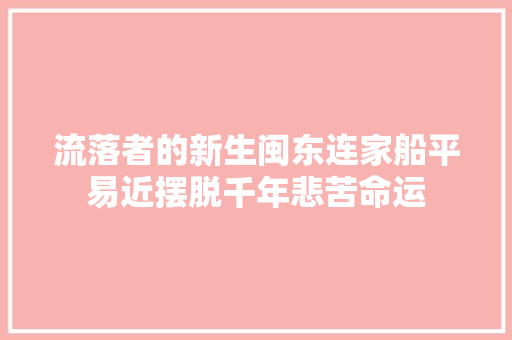2020年12月31日,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仪式现场,渔政司法船队从长江武汉段江面驶过。新华社 程敏 摄
在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渔船拆解现场,一名渔民注目着渔船的拆解事情(2019年12月25日摄)。新华社 肖艺九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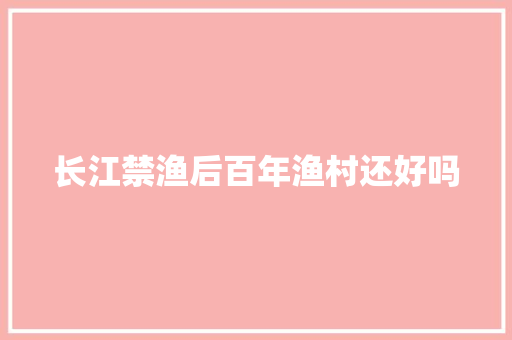
“上岸”后的徐保安(中)在一家鞋业公司生产车间内事情。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李思远、王贤)1月5日,《新华逐日电讯》刊载题为《百年渔村落禁渔后:禁了好,再也不用水上漂政策好,养须生计都有保》的宣布。
长江一级支流九道河,在湖北省宜都邑枝城镇蜿蜒汇入长江,在入口处形成一个天然渡口,称为白水渡。历史上,白水渡口曾做生意贾云集,是鄂西往湖南的主要节点。
“千斤腊子(中华鲟)万斤象(白鲟),黄排(胭脂鱼)大得不像样”,万里长江以鱼肥水美有名。靠水吃水,240多年来,渡口所在的白水港村落,以鱼为生,以舟为家,耕波犁浪。
今年1月1日起,白水港人在内的20多万渔民,正式告别他们早已习气的“水上漂”生活,退回到岸上重新出发,这是一次生活办法和生产办法的巨变。
十年禁渔,关键在渔民,难度也在渔民。
2015年3月、2019年11月,两次来到这个渔村落采访,理解渔民们的生活状况,谛听他们的心声;
2020年12月30日,距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履行历史性的十年禁渔仅30小时旁边,再次来到这里,与渔民和基层干部拉家常、话禁渔,感想熏染百年渔村落近5年来的巨变,探求渔民顺利上岸背后的现实逻辑。
(小标题)昔日“捕鱼没钱、上岸没地”
88岁的老渔民刘先向得空就会拄动手杖,来到村落里的白水渔村落陈设室,悄悄地待上一下子。
新落成的陈设室宽敞通亮,村落民捐献的渔船渔具、捕捞工具等物件,显得斑驳沧桑。
老人满脸沟壑身形佝偻,但聊起往事,精神头儿十足。
12岁那年,刘先向开始随着家人捕鱼。父亲撒网,他划船,18岁那年,父子俩分工互换,65岁时,刘先向再也“打不动了”。
去年8月,白水港村落渔船全部上岸,彻底结束了240多年的渔业捕捞史。
陈设室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条小船载着一个六口之家。刘先向回顾说,“从前间,渔民们都是上无片瓦下无弹丸之地,‘一条木船一个家,船头吵架船尾拉’‘栽架子屋绑架子床,水一来就去逃荒’。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渔民生活得到根本改变,部分人在岸上建了家。”
滚钩、排刷、大缉……站在大型鱼类捕获工具展示区,刘先向说:“早些年常常有大鱼入网。一次,有人捉到一只八百多斤的鲟鱼,好几个壮劳力花了半天工夫才抬上岸。”
那时,上缴完国家的配额任务,渔民相对闲钱多,日子过得还算有滋有味,娶媳妇也随意马虎一些。
地皮联产承包后,虽然渔船从扁舟演化为木船、铁船,拉纤划桨的号子声被发动机的轰鸣声取代,麻线编织的渔网变成了三层刺网,但渔业发展速率已经比不过农业。
白水港村落原党支部布告刘泽奎说,2000年往后,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长江渔业逐渐枯竭。“我记得从2003年开始,每年春季禁渔休养,但长江里的鱼还是越来越少,常常忙活一天打不到几斤鱼。捕鱼没钱、上岸没地,渔民成为当地最穷、最弱势的群体之一。”
2015年,新华逐日电讯拜访白水港创造,许多村落民在江边防洪区的空地上,违规建了两层楼房,但家里普遍没什么新电器。
当时,村落民鲁必华向反响,只管村落里让渔民在防洪区内建房,但办不到房产证。有的已成了危房,也领不了改造补贴款。自己40多岁了,一年捕鱼和打零工的收入只有2万元旁边,上熟年逾古稀的父母,下有读小学的孩子,每月生活费至少上千元,这点收入勉强温饱。
不少基层干部也反响,由于渔民的非农身份,他们每每成为屯子低保、医保、养老保险以及其他保障政策较难覆盖的地带。
不少渔民则希望,借长江经济带培植的东风,国家能一次性买断他们的渔船、渔具,同时出台合理的社会保障方法,让渔民能够转产转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小标题)上岸安居乐业,再也不要“水上漂”
白水渔村落陈设室隔壁是新修的渔民驿站,几位退休和灵巧就业的渔民听说朋友来了,相约到这里来叙旧。
大家围坐在一起,很快打开了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热烈地评论辩论小渔村落这5年的变革。
“禁渔,是国家大计,是为了保护中华鲟,保护我们的母亲河。现在全体长江流域都禁渔,我们肯定要相应国家号召。你看墙上挂着我们的祖训呢。”刘泽奎威望高,率先发言。一壁墙上,张贴着“以国事为先”5个赤色大字。
“大伙说说,禁渔了你们的生活有啥变革,是捕鱼好还是禁渔好?”问。
“禁了好,再也不用心惊肉跳了。两年前我老伴还在江上捕鱼,一起风我就心跳加快。”66岁的李启英曾和丈夫一起捕鱼,1985年在长江宜昌城区江段,1岁半的儿子欠妥心掉进江里短命,自此她回到岸上照顾家里。
这并非李启英第一次承受亲人被江水吞噬的痛楚。1978年10月,哥哥一家三口在捕鱼时翻船身亡。一提起这些,她的眼角噙满泪水。
“还是禁渔好!
如果不禁渔,这么冷的天,别人扎在被子里,我们却在水里‘扎猛子’。”58岁的渔民刘成志接过话头,“捕鱼太苦了,三面朝水一壁朝天,江里的船又多又大,起风起浪很危险。”
“以前一坐下来就要织网补网,现在有空了,到江边走走,打打牌,生活好多了。”渔民江代喷鼻香插话道。
“以前都说渔民是捕活的(捕鱼)、捞去世的(捞尸)、捡漂的(捡漂在水面上塑料瓶)、吸沉的(用磁铁网络沉在水底的废铁),现在我们是吃好的,穿好的。”村落民刘义风趣地说。
“大伙儿适应岸上的生活吗?生活有没有保障?”又问。
“我和爱人在镇上开了水果店,收入和捕鱼差不多,在岸上安全多了。”村落民刘泽刚抢先说。
“我还有两年才能拿退休金,就在附近的水泥厂打零工。去年受疫情影响,只赚了两万多元,不过基本生活没问题。”刘成志说。
“枝城这几年景长得不错,工厂比较多,政府也进行了多轮培训、组织招工,只要自己想事情,没有找不到活的。”年近七旬的刘泽奎说。
2015年见到时,这位老布告正在为自己的养老问题发愁;而今,老两口每月能拿到3000多元的养老金。
“年纪大的有新农保、被征地农人养老保险或者最低生活补贴,现在大家更关心自己的康健,在江边绿道涣散步、广场上跳舞蹈。”刘泽奎笑着说。
“村落里现在环境好得很,推开窗便是鸟语花香,还能瞥见一江净水、一片蓝天,飞机、轮船看得清清楚楚。”坐在一个角落的63岁渔民刘泽维抢着说,除了戴德国家的好政策,村落民凝聚力也更强了,邻里之间有抵牾,村落里就能化解。
“你看他每天笑着合不拢嘴,自己有退休金,两个儿子一个北京大学毕业,一个在表面当老板,别说多滋润津润了。”几位渔民笑着冲刘泽维说,“下一代再也不用当渔民了。”
白水港村落党支部布告李春梅说,全村落三百多名退捕渔民中,达到退休年事的有105人,在企业单位就业的108人,灵巧就业的143人。“以前渔民没有固定的收入,隔三岔五有渔民找到我反响困难,现在生活有了保障,安居乐业了,村落里的抵牾少多了。”
(小标题)下次来一定能看到江豚
2019年,第二次到访白水港村落,该村落所处的长江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已开始禁捕,村落民退捕上岸正在进行,百余艘被收缴征收的渔船堆成一片。
当时在村落委会,看到一张张渔民领取上岸补助的申请表。186户渔民每户补助10万元至17万元不等,兼业渔民、专业渔民,渔船网具代价大小,也有细致评估和分类。在村落委会,还看到10多年前下发的《关于确认被征地农人基本社会保障工具的关照》,已经被翻得又破又旧。
渔民转产上岸被认为是难中之难的“硬骨头”,白水港村落为什么这么顺利?
“首先是渔民们对长江大保护的认识很到位,这里的渔民都很淳厚、本色高,生理上很支持。”宜都邑农业屯子局局长施春燕说。
她接着说:“此外便是党委政府政策充分保障,除了各项补助落实到位,还将渔民纳入了失落地农人养老保险。现在每家基本都有一人买了保险,到龄后每月能领1000多元。当地经济发展不错,能够供应足够的就业岗位。办理了渔民的养老、生存问题,禁渔就轻松了。”
“我们正在组织成立一个18人的护鱼队,纳入公益性岗位,帮助部分没有生活保障和就业的渔民。”施春燕补充道。
渔民上岸了,但根不能丢。在白水港村落,“渔民陈设室”“渔民驿站”等独具特色的渔民文化场所,丹阳渔歌,展现渔文化的舞蹈、龙灯队,让乡愁有了寄托。
边走边看边听,天色渐晚。临走前,渔民激情亲切地约请过段韶光再来白水港。
“前几天,10多头江豚在江面上追赶鱼群。你们下次来这该当是常态了,一定能看到江豚。”一位渔民信心满满地说。
天完备黑了,江边小楼房里亮出发点点灯光,时时飘出阵阵饭菜喷鼻香味。村落口江滩公园里,只有几艘当作景不雅观的老渔船,彷佛还在诉说这个百年小渔村落的沧海桑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