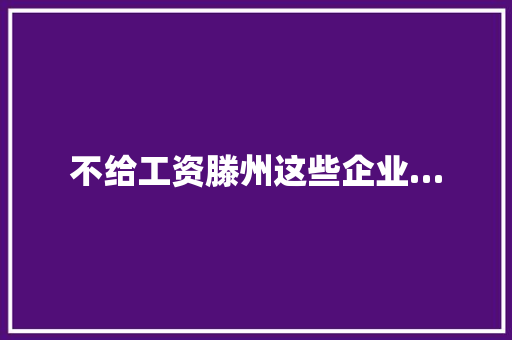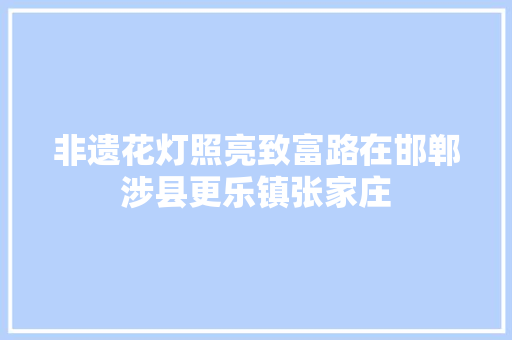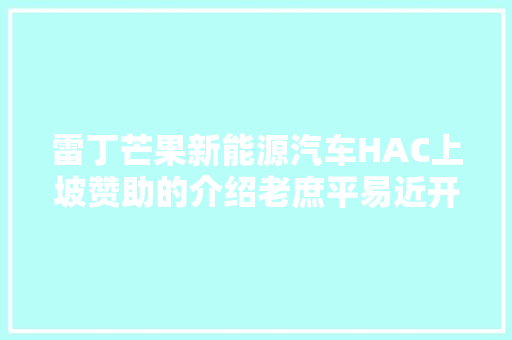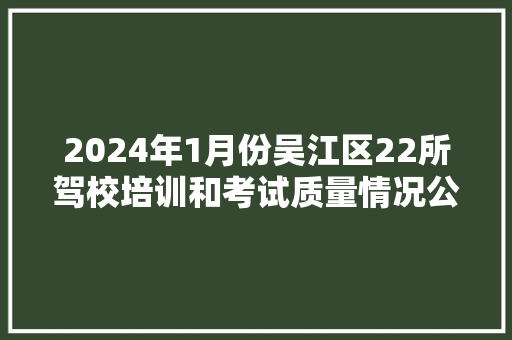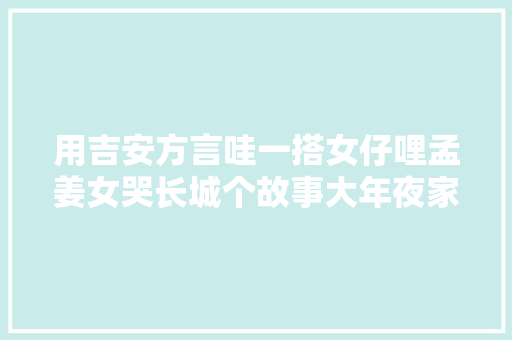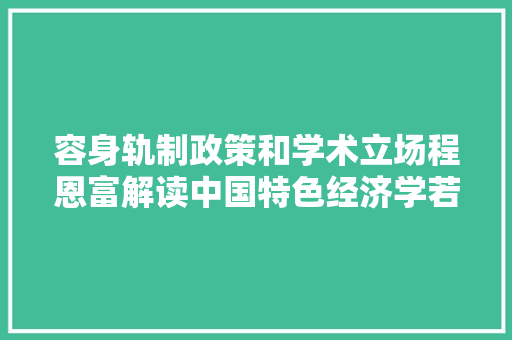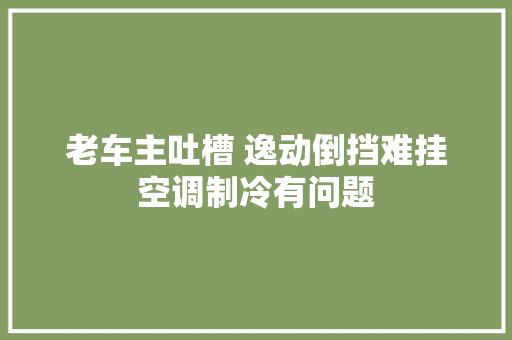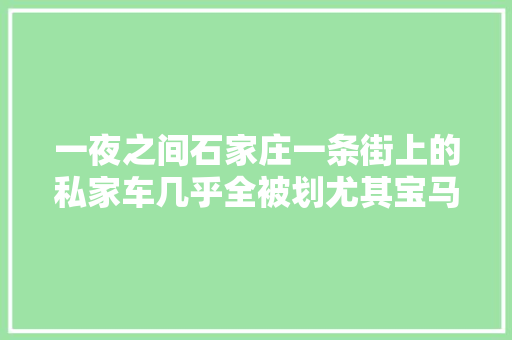王义胜笔下的仕女图淡雅脱俗
王义胜反响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之一《风雪行》

早春的沈城,乍暖还寒。虽然窗外的枝丫已悄悄挂满春花,但室内仍透着一丝早春的阴凉。
在鲁迅美术学院对面的一栋高层建筑里,一位个头不高、头发花白的老画家凝神静气地伫立在一张宽大的木质画案旁。为了抵御春寒,他穿了件格局极简的藏青色棉袄,炯炯有神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反复揣摩着桌案上的画作。他的脚边,是随意堆放的画稿……
这位不修边幅、脸上布满岁月痕迹的老者,便是有名连环画界、工笔画界的沈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鲁迅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义胜师长西席。在一盏温热菊花茶的暗香中,与王义胜师长西席环绕着平生、绘画、创作心得等话题聊了起来。
童年经历造就了简朴的生活质感
在凡人眼中,王义胜的家,绝对称得上闹市中的“豪宅”。除一处视野极佳的大露台外,全体房间被一段蜿蜒的楼梯分割成楼上和楼下两个空间。全体二楼,便是王义胜的专属空间。
可与优渥的地段和宽敞的空间比较,屋内的装饰却格外大略,乃至有些过于随意。尤其是王义胜的“地盘”,既没有讲究的家具、也没有彰显个性的陈设,一张大略的小床,靠在画台旁的墙边。反倒是墙上、桌上、地上随处可见的画作,可见一个绘画者的文雅。
他家的墙上挂了一幅对联,是公民鉴赏家杨仁恺师长西席为王义胜撰联并书写的:经年累月追摹古韵得三昧,浓墨淡彩求索新意成一家。杨师长西席简要地概括了王师长西席的绘画人生。实际上,在如今的字画市场里,王义胜的画有很好的口碑。但对身外之物,王义胜看得十分淡然。多年来,他就一门心思地扑在艺术创作上,身上那件朴实的棉衣也已跟随了他许多年。
王义胜说,这并非故意而为,而是童年贫穷的屯子生活,造就了他生平勤奋、朴素的生活办法。1941年,王义胜出生在辽南盖州花园坨阎峪村落,一个很小的山沟里,祖祖辈辈都是农人,生活大略且艰辛。可与村落里其他的孩子不同,从小王义胜就流露出对绘画的热爱。“当时家家户户都有伟人的挂像,每天放学后我就在条记本上,用家中墙壁里的石油灯烟灰画伟人像。”左邻右舍看到王义胜的作品都赞不绝口,有的更是面露惊异之色!
“他们都以为我画得特殊像。”
那一年,王义胜还不满10岁。
用借的铅笔考取鲁美附中
人们熟习王义胜,大多是从看他创作的连环画开始的。尤其是那本与他人互助的《白求恩在中国》,画意高超、主题光鲜、贴近生活,深受读者的喜好。
但理解王义胜的人都知道,在考入鲁迅美术学院附中之前,他没接管过任何与绘画有关的演习。就连当年报考附中时的美术专用铅笔,还是初中同学借给他的。“考鲁美附中时,考点在沈阳,那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父亲把我送到车站,临走时往我手里塞了几张东拼西凑的皱皱巴巴的路费。”回顾起旧时的光阴,王义胜说他十分感激父亲当年对他的支持,“家里只供了我一个人读书。”
告别了父亲和家乡,王义胜揣着梦想与希望,直奔沈阳。初到沈阳时,他的第一印象是沈阳城太大了!
“火车站的事情职员见告我,从沈阳站搭乘有轨电车就能到鲁迅美术学院附中。”可屯子孩子初到城里,就像刘姥姥进了大不雅观园哪哪都不认识,不知道如何是好的王义胜末了硬是从火车站徒步走到了考点。
沈城的7月,骄阳似火。在考场里,王义胜拿着那根借来的绘画铅笔,站在画板前,目不斜视地画着讲台上的静物。不经意间,他瞥了一眼身旁的另一名考生,“她带了有拳头粗那么一大捆绘画铅笔,各种各样的。”王义胜说,那一刻他意识到了出发点的差距。好在凭借着悟性和天分,那年夏天,王义胜幸运地考上了鲁迅美术学院附中,也离梦想更进了一步。在附中学习期间,王义胜基本上就靠着一年10块钱的奖学金支付日常开销。虽然生活捉襟见肘,但也让王义胜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学习上。
三尺讲台传承鲁艺精彩
翻看王义胜的早期作品,心中会有这样的感触:那些看似通俗俗通的生活点滴,在他笔之下却变成了美妙的画面。例如,工笔人物画《小房铭》《春色人间》《晨妆》等作品,无不流露出画家敏锐的洞察力和对平凡生活的艺术转换能力。王义胜说,这些技能都是在鲁迅美术学院习得的。
1959年,从附中毕业后,王义胜考入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画坛大家许勇师长西席和王盛烈师长西席。鲁艺的精髓也是从那时起,满满地沁入了他的内心。在王义胜的影象深处,不雅观察、体验生活,从生活里挖掘灵感,便是老师们传授给他的第一门课业。“当时许老师常常带我们到屯子写生,他教我们如何在充满泥土的‘大车轱辘’与‘套马绳子’中看到美,在平凡朴实中创造美。”也正因如此,王义胜早期的艺术表现形式与创作手腕,都是极为贴近生活的、现实的,而这也形成了异日后独特的艺术特点。
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王义胜留校成了国画系的老师。直到退休,王义胜在三尺讲台上,传承着鲁艺“反响现实生活”的传统。
不断创新追寻心中所想
2009年,退休后的王义胜获聘沈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在没有了繁复的传授教化任务后,王义胜将大段的韶光用以研磨画技和创作。他开始把创作题材转到仕女画上,并决定在这个领域作出一些有学术意义的探索。
在仕女画的探索中,王义胜不仅给人物授予了传统的精神,还将云卷云舒、寒枝雨露的意境融入创作。他笔下的仕女笔墨精妙、淡雅干净,与他的性情极为吻合。而采访中理解到,每一幅仕女画的背后都有着上百次的打磨。在一次次笔墨、色彩与构图中不断探索,王义胜逐渐达到心中所想的面貌。
例如一幅名为《明月梅花一梦》的仕女图,王义胜“画画就像跳高,直到你再也跳不过去了,失落败之前的那次便是你末了的成绩。”在王义胜心中,画画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近年来,在研讨仕女画的技法的同时,也总能捕捉到辽南的印记,《白求恩夜过封锁线》中的平顶瓦房、《梦回梨花峪》里的一簇簇绽放的梨花、《故乡除夕夜》中的山村落……王义胜用画笔怀念过往、抒发心中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多年前,王义胜还与他人互助完成了一幅长15米、高2.5米的《盛京缅胜图》,通过画笔再现了清朝初年盛京百业兴盛的繁荣风貌。后来,这组画还被缩印成邮册,成为宣扬、推广沈阳城市风采的一个名片。
在谈及挖掘城市亮点、发展城市文化时,与艺术创作相伴生平的王义胜认为,沈阳是清文化发祥地,满族文化不仅是沈阳宝贵的历史遗存,也是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由来的核心,“作为沈阳市文史馆馆员,研究沈阳历史、弘扬满族文化义不容辞。该当把满族文化提升到一个更高、更详细的宣扬高度上,把沈阳古城的名片传得更远。”王义胜如是说。
沈阳、沈报全媒体主任关彤 拍照孙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