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价纪念梅兰芳师长西席诞辰130周年,日前弘依梅和宛平剧院推出了“依依向梅”的纪梅主题演出。一周内,由史依弘主演的七出梅派经典剧目连缀上演。
“依依向梅”系列演出之《霸王别姬》(拍照:言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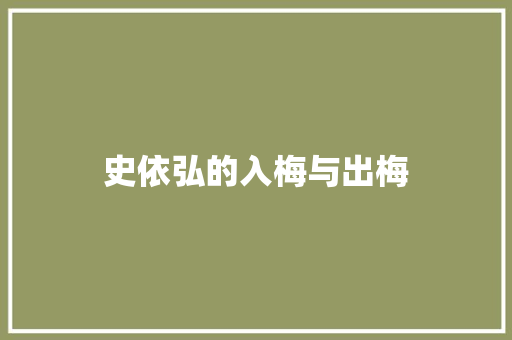
演出自然倍受不雅观众的热捧,媒体也在热追。确乎,当下能将梅派艺术演绎得如此精妙,且风华正茂者,非李胜素、史依弘、董圆圆等一众梅派俊彦莫属。而史依弘,则是个中独具风采的别样存在。
何谓独具风采,或别样的存在?我以为史依弘追寻梅派艺术的路径,与他人有所不同。梳理史依弘之分歧凡响,或容许以帮助我们思考一个颇为困扰的问题,即我们该当秉持若何的文化态度来传承戏曲艺术。
重“访师问学”之实,轻“认祖归宗”之虚
史依弘的艺术出发点,实在很普通。入戏校时,得益于她此前在体育宫受过一些武术演习,在一群白丁孩子中,是当然的“体育生”。翻身下腰不在话下的孩子,自然被当作武旦培养。在有“第一武旦”之誉的张美娟老师调教下,这位特殊能吃苦的“体育生”很快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作为在校生的演出,她的《火凤凰》一炮打响上海。
此时的她,只是受人称道的武旦,与同为旦行的花衫、青衣,遥不相及。不为人知的是,张美娟老师早已为爱徒担忧了。她知道自己学生的扮相气质、力量速率、韵律节奏,都堪称人才难得。唯有那嗓音,委实苦了点。所谓苦嗓,大凡是音色沉闷,高低难就。倘不能打破,便发展有限。于是,她悄然将史依弘送到了一位奇人门下。
那位奇人,便是卢文勤。还是他在同济大学物理牵挂捆扎书时,因拉得一手好琴,而与同窗的梅兰芳公子梅葆琛结交。那年梅师长西席在沪演出,突遇琴师生病。经梅葆琛推举,20岁的卢文勤便传奇般担当了梅兰芳师长西席的琴师,备受梅兰芳夸奖。主要的不是卢文勤因此荣誉鹊起,而是他就此弃理从艺,以理科生所长的学理思维,潜心研究梅派声腔了。多年后,他的著作《京剧声乐研究》成了京剧声腔研究的开山之作。
或许,当年的张美娟老师找到卢文勤,只求史依弘嗓音得以改进,成为出色的刀马旦。不承想,卢文勤对梅派声腔的精湛研究,以及对京剧发声的科学认知,为史依弘推开了一扇门,令她在梅派声腔的天下里流连难返。经由卢文勤一段韶光的调教,史依弘嗓音涌现积极转圜,声色堪当文戏了,显现出文武兼具的潜力。只是她刚入上海京剧院时,随剧院青春版《白蛇传》进京演出,担纲的只是武戏部分的白素贞,文戏则另有人担纲。但是,上海京剧院已经真切地看出她的文戏潜质,不久便为史依弘量身定制了新戏《扈三娘与王英》。
扈三娘的角色在老戏里是由刀马旦应工,可这是出笑剧色彩浓郁的新戏,扈三娘的演出吃重,文戏甚多,势必兼具花衫行当。结果史依弘在《扈三娘与王英》里大放异彩,尽显文武全才,令其在22岁的年纪便得到“梅花奖”。这是继《火凤凰》之后,史依弘跨上的一个主要台阶。
往后的岁月里,史依弘一贯按文武兼备的路子发展。大量的传统经典老戏,无论刀马还是花衫青衣,无论唱功戏还是做工戏,她一部一部地积累,一出一出地上演,且不设流派与门户界线。只要适宜自身条件且喜好的戏,便会乐此不疲地投入。但是一贯不归流派、不分门庭的她,却从未间断过在卢文勤老师那里叩问和探究梅派艺术。十余年不辍,直至老师谢世。
史依弘长期坚持不归派,不入门,却矢志不渝地追寻梅派艺术。相较于业内其他青年才俊通过拜师入门,成为流派入室弟子求得发展的传统习气,她求师问道的办法明显不同。
究其缘故原由,我以为紧张的是,史依弘重“访师问学”之实,而轻“认祖归宗”之虚。从她出科以来的经历看,师从的各方名家,不下二十。她每出戏的成功,险些都浸润着这些老师的心血。师生之间通过传授教化互动,很多名家大师对她都喜不释手,视若己出,如杜近芳和梅葆玖老师,还包括李玉茹、李金鸿、杨鞠萍、杨秋玲、陈正薇等。师生情意,融融暖人。
史依弘之求师问道还有一个特点,既找名师,也找明师。所谓明师,即业内的“明白之师”。他们名声不显,但见多识广,犹善思辨,对繁芜的艺术征象,每每会有醍醐灌顶式的灼见和手段。比如上海京剧院的于永华,在《扈三娘与王英》《狸猫换太子》创排中,对启示史依弘塑造人物,浸染不可或缺。史依弘对其感念,无以复加。又如许美玲雍容典雅的气度,至今还映射在史依弘的《西施》演出中。
不可回避的是,蒙师张美娟的不雅观念和言行,对史依弘也有深刻影响。张美娟为人为艺很是中正,但艺术不雅观念生动而开放。她没有画地为牢之念,更无意学生因“磕头入门”而囿于方寸,反是竭力为学生打开窗户,纵览大千。如此,史依弘将戏班倡导的转益多师风尚,融入自身实践,以免有“磕头”之名,而少“师生”之实。
秉持宗梅(兰芳)而不惟梅(兰芳)的不雅观念
按业内惯习,史依弘不是梅派入室弟子。但在不雅观众心目中,却普遍视她为隧道的梅派青衣。论表象缘故原由,一是史依弘孜孜以求梅派艺术的长期努力,二是她将梅派剧目演绎得鲜活而富有舞台魅力。论内在深层,是她对梅派艺术的认知,超出了通过外部动作和声线模拟来学习梅兰芳艺术的阶段,而趋于从发声办法技巧上和身体形体的节奏韵律上去找寻梅兰芳舞台行动的办法与方法。这,显然是受卢文勤的影响了。
卢文勤基于其学理思维,与惯常所见的模拟思维(“口传心授”)之不同,就在于对繁芜且难以言表的艺术行为和状态,进行分条析缕的归纳和严密的逻辑剖析,进而创造和整合其舞台行为的办法方法与生理机制。卢文勤《京剧声乐研究》和《戏曲声乐传授教化谈》两部著作,可以反响上述认识。史依弘对梅兰芳艺术,由喜好而崇拜。又在卢文勤的勾引下,因思考而有所创造。从而使得她对梅派的崇拜,靠近于理性认知状态,秉持宗梅(兰芳)而不惟梅(兰芳)的不雅观念。
史依弘曾对媒体说,梅派便是追求舞台的美,怎么美就怎么来(大意)。话很白,道理却不浅。美,是见仁见智的,但有普遍性。在史依弘看来,梅派之美,在于梅兰芳的韵律感。她的梅派演绎,之以是鲜活富有魅力,很大程度上是她对梅兰芳韵律之美的感悟和表现。史依弘之宗梅而不惟梅,要义就在她从整体精神本色上把握梅派艺术;她宗的是梅派之实,不惟的是梅派之表,更不在外部尺寸描摹上唯唯诺诺。
转益多师的求学之道,让史依弘有机缘打仗其他旦角流派。十年前,她的“梅尚程荀”系列演出得到成功,也收成了争议。我以为,对不同艺术流派的揣摩辨析,亦不失落为加深对梅派认知的一种路子。犹如我们在某一领域愈是深入,就愈是须要一个参照坐标那样。史依弘的“入梅”与“出梅”,亦与此干系。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她塑造角色的意识,被唤起得较早。在京剧传承领域,演员要不要塑造人物,进行角色创造,历来有不同的见地。史依弘从戏校到剧院,周遭的文化氛围,对此普遍持肯定态度。如前文所述,史依弘初入剧院便在多少新戏里担纲全新角色的塑造,亦使其在认知深处烙印下了:塑造角色乃演员本分。
她对塑造性情丰满之人物形象的强烈神往,从她对《情殇钟楼》《新龙门客栈》的题材选择和人物刻画中,可见一斑。即便是传承演绎经典老戏,她的唱念做打,都竭尽为塑造人物形象做事。她开门见山“艺术的有趣,就在于角色的生动”。显现在她的舞台上,宛如彷佛媒体对“依依向梅”的演出宣布,“她是坚毅断交的虞姬、她是娇俏灵动的李凤姐、她是故作痴癫的赵艳容、她是持重沉稳半含羞的程雪娥、她是凄苦刚毅的柳迎春、她是如花美眷的杜丽娘、她是含冤悲切的玉堂春。一人千面,唱尽古代女子的爱恨情仇。”史依弘深知,当代不雅观众的审美已经无可避免地融入了时期的需求,唯有生动,唯有精美,方能赢得不雅观众。
史依弘在很多场合表示,戏曲的传承与创新不是抵牾的对立,而是左腿与右腿的关系。纵不雅观史依弘追寻梅派艺术的路径,我以为正是她对京剧文化状态的精确认知和复苏态度,支撑着她在纷繁的京剧传承道路上,走得与他人不完备相同。史依弘走的是一条面向发展的传承之路,一条意在引发京剧内生创造力之路,一条我们时期文化艺术培植正在呼唤的康庄大道。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间的主要深意,便是将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灵魂植根于中国当代文化的培植与发展。以此不雅观之,更是期待史依弘的艺术及其京剧舞台演绎,进入更多平凡百姓的文化生活。
来源: 文申报请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