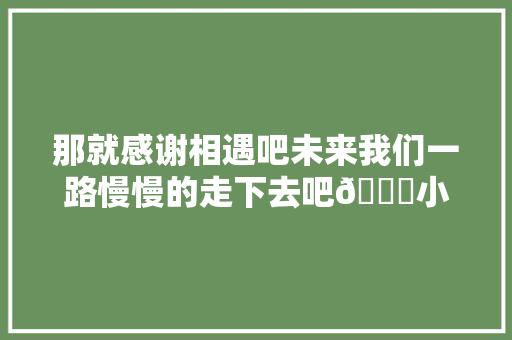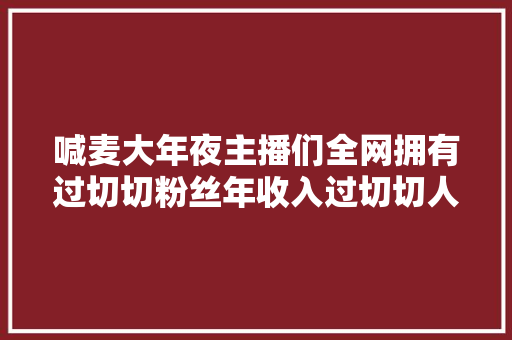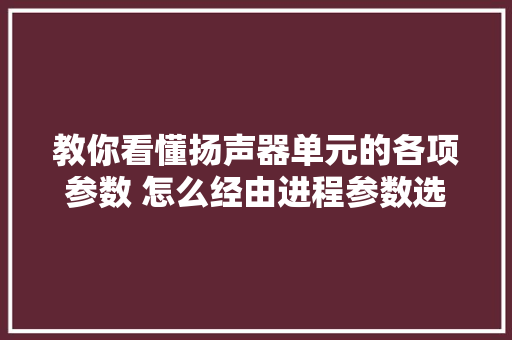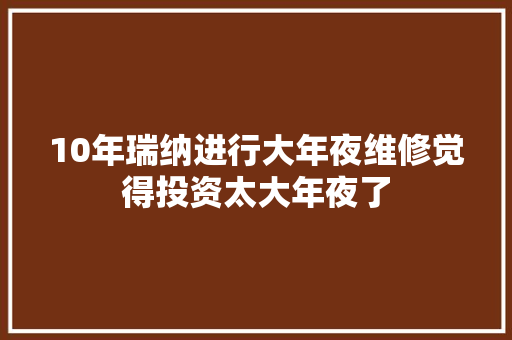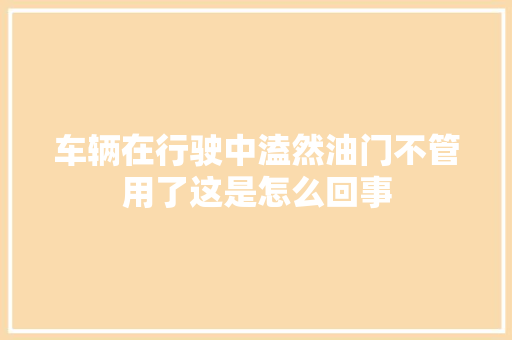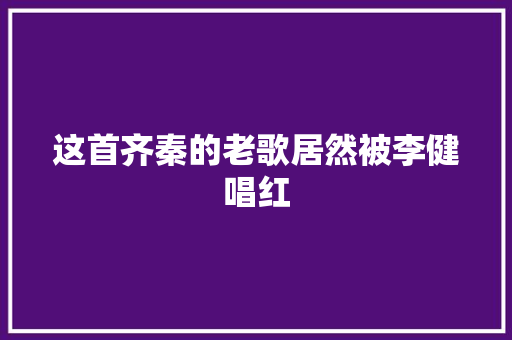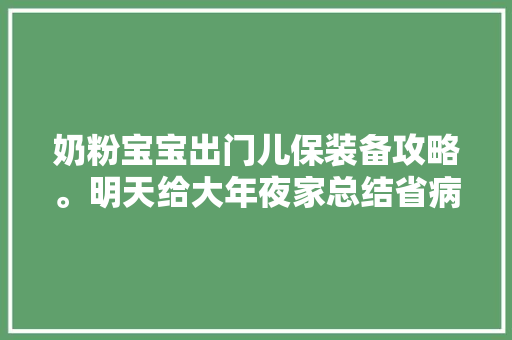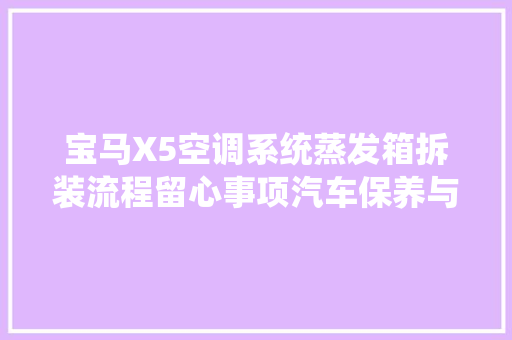周六晚上,蓝台音乐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发生了炸药味很足的一幕——高进和动力火车唱完《雨蝶》这首老歌,乐评人丁太升立时就喷射出一句特殊刺耳的话:
“高进的声音一出来,(我)就以为,哇哦,好土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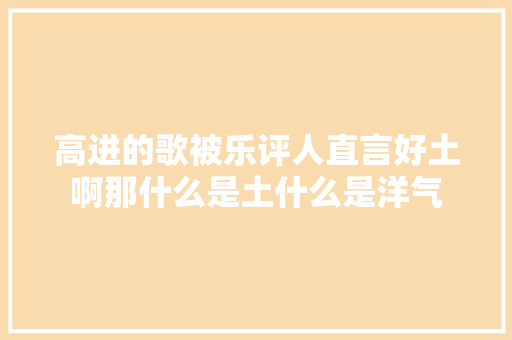
这种带着严重偏见和感情的评论,显得非常业余,完备不像一个专业的乐评人。如果你坐在那儿因此“专业乐评人”的身份说话,那么,这样的评价便是业余的,不用你说,任何一个普通的不雅观众都能说这样的话,无外乎便是说“觉得”嘛。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乐评人,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无论你说好还是坏,你得说出个一二三来。
人家刚唱完,你就说“他的声音一出来,我就以为好土”,还带一个感叹“哇哦”,这不是偏见是什么?声音这个东西都还可以分出土洋来?你可以说高进写的歌、唱的歌土,但在那个情境里,你就得就事论事,不要以为他的歌土,你就以为他唱什么都土,同样动力火车一起唱的,你怎么不说动力火车土呢?同台的明星们在没有什么改编的情形下翻唱过很多大盛行的歌,你怎么不说土呢?
听丁太升说完,高进就开始回嘴了,于是他们俩就开始了以下的对话。
高:老师,那我反问你一句,那什么样的音乐是洋气的,什么样的音乐是土的,您给我一个标准。
丁:如果把王力宏的音乐和《一人我饮酒醉》做一个比拟的话,实在即便没有学过音乐,大家也能知道这里边的音乐,哪个是土的哪个是音乐性更高的。
高:这个天下什么音乐都有,王力宏老师生活在洛杉矶,生活在美国,我从小生活在东北屯子,我想问一下,如果没有学过音乐,如果从小生活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没有资格做音乐?如果没有接管过音乐教诲,是不是不能写歌?
先说一下丁太升的“标准”吧,这个标准是不能称之为标准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学过音乐,他未必能知道王力宏的歌和《一人我饮酒醉》哪个音乐性更高。
就像你没学过画画,给你一张民间匠人的画和一张吴冠中的画,你可能就会以为民间匠人画的老虎或者素描更像、更好;如果你没有学过书法,你可能就会以为一个书法爱好者的小楷比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更好——这都是非常普遍的征象。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去帮一个收藏古典家具的老板写稿,那时候我对古典家具一无所知,一进门我就看中了那个雕龙画凤的柜子,老板说如果你喜好可以送给你,反而阁下一张“平平无奇”的八仙桌,代价200多万,我还说白送我我都不要。
丁太升的这个标准是站不住脚的,很多老百姓便是以为《一人我饮酒醉》更好听,就像20年前我奶奶听到盛行歌曲都还破口大骂,说唱的什么鬼,还不如办丧事的时候唱的孝歌好听。
当然,高进的回嘴也显得很无力,乃至都跑偏了,你是由于丁太升说你土而不服气的,你要回嘴他,你就要证明你的歌不土,说半天你还是承认了自己土,但表达了一种,“是,我是土,但求求你宽容我一下好吗”的态度——没必要,这么说你还不如直接骂丁太升耳朵聋呢。
当然,他们俩的撕扯并不主要,主要的是,什么是土、什么是洋气,什么是俗、什么是雅,这两个看起来对立的描述有什么差异,或者说土和洋的标准分别是什么,到底有没有标准——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一贯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事实上,差异是一定有的,标准也是一定有的,只是说,它有很多不同的判断标准,如果连标准都没有,那还发展啥、那还研究啥,那就乱写、乱画、乱唱、乱拍呗,反正又没有标准。
以是,说没有标准,只看个人喜好,对付普通人而言,那是很悲观、躲避的做法;对付专家而言,那是很不卖力的表现。
差异是什么呢?在大多数人的心里,标准一样平常有4个:
第一,土便是本土,洋便是外国
土和洋这一对反义词,便是一对非常糟糕的词,当然,由于它们出身于非常糟糕的背景——相信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往后,这种语义就会消逝。
土和洋的产生,是由于大清没落,外族入侵。谁强谁有理嘛,于是洋枪、洋炮、洋马儿、洋火、洋大人,成了前辈的代名词——由于在那个时候,他们确实更前辈。
全体中华民族在掉队往后,全民自卑就成了一种特殊普遍的生理征象,这种征象在一百多年的韶光内险些没有任何改不雅观。以是有些精明的贩子,他们就玩起了“出口转内销”的模式,本来是本土的东西,但国民不认啊,拿出海去,镀个金,表明是受到外国人认可的,然后再转回来,彷佛就高端大气上档次了许多——“外国人都认可了,你们还有什么情由不认可呢?”
这种崇洋媚外的思想,导致了一系列的荒谬征象,比如一个外国人,男的,只要他长着白皮肤黄头发,他彷佛就很随意马虎在中国泡到妞,在四五线城市这种征象更普遍;一个女的,只要她黄头发白皮肤,中国的男人娶到她,就会炫耀,以为是种无上的光彩。
可是在几百年前,古人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大家看到黄头发绿眼睛的人,更多是以为怪异,没人以为他们高等,女人更不会想着要嫁给他们。
以是,从民族生理层面说,在很多人眼里,土便是代表本土,洋就代表外国,用这个标准——你来自洛杉矶你就高等,你来自象牙山你就低级——这种标准就让它停滞吧。
第二,土代表大众,洋代表小众就像有些人,他们本来很喜好某个小众的歌手,但是后来某天,这个歌手溘然火了,他就不肯意、就脱粉了,由于大家喜好,他就以为自己的品位不再高等了。
本来歌手还是那个歌手、歌还是那首歌,只是由于它被更多人听到了,你就以为掉价了?歌手也很忧郁——我特么到底是做错了什么?
你去听很多小众的歌,评论区总会有很多类似的评论,“希望你不要火”“如果你某天火了,我就脱粉”……
就像很多奢侈品,它是真的本钱很高吗?它是真的不能扩大生产、降落价格、卖给大众吗?当然不是,它挣的便是那个人们认为高等、代表身份的钱,你贬价了,人家还怎么表明他的身份?
从这个角度讲,所谓“时尚是一个循环”就可以阐明了,以前,很少人穿喇叭裤,以是他们时尚,后来大家都穿喇叭裤了,人们就以为土了。等险些所有的人都以为喇叭裤彷佛真的很土、不再穿了,过一段韶光往后,有人又重新穿了起来,于是喇叭裤、阔腿裤又会重新盛行起来。
关于大众和小众的事,我以为有句话说得很好——所谓高雅,便是和公民群众为难刁难。
第三,土便是穷,洋便是有钱就像第一条里说的,我们全体国家、民族,在长达一百多年的韶光里都自卑,都以为自己土,以为欧美洋气,实质缘故原由,便是穷。
这个征象非常普遍,就像以前只有比较有钱有地位的人才穿西装,以是大家都梦寐以求要穿西装,乃至还蜕变出一种非常变态的想法,上个班、开个会啥的都要穿西装——西装是正装,不穿不正式,正式的场合都要穿西装。
但现在谁都穿得起了,尤其是西装成了很多普通职业的职业装往后,人们开始以为穿西装土了,乃至还有人害怕穿西装。以此类推,你都不用以为夸年夜,假如往后所谓上流男人都开始穿裙子了,那么男人穿裙子就会成为新的时尚。
我前段韶光跟我朋友谈天,聊遍地所言,他就说什么西北那些方言很难听,说是一听他们说话就觉得带着黄土的味道……黄土还有味道?我就说——如果中国的都城在西北、中国的经济中央在西北,那么,人们一定会以为西北的方言好听极了,就像以前很多歌手唱歌不好好吐字,非得要扯着嘴巴说话,我乃至还在以前的《好声音》里听汪峰说英语唱歌更好听……缘故原由便是以前港台音乐家当发达,实质便是他们更有钱而已。现在谁假如再扯着嘴巴唱歌、把“他”唱成“差”,大家都会以为他出缺点、很后进。
以此类推,如果全天下便是黑人最有钱、所有的领域都是黑人最厉害,你不用疑惑,全天下一定以黑为美,就像现在或者过去很长一段韶光,很多国人以为欧美人高鼻梁、深眼睛便是美一样。
第四,直接便是土,委婉便是洋这点比较分外,这是中国特有的委婉文化。就像以前很多歌写得很直接,一些专业人士就会以为很土,他们认为要拐弯抹角的表达才是艺术。
比如“哥练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人们就会以为土,但实在,英文歌基本都是这个样子、乃至比这个还直接乃至露骨,人们却以为洋气——这可以参考第一条。
以上四点,都是无数的人常常用来评判土或者洋的办法,当然,这些办法都不能作为真正的标准,更多是偏见。
什么才是更理性客不雅观的标准呢?标准实在很大略,便是看——有没有创新。
判断有没有创新,又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三个视角。
两个维度,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内容。
形式在相称长的韶光内是固定的,形式创新很难。比如,律诗、词,这是形式,你的律诗写得再好,但是这个东西在几百年内写的人太多了,你的内容写得再好,但形式太迂腐了,你写的那玩意儿就土了。
当诗的形式没落往后,新的形式“词”就涌现了,经由永劫光的发展,词的这种形式也没落了。在这个形式没落往后,你还用这个形式来搞创造,那么就有点不合时宜了。就像摇滚,摇滚是一种音乐形式,韶光久了,大家在形式上都听腻了,你内容再好,也难在火起来。
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没有第二个周杰伦这种引领潮流的人涌现,便是由于形式创新太难了——这个东西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当形式基本上是固定的情形下,我们判断是不是土的标准,更多讲的是内容。拿歌曲来讲,构成歌曲最紧张的内容是旋律、节奏、编曲这些音乐层面的东西,以及歌词。
有些歌,它那个旋律,你一听,就觉得这类似的旋律已经涌现得很多很多了,以是它就土;它那个歌词,你一听,觉得很多很多人都是这么写的,它就土了,比如什么“忧伤”“远方”“寂寞”这类似的词,实在是太多了。但如果现在只有很少的人写忧伤、远方、寂寞这些词,那么他们便是很洋气的。
当然,由于每个人的专业素养不一样,以是即便是把“是否具有创新性”作为标准,每个人的标准还是不一样的。
这就要讲到前面说的三个视角了。
三个视角分别是:大众视角、专家视角、个人视角。
拿听歌来讲,大众基本上都听过一些歌,但又不是很多。大众内部也是分裂的,有些人听得轻微多一些,有些人听得轻微少一些。有些人的各种音乐素养要轻微丰富一些,有些人的素养又稍微薄弱一些,但基本上会有比较大的同等性。就像现在,有钱人是少数,赤贫的人也是少数,大部分人就不穷不富。如果大家都没钱,自行车就会盛行;大家轻微好了一些,小汽车便是盛行。
专家——我说真正的专家哈,专家便是靠这个用饭的,他听过无数的歌,熟习创作规律,就像我们正凡人读书没那么多,但好歹也读过一些,以是大家都常常会选出自己“最喜好”的书——你就看过那么几本,你就随意马虎以为你看到的便是最好的。但专家不一样,专家看得太多了,你以为精彩的,人家可能看过几百原形似的,以是就“什么才是好的内容”这个问题,专家和大众之间,就随意马虎有不合。
比如,有人以为郭敬明写得好,有人以为韩寒写得好,有人以为金庸写得好——但他们都不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都是阅书无数的人,金庸韩寒们写的,叫“普通文学”——这些套路,很多人都写过了,它缺少创新性、它还是不足特殊。
除了大众视角和专家视角,还有一个很故意思的视角,便是个人视角,这个差异就很大。如果我听歌无数,那大部分的歌我都以为不新鲜,越不新鲜的我越以为土,但如果我很少听歌,我听一个“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天下、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我就会以为很新鲜,这首歌对付我而言,就一点都不土。
以是不要轻易跟任何一个人谈论审美或者艺术,比如你听歌无数,他听歌很少,你听得很多,哪些好、哪些不好,你大概会有一定的判断,但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没听过,那他很随意马虎就会以为某某最好,比如有些人只听欧美盛行,他就以为欧美盛行最高端,加上前面讲的四种判断标准,他就更以为自己无比优胜,而有些人只听高进、小沈阳们,他就以为高进和小沈阳是最好的。
从这个角度讲,不要随便跟谁谈论审美,你要谈论,就得大概知道对方在这方面知识的广度与深度,要不然末了都会变成相互鄙视。
总结一下:一首歌土不土,判断它好坏的条件,便是形式上、内容上它是否有创新、是否新鲜,但每个人的知识面不同,歌对付详细每个人的新鲜度不同,以是它是土还是洋,标准不一。从行业发展、个人发展的角度讲,标准该当看专家的标准;从大众接管程度,那就看大众的标准;如果你自己自娱自乐,那么就参考自己的标准。
如果把是否具有创新性作为判断一个作品好坏的条件,那么,它的标准该当由专家制订。但是,专家一定假如真正的专家,而且在评判的时候要冲破个人喜好、偏见,也要给出客不雅观、镇静、专业的情由。
当然了,希望老百姓对专家不要有偏见,专家也要尽可能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也不要对老百姓抱有偏见,由于这两个群体在谈论好坏的时候,很可能聊的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比如一盘菜,老百姓以为好,便是看它好不好吃、吃起来觉得怎么样,但专家可能要从医学、营养学、生理学等等各个角度去评判。
(就像一个电影,它是否得到威信大奖,跟它是否有高票房,不是同一件事,当然,他们可能会重叠,但这两个标准依然不是同一个维度的东西。一个电影得奖,不代表它能卖座,同样,一个电影卖座,不代表它便是艺术水准高。歌也这样,大家都喜好,未必它便是艺术性高的,专家们都以为好,它未必能被大众接管。)
写了5000多字,终极还是想说: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尽可能收受接管不同的不雅观点,乃至能收受接管相对立的不雅观点。你越偏执、越总是言“最”,可能表明你越浅薄、越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