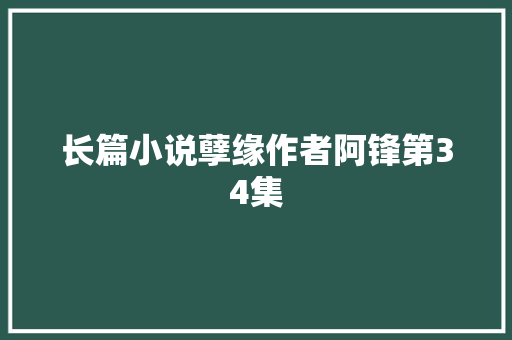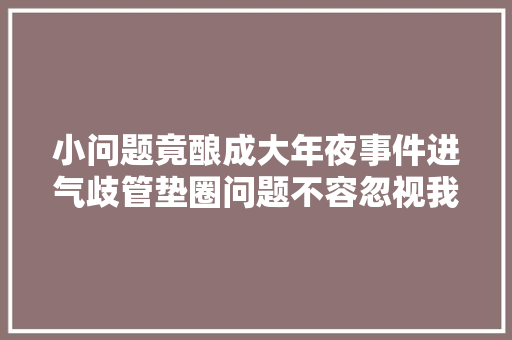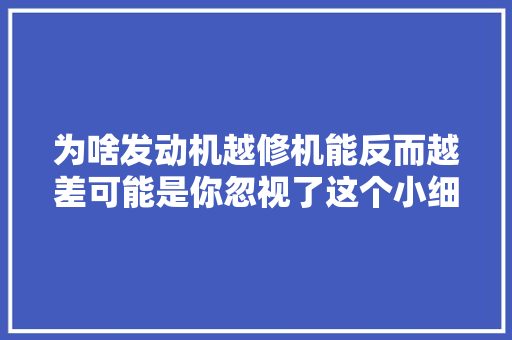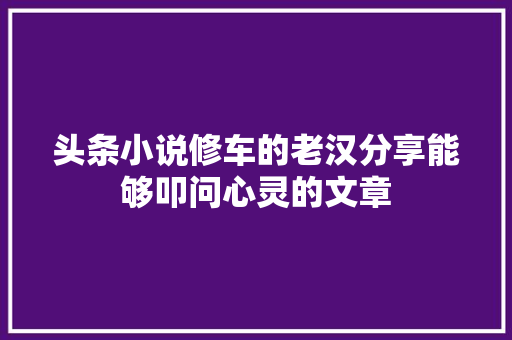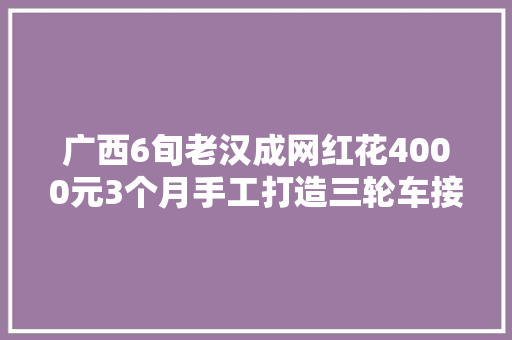1971年夏天,队里派我进城积肥。当时,县城除了革委会大楼里有水冲式厕所,其他机关、单位和居民区都用的是旱厕。酒泉人把旱厕叫做“圈”,我们这种人被称为垫圈的。全城有近千个垫圈的,先前干这活的都是些老社员,而且多是王老五骗子老汉,他们在屯子无家无舍,以是进城一干便是好多年,插队知青进入这个行道,是近两年的事。
我们的住处叫垫圈房,是城郊义士陵园边一间6平方大小的破窝棚。窝棚有门无窗,采光靠的是屋顶上一个不大的窟窿。窝棚前面有个堆积粪土的场子,场边的几棵洋槐树,恰好挡太阳、拴牲口。时有牛车、马车、毛驴车、骆驼车停放在场上,队里的乡亲们进城办事,多的在我们这儿打尖歇脚,垫圈房也是生产队在县城的接待站。散布在城边各个角落的几百个垫圈房,环境和这儿差不多。

除了我,垫圈房里还有一位姓马的独眼老汉。老汉个子终年夜、身板直溜,额高面长、悬胆鼻子、蓄着一抹八字胡,如果不是瞎了一只眼,够得上仪表堂堂。他进城已有些年头了,可以说是个资深垫圈的,对个中的行行道道清得很。我喊他老汉,他叫我眼镜儿,两人内外有别合营默契,拉土垫圈、清扫厕所我包了,烧水做饭、侍弄牲口就靠他。
垫圈房背后有条小路,小路走到尽头是文化巷,巷子直通五、七红专学校。我们垫的所谓圈便是学校的公厕。校园出进的人里,垫圈的地位最低下。见我蹑手蹑脚地走“猫步”,老汉冷笑道:“嗨!
眼镜儿,弯了弯是个榆棍,怂了怂是个男人,做啥劲呢?把腰杆放展!
”往后,我赶着臭气四溢的毛驴车穿过校园时,常把皮鞭甩的劈啪乱响。
每天,天亮以前,我都要把厕所里里外外打扫干净,仔细地用城墙土把茅坑里的粪便掩埋起来,那土不能厚,厚了肥的质量差,也不能薄,薄了压不住臭味。下午,我还要赶着驴车去城墙下,拉回第二天用的土,然后再把厕所打扫一遍。垫圈这活是又轻松又清闲,只是有时还要和其他社队的垫圈的们打斗殴,争抢粪土没得多少道理可讲,得靠拳脚办理问题。
老汉性情坚硬,身上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狠劲儿,平常处事挺横。但是,他对动不动斗殴很不以为然,他给我说:“知道吗?狼里头最狠的是那一种狼?是绵狼。剑里头最快的是那一种剑?是舌剑。大家都以为非斗殴不可的事,谁能说说就摆平才是本事。”
话说的老辣光滑油滑,我不知该怎么应对,就和他抬杠:“照你这么说,能说会道便是本事,咱大队几千号人里,数主任最能谝喘,他便是最有本事?”
“两码事!
说要说的人服气,说要说的人乐意。马靠笼头栓,人拿道理管,主任几时讲过道理?他那是满嘴跑舌头,活活一个‘卖嘴的’。要说他呀,还不如旧社会的窑姐儿,人家卖那家当的时候,就没想着立牌坊。”他忿忿地驳斥我。
空闲时,我俩喜好盘在土炕上吸着旱烟锅谈天。他问我:“你知道吗?我们穿的制服为什么是五个纽扣?”
他说:“那个五,代表的是五全宪法,是五族共和。”
他口音里时时夹杂着一半句京腔,动不动就来几句老子、小子什么的。他曾自满地给我说“老子是打过日本鬼子的革命军人。”除了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还有这等革命军人?他还常常提及一些地名如陕坝、归绥等等,提及百灵庙决斗苦战和傅作义将军,提及管喻宜萱夫人唱的《哪里来的骆驼客》……这些,我都闻所未闻。
老汉会唱《大刀进行曲》,他满嘴没几颗牙,唱得荒腔走板不成调。但从他的歌里,我听出与广播里不同的一句:“前面有二十九军的弟兄们,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你饶了我吧。怪声怪气的,我都起鸡皮疙瘩啦!
要不,你再讲讲忻口会战也行啊。” 他笑了笑,并不计较我的不敬。
那段期间,看到别的知青招工招生进城回家,而自己由于所谓家庭问题走不成,我心情十分忧郁,少不了长吁短叹。他不厌其烦地疏导我:
“人是打节节活的,保不住哪天太阳就从你的门前过的。”
“不下雨的云彩飘走了,还有下雨的云彩呢。”
“一辈子要想苦出个名堂来,要紧的是得有背受(承受力)!
为啥自古少年得志不得长?缺的便是背受。”
这些话,经得起琢磨,我一贯没有忘却。
我问他:“你是走南闯北的老江湖了,现在却比我还穷,过去你耍人过吗?你风光过吗?”
“咋没?当兵吃粮的临后几年,老子是有名的‘马斤半’。信不信由你,那节儿,几时几我身上都背着一斤半金子,凭啥把那么多军饷交给我保管,凭啥?就凭老子忠勇双全,主座信得过、弟兄们可靠。”吹了一下子,他忽然瞪着独眼,恶声恶气地叮嘱道:
“记住,两个人说下的话风吹了!
你可不能当走线绳绳(密告者)。”
我不会当什么走线绳绳,我记住的只是他在埋怨会上讲述的悲惨故事,还记住会场上议论激奋,口号不断:“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仇!
”
我对那斤半黄金没兴趣,也不管他曾经是士兵还是军需官。我爱听他说道兵器,什么八路的“老套筒”、国军的“中正式”、老毛子的“水连珠”、鬼子的“三八大盖”和捷克造的“马克沁”机关枪,等等。他特殊喜好模拟各种枪声,可是从他的嘟哝里,我实在是听不出什么差异。
老汉虽然连一床囫囵被子都没有,却一贯身穿中山服,无论衣服多么破旧肮脏,风纪口永久系的严严实实。走路,他喜好背过手迈方步;说话,他时时地冒出些训话的口气。一些社员讥笑他是“过的是求乞子日子,耍的是官家牌子。”
……村落里老辈人都记得当年他结婚的红火光景。听说“新媳妇生得桃红花色弯眉杏眼,像是从戏里走出来的”,那天,看热闹的人把小小的屯庄挤得水泄不通。
有人啧啧:“老马家咋就修得这么好的福泽来者?”
也有人嘀咕:“阳世上的事,太浑全了怕不大好啊。”
或许,说这话的真是个乌鸦嘴。
他把新媳妇娶进门不到两个月,就遇上抓兵。师管区的规矩是“家有三丁抽其一”,有钱还好说,没钱只有走人。看着正拉扯儿女的大哥和没成年的两个兄弟,他是掂量了再掂量,横下一条心就走了。
他多次给我提及离家前夜的情景:
“媳妇哭了整整一晚夕啊,泥人儿一样摊在炕上……,提起三十多年前往事,每每使老汉的独眼里泪光闪闪。
鬼子屈膝降服佩服后,他被编遣还乡了。他到家才知道,自己从兵营起身时,媳妇已是病病歪歪、命悬一线。等他回到家后,人已“发送”,还没有“出七”。
老汉对亡妻感情很深,他给我说:
“媳妇得的是相思病,她是想我想去世的!
”
“有时候,我在睡梦里问她,你能等那些年,为啥就不能再耐活十天半月?耐到我赶回来病就会好啊。”
我问过他:“你不是常说独柴难着,独人难活吗,后来你为啥在不再成个家呢?”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念叨着“你不知道她的尕样子容貌有多干散,她到上泉挑水,下庄的人都跑到上泉挑;她到下泉挑水,上庄的人又往下泉边跑……,后来,不让她挑水了,娘不放心。”
从绥远回来后,他再没有出过门。直到前些年修干渠把他媳妇的宅兆推平了,这才进城来垫圈。
老汉先前在大医院垫圈时还兼着一项“副业”——掩埋去世婴,用社员的话说便是“送死娃子”。他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这段经历:“那活儿,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得有胆!
老子是去世人堆里爬出来的,怕个球呢。”
“送一个两块钱,那么大的医院,几年下来也挣不少呢。”说话时他不无得意。
“这世上有些钱还真不好挣,就说送死娃,你得走远,送到荒郊野外没人烟的戈壁才行;得往深埋,如果前脚走,后脚就让野狗刨了,那你就等着晦气吧。”
老汉虽然胆大心硬,有时候也讲点迷信。他说自己从医院挣的钱末了都“还给”医院了,“为啥自那往后病多了?是不是把谁家的娃没送好,老天看不过眼,规整我呢。”
我回队不久,老汉的身体越来越扛不住活了,队里只得把他接回来,安顿在返城知青留下的一间空屋里养病,我们又成了邻居。回队后的他像是换了一个人,整天沉着脸,很少言语,也不怎么搭理我。看样子,有多少故事要烂在老人心里了,我想。
我进城上学前给老汉作别时,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大手,搓着我的乱发沉默许久才说:“我说过嘛,在世上找事就像是拾粪,弯的远了总能拾一泡。”这是垫圈的行话。
往后我再没见过老汉……
如今,高楼林立的城市里,旱厕早已成为被忘怀的历史,垫圈的作为一种职业,也从五行八作中消逝了。
有时,我会想起那些曾经处在社会生活边缘的人们。
我听说过,垫圈老汉中,解放前干什么的都有,贩卒车夫、驼户金客、散兵游勇、赌棍马贼……。
我也看到,垫圈的知青们在改革开放后各有千秋,媒体频频亮相的、买卖场上呼风唤雨的、下岗的、上访的、在高墙电网里怀念垫圈时的自由光阴的……。
城市完备翻新了,当年那么多的垫圈房一点点痕迹都没留下。
我想它会留在一些民气里的。对两代垫圈人来说,破褴褛烂的垫圈房何尝不是人生旅途难忘的驿站?
作者简介:陈新民,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曾执教与甘肃酒泉教诲学院。后任高台县委副布告、漳县县委布告兼县人大主任,定西行署副专员,甘肃人口委副主任,中心前辈性教诲活动办公室宣扬组副组长,中国国土部资源报党委副布告,国土资源部老干局副局长。现为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
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艺报》《中国作家》《中华辞赋》《中国散文诗》《美文》等报刊揭橥过散文、诗歌、文艺评论等作品。获第二届中国报人散文奖,“赞化杯”环球华文散文大赛三等奖,中国记协党报副刊作品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