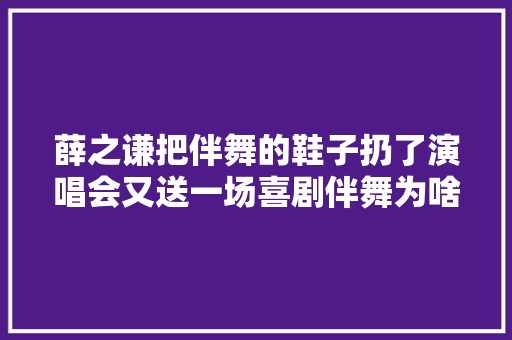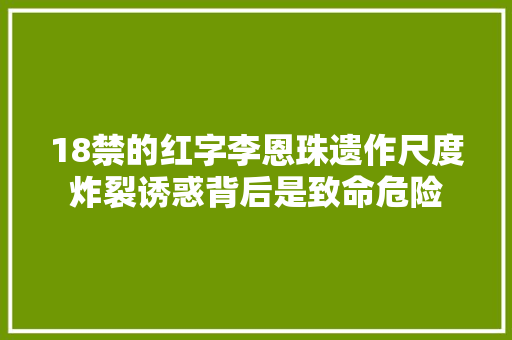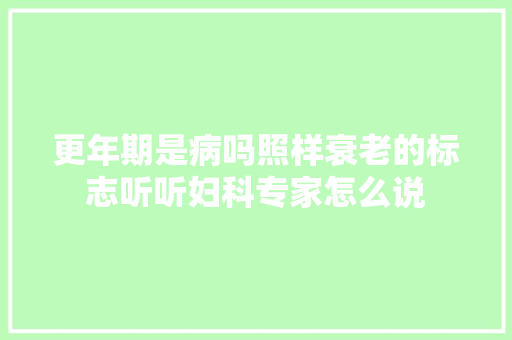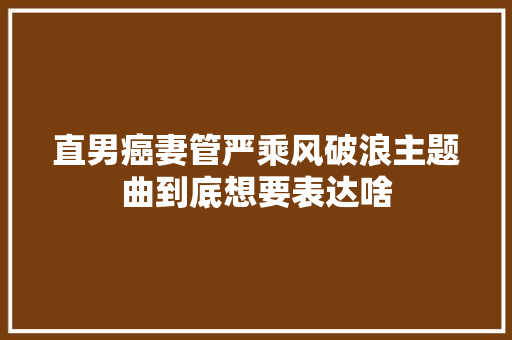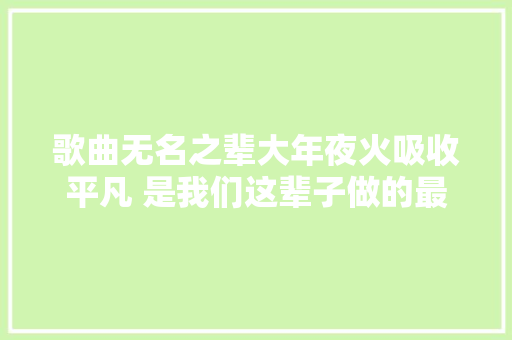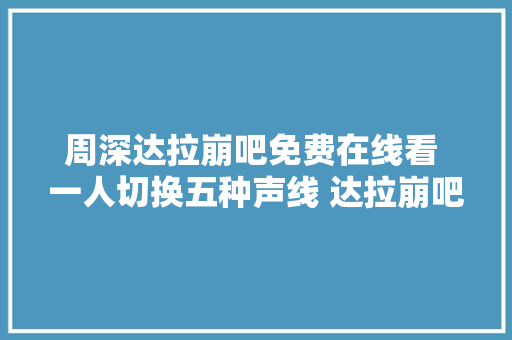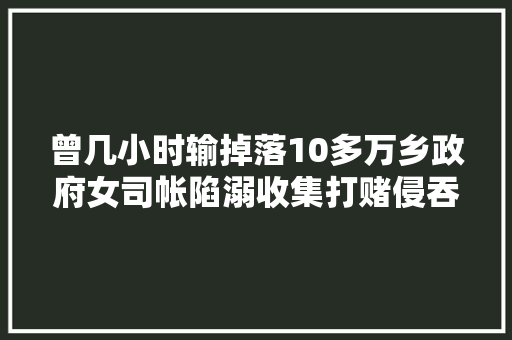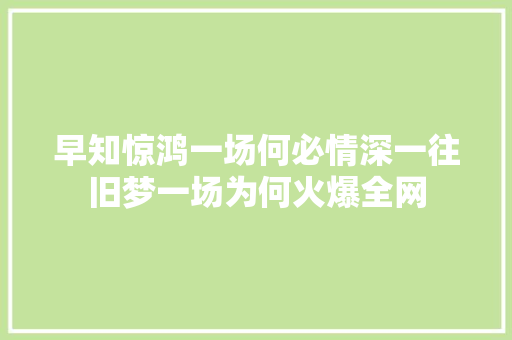慕 羽
“寂静”有多静?听说,通过科技手段,微软的Building 87消音室可以创造出-20.6分贝,靠近太空中粒子随机移动的声音,这便是环球最寂静的地方。故意思的是,早在1951年,美国先锋音乐家约翰·凯奇到哈佛大学的无反应舱做了一个实验,为的是证明这个天下上根本没有“寂静”这回事。只要还活着,便能听到自己的生命存在的声音。无声、无言的“寂静”是一种氛围,也是一种心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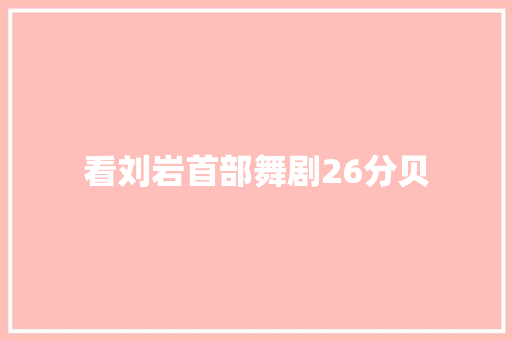
然而,这个天下上,还有一些人,他们生存的天下犹如太空般寂静。虽然,“26分贝”是他们差异于其他人的临边界,但负分贝、0分贝与26分贝对他们而言都是一回事。我很少打仗听障人群体,乃至在不雅观摩刘岩以此命名的舞剧之前,我对“26分贝”这个听力临界完备没有观点。直到今年1月尾的一天,我才感知到了它所谓“临边界”的含义。那时北京非常寒冷,演出当晚我却感想熏染到了一阵阵内心的暖流,让我想在北京最冷的冬夜,道一句感谢!感谢亲爱的小孩,感激你纯洁的心灵感化寒冰,驱散阴霾。感谢刘岩,感激你的存心,至真至纯。
刘岩,天生的舞者,圈内乃至曾有“刘一腿”的隽誉。然而,北京奥运会的一次开幕式彩排却成为刘岩人生的临边界,她不仅没有办法让她的腿再次凌空,乃至都没有办法脚踏实地。“奥运英雄”代替“刘一腿”成了她的新标签。标签好贴,人们的神经却随意马虎麻木,别人的残缺,与己何干?我也是近年才意识到,实在世上没有残缺的身体,而只有残缺的思想和残缺的社会。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切身体验他人的苦难,但至少我们不应该选择屏蔽。经历过最深的夜,刘岩意识到,只有从内心深处点燃的灯才能真正照亮阴郁,这是源于“自傲”与“自傲”的力量。
这几年,刘岩与轮椅合体一起前行,就像是折翼的天使坠落世间,而她却言,可爱的孩子们才是天使。她依然在舞蹈,只是换了别的办法,她悉心研究“手舞”,拿下了博士学位,她也帮助孤残儿童建立起自傲和勇气。从2011年起,以其名字命名的文艺专项基金开始帮助孤残儿童学习舞蹈。
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刘岩与法国舞蹈家、打击乐家互助推出了舞剧《红线》。和刘岩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遭遇了人生的临边界,失落去了听力,或是行动的能力。但全体作品却通报着温暖。3位舞者,十几位乐师,无论性别、国籍、年事……都渗透出残健共融的和谐。
没错!《红线》承载的“互惠共生”便是一种美好的社会关系。而且,从《对他说》到《26分贝》,刘岩看待天下的办法有了一些奇妙的差异:前者从健听人的视角出发,更多表现的是给予失落聪孩子以关爱,而后者已转向失落聪孩子的视角,引发出了更多的能量。健听人与失落聪者在一起,不是同情,而是尊重;不是迁就,而是乐在个中的分享。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有时失落聪的孩子,并没有失落去乐不雅观的天性;一个看上去光芒四射的默剧明星,却陷入了内心的阴霾。明星考试测验过很多方法,末了反而是孩子大略的快乐感化了他。
十分欣慰的是,《26分贝》的推出,使中国舞台上第一次涌现了“残健共融”的原创舞剧。每位角色无论大小,都有符合人物特点的动作构想。共融舞蹈本身便是要发展出属于每一个人的舞蹈,让每个人的身体和思想都能得到尊重,无论你是专业舞者、四肢健全、听障、视障、智障、肢障……
实在,在台上合乐跳街舞的演员大多数是听障儿童。但看上去,他们与一样平常孩子并无二致。戏里戏外的孩子,只管听不见,但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办法,去感知彼此的位置,以及舞伴何时动、何时停,并做出自己的呼应,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感想熏染到了自己对付作品的贡献。
一位名叫石头的失落聪男孩是作品的核心,他的动作自然、不造作,尤其是那些他身体主动产生的动作瞬间最令人动容;有时“触摸”便是他的“耳朵”,“动觉”便是他的“听力”;有光阴,他爱上了默剧,并开始追逐他的偶像。
另一位主角则是小男孩的偶像,他便是默剧明星安吉尔。关键点就在于此,舞蹈化的默剧是他最善于的高招。他的手中像是有一些看不见的“红线”,纵横交错地被他把玩,这也成为默剧演员的主题动作。
安吉尔的默剧戏中戏成为亮点,石头开始模拟着安吉尔的主题动作,也打手语描述着天下。在手语中,他们成为了自己的主人,天下的声音和颜色一样,都可以在手中呈现出来。
与轻阐述的当代舞剧《红线》不同,《26分贝》的叙事性很强,也更具亲和力。这是刘岩在艺术创作上的再次转型,能感想熏染到她希望用现实主义“以舞演故事”的办法,走进中国普通家庭的内心天下。
剧中的默剧明星安吉尔就像是连接有声与无声天下的一座桥,而且桥上不是一个人在走,刘岩正召唤着大家共筑这座桥。听力失落聪并不可怕,只要精神没有“寂静”,向孩子学习,不让生命“失落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