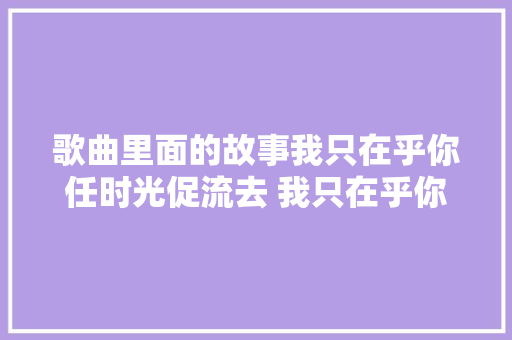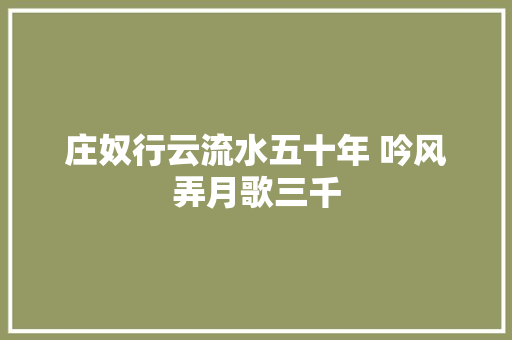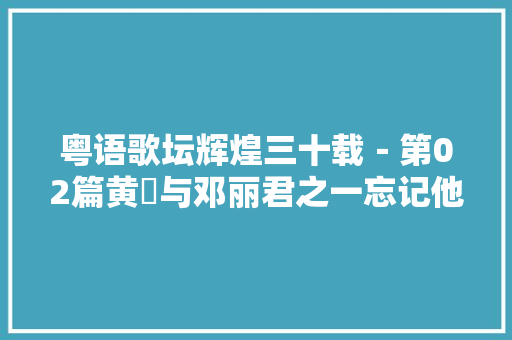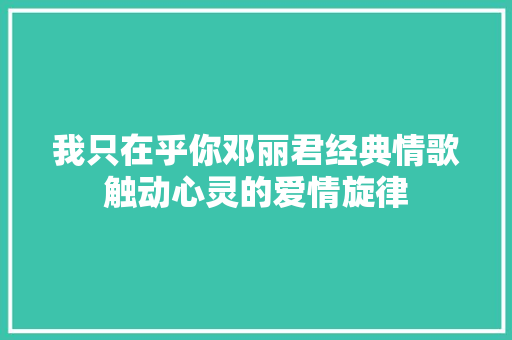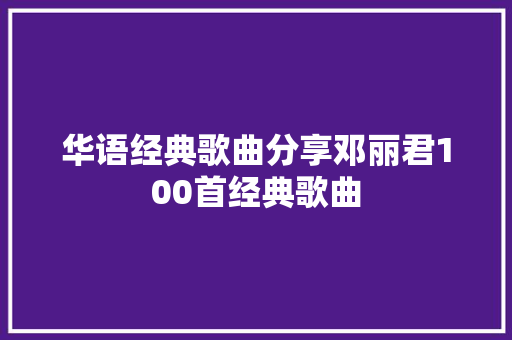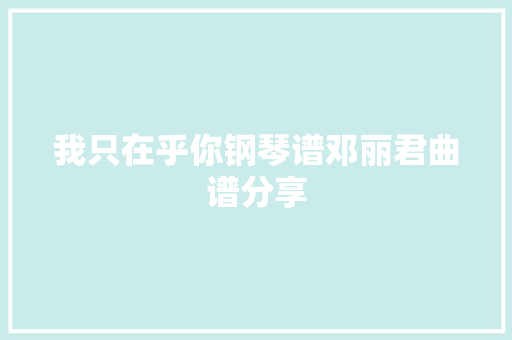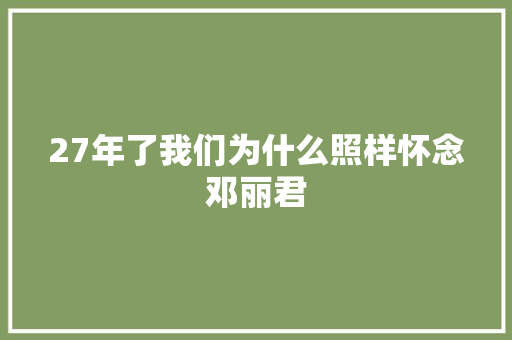——歌曲《在水一方》几个版本的比较与赏析
一、伊人在水一方,公子琴瑟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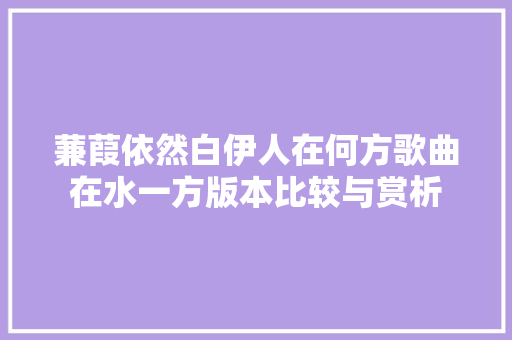
长发。墨镜。花格衬衣。穿着喇叭裤,蹬着自行车,提个双喇叭录音机,用3节5号电池驱动一盘邓丽君的磁带穿街走巷,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髦。
当时还是小屁孩的我便是随着这样一辆自行车,第一次听到邓丽君《在水一方》的。
一听入迷。这世上还有这么好听的歌?小街上人杂,断断续续听不真切,不过那很口语的歌词,很亲切的旋律,尤其那好似化骨绵掌一样的气息,以前闻所未闻。那种美,美得销魂蚀骨,弄得你迟疑未定,录音机里的歌声愣是把我活活牵引着,随着那花格衬衣的自行车跑了两条街!
花衬衣得意地对我笑,可那录音机里仿佛真有个缥缈柔美的仙子,袅袅娉娉依稀在向我招手……
后来知道,这首歌叫《在水一方》,由琼瑶填词,林家庆谱曲,最初在电影《在水一方》中由江蕾演唱。1980年,邓丽君翻唱了这首歌并将其收录于同名专辑《在水一方》中。随着大陆改革开放,这首歌迅速在中国大陆流传开来,可以说当时的大陆,凡有人烟处,便有邓丽君的歌,凡有邓丽君,必有《在水一方》。1988年,琼瑶推出《在水一方》的电视剧版本,歌曲改由李碧华演唱,作为电视剧的插曲每晚在电视机里反复。
看,已经有三个版本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已上大学,同学之间互换磁带,以是都听过。先入为主当然是邓丽君,甜美,富丽,深情、激情。她的歌把一幅《诗经》中才有的浪漫唯美画卷维妙维肖地展现在你面前,歌声中,你彷佛看得到那位佳人“在河之洲”遗世伫立;而李碧华的呢,起句平和,配器朴实,唱法平实,感情淡远,略显空茫忧郁,声音圆,亮,纯,加之吐字刻意延后一点点,营造了欲说还休,欲走还留,一步三转头的依依不舍,有种惆怅无奈的本色真情。比较起来,原唱江蕾反而影响较小。
其后,又有不少歌手翻唱过此曲,比方杨洪基、韦唯、高胜美、费玉清、黑鸭子等。此外,歌曲旋律还被改编成各式各样的版本,用泰西乐器、中国民乐器等等演奏,比方中心乐团、新爱乐乐团就出过交响乐版。版本各类各样,蔚为大不雅观。不知是林家庆的曲子做得好,还是《诗经》中古人那无拘无束的爱情太动听,不然咋会吸引这么多人不断来“炒陈饭”?但影响最大的还是邓丽君,我最喜好的,则是邓、李,以及爱乐交响版。咦,之前的没什么影响,之后的没什么影响,这正应了那句话:莫为之前,虽美弗扬,莫为之后,虽盛不彰。
二、当古诗词遇上邓丽君:谁造诣了谁?
你知道的,《在水一方》歌词是根据《诗经·秦风·蒹葭》的内容改编的,原文是这样: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心。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在水一方》的灵感虽然来源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歌词却没有照搬《蒹葭》,而是取其意而发挥,很大胆地、很亲切地作了口语改编。琼瑶改编的歌词你耳熟能详,是这样写的:
绿草苍苍 白雾茫茫
有位佳人 在水一方
我愿逆流而上 依偎在她身旁
无奈前有险滩 道路又远又长
我愿顺流而下 找寻她的方向
却见依稀仿佛 她在水的中心
绿草萋萋 白雾迷离
有位佳人 靠水而居
我愿逆流而上 与她轻言细语
无奈前有险滩 道路弯曲无已
我愿顺流而下 找寻她的踪迹
却见仿佛依稀 她在水中伫立
绿草苍苍 白雾茫茫
有位佳人 在水一方
明白如话,富有韵律。看似大略,没有深厚的文学教化,改不出这个效果。小时我不懂,现在我佩服。
《在水一方》歌词的灵感虽然来源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作曲家林家庆却没有利用中国古代的传统五音,而是采取当代常用的大调音阶,以梦幻平和的旋律为作品增长了一分神秘的他乡色彩,把一个缥缈柔美的“伊人”形象塑造得竹苞松茂、求之不得又不克不及自休。这三段歌词,当年听来以为平凡,现在看来,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乃至国学功底,和激情洋溢的音乐才华,口语歌词不可能这么呼之欲出、真切可感、动听肺腑。实在那个年代,港台的琼瑶啦,邓丽君啦,乃至金庸啦等等,虽是“普通”艺术家,但他们很多的灵感和意境却都来自中华古典诗词,他们的古典文化学养颇为深厚。个中最成功的范例之一,我以为便是这首《在水一方》。特殊经一代歌后邓丽君的演绎后,更成为经典中的经典。以此为标志,邓丽君的歌冲破了中国旧式音乐的桎梏,大量地把传统的诗歌转化为当代盛行歌曲,形成了她特有的风格。可以说邓版《在水一方》首创了当代音乐的一个新时期。
诗歌之以是叫做诗歌,便是由于可以歌唱。可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我们忙于挣钱忙于当官忙于及时行乐——实在又不知道若何行乐,不知道怎么才叫快乐,磨骨头养肠子的动物性生存状态下,那份与生俱来的、能应和四季变换的载歌载舞的节奏感,消逝了;能感悟斗转星移、能与大自然相和起舞的道心禅味,消逝了;我们血脉中的那份诗情画意,那份音乐灵感,消逝了……我们虚度了时日,磨灭了灵感,写不来诗,唱不来歌,舞不了剑,悟不了道,乃至就连古人那些随处颂扬的名篇佳作,我们也茫茫然似是而非起来。
是邓丽君,唤醒了那些沉睡在故纸堆中的春花秋月,复活了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金戈铁马。我言重了?好,让我们循着她的歌声,看看她帮我们唤起了哪些古典文学影象,循着她的歌声穿越到唐宋先秦,再来诵读诵读那些嘉言警句,再与秦不雅观李煜苏东坡等来一场匆匆膝长谈吧——
(限于我的制作水平以及版权成分,恕我不能将这些歌的音频视频逐一添加到本文里来):
1、《多少很多多少愁》
邓丽君歌曲《多少很多多少愁》的歌词来自南唐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顾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多少很多多少愁?宛如彷佛一江春水向东流。
2、《独上西楼》
歌词来自南唐后主李煜的名诗《相见欢》——
《相见欢·李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别是一样平常滋味在心头。
3、《但愿人长久》
歌词来自宋代名贯古今的大文学家苏东坡——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上苍。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4、《有谁知我此时情》
这一首歌的歌词特殊,来自一个南宋名妓!
《鹧鸪天·聂胜琼》
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
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五程。
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
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5、《万叶千声》
歌词也特殊,来自北宋高官、大文豪欧阳修——
《玉春楼·欧阳修》
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悲惨多少闷。
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
夜深风竹敲愁韵,万叶千声皆是恨。
故倚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双烬。
6、《清夜悠悠》
歌词来自北宋文学家秦不雅观——
《桃源忆故人·秦不雅观》
玉楼深锁薄情种,清夜悠悠谁共?
羞见枕衾鸳凤,闷则和衣拥。
无端画角严城动,惊破一番新梦。
窗外月华霜重,听彻梅花弄。
7、《胭脂泪》
歌词来自南唐后主李煜——
《乌夜啼·李煜》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
自是人成长恨水长东。
8、《思君》
歌词来自北宋文豪李之仪——
《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9、《人约薄暮后》
歌词来自大宋朝大政治家、大文豪欧阳修——
《生查子·元夕》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薄暮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我能想起的已有9首,已经太多的啦!
可能还有吧?我不是所谓的君迷,可能没听完。但我猜想,说不定有些君迷没读完以上9首诗词吧?从这个意义上讲,喜好邓丽君还可以增长点古典文学教化,也是意外收成。
哦对了,最著名的一首咋能掉呢——
10、《在水一方》
源出《诗经·秦风·蒹葭》
三、邓丽君与《在水一方》:穿越高下五千年的似水年华
邓丽君演唱过许多古典诗歌,唯《在水一方》入耳便入心,直至沁人心脾;《在水一方》问世以来有很多个版本,唯邓丽君传唱得销魂蚀骨,直至成为绝唱。邓版《在水一方》,歌、曲、词完美结合,大概这就叫天作之合吧?!
前奏大气磅礴,由交响乐队担纲,主声部由钢琴演奏,用连续的八度和弦快速奏出十六分音符,像溘然拉开了“伊人”寓所的大幕,让我们瞬间看到了一个“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的佳人仙居那不食人间烟火的绝美场景,这场景与随之而来的悠扬婉转曲调形成光鲜比拟,从气贯长虹到婉转悠扬,从仙气环抱到无奈惆怅,旋律欲弱先强,感情欲迎还拒,比拟强烈,先声夺人。
前奏过后,柔和的曲调开场。邓丽君用诉说般的语气描述出一幅水边“绿草苍苍”、“白雾茫茫”的凄清画面,“绿草”、“白雾”用低位置唱出,用的是胸腔共鸣,声音由唇齿间发出,气息沉得很低,仿佛附耳呢喃,到后面的“苍苍”、“茫茫”则是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音域溘然升高,跳进发展,歌曲改以高位置演唱,鼻腔共鸣以及头腔共鸣明显,发声部位由纯挚的唇齿间到全体“面罩”,这样发出来的声音通亮通透。四句对仗的歌词,邓丽君用了比拟的处理方法,带我们走进芳草萋萋的如画梦境,恰到好处地塑造了诗经中描述的秋水伊人形象。
众所周知,邓丽君对气息的奥妙利用首创了一个音乐时期,以至于当年我们认为邓丽君的歌是“靡靡之音”。她的柔声轻诉就如耳畔的窃窃密语,温顺的气息吹得耳朵痒痒,让我们这些习气了大喊大叫的“大老粗”惊奇得无所适从。自卑之下,必欲除之而后快,当年本人省吃俭用买的一盘邓丽君磁带,就被学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收去了,现在想来,多可笑。大概这也是有历史缘故原由的吧?我们从满清灭亡到抗日救亡,再到文革,百多年来的颠沛流离死活挣扎,已经忘了亲切呢喃的柔声轻诉,我们的平时说话以及各种歌曲戏剧,不都是声嘶力竭从喉咙里喊口号么?是邓丽君,溘然带来了耳鬓厮磨般的浅吟低唱,由唇齿发音和鼻腔共鸣的温顺敦厚,气息发自丹田肺腑,甜美的歌声柔和悦耳,亲切动听,有如东风化雨。
平常生活中,我们采取的是自然式呼吸,这是种无意识的呼吸,气吸得少而浅。以是我们激动的时候,说一句长一点的话的时候,就会接不上气,因此会大喊大叫面红耳赤。邓丽君在演唱这首歌时,气息平稳柔和,她的一次呼吸每每能保持几十秒,如第一句“绿草苍苍”后面有一个气口,但第二句“白雾茫茫”唱完后便没有换气,而是在中间“白雾”后面鼻和口同用,偷偷地、深深地换了一口气,“茫茫”后没换气直接过渡到第三句“有位佳人”,那一口气已经气若游丝了,那一口气却是一气呵成,平滑如丝。对,平滑如丝!
这样的处理,瞬间把个“伊人”刻画得“肤如凝脂”般圣洁、崇高、柔美而楚楚可怜。
气息足,唱这首歌的颤音就灵巧自若。邓丽君的颤音在这首歌是一大特色。不是炫技,是为了使歌曲有颠簸感、起伏感。如“草”“雾”“人”“水”“滩”等等,三拍的永劫价音太多了,险些每一句都有涌现,险些每一小节的第四拍,那个三拍子的连音,都用了颤音,颤音的频繁利用,是这支歌“波浪起伏”的哀求,给人以水雾茫茫中,佳人梨花带雨、娇艳欲滴之感。
听她的歌,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浪漫情调,一种割舍不了的思古幽情。设想一下吧,兼葭露白、秋水澄明的水边,一位白衣公子追求无着的惆怅无奈,是多么让人……让人放不下!
伊人……伊人谓谁?《诗经关雎》中的窈窕淑女么?理查德克莱德曼琴声中《水边的阿狄丽娜》么?汉乐府中的罗敷么?
多年后再听此曲,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终于明白,所谓伊人,便是邓丽君,所谓伊人,宛在水中心!
唉,邓丽君已经仙去了。“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借用苏东坡的话——“纵使相逢应不识”。那沁人心脾的温婉,那莺啼婉转的呢喃,那吹气如兰的“气声”,早已随着吹佛千年的秦风汉雨远去,更随着邓丽君的仙去,成为绝响。秋风中兴伊人去,天地阔远随风扬。
四、又是一年秋风起,又是一湾芦花白:多姿多彩的《在水一方》翻唱
在听过不少应景的、无病呻吟的、华美富丽的歌曲后,另一首《在水一方》,以空灵、文雅、脱俗的气质吸引了我。前奏由飘渺的长笛声开始,钢琴轻声伴奏,一下子就塑造了一个迷离的梦幻意境。这一清澈温润的前奏与邓丽君版的气势磅礴截然不同,于是吸引我听了下去。
这是李健翻唱的《在水一方》。新颖的配器,十分空濛的前奏,为全曲定下了更为幽怨、悠远、悠扬的基调,也更有画面感。你听他第一句,第一句由飘渺的长笛声开始,钢琴轻声伴奏,一反邓丽君版的气势磅礴,这觉得是不是很新颖、清澈?开口的“绿草”“白雾”,不似邓丽君那么一字一顿的清楚,而是柔柔地一带而过,如梦如烟的缥缈觉得瞬间涌现。接下来的演唱中,强弱比拟很大,连音滑音特殊多。比方“有位佳人”中的“位”;“道路又远又长”中的“远”,李健的处理不仅仅是单一强弱处理,而是强后即弱,强音开口,迅速弱收,这样的处理,有“渐行渐远渐无声”的效果。
他的唱腔后鼻音明显,有一种金属的清脆加陶瓷的质感,时而如清泉,清冽通亮;时而像星空,寂辽宽阔。比如“苍苍”“茫茫”“一方”等字,以及过门的“啦”,声音清脆,气息沉稳,随着音域逐渐升高,声音平稳向上、向远,声线和曲调水乳交融,合二为一。
尤其出彩的是歌曲中间的经由段。这段改编自电影《叶塞尼亚》主题曲的过渡,本身便是描写爱情的,浪漫而唯美,李健的哼唱与该电影的浪漫主义色彩完美契合,使音乐更浪漫、更华美、更丰满。两首曲子的旋律结合在一起,时空穿越,中西交错,让人不知今夕何夕!
钢琴和小提琴应时地、比较虔诚于原作的激情加入,更使这段间奏有了一种壮阔之美!
什么叫创新?什么叫推陈出新?有人或许还在那里批评叽讽人家乱弹琴瞎胡闹吧?我却要为这一段间奏年夜声喝采,拍案叫妙!
什么叫站在古人肩膀上?什么叫中西合璧?什么叫更上层楼?什么叫思接千载神游物外视通万里?这便是!
当然另一个版本,姜创的钢琴《在水一方》也是在中间经由段加入了《叶塞尼亚》,谁启示了谁我不知道,我只是对这一改骗,十分欣赏!
哼唱结束时,三声定音鼓响,钢琴变得铿锵有力,小提琴华美汇入,音乐形象瞬间激情壮阔起来,仿佛缥缈宁静的清泉瞬间波涛彭湃起来。“我~~愿逆流而上()”,一个拉长了的“我”,一个调高了的“上”,这位公子真的是“逆流而上”了呀!
冲动大方的伴奏,合唱的应时加入,配器和人声变得非常饱满,将整首歌拉向一个高潮。
结尾两句的浅吟低唱,更突显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种东方蕴藉幽远的意境之美。结尾 “一方”两字更是惊艳,清脆、空灵,如同一根银针射向晴空,在空中渐行渐远渐无声。伊人远逝,雪泥鸿爪,长空秋雁,风过无痕……
不知是不是受了这一启示,另一位美女歌手龚爽,她演唱的《在水一方》,在中间经由段也加入了泰西歌剧——普契尼《蝴蝶夫人》的旋律,给这支清丽脱俗的、民族味十足的歌曲增长了一抹华美的贵族气、洋气、阳气。这段高亮婉转的女高音,干净、纯粹、悠远,实在,在歌曲的引子部分及前段的伴奏中已经不着痕迹地融入了歌剧影子,丰富了歌曲感情内涵,也使《蝴蝶夫人》融入得自然而然。她居然敢这么加?这要多么丰富而浪漫的,并且是大胆的遐想啊!
这段美声的加入,使一支歌内利用了民族、美声、普通三种唱法,却又自然流畅,大气伸展,宽厚华美。只是不知这样的灵感和胆量,是怎么来的呀?
比较邓丽君版本的江南女子般的婉约,这般演绎更有天马行空般的洒脱。看来,创新便是生命力,创新,才是真正的继续和弘扬!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江山代有秀士出,伊人,已经换为敢作敢为的年青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