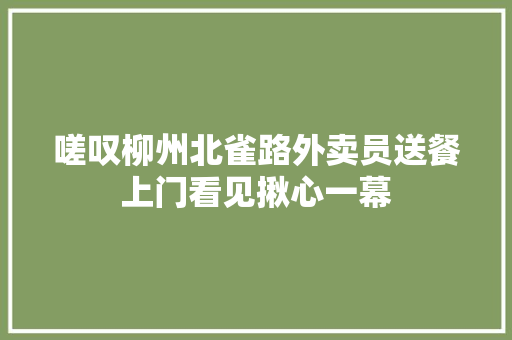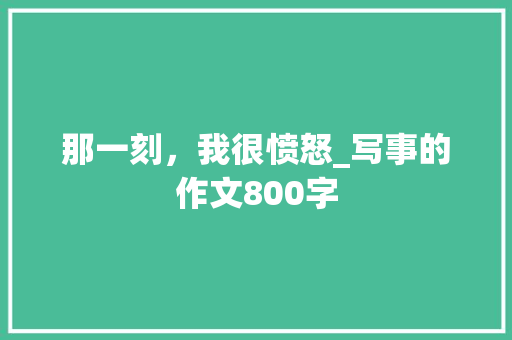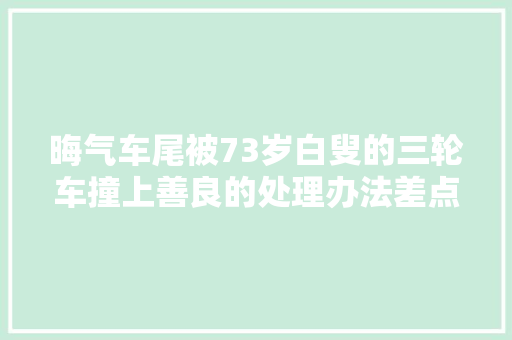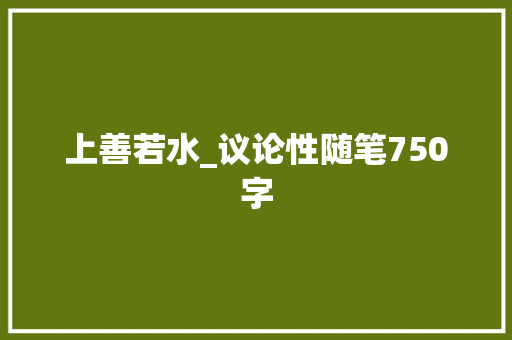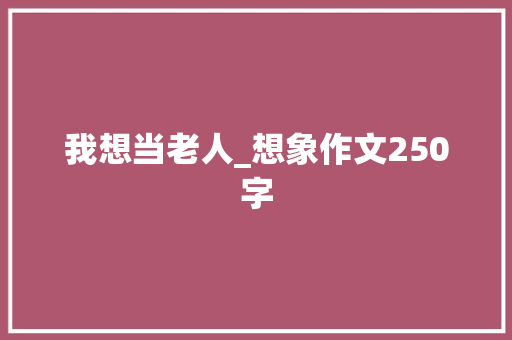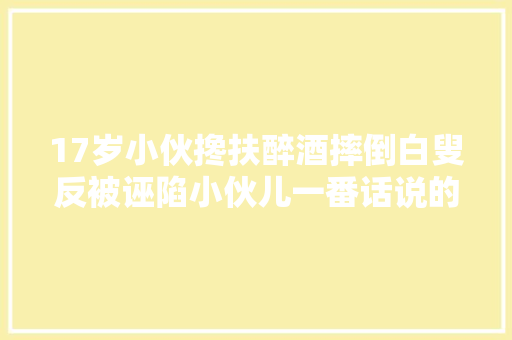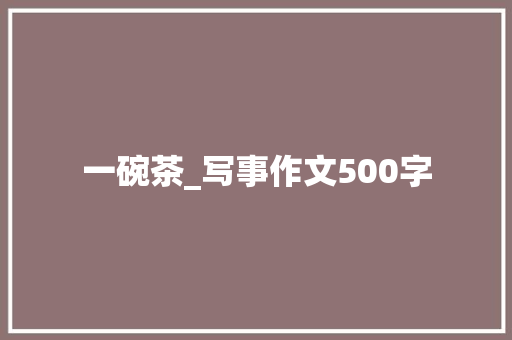5月5日,导演郭柯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组韦绍兰老人的照片。她是郭柯导演的记录短片《三十二》中的主人公,以及记录长片《二十二》中的出镜者之一。随着韦绍兰老人的去世,《二十二》中的老人仅剩5人。
《二十二》出镜老人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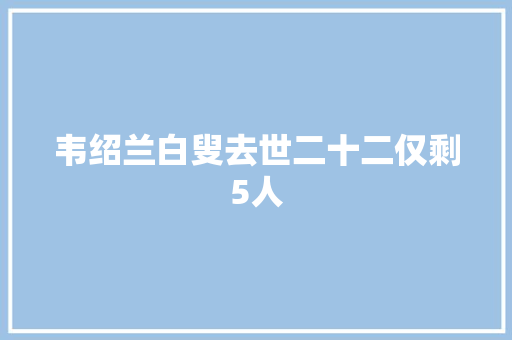
饱经沧桑仍认为天下真好
“慰安妇”这个词意味着苦难的历史,意味着阴郁与绝望,乃至有人会遐想到“耻辱”二字,可是在导演郭柯眼中,“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们是可敬可爱的祖辈,她们经受了凡人弗成思议的折磨之后,仍旧可以微笑着说“这天下真好”。
中国首部关于“慰安妇”的记录片电影《二十二》于2017年8月14日上映,这部之前没有人看好的电影票房打破1.5亿,一度创造了国产记录片的最高票房。导演郭柯拍摄这部电影,缘起便是韦绍兰老人,由于在《二十二》之前,他先拍了短片《三十二》。
2012年的一则宣布改变了80后导演郭柯的人生轨迹,做了十几年副导演的他有光阴看到一篇先容“慰安妇”韦绍兰老人的文章《一个慰安妇生下的日本孩子》,故事讲述了1944年,韦绍兰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3个月后困难逃离慰安所。逃出来后创造自己已经怀有身孕,当时她曾服药自尽但没去世成。如今韦绍兰老人的儿子罗善学已70多岁,母子俩相依为命,罗善学生平未婚,由于没有女人乐意嫁给他,“‘妹子’的家人不许可她们嫁给日本人。”
在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苏智良教授的帮助下,郭柯顺利地找到了韦绍兰老人,拍摄了记录短片《三十二》,该片在豆瓣评分高达9.4分。这位耄耋老人的笑颜、泪水、歌声打动了无数不雅观众,很多人情难自已,看的时候泪流满面。老人虽然生平饱经沧桑,会抹着眼泪说:“天高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闷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但她也会笑着说:“这天下真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导演最初拍摄想“打捞历史”
后来不忍再触碰细节
随着理解的深入,郭柯对“慰安妇”的态度从“猎奇”转变为“深情瞩目”。刚打仗这个题材时,郭柯说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想“打捞历史”,想让她们痛说悲惨,“幸好我末了良心创造”。
问郭柯在拍摄时是否会感情失落控,他说:“作为三十多岁的男性,我感情失落控的时候很少”,但还是有一次失落控了,而这次失落控也改变了他的创作态度。2012年拍《三十二》时,自己没履历,不考虑对方感想熏染,在韦绍兰老人说到痛楚处,比他年长五岁、更端庄的拍照师缄默关了机器,可是他却催着翻译连续为他阐明老人的话,让拍照师把机器打开,“我那时真是暴露出了妖怪的一壁。”
拍完之后,郭柯说自己背过身客岁夜哭了一场,“我想为什么我是这样的人?老人这么信赖我,为什么我要让她回顾那些让她那么痛楚的事情?就为了镜头须要的那种表现力?这样去对一个老人,我这样还像个人吗?”拍照师轻轻拍了拍大哭的郭柯,郭柯说:“他懂我,我以为自己不应该这样,不道德,从此,我再也没有这样主动地去问过她们那时的细节、感想熏染。”
不愿为电影好看而设计情节
如今片中主人公仅剩5人
韦绍兰上坟时痛哭的片段终极没有被郭柯剪到片中,而在2014年再拍《二十二》时,整部影片只剩下温和平淡,于是,“导演手腕有问题”“技巧不足”“剧情平淡、缺少冲突”等等批评之声充斥在郭柯的耳中,郭柯无奈之余却有自己的坚持,“都是普通人,作为导演,我听到这些自然心里也不舒畅,但是这些批评现在也不主要了,我便是要温和地对待她们。作为导演,我当然可以改变拍摄手腕,拍摄时丰富她们的生活,让她们活动活动,扫扫地,而不总是暮气沉沉地在椅子上坐着,老人就像小孩,她们跟你熟了后会听你的话,你可以勾引她们做你镜头里想呈现的事,可是有没有必要呢?”
郭柯坦承自己纠结了良久,要不要去刻意地设计“情节”,让电影更加跌宕好看,“这是个跟自己较劲的过程,后来我创造老人越不说,对付导演来说,这个故事就越难去讲述,而如何把这种难度利用导演手腕办理,这才是导演该当做的。”
改变了自己的心态后,郭柯不再那么“功利”了,“以前目的性很强,比如说跟老人两天混熟后,想着第三天就开始拍,可是想通之后就统统自然,每天就像玩一样,陪着她们,电影是否无聊对我来说不再主要,主要的是,在我心里,装载着与她们每天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
2012年郭柯开始打仗“慰安妇”题材时,中海内地公开身份的幸存者仅存32位,2014年人数减少到了22位,故影片片名设为《二十二》。2017年7月,影片中22位幸存者只剩9位了,而随着韦绍兰等老人的去世,如今这个数字减少至5位。( 肖扬 统筹/满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