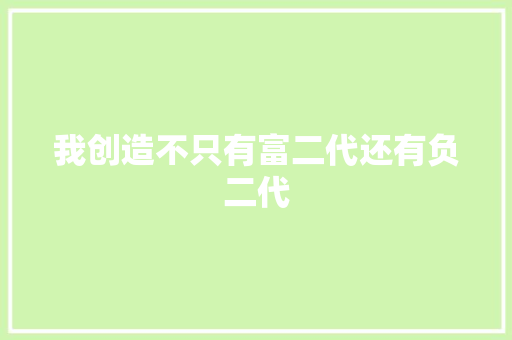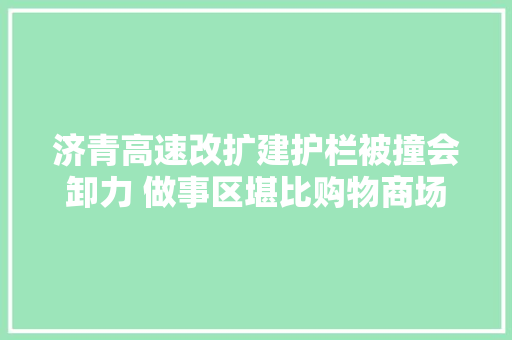一个爱情故事,很干脆,也很绸缪。
看上去像诱骗,但的确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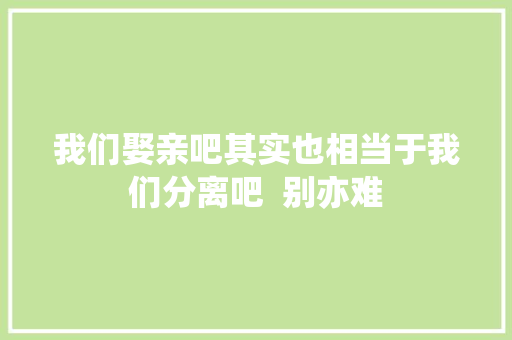
北方的沿海城市,大约是春天快过去的时候,小区里的月季都开了。
月季的品种不同,在傍晚散发出层层叠叠的花喷鼻香。夜色里看不清花,嗅觉却让人沉浸花海。
这里就连树也粗壮高大。看上去比小区的年纪大很多。
这么大的树,是从哪儿来的呢?
一棵已经长成的大树,为了装点陌生城市里的住宅,一样要背井离乡。
月季呢,月季不一样。
都说月季俊秀,惜乎难养,但这里不同。
月季是在这里出生的。
月季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在它们原来就该当在的地方,它们彷佛不须要被精心地栽培侍弄,只要插一支在地上,松松土,浇浇水,就能回馈百媚千娇。
小区的四周是高楼,中心是一片仿苏式的园林。虽然仿得不像,但也风雅奥妙,文雅可喜。入夜之后,太湖石和白墙花窗隐入夜色,园林小径上的路灯在脚下亮起来,给闲步的人指出一条路。
闲步的时候顾晓云收到一条。
顾晓云盯着那一条看了一下子,出了入迷。
对话框的记录里,上一条是两天之前。一张图片表情,没有详细的内容。是一种淡淡的无聊,没有话也找不出话来。
这种状况有多久了?有许家祯是一天,没许家祯也是一天。关系到了这种时候,不分离就必须要结婚,不结婚就必须要分离。
以是许家祯发来的或许也可以这样看:晓云,我们分离吧。
不知道怎么回答。结婚可以答应他,分离也可以答应他。
顾晓云把手机揣进兜里上楼,开门一瞬知道室友不在。
同一个地段,这个小区租金最贵,对付年轻租户来说性价比低,因此合租的屋子少。同样是两室一厅中的一间,顾晓云现在住的这间要比隔壁小区的单间贵六七百元。一年下来多花将近一万。但是最初顾晓云选择这一间,看了就付下房租和押金,没有犹豫。
相隔一条四车道的马路,这里是城市中物业费不菲的高等住宅区,对面是纺织厂在八十年代末时候起的几座老屋子。最早的时候顾晓云去看马路对面的屋子,选中老屋子最整洁的顶楼,且由于没有电梯而价格公道。她不怕多上楼梯,险些就要决定住下,福至心灵去厨房开了碗柜,瞥见几只蟑螂受到惊吓一样窸窸窣窣地躲起来。
顾晓云长到二十多岁没见过那么多蟑螂。
后来就选择了这一边。
封闭式管理的小区,院子里有花园。实木地板,客厅亮堂,卧房宽敞。代价不大不小:房租从一个月人为的“不到一半”变成“刚好超过一半”。
室友便是二房东,本地人,年纪与她差不多,像是在机关单位上班。家住得间隔单位太远,租一间房只为了上班方便,周一到周五有个睡觉的地方。
女孩起得早,洗漱也早,平常不该用厨房,顾晓云险些不怎么能见到她。偶尔在客厅相遇的时候,她们打个呼唤。每次都是女孩先开口,她说:“嗨。”
顾晓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呼唤。它的音调显然高于平常说话,迅速中带着一点急迫,彷佛在两人之中她必须抢先。常日如果有人这样与你打呼唤,就代表她只想与你打个呼唤,并期待你不要再和她说别的话。
很早就创造了这一点,于是也只管即便避免与室友碰面,免得“嗨”之后的尴尬。于是客厅三十多平米永久是空的,L型长条布艺沙发没有人坐。
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门锁“咔哒”一声。
心里乱糟糟的时候,她不愿意开灯。安全环境里的阴郁会让人以为更安全,安全之外还有宁静。
借着窗外的灯光能看清房间里的统统。房间不大,放下一张双人床,一个挂衣架和一副桌椅之后还能容人走动几步,乃至显得空旷。看屋子的时候室友看上去和气又热络,说房间虽然不大,但是客厅很大,公共空间宽敞。住进来之后又是另一番景象。
有时候她以为,合租因其“临时”,便有了各类可以暂且忍受的“常情”。
衣架是宜家最大略的一款,挂当季常穿的几套衣服,交往返回穿,余下的衣服都叠好放在大的收纳箱里,收纳箱跟行李箱一起推在床底下。溘然暖和起来便是前两天的事,衣架上挂的还是羊绒衫和大衣,与冬天时候一样。
与前年深秋,附近冬季,她来这里住下的第一个夜晚,千篇一律。
大门有钥匙旋转声响,接着是脚步声,隔壁开门声,隔壁关门声。声音极近又极远,热闹一阵,归于沉寂。不久手机屏幕在阴郁里亮起,是许家桢的语音通话。
想要接起来,但没接,拧开房门走过客厅,再坐电梯下楼去。
按电梯的时候第一个由于超时挂断,许家桢打来第二个,她心焦,又猛按了几下电梯按键。
走回花园的时候许家桢的电话打到第五个。她终于接起来,不说话。
还是许家桢先开口:“晓云。”
她说:“嗯。”
许家桢:“给你发的,你瞥见了吗?”
她说:“嗯。”
许家桢:“你是不是……还在公司?未便利说话吗?”
她说:“嗯。”
许家桢:“哦……这样……那你先忙。”
她说:“嗯。”
许家桢说:“晓云,我想你了。”
她说:“嗯。”
电话另一头的许家桢像是愣了一下子,终于说,“我晚点再给你打。”
她说,嗯。
夜色与雾气一道在花园里弥漫,雾气中的花喷鼻香平白像是揶揄。
冬天的时候蒙起被子在被窝里跟他说话,是上大学时候习气的延续。冬天之外的时候,他们的谈天都在夜色中的花园里。由于相隔两地,这样会让她以为他在同她一道闲步。之后就逐渐习气了在花园里等他的电话。再后来电话并非时时会来,只有她日日在夜晚的花园里走。
再后来便是本日,他溘然给她发说,“我们结婚吧”。
顾晓云溘然动了动机搬家,因她不想再瞥见这个花园。
按电梯上楼,出电梯门拐回家的时候愣在门口。门洞开,通亮刺眼的灯光从房间内洒出来照亮楼道。房间中模糊传来轻缓的爵士音乐。地板——
住处地板是原木色的复合地板,而这里的地板是深胡桃木的颜色。
她转身要走,劈面迎上背着一只冰箱向她走来的装卸工。
楼梯间走廊狭窄,而那只装在纸板箱里的冰箱显然是双开门的,她贴着墙也没法给装卸工让出一条路。只能是工人向前一步,她退却撤退一步,一步一步退进铺着深色胡桃木地板的客厅里。
客厅空荡荡,险些没有家具。四顾还没看到人,听见“哧”的一声笑。
顾晓云循声转身,瞥见林白。
厨房是开放式的,与客厅相隔的地方是一个吧台。林白穿着一件白T恤,站在吧台后面向她举杯:“来喝一杯?”
“我彷佛按错楼层了。”顾晓云说。
“你住几楼?这里是11。”
“18。”
林白摇摇头,“怪我,是我刚才按了电梯。搬冰箱的师傅好久没上来,我想下去看看怎么回事。刚按了电梯,就听他说已经停车了。”
顾晓云:“这样。”
林白:“我刚搬来。往后便是邻居——你不饮酒?”
竟然不太想推辞。彷佛本日这种时候该当饮酒。
顾晓云点点头。
“喝什么?”林白问她。
“随便。”顾晓云说。
“那就喝这个。”林白从身旁拿过一只酒瓶子,又拿过一只郁金喷鼻香杯,“不随便的话,也喝这个——只有这个。”
顾晓云笑笑。
“要加冰吗?”林白问她。
顾晓云摇摇头。
林白又笑,“没创造吗?这里也没有冰。”
——冰箱乃至还没拆封。
酒倒了小半杯,林白又问她,“酒里要不要加水?”
顾晓云愣一愣,像是没太明白这个问题,想了一下子说,“不用。”
“实在水还是有的。”林白从地上提起一瓶斐济。
“不用了,酒里加水,总觉得……有点奇怪。”
林白看着她,眼睛里有淡淡笑意,点点头。
顾晓云啜了一口酒。
很浓郁的味道,是烈酒。她举起杯子,重新在心中衡量这小半杯酒的分量。
“你平常是不是不太饮酒?”林白问她。
“不怎么喝。”顾晓云说,看着杯中琥珀色的液体。
林白理解地点点头,“我知道,看得出来。”
顾晓云:“有时候……喝点那种甜味的酒。便是他们说的,‘小糖水’。”
林白:“冰一冰,配火锅。”
顾晓云的眼睛彷佛亮一亮,“对。”
林白:“没怎么喝过威士忌?”
顾晓云摇摇头,“原来这便是威士忌。”
林白:“威士忌也能调咖啡。”
顾晓云失落笑,“那喝下去是什么觉得?”
林白向她举杯:“你这样说,值得庆祝。”
顾晓云:“庆祝什么?”
林白:“庆祝你的人生没有涌现须要威士忌加咖啡办理的问题。”
顾晓云:“须要威士忌加咖啡办理的——是什么问题?”
林白:“很难办理的问题。”
顾晓云:“那须要威士忌办理的问题呢?”
林白摇摇头,“威士忌办理不了任何问题。”
顾晓云:“但能办理自己。”
林白又笑,“完备对。”
顾晓云又啜了一口杯子里的酒。
林白问她,“真的不加水?”
顾晓云犹豫。
林白:“威士忌的一种喝法,便是往酒里加水。”
顾晓云:“那么加。”
矿泉水瓶子拧开,水顺着杯沿流动,泛出剔透宁静的光泽与酒相融。
林白把杯子推回顾晓云面前,“试试看。”
酒兑上水,竟然真的比不兑水更好喝。饮酒的时候,两个人说话。
顾晓云:“你常常饮酒?”
林白摇摇头,“我也很少喝。”
顾晓云摇头,“你看上去常常饮酒。”
林白:“为什么?”
顾晓云:“你倒酒的样子。”
林白:“倒酒是我事情的一部分。我开酒吧——开过。”
顾晓云:“开过?”
林白:“开到本日——昨天。”
顾晓云:“为什么不连续开下去?”
林白:“没钱。”
顾晓云抬开始,眯起眼睛看林白。她的双眼皮不明显,眼睛不算大,但眼珠很深。
林白被看得险些不清闲:“怎么了,以为我撒谎话。”
顾晓云:“你看上去不像缺钱。”
林白:“开酒吧总是要赢利的。没赢利,也不好连续赔,就关了。”
顾晓云:“你看上去也不怎么想赢利。”
林白:“你是平常就这么说话,还是喝了酒才这么说话?”
顾晓云愣一愣,“怎么说话?”
林白:“像一根探针那样说话。”
顾晓云没回答。
林白看着顾晓云的羽觞。
良久之后顾晓云问他:“开酒吧的时候,你快乐烦懑活?”
林白:“谈不上快乐或者烦懑活。由于——”
顾晓云的手机亮起来。语音通话,来自许家桢。
顾晓云看着闪烁的手机屏幕。
林白:“男朋友?”
顾晓云不响。
林白:“接吗?”
顾晓云点头。
电话接起来,林白看着顾晓云。
顾晓云的影子倒映在玄色的吧台桌面上。
许家桢:“忙完了吗?”
顾晓云:“嗯。”
许家桢:“到家了吗?”
顾晓云:“嗯。”
许家桢:“……晓云,你……你说句话。”
顾晓云缄默。
许家桢:“是不是……你不愿意?”
顾晓云:“以为不是时候。”
许家桢:“不是时候?”
顾晓云:“嗯。”
许家桢:“晓云,我可以等。”
顾晓云:“不是等的事。”
许家桢:“你知道的,我一贯在为结婚做准备。”
顾晓云:“我知道。”
许家桢:“以是——”
顾晓云:“我还没准备好。”
许家桢的笑声中彷佛有些释然,“以是——”
顾晓云:“——我不想做准备。”
许家桢缄默。
顾晓云听见电话另一头许家桢的叹气:“晓云你知道吗,在我心里,你确实——你确实便是一片云彩。飘飘悠悠的。形状不一定,在哪儿也不一定。本日在这儿,来日诰日在那儿。后天……你可能变成雨。然后再变回云彩。”
顾晓云轻轻笑。加了水的威士忌味道清雅,很随意马虎入喉。
林白坐在她身边,看她举着电话,喝完第一杯,自己学着他的样子如法炮制,调了第二杯。
许家祯:“可我是一块石头。我是确定的。我的读书,上学,专业,事情,都也须要是确定的。只有确定才能让我安心。”
顾晓云:“我明白。”
许家桢:“以是……”
顾晓云:“或许是我错了。就这样吧。”
许家桢:“……是分离吗?”
顾晓云:“是。”
电话另一头,许家桢彷佛哭了。
顾晓云听着电话另一头压抑的抽咽,逐步喝第二杯酒。
许家桢:“晓云,祝你好。”
顾晓云:“也祝你好。”
放下电话,第二杯酒也喝完。
林白看着顾晓云:“不是故意想听,但——”
顾晓云:“没紧要。”
林白:“是分离?”
顾晓云:“是分离。”
林白:“你平常酒量有这么好?”
顾晓云摇摇头,“没有。刚才我们说到哪儿?说到——”
林白:“快乐。”
顾晓云:“对,快乐。”
林白:“接着聊这个?”
顾晓云:“嗯。”
林白失落笑,“这么沉着的分离?”
顾晓云:“他有别人了。”
林白:“你一贯知道?”
顾晓云摇摇头,“觉得——但常日准。”
林白点点头,“开酒吧……谈不上快乐,也谈不上烦懑活。找件事情做,做不下去就算了。”
顾晓云:“你是富二代。”
林白愣一愣,答得诚笃:“可能算不上。”
顾晓云点点头,“那便是了。至少家里不须要你做什么。”
林白又笑,但这一次笑的意味有些繁芜:“也不是。”
顾晓云不追问。
然而听完面古人的分离电话,如不评论辩论一些自己,总显得什么地方失落了礼。
林白环视空房间,“这屋子我原来租出去。酒吧开了不到三年,这屋子租了……五年吧?这人是做生意的,我一次都没见过。租金半年付,他呢,一开始交租金还蛮及时的。前年的时候说年景不好,问我能不能把半年付改成月付,我以为好商量。到今年过年的时候,月付他也良久没交。我仔细一查,创造有半年多。我想催他,结果——结果我也抹不开面子,就给他发了条短信,没说别的,只问他房租什么时候交。”
顾晓云:“他回了吗?”
林白:“他回我一个电话。他跟我说,他经济状况不好,人已经搬走了。至于拖欠的房租刚好可以用押金付。”
顾晓云:“够吗?”
林白:“实在还差两个月。”
顾晓云:“但你决定算了。”
林白:“不然怎么办?他都说了他没钱。”
顾晓云笑,摇摇头。
“之后我自己店里不好,我也没心情回来看看。到上个月,总算下决心,要把店关了。开店的时候我在酒吧楼上租了屋子。酒吧不开,我租的屋子也就退了。这套屋子又空,刚好搬回来住。谁知道——”林白说着,竟然笑了。
顾晓云:“你笑什么?”
林白:“这屋子我父母从前自己住过,家具都是完好的。上个月我回来,一推门吓了一跳。”
顾晓云:“空房子。”
林白:“对,便是你看到的这样。空房子。也不知道这人的经济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把家具都卖了——倒是还给我留了张床。”
顾晓云:“你彷佛该当报警。”
林白:“他都那样了,算了。”
顾晓云:“你心肠软。”
林白:“我怕麻烦。”
顾晓云:“怕麻烦,怎么赢利?”
林白摆摆手,“以是不赚了,不给别人添麻烦。”
顾晓云:“别人。父母,也是别人?”
“不是父母。”林白顿一顿,“我弟弟。”
“弟弟?你年纪也不大。”
“我二十八,我弟弟比我小四岁。”
像是有话可以连续说,林白没有说下去。
夜深了,该当是告辞的时候。顾晓云坐在吧台凳上,彷佛没故意思要走。
林白也看她。看她白皮肤里透出一点粉红,睫毛长,玄色的眼睛折射灯光。
“你叫什么名字?”她看着他,溘然问。
“林白。”
“我叫顾晓云。”
林白点点头。
“知道名字好一些。”顾晓云说。
“好过不知道。”
一整夜两人未曾说话。
天亮的时候他忽然问她:“你这算不算……对你男朋友的报复?”
“前男友。”
“好,前男友。你饿不饿?我下去买点吃的。”
她说好。
林白提回来许多麦当劳的纸袋子。粥,油条,薯饼,麦满分,豆浆,咖啡。一样一样打开排在吧台桌上。
林白说,“不知道你想吃什么。你先挑,挑剩的给我。”
顾晓云缄默。林白买回与许家桢一样的东西,说出与许家桢一样的话。
林白:“你怎么了?你看上去神色不好看。”
顾晓云:“以前许家桢也是这样。”
林白:“许家桢,你——前男友。”
顾晓云:“上一次也是麦当劳的早餐。他来看我,就住在这里。以是我想该当是——同一家。”
林白:“明白了。那不吃这个,我们去吃别的。”
顾晓云摇头,拿起麦满分,“不用。麦当劳无辜,不能迁怒它。”
林白笑着开粥,“你心肠硬。”
顾晓云:“怎么说?”
林白:“触景不生情。”
顾晓云叹气,“我只有过一个男朋友。”
林白的手停一停。
顾晓云:“我曾经以为,总是说‘你先挑’的人,很宝贵。”
“不是的。”林白说。
顾晓云:“以是什么宝贵?”
林白怔一怔。
顾晓云:“我和许家桢,大学的时候开始的。他比我大一届。”
林白看着顾晓云眼睛里有水光闪闪烁烁。像是前一夜喝下去的酒,到此时才带来醉意。
顾晓云:“他学打算机。毕业的时候,他在上海找到事情。事情……挺好的。应届就有十几万的事情少。他家里没那么好,有这样一份事情,往后都不一样。”
林白:“你跟他去了上海。”
顾晓云点头。
顾晓云:“那个时候我们租了一个开间。屋子不大,但什么都有。地方偏一点,我上班近,他上班远。他有时候加班到十二点,回来就一点多。那时候我都睡了。第二天早上我醒的时候,他又走了。”
林白:“很辛劳。”
顾晓云:“那个时候不以为。总以为什么都是暂时的,往后总会好。大概过了一年,他就被调到了这儿。”
林白:“你又跟了过来。”
顾晓云摇头,“不是立时。我学文,毕业在出版社上班。这边对口的事情少。”
林白:“也是。”
顾晓云:“他调过来之后,我也逐步找这边的事情。找了半年多,只有家广告公司勉强以为凑合。”
林白:“你为了他来。”
顾晓云点头,“为了他。从上海走的时候我扔了很多东西。衣服,摆件,小家具。扔的时候特殊难过。由于……可能刚毕业之后第一次吧,和他一起住,把住的地方当家。”
林白:“没想过后来。”
顾晓云:“没想过后来居无定所。现在我已经不会轻易添置什么。”
林白:“之后你和他,就住在这儿?”
顾晓云:“当然不是这儿。在高新区。”
林白:“这么远。你事情的地方呢?”
顾晓云:“就在这儿,隔壁街。”
林白叹气。
顾晓云:“反正没住到半年。”
林白:“他又调走了?”
顾晓云笑,“这次是深圳。”
林白点头。
顾晓云:“我追不动了。”
林白没说话。
一下子想起许家桢的许多好。
顾晓云没去过深圳。条件许可的时候,许家祯见缝插针回来看她。
周五不加班的话,买最晚一班机票。落地是凌晨,到家的时候天快亮了。周六周日在一起也做不了什么。奔波劳累,还要见缝插针地处理事情。看展,逛街,看电影,最多选择一样,足够精疲力竭。
周日晚上再坐最晚一班飞机走。但是由于要去机场,两个人乃至不能在一起吃一顿晚饭。
跨年的那一夜,傍晚时候,顾晓云送许家桢下楼。
北方冬季薄暮灰沉沉的冷风里,许家桢推着行李箱子,顾晓云裹着旧羽绒服和旧围巾跑在前面,在小区门口替他拦出租汽车。
出租车停下。顾晓云替他开后备箱门,对司机说,“去机场。”
许家桢却站住了。
他抬手把后备箱扣上,放走司机,对顾晓云说,他不走了。要走也是等来日诰日。
公司出息无量,但同样纪律严明,员工没有请假自由,旷工更加任务重大。
顾晓云说,这样行吗?
许家桢说,他不能让她一个人过新年。
那天晚上许家桢穿着单衣单裤,套一件轻薄羽绒服,原来是为了在深圳落地的时候脱起来方便。而顾晓云一身衣服都是旧的,旧得颜色都模糊暧昧。
两个人就这样推着一只行李箱,去吃了一顿很贵的跨年夜大西餐。
许家桢对她的宽忍也是细细碎碎的。她不喜好抖脚,几年间许家祯一点一点改掉了这个毛病。她轻微有点洁癖,衣服最多穿两次就要进洗衣机,这逐渐也变成许家祯的纪律。
是她哀求许家桢,许家桢对她没有哀求。
“有别人……就有别人吧。是我亏欠他。”顾晓云说。
林白的表情有一瞬间不清闲,又迅速规复如常。像是不肯望顾晓云看出来。
顾晓云还是看出来。
“你想到什么?”顾晓云问。
林白:“在想你对自己的评价或许太严格。”
顾晓云:“为什么这么说?”
林白:“我不知道全部的事。但我总以为……怎么说好呢,毕业之后,你一贯随着他走?”
顾晓云想了一想,点了点头。
林白:“你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方案吗?或者说,你考虑的时候,都把他的事放在前面?”
顾晓云:“他那个事情确实难得,不好放弃。他家里压力挺大的,钱要紧。”
林白:“你呢?”
顾晓云:“我家里没什么压力。事情么……都差不多。”
林白:“不会差不多。”
也是的。如果从来没有许家桢,她怎么会以为“差不多”?
不是刚刚才明白的事,是转念就明白的事。
比较恍然大悟,人有时只须要停滞视而不见。
停滞对自己的妥协视而不见。
顾晓云的手机忽然震撼,是闹钟。每天早上,顾晓云被闹钟叫醒去上班。
闹钟的名字就叫“去公司”。
顾晓云把闹钟按掉。
林白:“去上班?”
顾晓云:“去辞职。”
交卸工浸染了半个月,同时关照室友要搬离的。
室友错愕,进而有点沮丧,像是溘然觉出她作为一个合租伙伴的无害,不愿面对要去挑选一个新的合租者的事实。
尘埃落定的那天,林白抱着一束花在写字楼下面欢迎她,对她说,“恭喜你开始新生活。”
之后林白帮她搬家。
不必考虑通勤之后,她把住处选在靠近海边的安谧街区,气氛宁静安闲,间隔原来住的地方颇远。那段韶光顾晓云开始接一些商业稿件和策划案。大同小异的事情越做越快,收入竟然比上班的时候还多一些。她的心里没有太多高兴,知道这样的日子不会很长。
但轻盈的觉得前所未有。
三个月之后,她辗转知道许家桢结婚的。新娘是比她更小一届的大学学妹,大家上学的时候就认识,眼下事情的地方与许家桢相邻。同样是大公司,薪资稳定,欣欣向荣。
答案揭开,统统有迹可循。
以为自己会难过,但实在没有。最浓稠的过去在她不知晓的时候早已悄然脱落,当她做决定的时候,丧失落的只是一层空壳。
实在林白也发起过,不必其余找地方住,只须要搬下楼。与他同住,没有开销。
她以为欠妥,林白就不再坚持。
对顾晓云来说,林白是什么,对林白来说,顾晓云是什么,谁都没问过,谁都不说破。
偶尔跟林白相约去很远的地方闲步。城市边缘的盐滩苇荡荒无人烟,像天涯海角。林白开车,车是一辆银灰色的老丰田,碰着颠簸的时候,顾晓云险些从副驾驶座上飞起来。
林白偏过分,看她一笑,“来日诰日换一辆车。”
顾晓云扶着车窗上的把手,“也不用。”
林白笑,“不是你说的吗?我是富二代。富二代家里,不该有的是好车?”
顾晓云以为林白的语气像是自嘲。
深秋的时候他们住在山中的民宿。
从山中回城,途经林白的住处。
“要不要上来看看?”林白问她。
搬走之后,很长一段韶光不愿意回到这儿。没再去过林白那儿,没再来过这附近,乃至有几次险些是可以绕道而行。
如今竟以为也没什么。
在车库碰着从前的室友。打了呼唤,又一起进了电梯。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么久,顾晓云没把稳过这女孩的心眼竟然是直的。她高下打量自己,又高下打量林白,不睬解隐蔽眼睛里的困惑与窥伺。
站在门口,要进门的时候忽然听见房间里有音乐的声音。
林白说,“林星来了。”
顾晓云:“林星是谁?”
林白:“我弟弟。”
推开门,房间陈设一应俱全,不再是空房子。屋子里烟雾环抱,林星叠着腿坐在沙发上。
看不出年纪的少年人,相称漂亮,深秋仍旧穿短裤,油头,山羊胡,劳力士腕表,卡地亚项链,从头到脚不重样的LOGO印花和喷鼻香水味比音箱里的音乐鼓噪一百倍。
听见开门的声音,林星仰起脸看林白,又看顾晓云。腰急速挺直,咧嘴一笑。
顾晓云于是看林白。
林白说:“干什么?”
林星哂然,“带女人回家,老蚌生珠,铁树着花。”
林白说:“我问你来干什么?”
林星叹气,“来看看你。”
林白推开房间里的每一扇窗散掉烟味:“我看你是来熏屋子。”
林星站起身,“得啦,我不在这里招讨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声音抑扬。
林白说:“知道了,快走吧。”
林星走到门口,又转过身看着林白,挺着身子,全体人向后仰,用手比划刷卡的动作,用下巴指顾晓云。
眼见林白变了神色,林星从门外关了门。
两人不说话。不多时候,窗外响起跑车声浪,自近而远,扬长而去。
林白终于开口:“我弟弟他……你别介意。”
顾晓云:“他像是故意要激怒我。”
林白怔一怔:“很明显?”
顾晓云:“明显到像在演话剧。”
林白重复她的话:“演话剧。”
顾晓云看着他。
林白:“我之前有没有见告过你,我在国外读书,没读完就回来?”
顾晓云:“你提过你在美国读书,别的没讲过。”
林白点点头,“上大学的时候我家出了点事。实在很多事情很早就有迹象。比如我上大二的时候,家里给我的账户上打钱就常常打得迟了。但我这个人不怎么能花,不特殊把稳,也就没创造。大三的时候有天林星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赶紧回来。他那时候有多大年纪,十七岁,上高二。我一开始的时候以为他逗我玩,但我创造我打不通我爸的电话,也打不通我妈的电话。回来我才知道,我父亲的买卖出了问题,他自己也溘然脑出血。林星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在ICU,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妈妈没经由这些事,精神一下子垮了,年夜夫说是急性精神分裂。”
顾晓云缄默。
林白接着说:“那段韶光我像是掉进了什么洞里,每天在医院陪妈妈,没有别的事。不知道林星在干什么,也不知道家里的事要怎么办。说是不知道,实在是没想过。说是没想过,实在也是不去想。等林星再涌如今我面前的时候,家里的厂子保了下来,债务也开始分批次地还。两年吧,就还清了。”
顾晓云:“林星一个人?”
林白点点头:“这两年林星是怎么过来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同样知道得不多。总之家里碰着这种事情,都是众叛亲离。老下属忙着趁火打劫,叔叔伯伯姑姑忙着争家产。他那个时候有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一听见这事,大人还没说什么,女孩自己先不跟他来往了——都是十七岁。十七岁的小孩,怎么——”
顾晓云:“那他刚才的样子也不奇怪。”
林白:“他才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什么都不能信了。等长到现在,你又让他信什么?后来林星还问我,我当时从美国走的时候,办的是休学还是退学?如果是休学,不如回去上完。”
顾晓云缄默。
林白:“你说演话剧。实在他小时候一贯想学演出。本来家里也供得起。我爸爸的意思,送他去学艺术,送我去读商学院,谁知道——林星小时候太不着调,我父亲不知道后来的事,很多意见到去世都没有改变。他以为林星扛不住什么。”
顾晓云:“以是让你去读商学院?”
林白:“他以为我也够呛。以是他的安排不是由于他有多理智,他只是不知道自己这么早就会去世。比较之下,反而是林星看得更明白。”
顾晓云:“怎么说?”
林白:“去年他才见告我,当年他把我叫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自己去整顿统统了。”
顾晓云:“为什么?”
林白:“他说,他以为他像爸爸,我像妈妈。妈妈已经疯了,一个家里不能有两个疯子——有道理。”
顾晓云:“你会么?”
林白:“读大学的时候我吃过抗烦闷的药。等回来经历这些事,反而什么也不吃了。这些事我没跟家里人说过,他实在该当不知道。”
顾晓云:“但他理解你。”
林白:“不应该有我这样的哥哥。跟我比,他现在可疯得厉害多了。”
顾晓云:“怎么说?”
林白:“他飙车,不要命。”
顾晓云:“你们的妈妈,现在怎么样?”
林白:“住调理院,身边有护工。什么都挺好,只要别出来。护工一个月放四天假,我就去陪她四天,说说话。”
顾晓云:“你们说什么话?”
林白:“说过去,说我和林星小时候,她小时候,我爸小时候,我爷爷我奶奶,我外公我外婆。”
后来顾晓云常常想,人生涯着,做不到求不得都是常态。有林星在,林白做一辈子闲人未尝不可。但人生涯着最不能违反的东西便是天意。如果你原来便是某一种人,而你不愿成为,命运会想尽办法将你推到那个你抗拒的方向。
那一天林白没有说出口的担心很快应验,林星的跑车撞在山上面孔全非,身后留下的账单比父亲去世的时候更长。
知道的时候新年将近,顾晓云和林白在邻市看雪。回程路上高速两旁银装素裹,行车路上只有飞溅的黑泥。车速太快,老丰田底盘轻,险些在路上漂浮。顾晓云抓着车窗上面的扶手,侧过脸仔细端详林白,在他的侧脸上层层叠叠地看到林星的影子,就算她只见过他一次,她也能认出那张脸,和那双眼睛。
林白说,“晓云,我们分开。”
顾晓云看着他:“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过?你是不是不记得,你从没有正式地提过这一件事?”
林白说不出话。
林白回避很多事。回避确定关系,回避承诺,回避谈论未来。就像从前他回避他父亲自后纠缠的乱麻,那也是在回避面对林星的人生决议。
更早的时候,商学院上不下去,是不是也在从潜意识里回避承担任务?
顾晓云回避他的回避。不是没有想过。某种意义上,她和林白是一类人。
追随另一个人,意味着回避做出选择。
总有避无可避的时候。底细毕露,事情显出原貌,无论它看上去是否宜人。
顾晓云:“我姑姑在云南有个茶园。这两年想做做品牌,也做个茶肆。事情挺多。原来也想年后过去帮忙。我春天走。”
林白:“你真的有这个姑姑?”
顾晓云笑,“给你台阶,你就该只管下。”
走的时候林白没送她。
再见面是两年往后。山重水复。顾晓云坐在窗下看远处的雪山。老街上行人不多,有居民也有游客。林白推门而入,顾晓云用了一下子才认出他。
顾晓云:“怎么找到这儿。”
林白:“晓云茶肆,牌子做得这么好,刷手机都刷得到。”
顾晓云:“谁乐意做那个?不抛头露面就没有饭吃。”
林白:“姑姑呢?”
顾晓云:“去下面收茶。”
林白:“多久回来?”
顾晓云:“要一阵子,十天半个月。”
林白:“是真有个姑姑,不是编出来骗我?”
顾晓云:“你来便是为了问这个。”
林白不说话。
顾晓云打量他。他黑了,也健壮了。不再弓着腰,肩膀伸展,显得个子更高。发型精细到眉梢鬓角,额头光亮。
顾晓云:“由于问不清,以是放不下。”
林白:“你没变,还是老样子。”
顾晓云摇头,“我变了很多。只是你变得更多,看不出从前的样子。”
林白:“一点也没有吗?”
顾晓云:“一点也没有。是好事。那些问题你一定办理得很好。”
林白:“旧的问题过去,新的问题会来。”
顾晓云:“没有问题的人在宅兆里。”
林白:“这两年我常常想,如果我早一点做出改变,林星现在会不会——在做演员。”
顾晓云:“这是你的来意。”
林白:“怎么这样说?”
顾晓云:“来聊聊过去。”
林白缄默。
顾晓云:“你妈妈,好不好?”
林白:“还好。”
顾晓云:“你每周还去陪她?”
林白摇头,“每个月,总还会有一天。”
顾晓云:“还是说过去?”
林白:“也说现在。实在说什么都可以,现在的事她记不太住。记住的那些呢,过一阵子就变了样。关于现在,她自己会讲出一个完全的故事。调理院的环境是真空,许可病人余生活在梦里。”
顾晓云:“不问你弟弟。”
林白笑,“他原来也不来。”
彼此不再说话,缄默喝了几道茶。
林白:“还想问问你——”
顾晓云:“想好再问。”
林白笑,“你知道我要问什么?”
顾晓云:“放不下我,不然不会来。可是你放不下的是什么?是我,还是过去?”
林白:“当年你走的时候我在躲避。你说,我从来没有正式跟你说过,想跟你在一起。”
顾晓云:“今时今日,不用躲避?”
林白:“是。”
顾晓云:“可你的这句话,当时只能对我说,现在却已经可以和很多人说。年轻有为,无家无累,身边多少好女孩,真抵不过一个放不下?我不是最好的选择。”
林白张张嘴,像是要说什么。顾晓云又说,“别为执念买单。”
林白缄默。
顾晓云:“回去吧。往后也别来。”
林白怔一怔,“为什么?”
顾晓云:“与其重新认识一次,不如彼此留个旧念想。就让我做你一个旧念想,多难得?多见几次,全都变样。”
林白:“知道我想到什么?”
顾晓云:“什么?”
林白:“想到第一次你坐在吧台后面说话。”
顾晓云笑,“你说,‘你是平常就这么说话,还是喝了酒才这么说话?’”
林白也笑,“‘像一根探针一样说话。’”
顾晓云缄默。
林白说,“晓云。你到底……是哪里变了呢?”
他的声音低沉柔和,像他们第一次相遇的那个夜晚。
顾晓云没回答,起身站到门边,等林白跟出来。
那一天她送林白走了很远。转出一个又一个街口,与他作别,看他的影子融入暮色,从胸中长长舒出一口气。
历来看清别人易,看清自己难。
旧念想,多难得?林白是她的旧念想,她舍不得看他变样。
惟其如此,在雨季那些辗转难眠的夜里,站在窗前勾勒回顾的轮廓,一帧一帧都是过去,无关现在。
谁的余生,不是活在梦里。
— 全文完 —
更多精彩内容请移步微信公众号 “戏局onStage”
作者 | 孟小莫 编辑 | 方悄悄
原文链接:《我们结婚吧,实在也相称于我们分离吧 | 别亦难》
本文图文版权均归属网易文创人间事情室,未经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