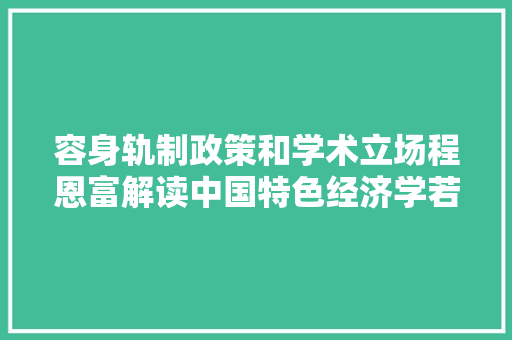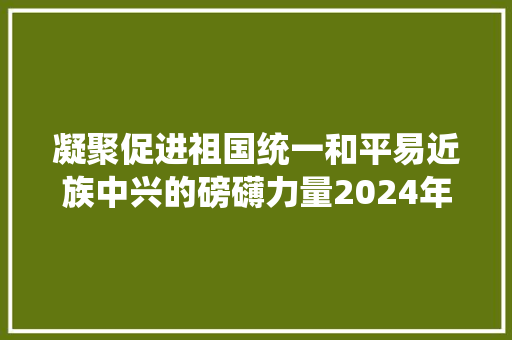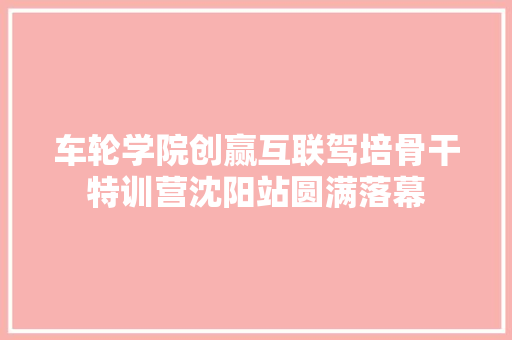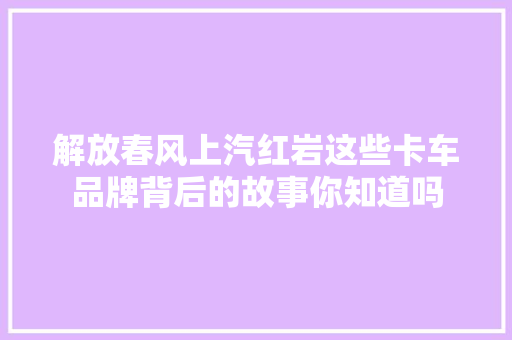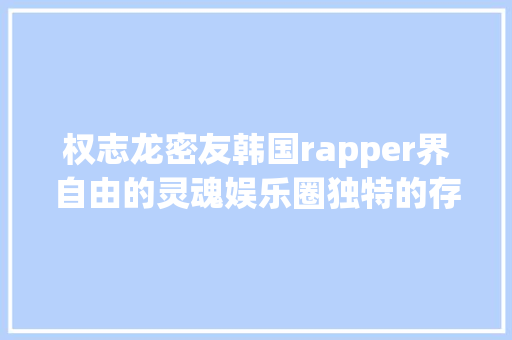作者|李小歪
编辑|吴怼怼

01
去韩国,选秀爱豆就有未来吗
今年上半年Mnet启动一档延续《Produce》系列的新选秀《Girls Planet 999》,来自中日韩三国各33名少女,共计99人参与一场女团出道位争夺赛。不雅观众被比喻成「Guardian」守护者,有点儿类似于中国版创造营101中「全民制作人」的角色,通过投票来守护参演者的梦想,助力她们成团出道。
事实上,从全体文娱家当的复苏节奏来看,2月女团传统回归月并未大势,公共舞台和活动不断收窄紧缩,偶像业的竞争更加激烈。选秀妹妹们已经由于疫情延误了一年黄金期,快等不起了。
偏偏疫情之下,面临经营困难的不仅是2018年偶像元年开启后喷涌而出的中国偶像公司,韩国的中小型娱乐公司也倒闭了一批。不仅是中国练习生,日本和韩国的选秀妹妹们都眼巴巴地指望这机会翻盘。
但聚焦到节目本身,仅仅依赖参加Mnet这档新选秀《Girls Planet 999》就走红,这场赌局本身赢面也不大。
众所周知,《Produce》系列节目在韩国走到第四季,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后期疲软的问题。根据Jazmine Media援引韩国尼尔森的数据,《Girls Planet 999》开局收视率极低,仅有0.46%,远远低于《Produce》系列此前任何一季的首集收视率。
这倒是猜想之中。一方面,从内容形式来说,没有打破性的赛制、形式或内容创新,综N代口碑和收视下滑是常事,另一方面,Mnet重启选秀综艺是在《Produce》系列被曝光操纵选票和贿选之后——毕竟是真金白银的打投,大众对此重修信心须要韶光。
纵然不以走低的收视率为依据,部分韩国媒体依然认为《Girls Planet 999》难以复制《Produce》系列的成功。大略点儿说,这档节目火不了。
「火不了」是一个对节目整体,包括中日韩三国选手的概括判断,但在整体之下,局部的中国选手出圈更为困难。
首先,被疑惑遭遇「恶剪」的中国选手符雅凝和蔡冰在韩国舆论场已经引起争议。前者在演出前的喊话中对已出道的韩国女团CLC成员崔有真(音译)说出了,「we go up helicopter, but you don’t」(类似于我上你下的表达)。
这是中国选秀battle中常见的「热场」环节,制作方为了综艺效果也每每会故意识地勾引对战双方发起这种「叫板喊话」来增加节目的冲突性、竞争性,但在韩国娱乐圈前子弟等级分明的文化语境下,这种行为被理解为挑衅和慢待。
和蔡冰力争C位和队长一样,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更多被解读成「独立自傲、大胆争取」的行为,在韩国舆论中带上了更多「心机、事儿多」的评价。而这类评价又影响了韩国网民对中国选手的整体风评。
今年五月,韩国Hankook Research的一份调查显示,20岁和30岁世代韩国年轻人比起日本,对中国有着更多的负面感情。这种大众感情某种程度上理应让制作方、参演者极其背后的选送公司产生顾虑——毕竟此前《Produce 48》在韩国播出时,也曾由于日本选手的加入而遭受部分抵制。
大众对选手政治态度的核阅险些贯穿始终,这一点在中韩别无二致。目前在《Girls Planet 999》,中国选手苏芮琪因转发抗美援朝的话题被韩网抵制,风评一起下滑。这和外国艺人在中国活动时必须态度武断是一个道理。
韩国盛行文化评论家Jeong Deok-hyun认为,考虑到目前的形势,Mnet的这档新偶像综艺在韩国很难成功。
02
作为商品的选秀和真人秀
一个值得谈论的话题是,不雅观众对这类选秀综艺的感情是繁芜的,尤其是《Produce》系列的女团季,受众一边心疼女性练习生出道的遥遥无期,无奈于节目对选手的花费,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这样的舞台和制作,毕竟它让参演者最快地进入偶像工业的流水生产线,成为一件看似被精细包装、完美无瑕的商品,只待成团出道之夜,进入大众挑选的货架。
当选择是她们的命运,乃至当选择更像是一种幸运,当这件完美的商品拥有氪金能力更强、体量更弘大的粉丝群体时,他们就有了成本眼中更高的商业代价。
和主题曲中的「Pick me」一样,有人认为,这种语态和设定,以及被动等待的姿态,或多或少有了归天女性的嫌疑。比拟之下,同类节目的男团季中,喊出的口号是「我是我的主角」。
讽刺的是,如果参与个中成为「出演者」或者「制作人」,你很大程度上感想熏染不到这种归天。
在中国版本创造营101中,节目色彩提炼上铺陈了大量粉色来营造一种仪式感和蔼氛感。这是种让人感官上无害,乃至能够放下戒备的颜色,详细的设置在于:女孩们入驻粉赤色的房间,出道路上有从天而降的粉赤色花瓣,宿舍内的陈设摆设多以萌宠、可爱风为主,练习室里的教练面色温顺,彷佛在这座粉色梦幻的「城堡」里,女孩们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
但与梦幻粉色城堡形成强烈比拟冲突的是,激烈的女团厮杀在此从未落幕。对年事和颜值颇为挑剔的娱乐圈从不会卸下它的残酷,竞争和角力才是这场游戏的主旋律。
于是,金色的皇冠和三角形,这些暗示等级、矩阵的符号化的形态不断闪现:出道位区的座椅与其他区域有所区隔,第一名的坐席高高在上,第二三名分列旁边递减一级台阶,这些隐秘的暗示才复刻了竞争的主旨,也强化了环境中的个体对成功、对名利的渴望。
当101个女孩整洁划一地站好并庄严宣誓「她们的命运由你这样的全民制作人决定」时,不雅观众不可避免地会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义务感和保护欲,把女孩们的出息和自己的努力划上直接的等号。
这便是制作方想达成的,给不雅观众造成的一种「被赋权」的错觉。这也阐明了为什么王菊喊出「你们手中握着的,是重新定义中国第一女团的权利」时,这种话术本身就糅合了对不雅观众的谄媚,也恰好符合了制作方的预期框架。
事实上,不雅观众,所谓的「全民制作人」真的被赋权了吗,他们真的在创造未来的女团这件事上拥有话语权吗?
如果有,那也是部分的、被限定的话语权。否则,每年针对「皇族」的谈论不会耐久不息,兔区鹅组和饭圈不会有那么多质疑数据注水或恶意压票的帖子,而节目组(或制作方)所代表的背后平台和成本,从来都不须要出面阐明。
我倒是相信,说出这番话的王菊内心是开阔的。当时她该当是真的相信,和那些身处个中的女孩一样,和那些拥有投票权的「全民制作人」一样,彼时大家都心存抱负。
而当这些视觉符号光鲜、流程细致规整的庄严仪式作为表象,包裹住残酷竞争的原形时,这种仪式的建构反而像是一种流于表面的做戏,假象的公正投票,粉饰的是背后的个体无力。
但不雅观众和参演者都须要这种仪式感来自我冲动,或者说,达成感情上的自我宽慰、消解和平衡,又或许参演者有几分心知肚明,但身在局中接管游戏规则就不能挑明说破。
而这场原来庄严的仪式,理应公正的投票,也逐渐演化成一场偶像工业的遮羞布。它用娱乐化的文本,完成了对庄严的嬉戏,并讨巧地隐蔽在一套「奋斗逐梦」的话语体系里。当你严明地核阅它、批驳它时,推戴者会为自己辩解,「本来便是图个乐子,大可不必这么较真」。
03
猖獗的守护,粉丝的反击
但我们为什么该当较真?
在韩国「Produce101」案件中,PD安俊英与CP金勇范由于投票造假而获刑,检⽅的陈述或许阐明了这种「较真」的必要——
「《Produce》系列在各个年事层得到⼈⽓的缘故原由是,与有⽆所属社规模⼤⼩⽆关,不雅观众为凭借努⼒和实⼒得到排名上升的练习⽣进⾏应援时,由于公道性⽽得到了代理满⾜感。当得知相称⼀部分是造假结果后,感到对这天下公道理念的强烈虚⽆感和背叛感。」
在平台和成本形成巨大的权力凑集体后,年轻的粉丝们纵然嗅到「暗箱操作」可能,也无法正面对抗。他们屈服地接管了这个规则,乃至可以说,他们在规则的框架体系下去探求打破性的、达成目标的可能。
此时的逻辑是,哥哥/妹妹(粉的偶像)只有我了,我要尽最大的力量去打投、去冲票,才有能保住他/她在成本心中的地位。
于是一个个年轻的粉丝个体,在饭圈中集结成出征群体,他们形成了「加密通话」,组织了「数据女工」,发起一场又一场打投保卫战,试图用一些浩大的声量影响、乃至改变成本的判断。
以是才有了「逆天改命」的说法。在中国版本的《偶像练习生》、《青春有你》等节目中,朱正廷、陆柯燃的出道都被称为「逆天改命」的案例,也被粉丝群体看做自身权力扩展,拥有话语权的范例。
在这场出道位的死活搏杀里,要把自己心中的偶像送上高位,一定就伴随着对其竞争者的贬损和踩踏。于是,抹黑正在日常化,举报正在家常便饭,年轻的粉丝们非常清楚,在这个文化语境中,杀去世对家的致命一击是什么。
而我所担心的是,年轻一代在这些追星娱乐里,得到的早已不是纯挚的快乐了。他们在年少时习得这些伪装、诡辩的话术,以及人性的弱点该如何攻破,当阴谋论、厚黑学在这里被利用得如鱼得水、适可而止,乃至可以完备不在乎那些被侵害的人,那些被倾倒的奶制品时,追星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应该被重新揣摩和衡量,整治和规范也应该应时参与了。
8月末,爱奇艺CEO龚宇在一场漫谈会上宣告,取消未来几年的偶像选秀节目和任何场外投票环节。
9月初,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职员管理的关照》,对「倒奶事宜」、「艺人违法失落德」等热议话题有了基本的盖棺定论。
如果说2018年偶像工业元年,那么2021年,便是重新核阅偶像的元年。下一代的偶像和粉圈该当是什么样子容貌,这个议题理应被提上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