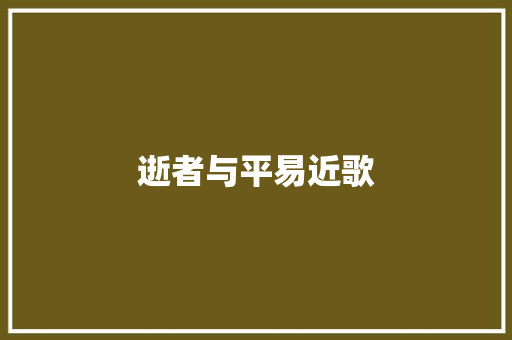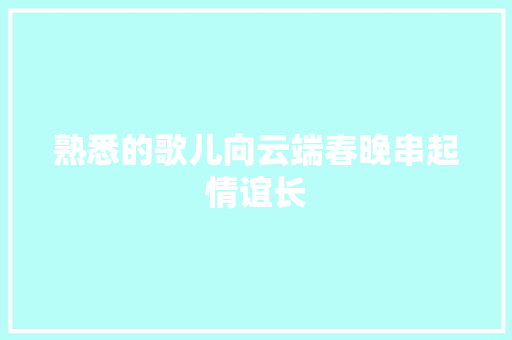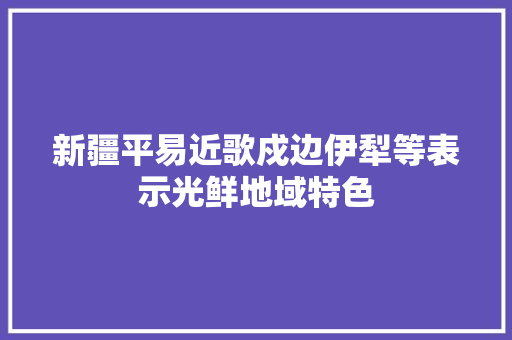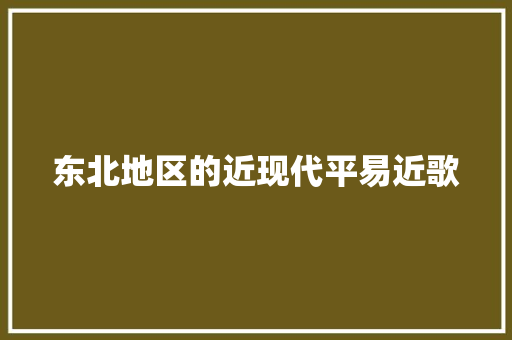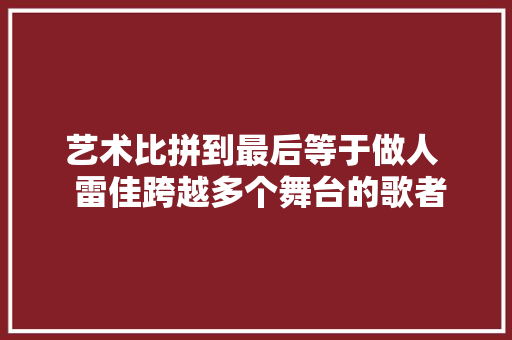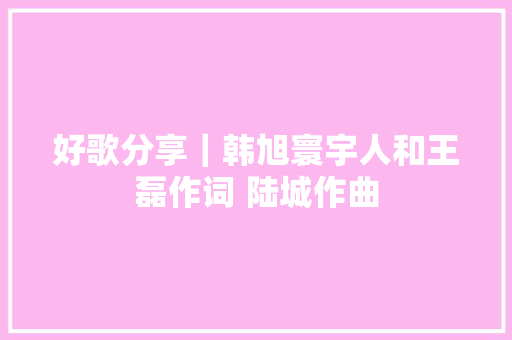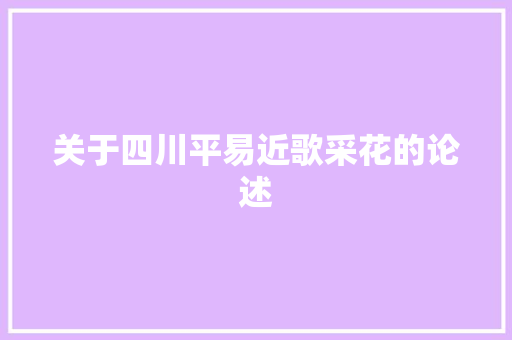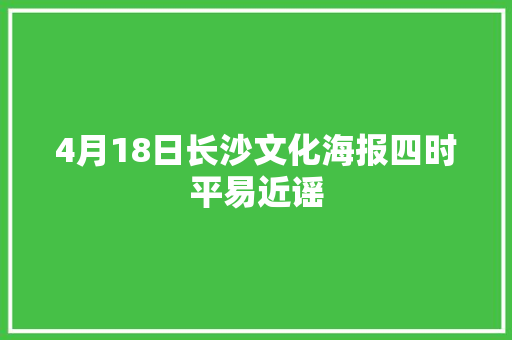春至花开日 民歌正当时
——在民歌发展路上创新探索的追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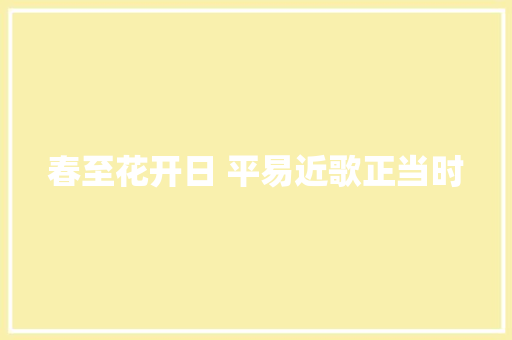
光明日报 彭景晖 李丹阳
灯光下,舞台上,呼麦从歌者的喉咙直抵听众的耳膜,声如苍穹之巅,如瀚海之底,如骏马嘶鸣。90后民歌歌手傲日其愣嗓门一开,把人们带到内蒙古的大草原,而他的思绪回到了二十多年前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一个家庭聚会上,羞涩的5岁男孩傲日其愣站活着人面前,鼓足勇气唱了一首民歌。热烈掌声里,男孩第一次感想熏染到嗓音的代价,悄悄把民歌梦“像小树苗一样种在了心里”。
这个梦登上岁月列车,来到“大大的舞台”——湖南卫视《春天花会开》节目。同一舞台,离傲日其愣几米的间隔,另一个做着民歌梦的孩子提起发话器。90后青年歌手麦麦提江·麦提喀斯木那高亢的维吾尔族唱腔,与呼麦声击撞开。强烈风格比拟下,两种声音在一首歌里毫无违和地领悟起来。
“一首带有欧洲风格的小曲《橄榄树》,让人感想熏染到的竟是中国的草原牧场和戈壁大漠,被年轻人玩出了中国民歌的味道!
”不雅观众这样感慨。
几年里,青年群体中掀起了一场民歌热,一批民歌青年不断探索,考试测验让传统民歌与当代音乐相互结合,让原生态的状态灵感与学院派的技能风格相互碰撞。《春天花会开》节目主创职员早早关注到这一征象,他们总结道:“青年人使民歌展现了别样风采,拥有了更丰富的表达办法和更强的传播力。”
在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胡廷江看来,作为中华民族精良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国民歌一个主要特点是传承,而青年人的创新顺应了民歌的实质,能得到持续而长久的生命力。
1.民歌没有被遗失落在故乡
几十年里,伴随城市化进程,人们从屯子奔向城市。在相称长一段期间内,紧张“成长”于农业生产和田园生活土壤的民歌彷佛被人们留存在故乡。在傲日其愣和麦麦提江·麦提喀斯木出生的20世纪90年代,盛行音乐早已开始盘踞人们手中的播放器和耳机,民歌逐渐淡出了很多人的视野。
“从小喜好,无法割舍,从未改变。”简洁有力的话语里,傲日其愣表达着他不同的意见,“实际上,我身边很多一起来到大城市的青年人,从来没有丢下民歌情结。”
在生养他的内蒙古大草原,生老病去世、婚丧嫁娶,人间间的各类经历,都有民歌相伴。“祖辈父辈个个能唱,任何心情都可用歌声表达,自然、纯洁、深刻。”傲日其愣少年时便立志走民歌道路,也从来没有疑惑过这条人生道路能不能走通。
这份自傲,源自他对民歌生命力的理解,也源自民歌带给他真切的感想熏染——幸福。来到城市发展后,他没忘却“自己身后那片草原”,舞台、地铁、街头,他走过的地方,脑海中始终萦绕的是草原民歌的背景音。他与很多青年一起,守护着传承民歌的欲望。
他的差错麦麦提江·麦提喀斯木“投奔”民歌的韶光不长,纵然在本日,他仍旧给自己定位为一名摇滚音乐人,“只不过民歌魅力太大,不可不学”。2011年,在一场国外的音乐节上,来自一支中国乐队的民歌与摇滚结合的歌曲,把他的心给“剜走了”。
“原来音乐可以这么做!
”齐心专心研讨摇滚乐的麦麦提江·麦提喀斯木看到,外国乐迷对这种带有强烈中国色彩的歌曲报以“近乎猖獗的叫好”。于是,他的“音乐实验”里,开始了各种民族音乐的领悟。一边学,一边打仗越来越多的人,在整理手机通讯录时,他才创造,研讨民歌与当代音乐相结合的同仁,“翻了好几页也翻不完”。
在《春天花会开》节目里,两个人还共同选择了蒙古族民歌《天国》,一个用蒙古族唱腔,一个用维吾尔族唱腔,抒发着共同的欲望:“见告所有出门在外的年轻人,正如民歌并没有被遗失落在故乡,我们的乡愁也不会迷失落在城市生活里。”
新华社发
傲日其愣(左)和麦麦提江·麦提喀斯木受访者供图
龚爽受访者供图
郭曲受访者供图
2.同一部作品,歌者授予它不同的时期烙印
青年职业歌手龚爽如今在中国音乐学院攻读声乐专业博士研究生,过去的十多年里,她在演唱中,存心探求着中国声乐表达办法和细节处理的更多路径,“搜集”着一种唱法、一首歌曲中能够汇聚的最大“情绪交集”。
“我们每个人的情绪都如一滴水,一群人的情绪便可聚成一朵浪花,无数人的情绪在一起,便有了江、有了河,有了中华儿女共通的心。”出生于湖北、发展在长江边的龚爽,把自己的歌声看作是长江的一滴水,她希望穿过河流,穿过湖泊,去往更远的地方,激荡更多人的耳朵;也希望在歌唱生涯中,始终明白自己从哪里来,又去往何处。
“我们赞颂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留恋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在殷秀梅等歌唱家的歌声中,《长江之歌》到了副歌部分,便如巨浪般澎湃彭湃、波澜壮阔。而成长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时期下的龚爽,对副歌利用了其余一种处理办法——平稳缓和如涓涓细流。
“像孩子躺在母亲的怀里,向母亲呢喃着轻声耳语。”龚爽说,“我们生活的年代稳定而幸福,我平时看到的母亲河便是这个样子。”犹如她那关于一滴水发展的感悟,整首歌缓缓而进,情绪逐渐浓厚,“涓涓细流不断搜集”,直至结尾处情绪喷发、“抵达大海”。这便是长江边终年夜的女孩用歌声诉说的长江。
类似的考试测验,龚爽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那时,我在一次演出中演唱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龚爽回顾,过去,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是进行曲节奏,由于要表现硝烟战火和战斗场景,所以是昂扬的、激情的。
龚爽将之改编成一个抒怀段落,并且用一种“伸展长线条”的演唱办法来演唱。“歌词中‘俏丽的祖国’‘强大的祖国’早已成为现实,我们当代青年人是用从容自傲的姿态步入新时期的。以是我想用歌声表达我们真实感想熏染的祖国。”龚爽说,同一部作品,歌者能授予它不同的时期烙印。
而这样的探索并非易事。在各国文化激烈碰撞交融的本日,很多像龚爽一样的青年歌者,都希望有更多持这种想法的人参与进来,一起思虑,一起考试测验,“唯有如此才能找到中国声乐、中国民歌更多的发展路径”。
3.尊重来自真实生活的每一个音符
青年音乐制作人郭曲最近也加入了“民歌大家庭”。“对民歌有两种情绪,一是喜好,二是敬畏。”有机会阅读民歌,考试测验民歌元素与电子音乐、盛行音乐的领悟,郭曲没有丝毫犹豫。
“在我打仗到的青年群体里,对付民歌是存在审美断层的。”郭曲先容,在他的一些作品里,《茉莉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歌曲的元素能唤醒很多父辈人的影象,可一些年轻人却难以产生共鸣。
一些学者也强调同样的问题,相较于盛行歌曲,民歌的传播渠道较为局限,原来来自民间的民歌逐渐“曲高和寡”。
“大概自己可以为办理这个问题做一点点事情”。郭曲很快创造,民歌与各种音乐的领悟,不是一个“包装”的过程,没有听众会为“大略嫁接”的作品买单。要办理审美断层问题,让民歌被更多年轻人接管,不可一挥而就。
“最大困难是如何准确地把握尺度,让作品既保留经典音乐的精神内核,又具备恰当的音乐措辞。”郭曲视之为最大寻衅,他说,“我们要有谨慎克制的原则,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要急着创新。”
在改编《乌苏里船歌》时,郭曲险些完全地保持了整首歌的音乐样貌。“实际上在气质等方面也没有做太大改变。原作品对人们的清闲快乐展现得淋漓尽致,完备不必做‘多此一举’的改变。”郭曲负责地践行着自己“谨慎克制”的原则,也看重理解民歌的出身背景,看重去实地采风。
这样的不雅观点被胡廷江赞许,在他看来,民歌不只是旋律上的呈现,更是一种生活的再现。青年人要传承和发扬民歌,就要扎根在民间的土壤,深入人们的生活,去体验、挖掘、凝练。“互联网越便利,我们搜索一段旋律越随意马虎,就越要尊重来自真实生活的每一个音符。”胡廷江说。
“不刻意,要自然而然。”在《春天花会开》舞台上,郭曲得意于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中一段平和而温暖的小号声。郭曲说:“没有特意拟定的意境,没有专门预设的情绪。就让音符本身去和不雅观众互换吧,让它成为一个台子,让不雅观众把自己想要的真实情绪放上去。”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2日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