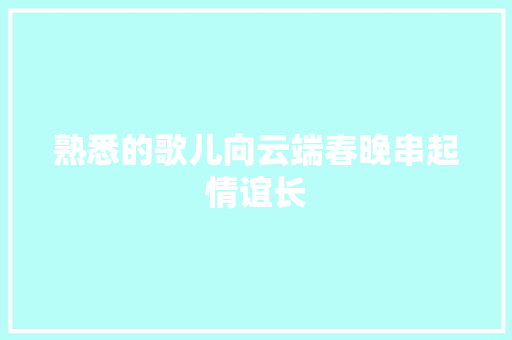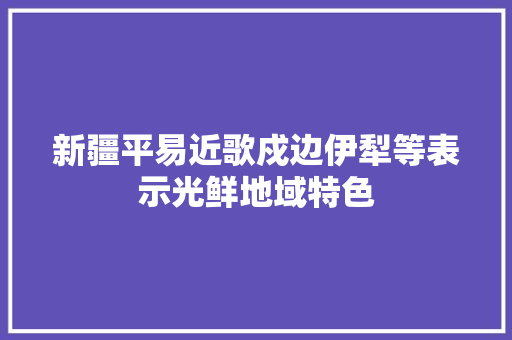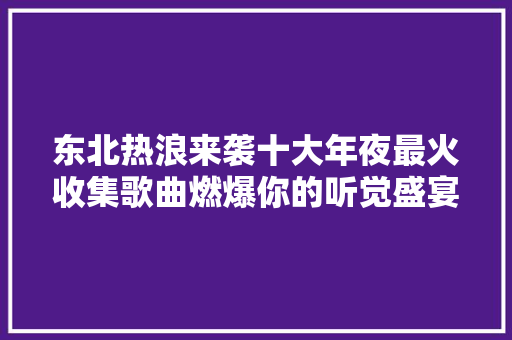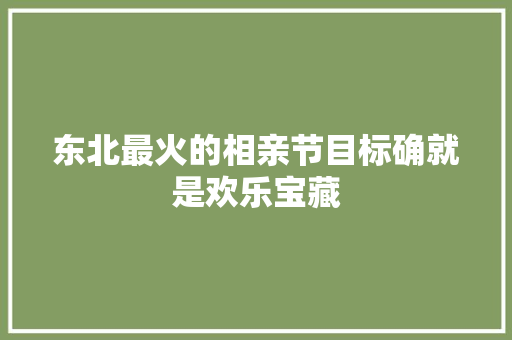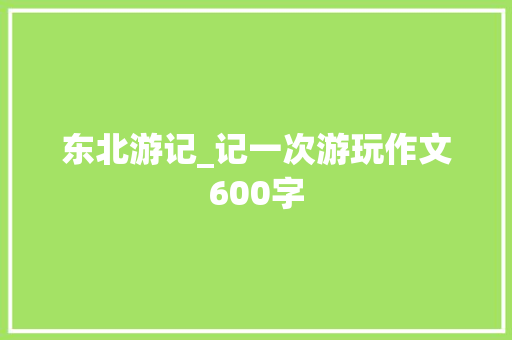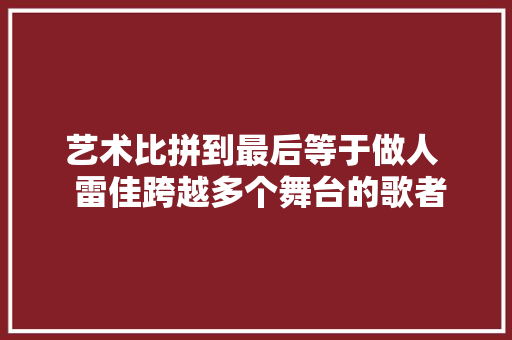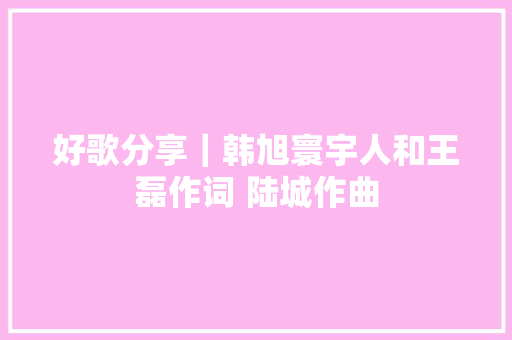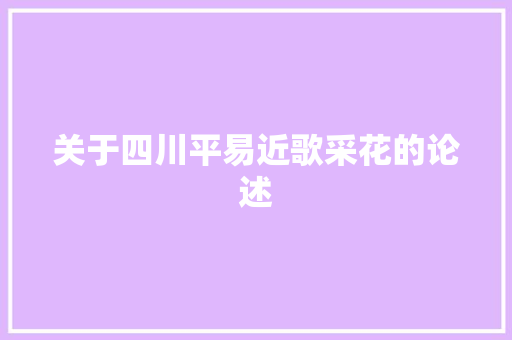我们先从经济、地域、民族等各个文化层面来梳理一下东北民歌的历史传承与演化。
从地域经济层面上讲,东北地区的地理条件和气温,使其形成了北部和东北边缘的森林区(大小兴安岭、长白山脉及其临近的河谷地等)、西部的草原区(呼伦贝尔草原及南部地区、松嫩平原的绝大部分等)及平原区(东北平原),并相应地形成了游牧、渔猎、农业经济地理带,造就出了清代东北各民族独特的游牧、渔猎、农耕生产办法和习俗文化,也产生了不同的东北音乐地理分区,出身了山歌、渔歌、草原歌曲等音乐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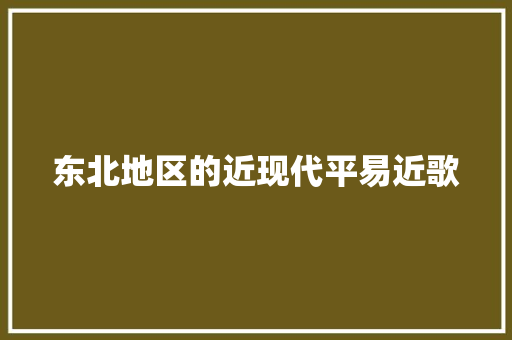
东北平原地区的农人,以农业生活为主,创作了一些相应内容的民歌,如黑龙江民歌《捡棉花》、辽宁民歌《姐妹上场院》、吉林民歌《生产忙》等。农人们还在长期的农耕生活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农业耕种周期与规律,并以民歌的形式进行表达和传承,如东北民歌《二十四节气歌》:“……惊蛰乌鸦叫,春分土地干(哪),清明忙种麦(呀),谷雨种大田……芒种正铲地,夏至不拿棉(哪)……立秋忙打靛(哪),处暑动刀镰,白露忙割地,秋分无生田(哪) ……立冬交十月(呀),小雪地封严……”这首民歌小调不仅给人们带来音乐上的娱乐性,更具有一定的知识性,丰富了民间音乐的内容。
在东北地区西部生活的蒙古族公民,过去曾经由着游牧生活,形成了特色光鲜的草原文化。他们长年以车帐为家,逐水草而迁徙,创作了大量具有草原风情的牧歌。牧歌的节奏一样平常比较悠长、徐缓、自由,多采取“密—疏—更密—疏”的节奏。一样平常情形下,牧歌的上行乐句节奏是悠长徐缓的;下行乐句则每每采取生动跳荡的三连音节奏,形成绚丽的华彩乐句。比如,呼伦贝尔草原的长调民歌《辽阔草原》《盗马姑娘》等激情亲切旷达;科尔沁草原的民歌《思乡曲》《威风矫健的马》等情调悠长。短调民歌紧张盛行于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地区,每每是即兴歌唱,灵巧性很强。比较盛行的有《成吉思汗的两匹青马》《美酒醇如喷鼻香蜜》《拉骆驼的哥哥十二属相》等。
东北地区河流浩瀚,适宜捕鱼,于是在很多地方形成了风格不一的渔歌,若有名的《乌苏里船歌》等。同时,也形成了一些劳动号子,如渤海海岸的《捞鱼号》《出仓号》《拉船号》《撒网号》等。
东北多山,长白山脉、大兴安岭的群山中生活着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他们创作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山歌,如《高高的兴安岭》《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我们是山林里的人》《大顶子山高又高》等。著名民歌《道拉基》,则表现了朝鲜族公民上山挖野菜的生活情景:“道拉基,道拉基,道拉基,洁白的桔梗哟长在山里,只要能挖上一两根,就可以装满我的小菜筐……你叫我多灾堪,由于你长的地方太偏僻。”
游牧、渔猎文化也授予了东北民歌激情亲切、旷达、明快的风格。
从地域文化层面上讲,东北自古便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东北土著民族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积淀。移民人口的流入,更给东北地区带来了富有各地特色的传统文化,如胶东文化、豫东文化、晋商文化、江浙文化、两湖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等,这些移民文化与东北传统文化交融、碰撞,奠定了多元的新型关东文化的根本。
随着山东、河北等地大量人口“闯关东”,很多关内民歌被带入东北,如当时盛行的民歌《五更调》《绣荷包调》《孟姜女调》《剪靛花调》《茉莉花调》等。这些民歌在东北产生了变体“民歌”小调,比如由《孟姜女调》产生的《送情郎》《送才郎》《摇篮曲》,由《剪靛花调》产生的《放鹞子》《叫五更》《摔西瓜》《下盘棋》《鄙视戏》,由《跌落金钱》产生的《月牙五更》《铺地锦》,等等。
须要特殊指出的是,东北汉族民歌受冀东民歌、山东民歌影响较大,同属一个民歌色彩区。很多民歌由山东、冀东流入东北后,有的变异较大,有的变异较小,有的险些一样。比如,东北民歌《十仲春》,就来自山东的《沂蒙山小调》;吉林民歌《绣中华》、辽宁民歌《绣红灯》与冀东民歌《丢戒指》大同小异;冀东民歌《跑关东》《正月里来正月正》与吉林民歌《庆新春》、黑龙江民歌《秧歌调》也有很多传承……只管冀东民歌、山东民歌与东北汉族民歌同根同源,但是如果仔细品味的话,也能创造个中的差异,东北民歌更加明快粗犷,冀东、山东民歌则侧重细腻抒怀。
东北的许多民歌发源于关内各地乃至国外,但这些歌曲搜集于东北,经由改造与领悟,形成了具有光鲜地方特色的民歌。
从宗教层面上讲,历史上的东北宗教具有多元化色彩,在民歌领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弯腰挂》的音乐来源于萨满歌曲《祭天》,加入了山东民歌的风格;《拜愿》《望江南》等,是佛教风格的音乐;《梅花引》等,是东北地区所创的玄门音乐“东北新韵”;《全幸福》等,则是具有浓郁蒙古族风格的喇嘛教民歌。
从民族互换层面上讲,东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形成了多民族共荣的局势。东北地区的公民因此关内各省移来的汉族为主体,包括满族、蒙古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在内的复合群体,通过民族领悟,构成了一体多元的东北文化格局。这些民族能歌善舞,创作和传承了有本民族特色的民歌,且自成体系,别具一格。
东北汉族民歌的节拍以 2/4 拍和 4/4 拍为主,节奏特点因此均匀型、节奏型,穿插切分型、是非型等特性节奏构成。民歌形式有劳动号子、叫卖调、秧歌调、小调四种。满族民歌以一段体为主,风格朴实、稳健,旋律以宫、商、角为骨干音,多五声旋律及宫调式,如《出征歌》《子孙万代歌》等。蒙古族民歌以声音伟大雄浑、曲调高亢悠扬而有名,节奏自由,装饰音多而细腻,具有较强的朗诵性。从音乐特点来讲,蒙古族民歌大致分为“长调”和“短调”两大类。朝鲜族音乐旋律清新、流畅、婉转、轻快,节奏多为三拍子、五声音阶。著名朝鲜族民歌《桔梗谣》《阿里郎》《诺多尔江边》等,险些家喻户晓,大家传唱。源于黑龙江流域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赫哲族因历史上与满族和蒙古族互换较多,民歌也受其影响较多,但均以宫调式、五声旋律为主,具有简约、明朗、朴实的性情。
少数民族民歌的各种文体和形式,表示了东北民歌的多样性。
从国际层面上讲,历史上的关东文化处于东北亚区域中央地带,尤其是清末以来,内忧外祸之下,东北封禁的大门逐渐被打开,俄国、日本、朝鲜等各国人不断流入,个中相称一部分携带自身文化融入关东文化之中。各种他乡文化在东北地区汇流、交融、碰撞,而中华文化也从这里向邻国传播。
在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地区后,日本歌曲也随之传入,如《去野游》《家乡》《旅愁》《荒城之月》《萤之光》等,并以东洋风格创作了《蒙古之旅》《娘娘庙会》等歌曲。这些歌曲充满殖民色彩,反响了东北地区一段屈辱的历史。
此外,我国赫哲族的“嫁令阔”与俄罗斯那乃族的“嫁利”也有很多共同特点,反响了国际层面的互换与影响。
通过追溯东北民歌的传承与演化,我们可以概括出它的紧张特色:
多元文化影响下的东北民歌,具有很强的原谅性和多样性。传统东北民歌按内容紧张可以划分为十类:历史传说歌,如《九反朝阳》(清咸丰年间朝阳农人李凤奎叛逆故事)、《六十三》(清末辽宁地区的反清反帝斗争故事)、《东北失落守十四年》等;民间风尚歌,如《小拜年》《看秧歌》《放鹞子》《新婚喜歌》等;劳动歌,如《打水歌》《捡棉花》《生产忙》等;地方名胜歌,如《夸哈尔滨》《夸沈阳》《山水醉了咱赫哲人》等;情歌,如《绣云肩》《盼情郎》《佃猎的哥哥回来了》等;家庭歌,如《补母十重恩》《十大想》等;劝戒歌,如《九劝人》《劝情郎》《劝夫别耍钱》等;讽刺歌,如《拙姑娘》《拙老婆》等;知识歌,如《正对花》《反对花》等;寓言故事歌,如《鸳鸯嫁老雕》《乌鸦反哺》等。
东北民歌之以是丰富多彩,就在于它是动态的,具有很强的流变性。比如很多关内的民歌小调流传到东北后,都产生了一定的转型。个中,以“五更”调为变体的有几十首之多,如《大将五更》《叫五更》《盼郎五更》等;以“绣荷包”调为变体的有二十多种,如《绣门帘》《绣云肩》《绣八仙》等;以“四季”调为变体的有十多种,如《渔民四季歌》《孟姜女四季歌》等;以“十仲春”调为变体的也有十来种,如《画扇面》《夸沈阳》《夸哈尔滨》等。
东北民歌除了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外,还能与时俱进,具有很强的时期性。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东北民歌表现了公民群众在不同历史期间的生活和精神面貌,表达了他们的时期心声。如反响清末民初“闯关东”移民离愁的《月牙五更》,表现生活困苦的《贫农四季歌》;表现日本侵略者铁蹄下东北公民血泪控诉的《九一八小调》;还有激情亲切歌颂抗联英雄的《松花江水流一直》;新期间又有了新民歌《幸福生活切切年》《越走越亮堂》……可以说,东北民歌内容紧跟时期节拍,反响时期变迁。
(作者王广义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当代史教研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