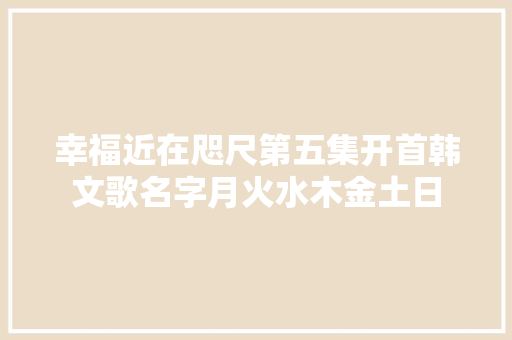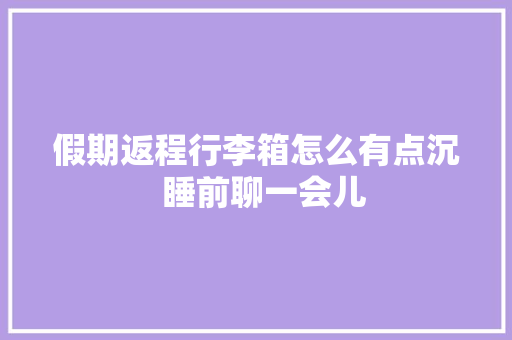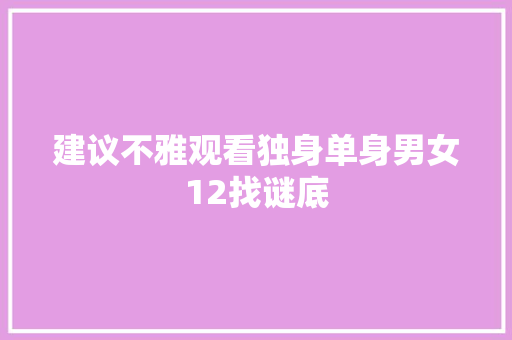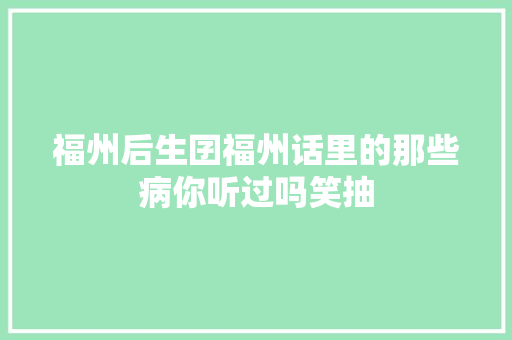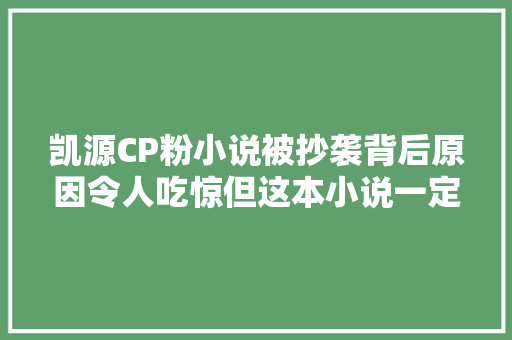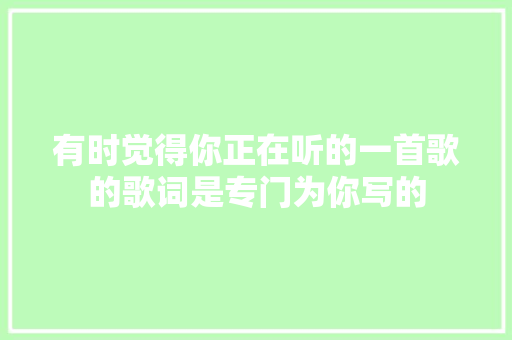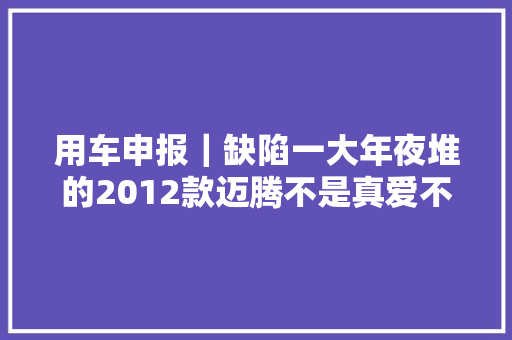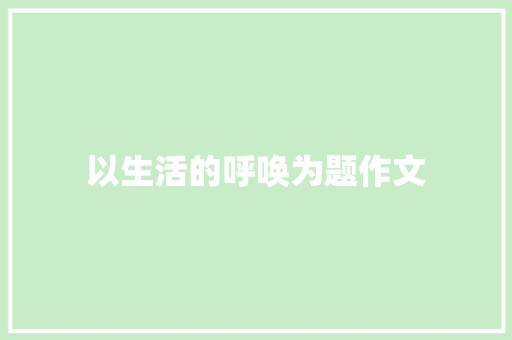饭后的人们三三两两的来到楼兰广场,十几位广场舞大妈在音响伴奏下顾自起舞,与高举花篮的楼兰美女相应成彰。
我无心留恋歌舞升平的美景,心早已经又飞回了矿山,飞回到来时的那条路上。

前天,一位在青海花土沟认识的焦作老乡,一贯打电话让帮个忙,他在玉素莆检讨站里面一个铁矿拉货时,被拖欠了将近万元的运费,让我帮忙找人活动活动。我来新疆韶光不长,只认识两个人在当地还有些道路,一个在米兰三十六团,一个在若羌县城。
我这个人喜好交朋友,是那种只要你对我好,就能把心取出来送给你的人。眼见得老乡碰着困难,也真替他焦急,就让席桑他们先跑着车,自己一个人驾车先去米兰。
依吞布拉克间隔米兰镇二百二十公里。从开拓区出来时已经是傍晚,右转驶上依铁线,十来分钟就瞥见了依吞布拉克镇。
靠近路口时,有一个沙土堆积的减速带,左边是一家汽车电器修理铺,右侧是个饭店,一个女做事员蹲在门口剥葱择菜。
一辆黄色的后八轮正在路口调头,看样子像是拉石棉石的车子,折返回来后对我说:
“整整堵了两天车了,弗成走老315吧。”
重新疆石棉矿出来有一条路,穿过厂区,直直向西,过依铁线十字路口再向西,便是老三一五国道,它紧靠着阿尔金山,由于废弃多年,早已经没有一点玄色路面,除了让民气烦的搓板路面,便是坑坑洼洼的突出洼地,时而路的两侧还会涌现几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这条路从地形上看与新三一五国道没有什么差异,都是如莲花托盘式的平台,然后下坡、陡峭的下坡,进入谷底后,再连绵起伏的延伸,一起向西。不过,新路上,车来车往不寂寞,老路中,无人无车更寂静,放眼望去,除了土黄色的山体便是簇簇尚有新绿的骆驼刺。
勃朗特在《简爱》中说过:如果你避免不了,就得去忍受,不能忍受生命中注定要忍受的事情,便是懦弱和屈曲的表现。
这句话在我初到青疆、遭受巨大挫折的时候,曾经认同过,可是身处高原韶光久了,我却将“忍受”变成了热爱,由于我以为随着韶光的徙转与岁月的加持,自己正在与戈壁幻化成同一种颜色,与高山共同拥有一种性情,把自己当成了雪山上一块被冰封了的石头,成了一个名副实在的西部人。就像穿越藏北羌塘第一人杨柳松说过的那样:
荒原永久还是荒原,亘古未变,你须要改变的只是自己!
此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在内地早就入夜了,这里还是亮如日间。到了谷底往后,老三一五国道彻底失落去了踪迹,一团团的骆驼刺彷佛围棋的黑白子,把大地这个棋盘布成了迷局。
我站在路口前一筹莫展,面前四五条小道摆在面前,不知道该究竟走哪条路。临走以前,姐夫再三交代,一个人出来最好不要走小路,那里无人无车无旗子暗记,而且依吞布拉克地处阿尔金山的边缘,稍不把稳,就会被错综繁芜的小路带进深山,由于随着风吹雨淋,大多数的冷车辙都是有头无尾。在有些偏僻的令人发指的地方,有些车辙或许是几天前的,也可能是几年前的。
下了车,沿着一条路走了一两公里后,就没有了车子驶过的痕迹,无奈原路返回,连续走另一条路,也是如此,就这样折腾了几次天就暗了下来,心中开始有点发慌了。
正当我心急如焚时,忽然,南面几十米处竟然涌现了灯光,红红的,两个灯光的间距不大,该当是小车的,停在那里。
“有人”,我惊喜万分,赶忙高喊“等等我。”
话音未落,前车就缓缓移动,手灯下,从右侧副驾驶的位置,有一个维族装扮的女人探出头来,绣花帽,绣花衣,脸上蒙着白纱巾,眼神哀怨,左眉眉尾彷佛有一颗黑痣……
“随着她肯定能出去”我想着,手里拧动钥匙发动车,跟了过去。
黑夜犹如妖怪手中的一块幕布,把天与地遮盖的严严实实,牢牢盯着着灯光,尾随着前车向前走,大气也不敢多喘一下。那辆车子彷佛在故意逗我,我快它也快,我慢它也慢,便是不让你靠近。左转右转,上坡下坡,在戈壁滩上随着它走了将近有一个小时,还是没有驶上新三一五国道,我觉得有点不妙。在依吞布拉克时,那位同行说了,最多数个多小时就能穿越戈壁滩,驶上大路。
迟疑中,我停了下来,前面那辆车竟然也停下了,而且还关闭了小灯。我有些朝气,心想,都是司机,何苦故意领着我在这鸟不拉屎的戈壁滩里兜风呢?
开门下车,向小车方向走去,间隔车子有四五米的地方,才大概看清车子的轮廓,该当是一部老式北京212吉普车。
在西部,无论青海、新疆的牧民都喜好这种车子,虽然费油,但是结实耐用。
我又向前走了两步,迟疑了一下又愣住了,内心溘然生出一种恐怖,是第六感不雅观在预警,还是四维天下通报过来的某种信息?一股去世亡的味道,如云似雾环抱在周围。虽然很怕,但是除了冒险一试,难道还有其他分开困境的办法吗?
我壮了壮胆。走到跟前,车门大开,彷佛司机刚刚离开一样,头灯下,是一辆废弃多年的破车,驾驶室的顶棚上堆砌着沙子,驾驶座上也操作台上还有一个“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铭牌。前后座位上褴褛不堪,扔着一只破油桶,根本没有人一丝一毫有人坐过的痕迹。再看看车子的前面,锈迹斑斑的保险杠上竟然还有一副车牌新M,当中两个字看不清,只能依稀的看到末了三个数字333。
“我靠,鬼车”,我大吃一惊,扭头就走,忽然一排雪亮的光柱射来,一台半挂车在前方四五百米的地方呼啸而过,天呐,我大叫一声,阴差阳错的竟然来到了国道边。
驶入国道,车子多了起来,以前刺眼的灯光,现在却感到特殊的亲切,自己也从刚才的惊惧中回过神来,跑了这么多年车,经历过许多离奇古怪的事情,像湘西午夜做事区,晋东南阴阳河奇遇,虽然惊悚胆怯,可是与这一次的比较,还真他娘的小巫见大巫了。
下了一个二十四公里的长坡,就钻入阿尔金山山谷,经由“新龙门客栈”,再向前四五公里,国道右侧有些阴暗的灯光,柴油发电机“突突突”喧哗着,在这宁静的山谷里,显得特殊的刺耳,那里是一个加水站,来自重庆的老黄和他的胖媳妇在此安营扎寨,自东向西搭了一溜儿的蓝色铁皮房,有卖日用品的商店、饭店,以及一个小玉器店,屋子东侧又平整了一下,兼营补胎充气、小电焊,那里缭乱堆放着气泵、风炮和张着大嘴巴的破轮胎。
一起上惊惧交加,早已经年夜肠告小肠,车子停好,跳下车,进屋就嚷嚷着黄嫂做饭:
“嫂子,一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四个鸡蛋,两个炒两个合泡。”
老黄不在,这两天环保和消防又上门找事儿,他只好去若羌走关系疏通。黄嫂扭着肥嘟嘟的身子烧锅起油,叮叮当当,三下五除二就把饭端了上来。
我端起碗,“嘘嘘”吹着热汤,急不可耐的挑起面条敬拜五脏庙,嘴里还不忘和黄嫂开玩笑:
“嫂子,你是不是练过功夫啊?”
“啥功夫?”黄嫂不解的问。
“吸星大法呗,你看黄哥都快被你榨干了!
”
“你这个坏家伙,再榨也不会榨你,用饭也堵不住臭嘴!
”她佯装生气的举起了手。
正吃得起劲儿,门帘撩开,一位女人走了进来,三十岁高下的年事,穿着维族女人特有的衣饰,绣花衣、绣花帽,绣花鞋,看不清长相,脸上蒙着白色的头巾,不过看着深邃的眼睛彷佛有点哀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左眉眉尾有一颗黑痣,《周易八卦》上称之为“喜上眉梢”,有这种痣的女人,有好有坏,好的一壁是善痣,预示夫妻关系和蔼;坏的一壁是算是桃花痣,感情生活上可能会比较混乱。
她向屋里看了看,没有说话也没有进来,转身就出去了,随即,屋外响起了汽车马达声。
听着汽车发动机的响声,职业的敏感,让我立即判断出这是一台北京212吉普车,又想起刚才她看我的眼神,立即抓起手电跑到室外,可是车子已经调过了头,灯光下,那辆车与我刚才在黑戈壁里迷路时碰着的千篇一律,车牌新M,尾数333。
到米兰时已经是半夜,朋友还在等我。他叫何倔强,说话干脆,办事利落,大个子,黑面庞,两道剑眉,一年四季还是穿着作训服。他是河南新郑人,原来在南疆红其拉甫边防部队服役,整整奉献了八年的宝贵光阴,与我一样,同有新疆情结,退役后来到若羌,利用手里的退役金,在这里包了几百亩地种枣树,不过最近几年枣价低迷,浇水的本钱也越来越高,基本上没有什么赚头,也就没有原来那么存心了。闲时开着皮卡车进山寻玉、找奇石,一年下来竟也收入不菲。
说罢了正事儿,我把今晚碰着的怪事给他说了说。
他听着听着,眉头紧锁起来,后来,干脆站起身,望着窗外的星空入迷。
此时的古城已经坠入沉沉的梦乡。米兰,西汉时,此地为西域楼兰国之伊循城,位于丝绸之路上罗布泊与阿尔金山脉的交会处,有东大寺、佛塔等文物古迹。
许久许久,谁都没有说话,终于,他还是转过身,看着我,一脸的严明,说:
“我先给你讲一段我在罗布泊寻玉时碰着的事情吧。”
我参军队退役后来到了米兰,认识了隔院的邻居关山峰。他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曾在罗布泊马兰基地服役。他的父亲关总是培植罗布泊的第一代人,进入沙漠12个工程兵团中的一个,工程兵建筑第101团,部队代号7169。
关老见证了罗布泊基地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与大家聊起他们初到罗布泊时的艰巨生活,缺水,只能一三五洗脸;没有新鲜蔬菜,只能吃干菜、烂菜;可是,每当提起有名于世的“双鱼玉佩”这件事儿时,关老都会变得特殊浮躁,神色阴沉,转身拜别,让何倔强和关山峰两个人大惑不解……
罗布泊
“去年夏天”,何倔强点燃一根烟,狠狠的吸了一口,迟滞了好大一下子,才吐了出来,弥散的烟雾下彷佛罩着的一个个谜团,耐久未散,他接着说,去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儿,让我至今难以释怀。
常常在西部寻玉的人都知道,每次沙尘暴之后的几天,是最有可能大的收成的韶光。巨风席卷着浩瀚无边的沙漠,可以把一座沙山移到数公里之外,那些久埋于地下的宝贝就会被掀开面纱、重见天日。
何倔强和关山峰以及他的维族女友阿依夏木,便是在沙尘暴之后的第一个清晨出发的。倔强开着一辆皮卡在前,关山峰两个人驾驶一辆越野车在后,他们从米兰镇出发,朝着东北方向的库木塔格沙漠而去,经由墩里克烽燧遗址后,
墩里克烽燧遗址
一头扎入浩瀚无际的黄沙之中。
中午时分,他们到达一处荒谷,在一处黑砂岩崖壁下创造了许多壁画,岩面朝东旭日,岩画采取粗线条的阴刻,内容彷佛在描述古人敬拜时的场景。不过让人觉得特殊诡异的是,所有的人都长得千篇一律,彷佛是从某种模子里复制出来的。崖壁正对着的河谷地带,还有一尊尊石雕人像,也是一摸一样,连眇小的线条也分绝不差,几十个石像排成两列,目视东方。
何倔强望着石像,眉头拧成了疙瘩,不由自主的又想起了“双鱼玉佩”!
关老曾经说过,中国科学院植物专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落踪后,他也到处所上的人一起去沙漠里找过,那时的他已经退役了。同行征采的人都说,彭加木的科考队在罗布泊的遗址中创造了一块双鱼玉佩,这个玉佩可以对任何物体进行“镜像复制”。有人说彭加木便是被复制成两个人后,担心透露,造成惶恐,以是才对别传播宣传是失落踪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失落踪事宜之后没多久,罗布泊又发生了三十万镜像人事宜,镜像人是指这种人与正凡人不同,他们的五脏六腑全对调,心在右肝在左,和平面镜的成像事理一样。这些镜像人与本体千篇一律,就连自己都分不清谁才是“真假悟空。听说,这些镜像人的数量达到了三十万,而造就这些镜像人的,便是传说中能够复制生命的双鱼玉佩。
所有的这些事情,在何倔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看了看仍旧端详岩画的关山峰和阿依夏木,不由的叹了一口气,了望无边无涯的沙丘,鱼鳞般的金色条纹似波浪起伏。罗布泊啊罗布泊,你究竟还隐蔽了多少的秘密?
正在此时,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一辆分不清颜色的越野车从沙丘后驶来,“吱”的一下停在他的前面。
罗布泊保护站的老杨愉快的从车上跳下来,一拳头砸在倔强的臂膀上,说:
“倔强,你小子长翅膀了吗,上午还在科什兰孜,一下子就跑到这儿了?”
何倔强被他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住的摇头:
“没有没有,我们刚从家里来到这里,怎么会去科什兰孜呢?”
老杨见他不信,指着他笑骂到:
“别给我装糊涂,你小子上午还说晚上请我们到米兰吃手抓呢,怎么了,一下子就反悔了?”
说罢,拿脱手机,翻出图片,让走过来的关山峰和阿依夏木两个人看:
“小岳,还有你们两个人呢,不会都是在骗我这个半老头目吧!
”
三个人看着照片都惊呆了,一座彷佛克隆出来的雅丹地貌下,站着四个人,何倔强、老杨、关山峰和阿依夏木……
何倔强说罢,屋里陷入去世一样平常的沉寂,我也听得不寒而栗,相隔几百公里,与他们三个人千篇一律的人究竟是谁,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忽然,我猛然想起来一件事来,赶紧敦促他把手机里阿依夏木的照片翻出来:绣花衣、绣花帽,绣花鞋,脸上蒙着白色的头巾,深邃的眼睛彷佛有些许哀怨,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左眉眉尾有一颗黑痣,她与我在戈壁滩迷路、红柳沟饭店见过的女人千篇一律。
一股凉气从头到脚浇下,身子凉冰冰的,脑袋也凉冰冰的,光阴的钟摆停滞了摇动,思维僵去世,天下凝滞,韶光定格在了零时,夜从未如此寂静,夜从未如此惊悚。
溘然,“咚咚咚”,屋门竟然被敲响了,去世寂之下,格外刺耳,此时都已经半夜了,谁还会来访呢?
“谁啊”,何倔强问。
“我,阿依夏木。”
……
后语:
东晋高僧鸠摩罗什说:统统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不雅观。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统统分缘和合而生的事物,都是不真实的、不永恒的存在。如梦,如幻,如露,如电……
实在,跑了三十年的货车,历经了冷眼、剥削还有陵暴、殴打,当然也有无数好心人的帮忙、声援,现在想起来,都像一席风般,悄然远去。
世间万物本来便是一个混沌领悟的球体,哪里有什么真假之分,认它是假,轻松清闲放下,看它是真,惆怅忧郁,熬尽光阴到花甲。
感谢您的阅读,感激您的关注!
近期推出《阿尔金山拉矿人》之七 祁曼塔格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