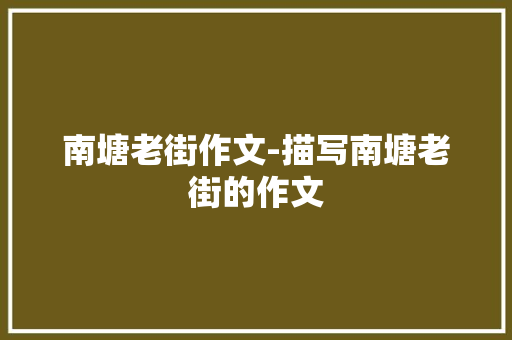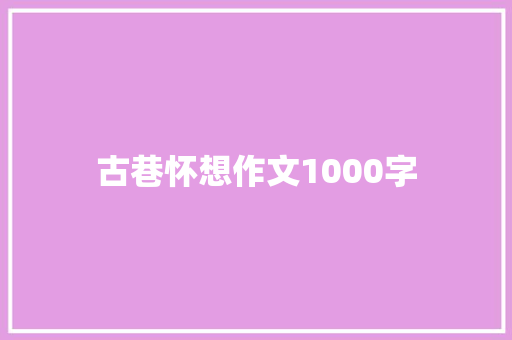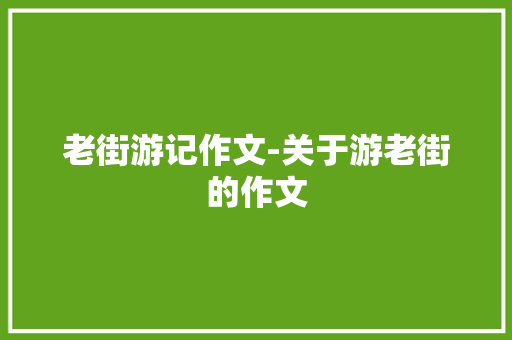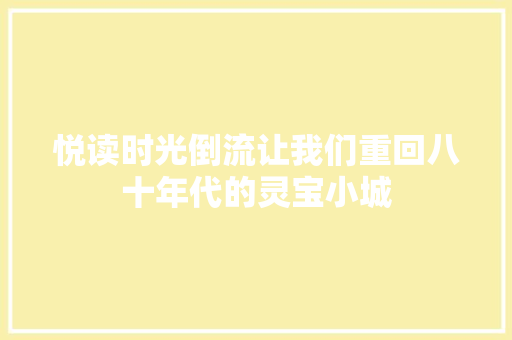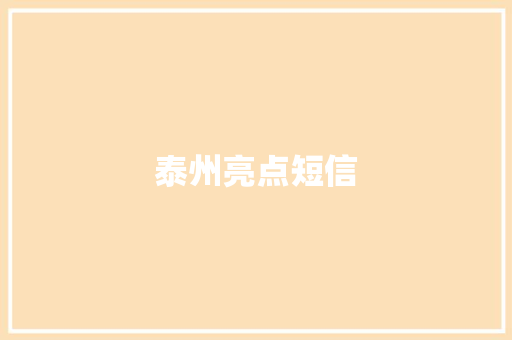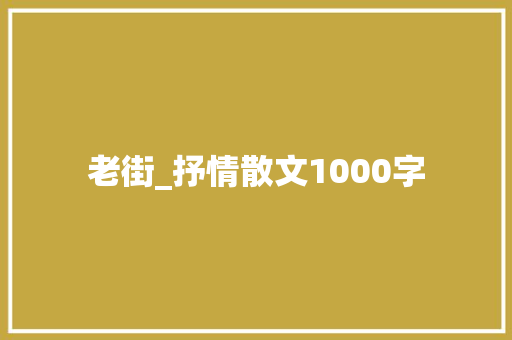老廖经营的林玲摄影馆,是奉城老城(位于今上海奉贤区奉城镇内)仅存的、“活”着的老街影象。千余米长的老街,曾是老城最热闹的集镇区域。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战火中,老城遗迹消逝大半,留下末了一段古城墙和一座重修的比丘尼道场;东、西、南、北老街,则随着此后一代代原住民的迁徙,变得冷落。
只有这气味湿润、灯时间暗的“三平方米”,以从前的面貌,陪伴老街度过了悠悠90载。老廖是继祖父、父亲之后,这间摄影馆的第三代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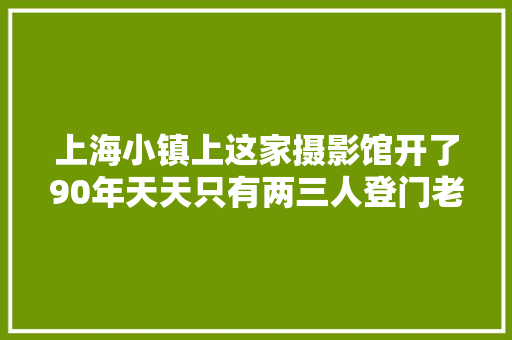
廖志维坚持每天开门,不忍心关掉它。只管摄影馆的经营,早已随老街一同沉寂下去,时常让等待与愿望徒劳无功。但它毕竟寄存了数不清的老街人青春的印记,寄存了老街曾经历过的日月星辰。
而即便不是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影象,老廖仍有不舍的情由:“就怕关了店,以前的邻居们认不得回来的路。”
廖志维和他三平米的拍照室。本文照片:杜晨薇/摄
失落落的匠人
“摄影能有多少技能?”这话从廖志维嘴里说出,不屑的洒脱中,带着那么几分物是人非的味道。
曾经何时,谁也想不到摄影这件事会从一门少部分人节制的精英技能,变成毫无门槛的遍及技能。举起手机,大家都可以是拍照师。前辈的摄影设备,可以高速、高清地记录下任何场景、任何画面,乃至把拍照师变成一个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行光与影的艺术创作的“傻瓜”。
躲不开技能改造的巨浪,廖志维成了最无奈的一代拍照人。
1930年,上海见过摄影机这一“泰西景”的人尚不多。凭着一身“洋技能”,廖志维的祖父林葆英把林玲摄影馆的前身,竹影轩摄影馆开在了奉城东街上。
祖父林葆英
这是当时全体浦南地区唯一的摄影馆。由于奇异,起初的买卖并不热闹。老城里的和周边城镇村落庄的人们乃至一度疑惑,假如被那黑突突的盒子“咔嚓”闪一下子,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侵害。
可猎奇是人类的本性。随着林葆英的拍照作品流传出去,越来越多的人踏进林家的大门,穿上自认为隆重的衣服,记录下宝贵的一瞬。一些不识字的顾客,哪怕从头到尾不认得“竹影轩”三个字,也清楚记住它在东街93号,并亲切地唤一声“林家摄影馆”。
林家摄影馆拍摄的老照片。
到了廖志维父亲手里,林家摄影馆真正迎来它的黄金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拍照渐成风气。市区的顾客知王开摄影馆,黄浦江南岸广袤的地皮上,“林家”的名头也颇为响亮。
白天,父亲和祖父扛着机器、骑上自行车四下劳碌,年仅几岁的廖志维就捡起一张张厚厚的胶片把玩。这是廖志维闯进拍照天下的起始点。最初,是学着摸胶片。书今年夜小的老胶片,一张仅能成像一次,这还是在准确安装的条件下。若是搞错正反面,拍摄的照片就“糊”了。廖志维摸索了大半年,总算过了这一关。
而接下来要口传心授的,是显影药水和定影药水的配方。在尚不能家家用电的时期,摄影馆做得是晴天买卖。林家的拍照室便是一处装着玻璃顶篷的小屋,屋顶挂着几条长长的布,光影变幻,就靠摆弄这几个布条的空间位置。遇上雨天,光芒不足了,就直接闭门谢客。而囿于每家摄影馆搭建的拍照棚光照条件均不相同,决定终极成像效果的这两种药水,就成了绝密的法宝。
“十几种化学身分,先加什么,后放什么,放多少量,是老一辈根据习气和拍照棚独特条件试验出来的。父亲把它们写在一张字条上,每次调药水,都要拿出药房用的小杆子称,仔细地确认,单位精确到‘钱’。我在一旁学习,错一次,药水报废;错两次,就要挨打了。”廖志维也记不得详细哪一年出师,但学徒的路走得并不随意马虎,廖志维终极还是放弃了学习修片和着色两个更高阶的环节。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一度公私合营的林家摄影馆又一次面临转制。当时已挑大梁的廖志维从公家手中接回摄影馆,正式更名为林玲摄影馆,重新开始了私人经营。原以为可以连续守着一成不变的技能过活,2000年前后,全国第一台数码相机正式进入上海市场,一代拍照人的技能动作随之转变。也是自那时起,摄影这门精英手艺开始跌下神坛。
从胶片相机的盛行,到数码相机的涌现,至少经历了两辈人。而一台数码相机从30万像素到3000万像素的演化,却只花了十数年。廖志维用半年韶光学会的第一代全英文电脑修图软件,则在更短的韶光里,完成了又一次的更新和升级。
廖志维时常还会反问几句,难道学了半辈子的手艺,就这样再也用不上了?答案略显残酷:再好的匠人,终将拜倒在高速迭代的技能面前。
摆弄动手中的数码相机,廖志维总以为自己身上少了点匠气。
回不去的老城故事
在拍照师的不雅观念里,韶光要精确到秒,乃至更小的单位。
胶片时期,按下气动球阀的速率和底片放入显影药水的韶光密切干系,为了让照片的感光效果达到最佳,拍照师必须反复练习,把握二者精确的函数关系;数码时期,拍照师不断调节光圈和快门速率,以便掌握进光量在最合理的区间,捕捉到最佳的图像效果。
这是这个职业独占的,对韶光的机警。然而,当时间被不断放大到以年计数、乃至以年代计数的时空观点里,拍照师却极有可能变得“木讷”。
直到奉城东街拓宽后很多年,廖志维才意识到,老城的辉煌再也回不去了。
改革开放后,老城开始拓路,青石板变水泥,临街的林家摄影馆个中一间屋子也为让路而拆除。城市化和当代化的进程,让每个老城人都为之振奋。老城里逐渐有了烟囱高筑的厂房,有了小汽车开进开出,有了外村落夫……
老城里那些须要办工厂事情证的、身份证的、企业单位证明的人,每个都要跑到林玲摄影馆,拍一张证件照。最劳碌的20世纪90年代初,廖志维的妻子缪彩珍索性辞了工厂里的事情,回家专职给老廖打下手。“那时候,一天接待几百个顾客是常有的事情。一家人齐上阵,都要轮着吃午饭才干得过来。”
老街上的工厂越来越多,像是某种潜在的置换条件,原住民则一个接着一个的搬走。有一些是由于生活条件好了,买了城镇里的屋子;有一些则是为了表面更多的选择和发展机会。像廖志维这样确当地经营户,陆陆续续都关了店门。老街上的人,看着面生。
廖志维的眼睛只盯着摄影机上那枚小小的取景器,并未察觉到这统统。老街坊虽然搬走了,须要拍照时,还是会专程跑回来找“林家”这块金字招牌。外乡的“新邻居”则把老城的拍照市场变得更大:他们不知足于廖志维供应的一寸照、两寸照的业务,提出新的哀求。
“这些打工仔几年回不了一趟老家,想在我这拍一张带背景的全身照,寄回家里给老人小孩报个安然。”廖志维便专程跑了一趟市区,买来几幅有山有水的背景板,依旧在那三平米大的小房间里,制造着人们的梦和念想。
直到有一天,廖志维不忙了。乃至在拍照室呆坐上一天,也不会有人上门叨扰。老廖恍然意识到,表面的天下变了。
老街上新开了几家摄影馆,有些乃至可以承接更加繁芜的婚纱拍照业务。证件照的拍摄也打破了场景的唯一性,身份证件照可以在派出所拍了,外来人口登记照可以在镇上的社保中央拍了,普通人哪怕举起手机随意按下快门,也能即时得到一张自拍照。“谁会专门跑一趟,来寻我这个老头目呢。”
当然,这还不敷以抹杀一个老拍照师的自傲心。强烈的挫败感来自长期坚持的习气,有天被剖断是错的。
这几年,开始不断有人“责怪”,廖志维那些把人脸拍出明暗面光影效果的证件照“弗成”。人们哀求他,“把脸再P(修图)白一点”。白,更白,白到五官不再有阴影层次和立体感时,处于强烈的抵牾和自我疑惑中的廖志维,却总能听到一句来自顾客的“感激”。
这还是原来的老城吗?廖志维从来不敢想这个问题。
客人时常会提出哀求,照片要P得更白一些。
准百年迈店的隐痛
今年是林玲摄影馆经营史上的第90年。多数老客人临走时不忘补一句玩笑:小林,你这里很快便是百年迈店了呀。
小林便是老廖,十几岁时就从了母姓“廖”,但老城里的旧相识依然改不了口。就像老廖该当姓林一样,人们以为,这家摄影馆,也该当永久姓林。
结束几十年的公私合营后,廖志维把曾更名为奉城摄影馆的小店,重新换上了林家的招牌,林玲摄影馆。
“林”,自不用说,而“玲”,则取了女儿的名字。老廖的心思浅近:他想让女儿把小店传承下去,开成真正的百年迈店。
“要说开店不是为了赢利,那肯定是假话。”老廖的店,虽是自家买卖,没有房租本钱,但只要开着门,总要牵扯人力进去。如今营收惨淡,一个月的买卖只够零散补贴家用。老廖几次想着“要不要涨点儿价?”想想又作罢。
林玲摄影馆至今仍沿用10年前的价格体系,一寸照15元,两寸照20元,即便周围其他摄影馆的价格已翻至两倍以上。
但寂寥的老城,命运已注定——随着近年来周边工厂的陆续关停,老街上的住户又一次选择搬离,林玲摄影馆虽颇具价格上风,依然逃不开门庭冷落的结局。
老廖也曾试着把摄影馆迁到人流密集的奉城镇沿街店铺里。可不到半年光景,林玲摄影馆还是回了原址。“的确,买卖好了,可好多老顾客都不认了,说那是冒牌的‘林玲’。我还折腾什么呢。”
廖志维想起一桩往事。2000年初,作为上海当时为数不多节制修图技能和数码摄影机技能的拍照师,柯达公司曾组织了一批在市中央开店的“老法师”远赴奉城老街,找廖志维取经。当时就有人劝老廖,乡下拍照的人毕竟少,去市里开个店,准火。
老廖没走,个中原因如今也很难说清,可能包括难以承担的本钱,以及背井离乡再立门户的风险。老廖乃至怕,“关了店,以前的邻居们就认不得回来的路咯。”
总之,老廖和这条老街,深深地捆绑在了一起。离了老街,林玲摄影馆就不再是准“百年迈店”。而离了这家摄影馆,老街也将失落去末了的、活的历史记录者。
那天和廖志维聊了足足一个下午,未见到一位顾客登门。临走时我问廖叔,“能帮我拍张照吗?我不要P(修图)白的那种。”廖志维爽快答应。
他起身从裤兜取出一串钥匙,用里面最短的那一把打开了书桌左侧的抽屉,取出一台数码相机,并示意我,坐在蓝色的背景板前。他像个指挥战事的将军,勾引我如何转头、摆手,统统落停的瞬间,他抓起相机按动快门,成了。
那一刻的廖志维,眼睛里有光。
廖志维与他的林玲摄影馆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通报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缺点或陵犯了您的合法权柄,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