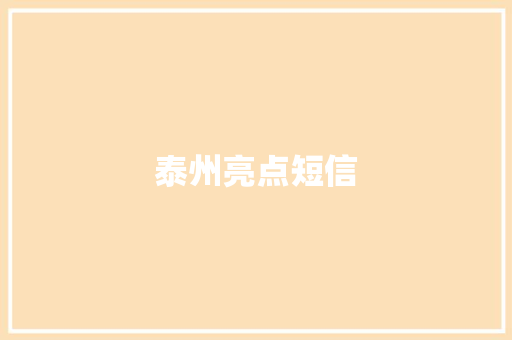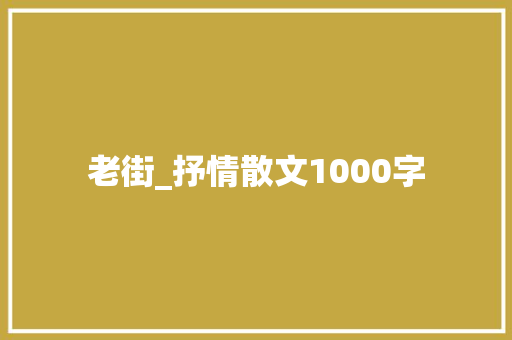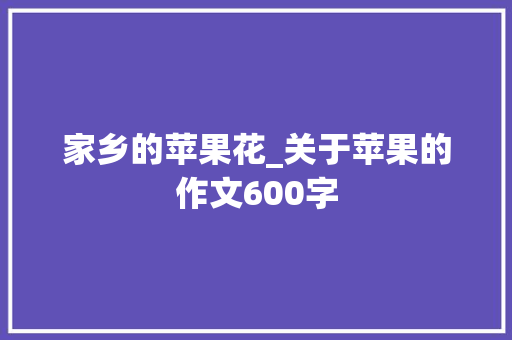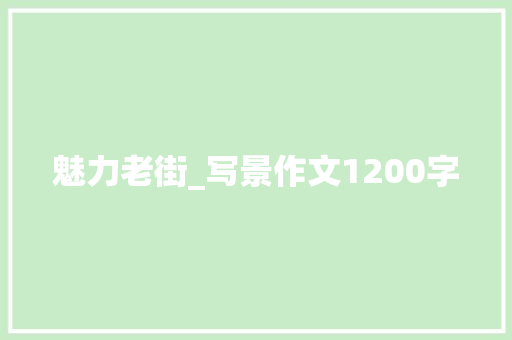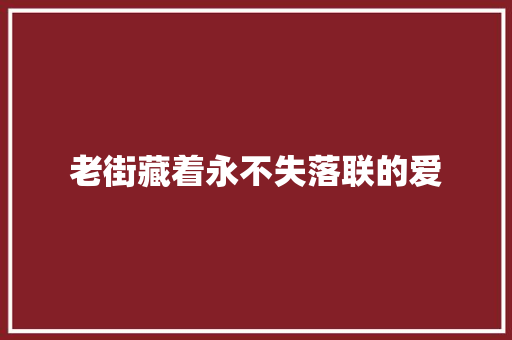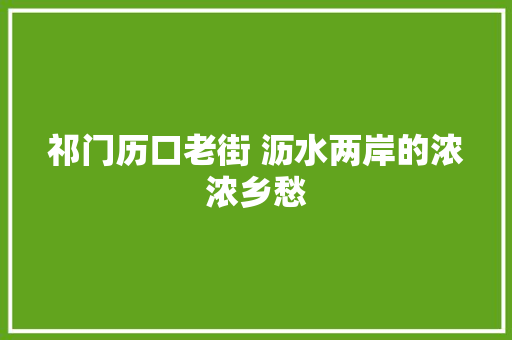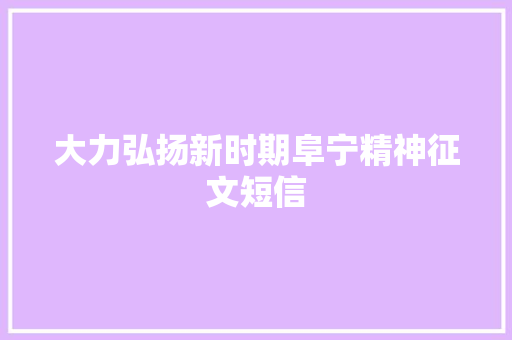我要用笔墨重修一座城市。
在我的笔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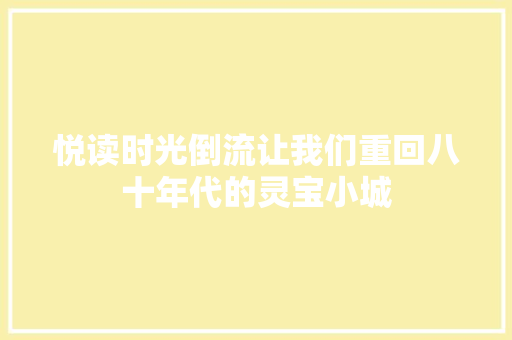
韶光倒流,否极泰来,
消逝的气味、声音和光芒被召回,
被拆除的院落,小巷和各种建筑恢复原貌,
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涯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
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革,居民们胸有方向感。
——题记(北岛)
八十年代的灵宝小城
八十年代初的灵宝县城,从色彩上来讲还是略带一些灰暗的,县城里的各式建筑大都是青砖灰瓦,低矮破败,给人一种迂腐的岁月感。大概由于县城太小的缘故,那时的天空非常的辽远高阔,湛蓝湛蓝的,宁静,深邃,好似一壁清澈无尘的湖,又仿佛一个漂渺漾荡的梦。刚刚进入改革开放之初的灵宝城,仍旧还保留有岁月沉淀下来的古朴和宁静。
清晨时分,东边天涯连绵的土塬之上跃起一轮朝阳,将全体小城拢在了她光辉的怀里,鸟雀们在枝头细碎鸣叫,灰色的鸽子在晨光里扑闪着翅膀飞来飞去,骑着自行车上班的大人从清洁的街道上一掠而过,三三两两的孩童屁股后面吊着个大书包浪花般穿行在大街小巷,县城南边的陇海铁路上时有老式火车轰隆隆奔跑而来,长笛冲天,蒸汽环抱,远处的娘娘山俊秀,多情,尽显妍丽姿态。
彼时的小城不大,只有纵横五条街道,大片大片的田地和菜园围拢在它的四周。乡下的人要进城,必要从街道两旁葱郁茂盛的菜园边经由。夏日里,火红的辣椒,鲜嫩的黄瓜,紫色的茄子,垂挂的豆角交织而成的田园风光,引得孩子们馋涎欲滴,放慢了脚步,瞅四下无人,猫着腰哧溜一下钻进菜地,摸几个西红柿,摘两根嫩黄瓜,偷偷装到书包里,然后伪装若无其事,一起欢呼着飞跑而去。
三十多年前的灵宝城,宛若一幅画,又似一首诗,总会令人在漫长的岁月中自心头想起,念念不忘。
新华路
新华路过去被称作老街,也便是从东关桥西到灵宝浴池的这一段路。既然被称作老街,想必过往该当商铺繁杂,热闹非常。但在八十年代初,这里只有零散几家商铺,且大都是些花圈店缝纫店茶馆之类的小模营生。除过街道两旁的老屋子外,老街的西头,东头和中间地带,夹杂有大量低矮凌乱的院落,聚拢着小城里的各色人等,纷杂,繁盛热闹繁荣,烟火味道十足。老街自东向西依次分布有决镇三小,决镇医院,老街茶馆、废品收购站,文化馆,灯光球场、电影院、灵宝浴池、实验小学等单位。
决镇三小在老街东,与决镇医院一南一北隔街相望。学校不大,房屋老旧,院子正中生有几棵老槐,亭亭如盖,枝叶繁茂,多数校舍都遮蔽在它的荫凉里。每至春天,槐花盛开,暗香扑鼻,即便站在老街上,也能闻到飘散而来的甘甜味道。记得学校里一个姓武的数学老师,敲得一手绝妙的木琴。晚饭过后,便将木琴搬至院中,在夜色即将弥漫开来之际,兴之所至,敲上一曲,或清脆,或幽怨,或冲动大方,或缠绵,煞是好听。听其他同学讲,武老师是南阳人,妻儿老小全在老家,他背井离乡来灵宝做民办西席,心里相思的苦全请托给了手里的木琴。
老街茶馆位于大南巷北头,只一间木架构造的瓦房,置三五张木桌,摆八九条长凳。茶馆正中,生有一炉煤火,上面坐一只铁壶,整日里突突突地冒着热气。不大的茶馆内面,烟雾环抱,人声喧哗,弥漫着人生的千般滋味。但凡遇有执绋或迎亲的军队从茶馆门前经由的话,茶馆里常日会有热心人拉出一条长凳,摆放在老街中间,然后搁上两盒喷鼻香烟,拦住行进的军队,让门上的乐队在此热闹奏乐一番。或一曲《百鸟朝凤》,或一曲《三哭殿》,吹得新娘娇滴滴,吹得孝子泪涟涟,吹得天是蓝莹莹,吹得地是悲戚戚,吹得围不雅观的人越来越多。这场面,这架势,既长了主家的脸面,又让老街的人情光滑油滑四散开来,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
县文化馆居于老街中段,坐北朝南,与弘农路相接,构成了一个丁字路口。逢年过节,这里最为热闹,炒凉粉的小摊,炸糖糕的油锅,卖黄酒的农夫,捏糖人的大爷,卖葵花子的奶奶,还有摆小人书的白头发老头儿……,随便那一样,都会令人在清贫的生活里生出热切的愿望。正月十五元宵节,文化馆门前猜谜语,灯光球场看篮球,电影院里人挤人,还有培植村落解放村落的社火队和舞龙灯,愣是把这一道宽不敷十米的悠长街道渲染得流光溢彩,如梦如幻。
灵宝小城的沧桑岁月全都铺陈在老街上,在她古旧的房檐上,在她醇厚的人情中,在她生生不息飘荡绵延的气息中......
弘农路
顺着文化馆向南走,便是现在的弘农路了。
不记得这道街过去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那时的街道两侧大都是一些老式的门面房,大约该当是解放前的屋子吧。路西,第三食堂五大间大瓦房,内面全都是卖吃食的,鏊子上的炒生平凉粉,热气腾腾,喷鼻香味满屋;还有一桶桶凝脂如玉的豆腐脑,小风箱把火弄得旺旺的,小葱、喷鼻香菜、黄豆、芹丁,再加上一点儿本地出产的红薯粉条,在锅里咕嘟咕嘟翻滚着,色喷鼻香味俱佳,引人胃口,不克不及自休。路东,大都是些公私合营的门市部,有修锁的修钢笔的还有卖碗卖秤的。公私合营的南边是当时灵宝最大的医药门市部,两层小楼,青砖红瓦,很是古朴,听说是一位留俄回来的大户人家的子弟设计的。木楼梯木地板,走起来吱吱呀呀的,每次都把我们这些附近的孩子吓得忐忑不定。
医药门市部南边,有一家是卖布的——花木兰门市部。木制柜台上摆放着各种被称作洋布的机制布匹,品种丰富,色彩绚丽。最有趣的是收帐时,售货员用一个铁夹子,夹着钱、布票和发票,哧溜一下甩出去。只见铁丝线上的票夹子吱吱吜吜地叫着飞到了收帐台。然后,收账员一番忙活后,票夹子又吱吱吜吜带着尖叫飞到了柜台上,煞是好看。那时候,最贵的布便是的确良,能买起这种布料的至少都是吃商品粮或者双职工,他们拿着单位配发的布票,从门市部出来时的眼神里不乏高人一等的优胜。
再往前便是猪娃市场、糖烟酒公司和饮食做事公司开的卤肉店。碰着集市,这儿啥都卖,乡下窑上出的瓦盆瓦罐,上了深釉的大水瓮大陶盆,苇编的席子,铁匠铺里低廉甜头的镰刀、斧头、锄头,还有铡刀麦叉,明晃晃寒气逼人,却总是引得过往行人乐不思蜀。影象最深的是猪娃市场临街处有个老摄影馆,表面玻璃橱窗里挂着大大小小的人物肖像照片。蹲在一旁,盯着着照片里那些陌生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只一下子,心里就会被照片里的人看得发毛,赶紧一起悻悻跑掉。
少年时期,任何一件细微的事情,都会带给人莫大的欢快和遐思。如今回忆起来,就像是饮下一杯陈年迈酒,余味悠长,只愿岁月长留,沉醉不醒。
新灵路
沿着弘农路一起向南,过搬运社大院、副食品店、回民食堂、新灵食堂,就到了县城的十字路口。从十字路口向西走,新灵路临街的各式门店和各家单位依次呈现。若从建筑风格来看,这条街比较于其它街道更为体面和气派。当时,这里是灵宝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央。
百货楼位于十字路口西南处,两层楼房。一楼卖日用百货,二楼卖大件商品,诸如自行车、缝纫机等之类的东西。上初中时,最喜好逛的是一楼的学习用品柜台,玻璃柜台里摆摊开花花绿绿的各式钢笔,常惹得人眼睛发直、发光。犹记得二楼有一个柜台专门买橡胶雨鞋,每次从前面经由都梦想着自己能拥有一双,不才雨天穿着它,无比骄傲和自满地从水潭泥坑里一趟而过。可惜,这个心愿一贯都未能实现。
百货楼西边,是大楼理发店。全县城的人大概都在此理发。在这儿理发要排队期待。星期天,大人看孩子的头发长得跟茅草一样,便会给上五毛钱让我们自个去理发。坐在大楼理发店前厅的长条木椅上,两只眼睛骨碌碌地瞅着内面的理发师傅,心里有一种难言的滋味。但见一个白胖胖的高个男师傅,右手操一刮刀,左手持一条长布,刀迅疾地飞起,落下;落下,又飞起,在布条上面“唰唰唰”地蹭着,寒光四射,甚为吓人,搞得我们心里蹦蹦乱跳,无论怎么讲,对付孩子们而言,剃头永久都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
大楼理发店往西,过大楼饭店,便是老邮局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老邮局门前可以说是县城里最繁华的一个地方了。碰着好天气,或者是周末,来邮局门前办事或是闲逛的人就会特殊的多,有背着绿挎包来寄信的小战士,有颤微着脚步来取款的老大爷,有刚长出青青胡渣的高中生,也有从附近村落庄里跑来逛街的大姑娘,人来人往的,颇为热闹。而这里最吸引人的还是要数邮局斜对面五四储蓄所门前那一块空地了,那儿有卖老鼠药的,有卖跌打损伤丸的,还有走江湖的耍猴人和练硬气功的手艺人——他们手中的铜锣咣咣一响,周围的人潮水一样涌来,自觉地站成一个圆圈,各自伸长了脖颈,瞪大了眼睛,那种既好奇又愉快的神色,好似一只只惊觉的鹅。
对付我们这些读初中的孩子来说,则常常会溜到与邮局一街之隔的新华书店,挨着一节节的玻璃柜台,瞅一瞅书架上的新书,看一看挂在墙上的年画,然后摸摸空空的口袋又一起小跑来到老邮局门前,蹲在卖邮票的小摊前,把人家的邮册捧到面前,一边大惊小呼,一边细细不雅观赏,目光中尽是贪婪和无奈;有时就干脆站在卖杂志报刊的小书摊前,一本一本,把手中的杂志翻得哗哗乱响,直气得书摊的主人一直地朝我们翻白眼,我们才讪笑着哈哈走开。
再往西走。街北,依次是县委大院、武装部和公安局;街南,分别是部队留守处、县委党校和影剧院。
影象当中最难堪忘的有两处地方。一个是新华大楼门前的广场,每年都要举行公审大会。一溜儿解放牌大卡车森严地排列开去,罪犯们全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写有罪名的硬纸牌子,一个个低头垂立,神色惨白,仿佛在后悔着自己的罪过。这一天,小城里万人空巷,大家都不谋而合搜集在这里,愉快的就像过节似的。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大概都太过于寂寞清净了吧。其余一处地方便是公安局大门靠左的布告墙,每过几个月都要贴出一张公民法院的布告。看布告的人很多,尤其是刚帖出来那几天,常会引来一些闲人聚在那里指手指脚,说个一直。放学回来,我们这些孩子也要站在布告前看上一下子,一行一行地去读发生在这个县城的各种案子。那些稀奇古怪的刑事案件和年事大小不等的各色案犯常常将我置入一种深深的恐怖当中。但高兴的是法院院长在布告下面的那一个署名和那一个红勾儿,总让我以为那个姓潘的院长只需用红颜色的笔轻轻一抹,人间间的各类邪恶将会统统被一笔挥去。
在这条街上,我对好几个人都有着不能磨灭的深刻印象。
我上初三那会儿,小县城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被活气盎然的东风撞了个满怀,影象最深的是街上开始盛行喇叭裤和花卷头了。县委大院有一个刚从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青年男子,穿一条喇叭裤,留一头茂密的长发。放工时,骑辆飞鸽牌自行车,一手捉车把,一手提个录音机,骄傲地仰着头,从街上飞驰而过。走老远了,还能听得见录音机里传来的“哐当哐当”的音乐声。回到家很好奇,把这些见告大人,大人瞪着个眼睛训斥我,让我不要学坏。彷佛他的孩子只要穿上喇叭裤,烫个花卷头,就会成为街上的小混混小泼皮一样。
影剧院门口铁皮屋子前,常年摆有一个打脂油烧饼的小摊。经营摊位的是一对老年夫妇。男的精瘦干练,眼睛里有光;女的敦厚和蔼,目光里有爱。他们打起脂油烧饼来,熟谙,优雅,虔诚而富有激情亲切,好似在从事一项无比神圣的奇迹,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苟地恪守着传统的手艺,做出的饼子又脆又软,诱人垂诞,在小城里享有极高的盛誉,分明是光阴酿造的美食。
在这条街上,还常常会看到一位老红军(听说做过毛主席的警卫员)。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小,精神矍铄,着一身绿军装,无论晨昏,都定时在影剧院的广场上踱步。有次,在清晨的阳光中,我看到老红军的身边有成群的鸽子拍打着翅膀咕咕叫着飞向天空,老人凝神而立,目光沉静悠远。天地之间,顿觉老人犹显高大,使人不禁肃然起敬。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老红军是神一样的存在,他的周身无时无刻不散发着一种摄民气魄的残酷光辉。
黄河路
从公安局西边往南拐,便是后来才建成的黄河路。1985年,我上初中时,这条路上还是颇有一些寂寥和空落的,要等很永劫光,才会看到一辆拉砖的车笨重地从街上驰过。到了高中,这里就完备变了样子容貌,先是零零散星有了摩托车,一年两年一过,摩托车已经不再稀奇了,一辆接着一辆,相继而来。逐渐地,吉普车和拉达车也会从满是坑洼的道路上携带着一起灰尘飞驰而去。
曾经落寞的黄河路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盛热闹繁荣。
八十年代中期,黄河路西边还没有开拓,全是一垄一垄的田地,种着各种季候蔬菜。那时,武侠热刚刚兴起。每到放学,我们几个孩子,就跑到对面的田里,找一块草地,练习“鲤鱼打挺”。躺在杂草丛生的地里,蚂蚱从面前跳过,狗尾巴草在头顶晃动。我们并排躺着,用尽全身的力气,扑腾扑腾地打个一直,直打到太阳落山,还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功。索性,我们就找个废弃的树桩,一只脚站在上面,做金鸡独立,或是雄鹰展翅,尔后,像个兔子似的满地里飞窜,抱负着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那个飞檐走壁替天行道的武林高手。
与公安局后院一墙之隔的是县蒲剧团。蒲剧团是个两层小楼。平时有演出,蒲剧团的院子就会显得格外的寂静,房檐上或是树梢间会落着一些灰色的麻雀,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不但没有给这院落里增长上几分热闹,反倒让这儿更为寂寥和落寞了。一旦演出归来,小小的一方院落里,立即就充斥着一种特殊喜庆和欢畅的繁盛热闹繁荣。天还没亮,便有“咿咿呀呀”的唱戏声一波三折地响起,环抱在灰蒙蒙的天空久久不散。那个年代,团里比较有名的演员,我记得住名字的有李金霞、赵瑞和贺明礼。至于他们演过什么角色和剧目,还是孩子的我倒是不十分关心。听父亲讲,演旦角的李金霞是个厉害角色,曾经得到过李宗仁和清朝末了一个天子溥仪的接见。在我眼中,这个女人一定是妖娆万分、顾盼流转、让人分外着迷的。但当我在邻居的指引下远远看到她时,心里却有一种深重的失落落。已经上了年纪的她身材发胖,头发缭乱,脸庞干瘪,步态笨重,怎么都无法和我心中那个在戏台上轻盈如飞、婀娜多姿的青衣相提并论。看来,流逝而去的不仅是过往的岁月,还有那似梦的青春,如花的笑魇。
每至冬天,年已垂老的孟老师(灵宝一高的一位美术西席)都要牵着老伴的手坐在黄河路上的道沿上晒太阳。他总是歪着头,幸福而又眷恋地看着面前多病的老伴。有时,他会取出个小剪,捉着老伴的手,收视反听地给她剪指甲。他那始终充满怜惜和关爱的眼神,让我一次次体味到相守终老所饱含着的无限深情。
蒲剧团门口那间平房上翻跟头的姐弟俩,不管刮风下雨,准会涌如今房顶上练功。他们的年事大约只有八九岁,身材瘦小,肤色暗红,翻起跟头来像飞转的风车,令人眼花缭乱,惊为异人。
我曾经在这条街上住了六年,这里的统统都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永恒的影象。
弘农涧河和西华土塬
八十年代初的灵宝城,基本上以涧河为界。弘农涧河以西,西华土塬以东,这中间地带,即是小小的灵宝城。
我幼时住在老街,最喜好去的地方便是河坝滩。人们口头上的“河坝滩”也便是现在的涧河西岸。站在用石头砌成的堤坝上放眼望去,清澈舒缓的涧河水蜿蜒流淌,一起向北;横架在河水之上的木架桥,在清晨的晨曦中迎来了从东关村落疾步走来的村落夫小贩。他们或担着吱吱呀呀一起作响的豆腐挑子,或挎着新鲜的带有泥土露珠的季候蔬菜,一摇三晃,颤颤巍巍走过木架桥,将一串串响亮清脆的叫卖声连着片片白云,撒向湛蓝宁静的天空。到了夏日,这里便成了城里人最常去的地方。放学归来,少年们三五结伴,踩一地跳跃的阳光,飞奔至此,戏水打闹,笑语飞扬;夕阳西下,洗衣回家的姑娘眉眼含笑,身姿婀娜,宛如天上的云彩,俏丽动人;夜色来临,清风拂面,乘凉的人儿两两三三,清闲溜达,只管已是月上枝头,繁星满天,仍迟迟不愿归去。
当然,涧河水也不是一年四季都这样清柔动人。到了夏天,一场暴雨之后,全体涧河河道就会从上游涌荡而来一河的滔滔黄汤,激流澎湃,颇为壮不雅观。这便是小城人嘴上说的“发大水了”。围不雅观大水的人总是很多,胆大的站在堤坝上,胆小的就躲在堤坝下探出头来,露出一脸愉快的神色。有时候,彭湃的河水中会漂浮着一只挣扎扭动的猪,这种场面顿时让大家沸腾了起来,嗷嗷叫着,场面极为壮不雅观,跟过年一样。
新灵桥下也是个有趣的地方,这里的牲口市场最好玩。逢五逢十,四乡八村落的农夫牵着毛驴、黄牛、骡子和马赶到这里进行交易卖买。尤其到了中午,河滩上最为繁盛热闹繁荣,到处都是牲口的叫声。牛的“哞哞”,马的“嘶嘶”,驴的“啊喔啊喔”,和着喧哗的人声、欢畅的流水声,合奏出一曲人间的欢唱。最能迷住孩子的,是新灵桥下面一个专为牲口钉掌的铺子。钉掌的伙计腰上系一圈皮质的围裙,往马或是骡子前面凛然一站,宛若一根深扎在地里的木桩。只见他弓下腰身,把牲口的一只蹄掌搂在怀中,先是用锋利的刀具将它们僵硬的老旧蹄掌一刀一刀剔去,然后拣起一个在水中浸泡了许久的蹄铁,右手持一只小锤,叮叮当当,就在一串美妙的音乐声中轻快地完成了手里的活计。孩子们蹲在地上,围成一圈,痴迷地看着,被钉掌师傅娴熟的技艺深深折服,以为这个天下原来竟是这样的有趣和神奇。看完钉掌,仍不想走,就会弯腰捡拾一些掉落在地上的蹄掌放在口袋里。回去后,偷偷把它们埋在花盆中。听大人们说,这是最好的肥料。
逛完牲口市场,就沿着涧河的堤坝一起向南,去到火车大桥那里看稀奇。夏日里,涧河水悠悠地流,知了吱吱地唱,河边的杨柳在微风里轻轻地摇,远处高大宏伟的铁路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森森然带有一种神秘的庄严。在孩子们眼里,火车桥和火车桥上驶过的火车,带走了我们年少时多少的渴望和期盼。那通向外部天下的铁轨,像影象一样长。
在城关中学读初中时,每逢下午放学,我们这些野小子常常会结伴而行,跑到西华塬上看火车。站在火车道边,仰着一张稚嫩的小脸,目视着冒着白色浓雾的蒸汽火车从城南的陇海铁路上哐当哐当驶来,既愉快又害怕。当火车带着巨大的声浪从身旁一驰而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紧捂耳朵,呈现出一脸的惊骇。这俏丽而又蛮横的火车啊,什么时候才能载上少年的心奔向远方?
最让人惬意愉快的还是站在西华塬上举目东望。此刻,灵宝小城尽收眼底,一览无遗。视线的远处,全是火柴盒一样拥挤的灰色屋子。傍晚时,近处的西华村落会有缕缕炊烟袅袅升向天空,并伴有依稀可闻的鸡鸣狗叫声。暮色将临,塬上的风轻拂而来,我们几个半大小子一边仔细地在瓦浪般排向天涯的小房子里搜索着自己的家,一边愉快地手舞足蹈大呼小叫,彷佛一棵棵迎风站立的小树,每一片枝叶都饱含着翠绿欲滴的情愫。
八十年代的灵宝小城,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幻化成了心头永久的回顾。那个稚嫩的调皮小儿,懵懂的快乐顽童,青涩的骑行少年,像风一样穿行在她的胸襟和怀抱里,走过了生命中最清纯最美好的年华。三十多年后的本日,昔日的那个孩子已经鬓染秋霜,人至中年。但关于小城的镜像和影象,他都记得,一刻也未曾忘却,一刻也不敢忘却。我的灵宝我的城啊,纵使我已苍苍白发,垂老晚年,想起你来,我都会在莞然一笑中生出无限的感慨和眷恋……
作者:石子
来源:中国金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