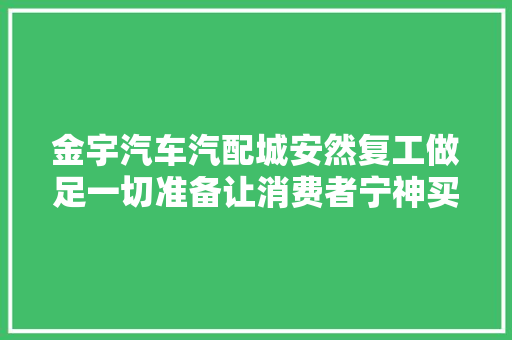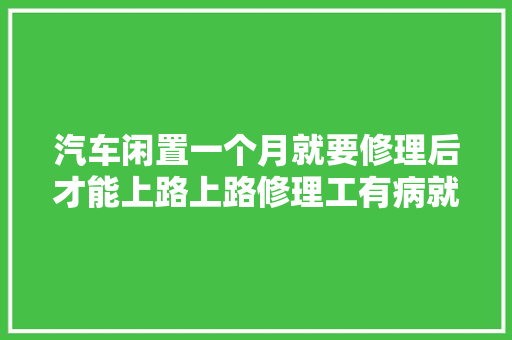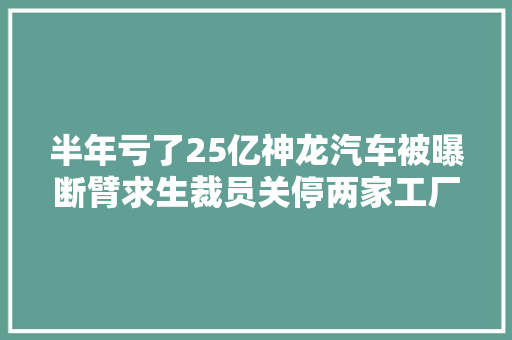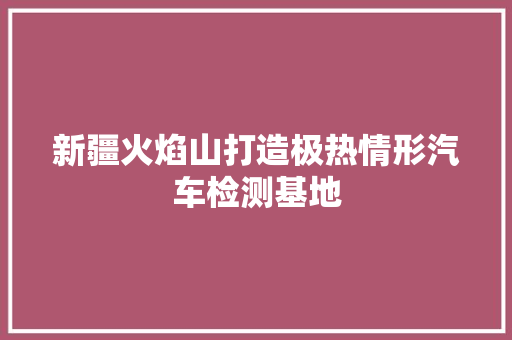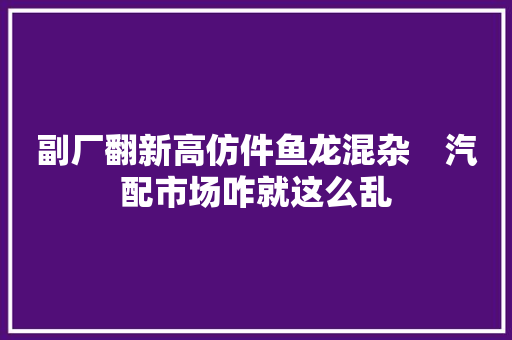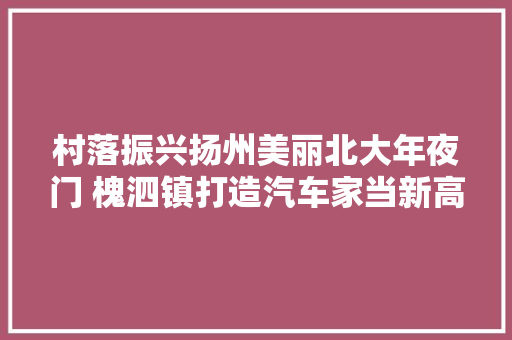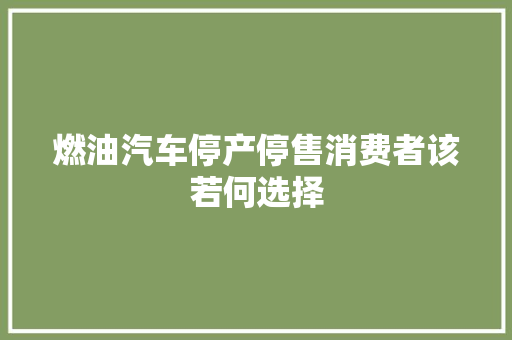兵团人白手起身,艰巨奋斗,虔诚履行着国家授予的屯垦戍边的光荣义务,把亘古戈壁荒原改造成生态绿洲,建起了一座座新型城镇。兵团为推动新疆发展、匆匆进民族联络、掩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在兵团人屯垦戍边的岁月中,特殊是初创期间,一个曾发挥过独特浸染的群体--汽车驾驶员,被着墨较少。为了让众人认识他们、记住他们,特以此文追忆这一群体,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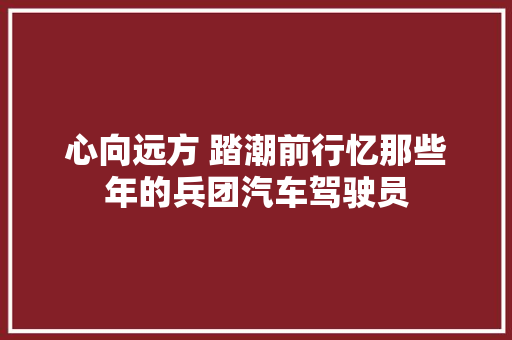
勤勤恳恳先锋兵
新疆地域辽阔,解放初期,交通极其不便,特殊是南疆地区,根本没有像样的公路,只有驼队踩出的蹄印小道,随着风沙的肆虐,只能依稀辨认。当时,新疆各族群众的生活品供应也十分匮乏。以伊犁、塔城地区为例,市场上的纸张、肥皂和瓷器等百货都是清一色从霍尔果斯入口的苏联货。连少数民族群众喜饮用的砖茶,亦是由中国东北地区出口到苏联,经调换外包装后又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口到新疆。记得笔者当年参加六道湾露天煤矿开挖时,利用的劳动工具坎土曼也是从苏联入口的。当时新疆首府--迪化市(现乌鲁木齐市)马路不平、电灯不亮,城市居民用水仅靠浩瀚的毛驴车拉运供售。至于铁路,名义上已通车至甘肃省兰州市,但由于宝鸡至天水段隧道塌方,实际只能至陕西省西安市。
面对这种状况,当时新疆军民所需的粮食、布匹、日用百货、五金配件和军队装备,只能靠那时的2个汽车团、3个汽车独立营来承担运输任务,汽车兵们奔驶在南北疆和远赴兰州、西安数千公里的运输线上。
当时承担最大宗的运输任务,一是粮食,由于新疆在这一块还无法自给,特殊是军粮,靠向内地购买后运回新疆,此项任务一贯持续到部队开垦种粮,粮食收成能自给才停滞。上世纪60年代后期,北疆各农业师向南疆新建师调粮,又掀起“北粮南调”的运粮小高潮,亦有数年之久。二是大量职员进疆,当初八千湘女赴天山,以及后来被誉为戈壁母亲、恒河沙数的山东女兵参军进疆,她们都是在陕西省西安市或甘肃省兰州市下火车后,乘解放牌卡车进疆的。兵团汽车驾驶员起早贪黑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军人素养,都成为她们进疆途中难以忘怀的影象。
1956年,河南大批支疆来兵团职员在甘肃省武威站下火车后,搭乘卡车进疆,首先打仗到的兵团人便是汽车驾驶员。驾驶员激情亲切的接待做事、娴熟的驾驶技能,使他们安然顺利到达兵团各师团,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影象。
后来,纵然火车已通达新疆,上世纪60年代初期10万上海支青抵达乌鲁木齐,下火车后分别奔赴兵团各师团所在地,亦是汽车驾驶员承担的重任。
为了尽快改变新疆掉队的工业面貌,部队节衣缩食,两年发一套棉军服,毛巾也减发1条,每月仅几块钱的津贴费只领取一半,另一半投入到培植中去。随着经济培植序幕的拉开,在乌鲁木齐首批培植的八一钢铁厂(系上海某钢铁厂整体迁居)、七一棉纺织厂、八一壁粉厂、火电厂和苏联援华项目十月汽车修配厂(后为十月拖沓机厂),以及关乎民生的各地州的八一壁粉厂培植等项目,从每一颗螺丝钉、单机到整套机器设备,都是靠汽车从西安、兰州火车站分别运抵新疆的。从上海增援新疆培植的钢铁、纺织家当工人、技能骨干和管理职员都是搭乘军用卡车进新疆的。大批汽车驾驶员除费力外,还要确保职员和运输物资的安全。兵团的汽车驾驶员是名实符合的先锋兵。
车轮滚滚遍全疆
随着全疆经济培植的全面铺开,兵地培植项目纷纭上马,兵团汽车驾驶员又迈入新的征程。
农一师(现一师)建筑阿克苏至阿拉尔、延伸至塔里木的公路时,汽车驾驶员们承担运输沙石料的任务,长年累月吃住在临时工地上。某汽车连远在喀什地区,驾驶员的妻子们也只得分批来工地上探亲。建筑铁门关水电站时,由于工程的须要,驾驶员们须要常年住在深山沟里,住的是帐篷,历经酷暑和隆冬,没有电,自己白天发电,只供汽车修理用;晚上从帐篷的缝隙中睁眼看着玉轮,还要承受虫叮蚊咬,直到水电站建成。历时数年的“北粮南调”、开拓克拉玛依油田、和田机场的建筑、兰新铁路新疆境内的建筑,各类各样都留下了汽车驾驶员的脚印和车轮滚滚的印迹。至于农业团(场)从开垦到年底的农资供应、粮食调拨是年年都须要承担的运输任务。
开拓克拉玛依油田时的物资运输任务颇为艰辛,可以说因此命相搏。
1956年克拉玛依油田开拓时,需从霍尔果斯口岸将一批入口的苏联产石油钻杆和无缝钢管运抵克拉玛依及其腹地乌尔禾,当时既没有特型车,又没有大吨位的载重卡车,部队的军车还是从沙场缴获的美国1944年产的T-234载重两吨半的大道奇车,但这些钻杆和钢管均超长,装载时的平衡和固定是大难题。驾驶员们就在驾驶室两边车厢板前后各开一个与钢管直径相同的洞,穿过前后洞一边装1根,其长度超出车长3米多,虽然做了固定,但在行驶中由于晃运的惯性浸染,汽车一蹶一跳地困难行进,像大海波涛中的小舟。
特殊是途经果子沟下山坡时,山路又陡又长,车辆的前冲劲和颠簸度已达到车速可掌握的极限,稍有不慎将车毁人亡,每一趟运送都似一次闯关。更苦的是由于钢管的阻挡,两边驾驶室门都无法开启,驾驶员只好从车的边窗里爬进爬出,身高体壮的驾驶员进出更加困难,为了减少进出次数,驾驶员只得只管即便少喝水,用饭托同行的战友带点馒头和咸菜在车内吃。就这样,奋战两年多,汽车驾驶员完成了这次以命相搏的运输任务,圆满完成了保障克拉玛依油田开拓中急需而关键的物资运输任务。
昼夜兼程运粮食
上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自然磨难的影响,汽车驾驶员承担的运输任务更加繁重。奉命将南疆各地州县粮库内多年的存粮分别运往库尔勒机场,再由飞机、火车转运往内地救灾。那时兰新铁路只通到吐鲁番火车站,汽车驾驶员昼夜兼程,团营连各级干部也随车共同奔驶在千里运输线上,确保粮食运输的安全。
当时,汽车驾驶员们吃的因此石河子八一糖厂榨完糖的下脚料(即糖萝卜渣)为馅的“水晶”包子,馅中残留的石灰渣时时时硌牙,糖萝卜渣纤维极粗,真是难以下咽。机关干部去农六师(现六师)收割过的苜蓿地里,用手选取残留的苜蓿茬子,回来跺碎和点玉米面蒸来吃。偶尔也能发下一点大米,只够煮粥喝。面对满车装载的一包包小麦、玉米,谁也没有动一粒,由于他们深深懂得,这是内地公民的救命粮。
当时,为理解决橡胶轮胎奇缺的问题,某汽车营修理连在连长带领下,制作现今看来弗成思议的和不科学的木质“钢板”和木头轮胎,他们把榆木按轮胎形状、尺寸分解成多少模块,再拼装,又用长螺丝串联成型,外层包上废橡胶轮胎的外层胶皮贴面,放在汽车后轮与橡胶轮胎搭配利用。木质钢板制成后,与钢质钢板按1:3的比例搭配,紧张供拖车利用,这样使车轮动了起来。记得汽车驾驶员李凤龙等驾驶的3辆车从莫索湾垦区返程回乌鲁木齐时,由于木头轮包裹的胶皮已部分脱落,路子西大桥时,在大街上发出“伯脱伯脱”的声响,指挥交通的交警追着喊“轮胎、轮胎……”而交警哪里知道兵团汽车驾驶员战胜困难的艰辛和奇想,但这些奇想办理了当时的燃眉之急。没有使一辆车停下来,没有等靠要。不久,在国家的支持下,汽车配件供应得到了保障。
兵团汽车驾驶员在屯垦戍边的艰辛岁月中,无论什么样的运输任务,总会战胜困难去努力完成。同时,在车辆操作、降落油料花费、提高配件利用寿命及车辆延长大修韶光等方面刻苦研讨,创造出了新的古迹和记录,为兵团、为当时的兵团运输处增光添彩。
国防培植共承担
兵团的汽车驾驶员们一贯牢记自己来自于公民军队,“国防培植有须要,我们来承担”是大家的共识。
1983年,喀什军分区在帕米尔高原进行边防部队营房培植;1984年,南疆军区在昆仑山上各边防哨所进行施工培植,汽车驾驶员们都承担了建材军运任务,战胜高山缺氧、道路泥泞坑洼等各类困难,把4200多吨物资送上了高原和高山之巅,有力地合营工程施工的提前完成,并使部队减少军费开支近30万元。任务完成后,喀什军分区和南疆军区分别赠予了锦旗,共同赠言:“同心干四化,协力建边防。”
驻喀什的汽车独立第三营曾为克孜勒苏军分区汽车连培训驾驶员,使该连很快成军。该营汽车修理厂组织综合性的维修做事队定期赴炮兵团上门做事,同样受到了赞誉。
1984年,中石油供应系统编制改革,南疆军区的军用油品供应、中石油喀什分公司对油品的运费结算只承担到喀什。但南疆军区每年数千吨的油品必须调运到叶城基地,兵团的运输单位承担了此项任务。年减少运费收入263万元。
汽车驾驶员们在反恐稳边的战线上同样从不缺位。就以驻喀什的兵团汽车独立第三营为例,以驾驶员与修理工为主组建的民兵连,几十年来一贯承担着重大节庆日的值班任务,确保新疆各族公民安然欢快地度过节庆日。
兵团“老兵”显风采
新藏公路由新疆叶城县出发点至西藏阿里地区,1000多公里的公路蜿蜒在昆仑山脉之中。解放军在山上设立多少兵站,专供部队、车辆的食宿,同时照顾部分非部队的车辆和职员。沿途兵站的官兵们习气性地把兵团的汽车驾驶员称为“老兵”,只要瞥见兵团的车辆就会直呼“老兵”来了。
关于“老兵”的业绩有很多。
新藏公路通车以来,这些“老兵”一贯承担着民军用物资的运输任务。昆仑山是高海拔险要的山区公路,新藏边界线上的界山达坂海拔在5千米以上,全线变幻难测的雨雪景象对道路毁坏性极强,汽车驾驶员冒着缺氧、道路坑洼和落石的危险,年复一年地行驶在这条运输线上,从而支持了西藏阿里地区的边防巩固和经济发展。
个中最应提起两件事,一件事是当时年已半百、两鬓斑白、瘦弱的连长张林孝,带上十多辆车行驶到黑卡达坂时,碰着山体塌方,前面100多辆车无法通过,他就站在最危险的地段上,指挥大家搬运路中心的石头,如创造有石头下滑的迹象,他便紧急吹哨提示大家立即躲开。经由两个多小时的冒死奋战,终于打消了路上的落石,车辆全部安全通过,连忙驰往前哨。
另一件事是配属前哨战斗部队的汽车驾驶员们,以不怕捐躯的精神大胆奋战,配属炮兵团一营奔赴海拔6400米的11号阵地,汽车驾驶员刘增新、李石海等驾车曳引着火炮,装载炮弹和职员,穿越印军火力封锁线,提前4天赶到11号阵地。驾驶员刘四功因高山反应呕吐7天不能进食,也硬是坚持不下支前运输线,显尽了兵团“老兵”的风采。
多年来,兵团的汽车驾驶员们沿途帮助和救助过无数各民族汽车司机,从技能上、汽车配件上供应无私声援,年年都有谱写民族情深的新乐章,“老兵”的称呼誉满新藏公路线。
汽车驾驶员的苦与乐
当年,兵团的汽车驾驶员都是全能兵,既有娴熟的安全驾车技能,又具备修理和打消各种机器故障的能力。那时,驾驶员们长期行驶在喀什、乌鲁木齐,并远至兰州、西安等地,一个来回需2个月的韶光。在长途奔驶中,啃干馒头、露宿戈壁、荒原是平常事,饥一餐、饱一餐导致的胃病,成了驾驶员普遍的职业病。
车辆一旦出发,就没有节假日,没有高下班的韶光观点,总是迎来朝阳,又迎来玉轮,两头摸黑。尤其行驶在南疆地域时,面前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难见村落舍和人影,耳畔响着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和轮胎与路面摩擦的沙沙声,每天十多个小时处在单调和寂寞之中,汽车驾驶员哼家乡小调排解寂寞,吼唱着陕甘秦腔和青海花儿居多,集演唱员和听众于一身,度过岁岁年年。
汽车驾驶员方志中记录着,一些驾驶员在驾驶室内备有手鼓,车子抛锚时,不论爆胎或轮轴折断,他下车后敲动手鼓,跳着舞蹈,绕着汽车转一圈,再笑哈哈地去修车,这也是汽车驾驶员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一旦碰着车辆紧张部件破坏,只得忍饥受饿地等待数百公里外的单位抢修车到来。为了抢韶光赶路,在戈壁滩小憩过,在大城市大街边的人行道上入睡过。1955年秋季,笔者随车队去陕西省西安市装运物资,到西安已是深夜。汽车驾驶员们就在较僻静的街边人行道上打地铺睡觉,刚眯上眼,天已蒙蒙亮了,一群戴着红围巾的小学生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走在路上,边走边说,“解放军叔叔还睡
汽车驾驶员们在降服自我的同时,还要与自然景象斗。春末夏初,公路地表浅层已化冻,而地表深层仍是冻土层,雨雪融化的积水无法往下渗透,道路翻浆成海绵状,加上水的浸染,极易使车辆陷进去,一旦陷入,必须挖开路面填入砂石或树枝才能前行。
夏秋时令,戈壁滩会突发大水,其洪峰可将汽车冲出公路,又在大水冲刷下,使汽车隐入深深的沙土中,达半个车身,大水一样平常持续2天至3天,驾驶员们必须耐心地等待。
冬季寒冷,为防汽车水箱冻裂,夜间必须把水放尽,有运输站的地方,清晨由站上供应热水加注水箱。碰着不设站或缺水区域,驾驶员必须蜷缩在驾驶室内,每两小时启动一次发动机给水加温防冻。就这样,每一年度过春夏秋冬。
兵团的汽车驾驶员们陆续成了家,虽然汽车驾驶员在当时是很令人倾慕的职业,但那时也流传着一段顺口溜:“好女不嫁司机郎,外出韶光比家长,回家一身油衣裳,孩子见爸不喊爸。”可以说,汽车驾驶员的儿女都是母亲抚养大的,这绝不是夸年夜。
1961年,笔者奉命从北疆赴南疆驻站蹲点,承担折衷宣扬运粮的事情,8个月后才回家,高高兴兴地去托儿所接女儿。在小班的孩子中,我认不出来自己的女儿。在保育员的指引下,一个瘦小的女孩“哇”地哭起来了,抱女儿回家的途中,她还直嚷嚷“找爸爸、找爸爸……”我再三说“我是爸爸,我是爸爸……”她还是嚷个一直,我心中的苦涩难以言表。驾驶员的子女们小时候很多是见爸爸喊叔叔的。
要问汽车驾驶员的“乐”呢?那便是看到战友们开垦出一个个新的绿洲,地里长满绿油油的稻麦和洁白的棉花时;看到自己参与培植的重大工程竣工时,汽车驾驶员的心中充满了造诣感和自满感,由于,他们没有辜负屯垦戍边的担当和历史义务。
光阴飞逝,如今,兵团汽车驾驶员的孙辈们仍在汽车运输和其他不同的职业岗位上,连续承担着父辈们屯垦戍边的光荣义务,并不断取得更辉煌的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