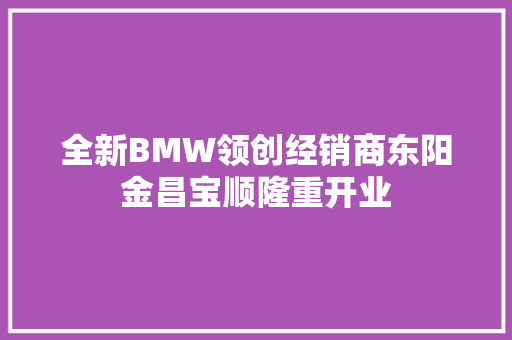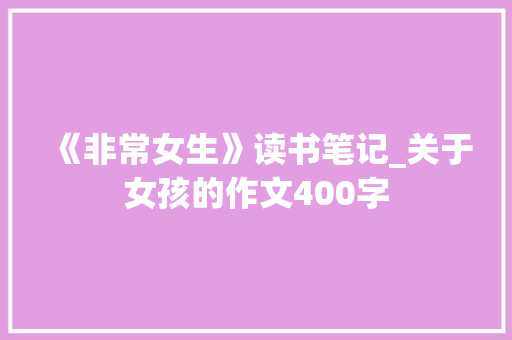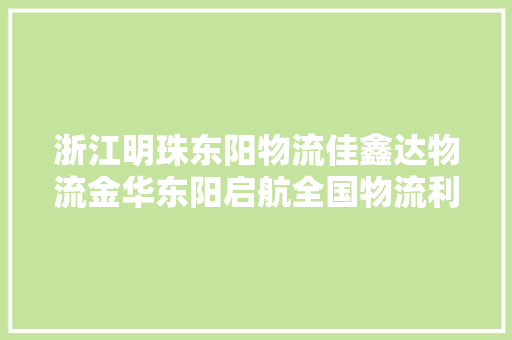资料图片
东阳始建县名见诸正史的都持“吴宁”说,“汉宁”说始见于南宋《嘉泰会稽志》。引起争议的是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当今考辨,要从东汉末年的中华文明时态、政治形态、豪族权势、史不雅观演化等作出综合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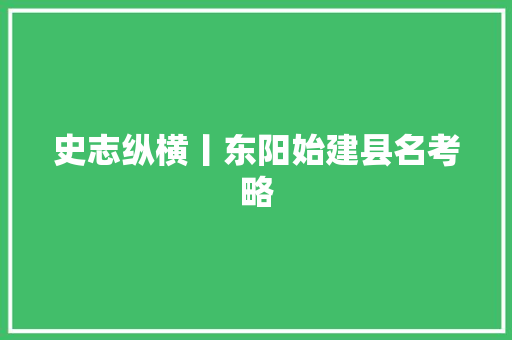
“吴宁”说
在南朝人范晔(398—446)撰的《后汉书·郡国志》会稽郡眼前,有梁(502—556)刘昭注:“诸暨,《越绝》曰:‘兴平二年分立吴宁县’。”
如果刘昭引用确有所据,那可以说最早涌现“吴宁”说法的是《越绝书》。然《越绝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卷数等至今仍存异说。而今“不以新旧为别,惟以善本是求”的中华国学文库中华书局2018年版的《越绝书校释》应属研究汇辑、择善而从的善本。其附录一:越绝书佚文校笺一五有“兴平二年,分立吴宁县。《后汉书·郡国志注》”,彷佛《越绝书》佚文是引用《后汉书·郡国志注》的,这给我们留下一个谜团!
好在本书校释者有如下一段笔墨:
【校笺】“兴平”为后汉献帝年号,“兴平二年”,为公元195年。此条不见他书所引,唯见《后汉书·郡国志四》刘昭注引《越绝》。考《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云:“吴宁令,汉献帝兴平二年,孙氏分诸暨立。”所记为设立吴宁令之事,然韶光与《越绝书》此佚文合。
据《越绝书》2018版校释,刘昭注引《越绝》和沈约《宋书·州郡志》互证,东汉兴平二年置吴宁的记述是可信的。
沈约撰的《宋书》三五《州郡志》的记述是:
东阳太守,本会稽西部都尉,吴孙皓宝鼎元年立,领县九。户一万六千二十二,口一十万七千九百六十五。去京都水一千七百,陆同。
长山令,汉献帝初平二年,分乌伤立。
太末令,汉旧县。
乌伤令。
永康令,赤乌八年分乌伤上浦立。
信安令,汉献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曰新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吴宁令,汉献帝兴平二年,孙氏分诸暨立。
丰安令,汉献帝兴平二年,孙氏分诸暨立。
定阳令,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孙氏分信安立。
遂昌令,孙权赤乌二年分太末立,曰平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这里有必要先认识我国传统文化中史学档案在“再现历史真实”中的浸染。周王朝时我国就涌现了管理文书档案的机构——天府。汉初建石渠阁收藏秦朝档案。汉王朝建有许多贮藏档案的场所,如西汉的兰台,东汉的东不雅观(由校书郎管理)、石室、鸿都等等。正如司马迁利用“石室金匮之书”撰《史记》,班固利用“兰台”之书撰《汉书》一样,沈约也是利用“金匮石室”收藏的档案撰就《宋书》的。
沈约撰《宋书》,纪传成于南朝齐永明六年(488),志成于隆昌元年(494)后。沈约(441—513)是著名的文史学家。《宋书》收录原始文献甚多,各志多上溯制度源流,堪补前史之缺。据此可以解释三点:第一,沈约撰写《宋书》在南朝齐(479—502)的前期,而《后汉书》郡国志由梁(502—566)刘昭作注,纪传由唐李贤作注,因此,除却《越绝书》,沈约的“吴宁令,汉献平二年孙氏分诸暨立”为“吴宁”说最明确、最早的依据。第二,沈约是著名的文史大学,累官尚书令、侍中、太子少傅,是身处皇家高层,可直接掌控并利用档案的高官。他持“吴宁”说该当是有原始文献为依据的,是根据第一手资料得出的结论。第三,汉献帝兴平二年分诸暨立吴宁的结论是根据孙氏权力和势力范围所及的结论。
纵不雅观所有依据金匮石室之书撰就的历朝正史,都持“吴宁”说,绝无“汉宁”说,这是历史的现实。
“汉宁”说
“汉宁”说始见于南宋《嘉泰会稽志》。
《嘉泰会稽志》成书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陆游(1125—1209)为之序。据陆游所述,此志历经一方官员沈公、赵公、袁公之积劳累月,而始终其事者为施宿。而后有《会稽续志》于前志有所补正,成书于南宋宝庆元年(1225)。
南宋《嘉泰会稽志》提出“汉宁”说,离东汉兴平二年(195)已是1006年后的事。从隋开皇九年(589)废吴宁,唐垂拱二年(686)以义乌东要冲地及废吴宁故地置东阳县,到《嘉泰会稽志》成书也足有六百年,如此去翻陈年往事,而且去寻衅许多文史大家的史学结论,那该当是有充分情由和充分根据的,但是它见告人们的,只是遗憾和不解。《嘉泰会稽志》关于汉宁的记述有多处,摘录如下:
历代属州
孙皓宝鼎元年(266)又以汉末以来分乌伤、太末之地所立新安、丰安、长山、吴宁、遂昌、永康、定阳并乌伤、太末九县置东阳郡。
历代属县
兴平二年(195)分诸暨之大门村落为汉宁县。
建安二十三年(218)……又分乌伤之上浦为永康县,分章安立临海县,改章安为罗阳县,余暨曰永兴县,汉宁曰吴宁县。
孙皓宝鼎元年(266)分会稽为东阳郡,以乌伤、太末、新安、丰安、长山、吴宁、平昌、永康、定阳九县属焉。
废县
兴平二年分诸暨大门村落为汉宁县,吴改为吴宁县,宝鼎元年割隶东阳郡,后复并入诸暨,今县有大门里,或云即其地也。
上述引文有四种说法,一是东汉兴平二年(195)“分诸暨之大门村落为汉宁县”;二是东汉建安二十三年(218)汉宁改为吴宁;三是“吴改为吴宁,宝鼎元年(266)割隶东阳郡”,意为吴立国之黄武元年(222)由汉宁改为吴宁;四是置东阳郡时由“汉末以来所立之吴宁等九县组成”。《嘉泰会稽志》的上述笔墨用订正学的措辞说是莫名其妙的。清代著名订正学家李慈铭在《乾隆绍兴府志校记》中指出“记载舛驳之处颇多”,并在《越缦堂日记》中指出《嘉泰会稽志》有四病,个中就有“记载无法,去取失落当,考察多疏”。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在《会稽二志》一文中沿用李慈铭的话指出《嘉泰会稽志》的缺陷,其一是“析指沿革,即是胥抄,莫从考察”(见《绍发兵专学报》1985第2期)。《嘉泰会稽志》或“吴宁”或“汉宁”,或此时或彼时的记述,按史学的哀求,确属无稽之说,是莫从考察的,因此,史志学界一样平常不予沿用,更无异说引起的风波。
辩论缘起
“吴宁”说历经十多个世纪,并无涉及史学内涵的异议。唯明代嘉靖《浙江通志·地理志》持汉宁说。古代订正学界有“明人好刻书而古书亡”的诟病,大概明代嘉靖《浙江通志·地理志》也在诟病之列。后来的浙江通志、金华府志都持吴宁说,而且没有引发辩论风波。东阳历史上的县志宋宝祐志、元至治志、明永乐志、明成化志、明隆庆志、清道光志以及民国县志稿均持吴宁说。真正提出异议引发辩论的是东阳境内的文史事情者和部分文史爱好者。首先亮明史不雅观提出“汉宁”说的是清代康熙《新修东阳县志》的主撰,邑人赵衍。《新修东阳县志》卷一建置有如下一段话:
汉兴平二年,初置汉宁县。此置县之权舆也。其地在乌伤、暨阳间。稽《禹贡》,属扬州,为越地。自秦并天下,分三十六郡,县地故属暨阳,隶会稽。至是始析其地置县,名汉宁。郡志:“汉献帝兴平二年,置吴宁县。”旧志因之。注云:“时孙吴据之,故名。”未是。按《通鉴》,兴平二年,孙策方渡江,而东犹采石也。是时会稽尚为王朗所据,至建安元年,策始渡钱塘,取会稽,降王朗,自主为会稽太守,相去熟年矣。谨按《浙通志》:“汉献帝兴平二年,太守许贡奏分乌程置永安县,析诸暨水门村落置汉宁县。”固历历也。因改正如右。水门村落,详见古迹。
吴宝鼎元年,改名吴宁,隶东阳。时分会稽置东阳郡,领县九,长山、太末、乌伤、永康、信安、吴宁、丰安、定阳、遂昌皆隶焉。此本邑隶郡之始,亦本邑得名之始也。郑志不言所隶,盖略之也。旧云:“汉名汉宁,吴名吴宁。”亦揣摩之说。盖孙氏建丹杨,黄武珍宝鼎已经七易,凡三十五年矣。
这里,赵衍明确地见告人们,东阳初置韶光是“兴平二年”,初名是“汉宁县”,并指出这是“置县之权舆”,因而断定历史上所有“吴宁”说都是错的。赵衍此说的凭仗是其明确的历史不雅观。这在同书卷十二斯敦的一段按语中说得很明白:
敦生于黄武五年丙午,卒于永兴甲子。旧志作吴人。按《大纲》,三国以汉为正统,今考黄武五年,为汉建兴四年,而赤乌元年,即汉延禧元年,时本郡未置,邑称汉宁,属会稽郡,即以为汉人可矣。王十朋《会稽赋》“邓斯祁樊,自尽代罪”。注云:斯名敦,吴宁人。朱育之《对濮阳兴》亦云吴宁斯敦,皆误。
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历史定识,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涌现浩瀚的文史大家和订正学家,形成既有恢廓的历史视野,又有光鲜的时期精神,并具有求实与经世同等,思辨和考据结合的史学不雅观念。赵衍作为清皇朝的官员,“尊朝廷,重故里”,为《新修东阳县志》穷搜博访,惨淡经营,东阳历史不会忘却他的功绩,他坚守“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正统不雅观,是历史的局限,然而他忽略中华文明史发展的客不雅观事实,忽略思辨考据的史学传统,忽略浩瀚文史大家的结论,凭臆断天生“汉宁”说,而且振振有辞。这就违背孔子所倡导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四绝精神,从哲学不雅观点说是属于唯心了。
封建社会的正统不雅观,即“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欧阳修《正统论》)。我国自秦汉以来,便成为中心集权的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以血缘维系的统治者都以封建一统为目标,想强化自我,以至万世。然而,现实见告人们,居正难,一统更难。欲求万世,传至无穷的秦王朝居正十多年,在陈涉起兵、楚汉争霸中灭亡;刘汉居正,历经王莽代汉、黄巾叛逆、豪族崛起,走向“五胡乱华”。就企求居正一统的思想体系说,汉初重黄老之术,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初,儒家中崇尚理性的一派占上风。两汉期间,杨雄、桓谭、王充等批驳“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而后玄学思潮代之而起……可以说,自汉以降的中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思想体系都见告人们,统治者有求“正统”的野心,却都没有达到居正一统,世系沿袭的目的。探索正统之源,该当始于宋朝,北宋之欧阳修、司马光、苏轼,南宋之朱熹各有论说,由于态度不同,立论互异,司马光为北宋立论,以三国魏为正统;朱熹为南宋立论,以蜀汉为正统。东阳始建县名以赵衍为代表的“汉宁”说者,拘泥于封建“正统”论,不循史迹,又乏炉锤,只能说是朱熹“正统”论的追随者。
道光《东阳县志》没有延续康熙《新修东阳县志》“汉宁”说,并作出如下简要的辨析:
《汉书·地理志》:“会稽郡,秦置。高帝六年为荆国,十二年更名吴,景帝四年属江都,属扬州。”县二十六,七曰诸暨。《东阳记》:“此境为会稽西部,尝置都尉理于此。”
《后汉书·地理志》“会稽郡诸暨”,刘昭注:“《越绝》曰‘兴平二年分立吴宁县’。”施宿嘉泰《会稽志》:“兴平二年,分诸暨大门村落为汉宁县,吴改吴宁。本年夜门里或即其地。”《诸暨志》:“今四十都开化乡有大门里。”按旧志“汉曰汉宁,吴曰吴宁”,其说别无左验。曾贲《进士题名记》、施宿《会稽记》,说者遂或以为永安改,或以为宝鼎改,皆臆说也。据《后汉书·地理志》注、《宋书·州郡志》皆不言汉宁,况孙策于兴平二年自领会稽太守,且能分豫章为庐陵郡,何不能分诸暨为吴宁县?故附见汉宁于此,仍不入表。
《三国志》:宝鼎元年冬十月,丁固、诸葛靓败永安山贼施但即是牛屯,分会稽为东阳郡,属扬州,领县九,吴宁属焉。按:吴五州,有郡四十三。
道光《东阳县志》以其学识功力,遵照订正学的精确方法,断定康熙《新修东阳县志》之谬,民国《东阳县志稿》延续《道光东阳县志》的“吴宁”说,也作出考证剖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撰写《浙江分县简志·东阳县》时,没能雕琢濯磨就仓促成稿,想当然地认为汉置“汉宁”,吴改“吴宁”是自然的,暴露了主撰者我于史学的无知和浅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编纂《东阳市志》在爬梳剔抉中以为东阳始建县名是东阳方志必须明确的第一个问题,于是决定请杭州大学历史地理学专家研究拟稿。末了敲定,正文取“吴宁”说,“汉宁”说录以备考。此法是遵照中国史学传统的“承讹当改。别有依据,不可妄改。义可两存,不必遽改”的原则,是唯物辨证而又兼容稳妥的。但《东阳市志》总纂期间和出版往后,东阳境内仍有责备问疑之声,并引发涉及史学层面的辩论。辩论的焦点是权属问题。一是皇权,按他们的不雅观点,刘汉的天下,献帝的王土,怎容得下孙氏擅自分土置县?二是地理,普天之下皆为刘汉之地(按赵衍的说法,三国以汉为正统,吴地也属汉),地载万物,怎能涌现“吴地”?
历史研究要依赖史料。然而史料本身却不构成真正的完备的历史知识,末了授予史料以生命或者使史料成为史学的,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历史学家的思维方法,英·沃尔什称之为综合法。“所谓综合法便是对一个事宜,要追溯它和其他事宜的内在联系,并从而给它在历史的网络之中定位的方法”([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译序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初版)。这便是说,史学事情者的主体意识、历史事实、社会文明史的发展规律等等,必须作出综合剖析。东汉末年的社会政治形态,中华文明发展的特定形态和发展规律等等,是辨析东阳始建县名的依据。
权属问题
中国是带着氏族社会后期父权制或家长制的遗风进入文明社会的,这种制度的嬗变因此血缘为依据的执拗的族制系统。宗法、族制牢牢地规范着社会、政治、精神生活。在封建社会,以血缘为依据的皇权、族权、官僚集权、豪族社会权力分配有其特定的时期特色。198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区域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与此同时,日本史学界在日本著名史学家谷川道雄倡议下也参与共同研究。“汉代的政治是中心和地方互助的政治,仅仅是中心政权的单方行政,是不可能实施统一政治的”(谷川道雄《六朝地域社会丛书》总序)。中国封建社会,不论哪个时期,地方社会对中心政权都有一定的自主性,其自主性,东汉帝国崩溃到六朝地域社会尤为明显。现存有笔墨记载的《盐铁论》,是国家财政政策听证会的综录,实际是汉朝廷平衡朝野关系,是权力分配问题。王充(27—97)在《论衡》一书中公开激烈地反对孔孟的儒学,驳斥反动的“君权神授”说,也反响了后汉期间中原和吴会的域地差别和权力分配问题。“两汉四百年统治之后,继之而来的四百年也容许以称之为分裂期间……中国南方分裂为许多统治韶光不长的小国,北方也同样分裂成这样一批小国。有些北朝的小国由非汉族的游牧民族组成,却超过长城,在长城以南建立了国家。过去中国历史上,把这一期间看作‘五胡乱华’,看作‘阴郁期间’”(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版编者弁言)。
后汉期间日益残酷的官宦之争,即外戚与宦官之争,是后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之争;党锢之祸,即一批官僚与士人反对宦官专权遭罢黜禁锢、牵连杀害之争,甚至东汉政权进入最阴郁的时期。顺帝刘保(125—144)去世亡,冲帝刘炳(145)二岁即位,三岁去世亡;质帝刘缵(146)八岁即位,当年被毒去世。一两年之内,连遭不幸,汉家衰败从此开始。至灵帝刘宏(168—189)十二岁即位,184年黄巾叛逆。灵帝去世,少帝刘辩(189)十七岁即位,5个月后董卓废少帝,立献帝(189—220),自封相国。初平元年(190),东方部分州郡刺、史太守十余人自封相国,推袁绍为盟主,起兵声讨董卓。董卓怕洛阳腹背受敌,决定迁都长安。初平三年(193)献帝十三岁,王允策动吕布杀董卓,董卓部将收罗散兵叛乱,攻占长安,杀王允。不久,董卓部将争权夺利,相互残杀,长安城中白骨堆积,臭秽满路。从此,汉献帝已徒具浮名,东汉王朝已不成其为统一王朝。各地势力乘机盘据一方,纵横捭阖,图谋霸业(《中国通史》637页)。孙氏等地方豪族势力,已得到令帝皇成为傀儡式存在的政治力量。沈约撰《宋书·州郡志》“吴宁令,汉献帝兴平二年分诸暨立”的记述决非臆断,而是依据历史档案的如实记载。
地理问题
从后汉中心集权的状况来剖析,后汉末至三国时期,中心与地方行政上的均衡是明显方向于后者的。原为常驻地方作为中心政府监察官的州刺史,演化成盘据一方的地方行政主座的过程便是最好的解释。乃至中心政府在各地设置的都督诸州军事“也随着韶光的推移地方化了”(谷川道雄《六朝地域社会丛书总序》)。地方社会中,乡三老、县三老对地域民众的领导权是公认的,豪族政权更是这一期间突出的社会征象。
东汉末年,宦官、党锢的内斗,引发了清流的崛起,士大夫舆论是清流组合联络的根本。加上与之关联的逸民及由贫民阶层组成的黄巾叛逆等,此时“汉帝国已经朝着异质政权转化,变成了正在领主化的豪族政权”(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64页)。在吴会域地——即吴郡和会稽郡为中央的豪族,如东汉熹平元年(172)会稽人许昌在句章起兵,煽众数万,是吴会豪族崛起的力量显示。“富春孙氏崛起是继秦朝一统越国故地之后,吴会历史发展的又一个迁移转变点(王志邦《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第180页)。孙坚,孙武之后,平息句章之乱有功,任盐渎侯,东汉中平元年(184)弹压黄巾叛逆,至初平元年(190)发兵伐董卓,举为破虏将军,转战长江以北中原地区,先后任别部司马、长沙太守、乌程侯、豫州牧。到192年战去世为止,孙坚以其豪族的权势,善战的兵力,宏不雅观的打算,在政治竞赛中,已在长江以北立稳脚跟。而江东是孙氏的隆兴之地,孙坚去世后,其子孙策遂统领部队、渡江居江东,兴平元年(194)孙策已成为吴会群雄中最具政治、军事实力者。
此时,汉室宫廷内斗,皇室性命不保;中原战乱,豪族霸占领主地位。汉之宁已失落度,吴会地近蛮荒,汉家王朝根本无法顾及。吴地之宁,析地置县,完备在孙氏权势之内,更是霸占领主地位的豪族社会制度下吴地百姓和霸占领主地位的孙氏的一种企求。命名吴宁,天经地义。而且此吴是存在已久的地理之吴,绝非三国孙吴国度之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