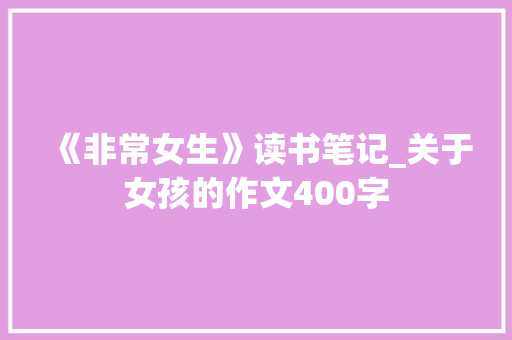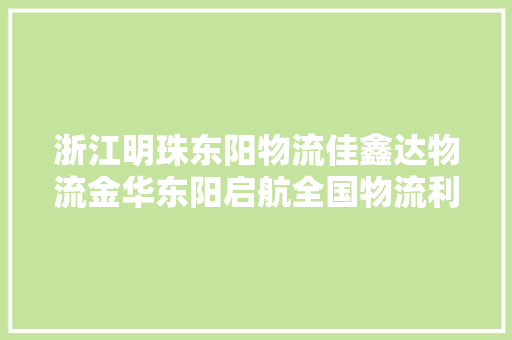岩石,坚挺,沉默;春天,温暖,焕然。
没有小说上的故弄玄虚,舞台中的弯曲离奇。

旧时中国青年警官杜,在奥地利国警察演习中央学习,幸获维也纳美女格特鲁德·瓦格纳的芳心。
金色大厅未曾演过的经典,比“梁祝”缘分,比“罗密欧与朱丽叶”幸运。
知更鸟一样,俏丽而可爱。
瓦格纳十七八岁情窦初开,不知男欢女爱生儿育女为何事,学校里没有此类课程,长辈们也从不透露这方面密笈。
异国他乡,在水何方,杜家多远,全然不晓。
别了妈妈,别了爸爸冰冰的目光,别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奥地利海尔马克街26号,从阿尔卑斯山迢遥别离,火车似箭,直指意大利特利耶斯特港。
马六甲海峡“玫瑰号”乘风破浪,整整二十六个昼夜风雨兼程,睡不着四三二一数到天亮,独身只身流落漂到喷鼻香港,漂到上海,终极漂到了保俶塔下西子湖畔的新新饭店。
菱花镜前独坐,想起妈,想起脸拉得长长的爸,泪水汩汩地从眼眶流出,流过腮帮,滴在膝盖。
儿的爸呀,儿的妈,看看你们的女儿,梳起中国妇女的发髻,穿起中国妇女的旗袍,像不像地隧道道的中国媳妇?
——你是我全部心灵之所在。
你们该当为女儿高兴,你们该当为女儿祝福。
想不到好梦难圆,命途多舛。
逃警报一家子枪林弹雨,白天黑夜四处去世伤者横陈,炸弹震坍住屋天花板。
无数血腥用惨状告诫众人:眼泪难以缓却惶恐,怨言无法抹平疤痕。
瓦格纳自顾自一窝窝生产,一口气生了三男三女,取名:强华、兴华、丽华、卫华、年光时间和爱华——痴痴地企盼中华崛起。
瓦格纳夫妇与两个孩子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不去宝岛享受安逸富贵,拖家带口回到东阳江畔小小湖仓村落,住进两间有木雕门窗的老屋——木梁上燕子筑窝叽叽喳喳,堂屋里杜家太公挂在画像,杜氏花厅肥梁胖柱有条不紊——断然决然,停用儿子女儿洋名字。
在小村落庄悄悄过起田舍人日子。村落里有人背地里叫她:奥国婆。
处处都有生动的细节,年年都有悱恻缠绵的故事。
俏丽可爱的知更鸟,小巧玲珑在东阳江畔,善气迎人在东阳江畔,挺着胸脯在东阳江畔,叽喳婉转在东阳江畔。
与知更鸟一样,一辈子只守着一个伴侣。
用“凤仙花蓬蓬开”“麻雀娘退砻糠”的曲子唱起——
我愿成为东阳江畔一粒沙子,只要无人把我从滩头剔出。
我愿成为东阳江里一勺江水,期待着可以滋润津润一棵庄稼。
我愿成为东阳江畔一棵小草,虽然弱小也想着茂盛堤岸。
我愿成为东阳江里一只米虾,沐浴爱河是我终生的企盼。
——平凡得下里巴人,世俗得平头百姓。
村落里男女老少,都亲切地叫她:奥国婆。
东阳江上,成群迁徙的候鸟斑嘴鸭游弋、觅食,拍打翅膀掠过水面。CFP。
用“豆腐做的手”,身背着孩子推磨,磨出面粉烙饼蒸馍,味道很湖仓。
用“豆腐做的手”,傍晚光阴来到村落口塘埠头,一边用木棒用力槌洗衣裳,一边跟旁人大声说话。
用“豆腐做的手”,拿一条小凳廊下独坐,卷起裤管在白白大腿上搓麻线。
用“豆腐做的手”,当众解开衣襟露出大半只乳房,不顾害臊给女儿喂奶。
用“豆腐做的手”,偷偷敲打酸疼快要断掉的腰膀,不让父母、丈夫知道。
用“豆腐做的手”,年初逐一早换上新衣端着鸡蛋桂圆汤,上门孝敬公婆。
婆婆说:瓦格纳这双豆腐做的手又白又嫩,又好看。
瓦格纳自己说:我这双手呀,是从外家带来干活的。
光阴倒流几十年,破天荒磨练人嘴巴肠胃脑瓜的那几年,一家老少不怨天不恨地,跟村落人们一起勒紧腰带过日子。
坦白地说,曾经为硬板床辗转不眠流过泪,曾经为玉米糊淡然无味流过泪,曾经为东阳话艰涩难学流过泪,曾经为土灶头冒烟呛鼻流过泪,曾经为老锄头不听使唤流过泪,真的。
但是,只在孩子们看不到的地方、听不到的时候暗暗地流,只在公公婆婆丈夫都看不到的地方、听不到的时候偷偷地流。
人们看到的瓦格纳,蓝眼珠亮晶晶,个子不胖不瘦,胸部挺得高高,嘴角抿着浅浅微笑——不能给公公婆婆丈夫孩子们丢脸。
孩子们记下,外婆给妈妈的金手镯剪成了三段:一段给公公抓中药,治哮喘;一段给老大缴学费,领新书;一段给田亩找种子,买农药。
儿女们忘不掉,妈妈坐在15支光的暗淡下,一边嗞拉嗞拉的拉麻线纳鞋底,一边绘声绘色讲大克劳斯与小克劳斯。
孩子们至今还念叨,妈妈给两个女儿做布娃娃和玩具熊,把布娃娃取名为丽丽,把玩具熊取名为比利。
儿女们常常回顾,妈妈亲手做的圣诞树茂盛在老屋一角,妈妈说一年一度的圣诞礼品,不能不给孩子们准备。
有一年瓦格纳回到阔别半个多世纪的故乡,笑眯眯对大家说——
我现在名叫华知萍——萍水逢心腹,人生植中华——这是新婚夜师长西席为我取的中文名。
亲爱的市长师长西席,亲爱的同窗好友、弟弟们!
我嫁的不是那个曾经风雨交加的年代,也不是那块曾经板结了的地皮。
我嫁的人属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也不主要,主要的是他以春天般的温暖焕然,岩石般的沉默坚挺,走进我的生活,融入我的日昼夜夜分分秒秒,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我们在一起,可以把统统痛楚化为幸福。
如果再让我年轻一次,我还要嫁给他——东阳江之子。
奥国婆瓦格纳如是说。
瓦格纳及子女与村落人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喜好天未大亮,听村落里孩子呀呀呀早读声,比鸟雀鸣叫声悦耳;
喜好湖仓夏夜,点一支土得掉渣的蚊喷鼻香,舒舒畅服睡到大天亮;
喜好烧一大碗霉干菜炒猪肉,下饭或下酒都是喷鼻香飘十里的首选;
喜好新年元宵节,一条龙灯把正月的每个夜晚,闹得彻夜不眠;
这便是我一家子住着的东阳江畔的小村落落。
这便是我为什么一辈子只守着一个家、只守着一个伴侣的起因。
希望各位包涵!
中国有我华知萍的家,东阳江畔有我丈夫的坟,一大堆孩子在等我这个妈。
我们东阳有个乡风:“生同寝,去世同穴”。
——便是夫妻俩去世后安葬在一起,同个墓。
“你是我全部心灵之所在”,这是我与师长西席热恋在维也纳,听莱哈尔轻歌剧《微笑的国度》中一句经典。
“你是我全部心灵之所在”,这是我与师长西席晚风里在东阳江畔手挽手溜达,两个人轻轻哼唱不息的歌词。
“你是我全部心灵之所在”,这是我在师长西席出门遭遇非礼之前、捉住师长西席双手用眼神传给师长西席的定心剂。
“你是我全部心灵之所在”,这是我与师长西席坐在夏夜院子里乘凉,两人一边摇着麦秆扇一边吟唱的小夜曲。
“你是我全部心灵之所在”,这是师长西席停滞呼吸离开人间之际,我抱着师长西席身子在他耳旁一字字重复的一句话,是我给师长西席送行的临终承诺。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曲曲弯弯的东阳江,没有多瑙河迷人的圆舞曲;
南北两岸的仙霞岭、会稽山,没有阿尔卑斯山的终年白雪。
但,东阳江曲曲弯弯千年万年地滚滚而流,东水西流地滚滚而流,已经流进我的内心;南北两岸的仙霞岭、会稽山,春夏秋冬的容颜不变,相依相伴的风采不变,已经将一年四季融进我的血液。
我与知更鸟绝对地不一样,我不但喜好东阳江畔温暖的春天,也习气了东阳江畔寒冷的冬季。
忘不掉二十年前仲春十九日,千万里之遥从奥地利嫁给中国的女人去世了。
那年,那月,那日,那时——
小小湖仓村落800多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手提竹丝编织、棉纸裱糊、桐油刷过粘着大红“杜”字灯笼,站在村落口欢迎这位会说一口地隧道道东阳方言、会唱很多很多东阳民歌、彻里彻外湖仓化了的洋媳妇,魂-归-湖-仓。
——你是我全部心灵之所在。
歌声轻轻地飘荡在东阳江上空,飘进小小的湖仓村落,飘进两间有木雕门窗的老屋——
旧式橱柜里放着瓦格纳常用的带托盘的咖啡杯,瓦格纳特喜好的插着宝蓝色烛炬的银质小烛炬台,瓦格纳亲自挂在墙上的奥地利风光装饰画。
还有,瓦格纳与杜承荣的黑白结婚照,还有放在桌子上的、瓦格纳特喜好的歌剧唱片《微笑的国度》和厚厚的原版《德语词典》……
彷佛这些东东,也在轻轻吟唱,抑或也在悄悄地谛听?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