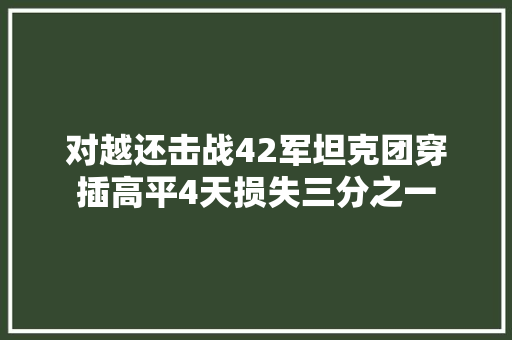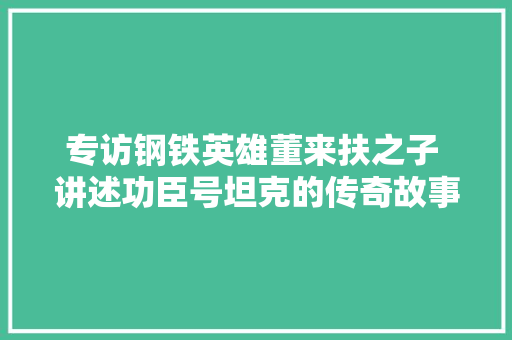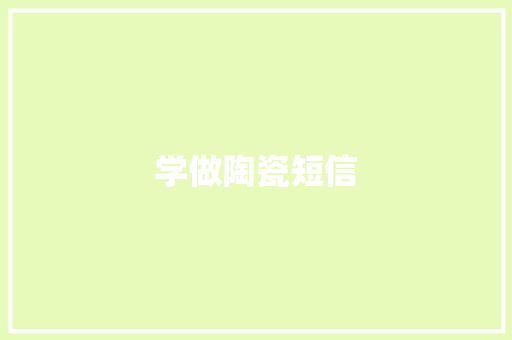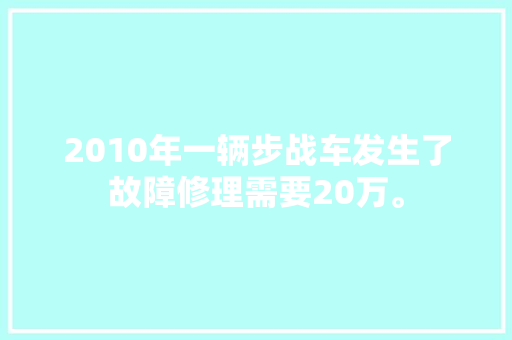1984年春,我到北京组稿。那些天连续拜访了很多老作家、老革命。时隔38年,已经想不起来是谁先容我去见的蓝曼。那时,他住在北京南礼士路头条1号第二炮兵后勤招待所。听说我是《长春日报》副刊的编辑,蓝曼很愉快地对我说:“啊,长春那片地皮留下了我战斗的足迹。多年没有回去,很是惦记啊!
”
交谈之后,我得知蓝曼的原名叫蓝文瑞,后改名蓝曼,曾用笔名叶柏,1922年4月2日出生于河北武强县城。少时,他勉强读完小学后,因家中生活穷苦而辍学。抗日战役爆发后,他曾流亡大后方。1939年他参加共产党南方局事情。1940年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先容,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转入延安外国语学校专修俄语。学习期间,他参加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青年蓝曼漂亮洒脱
1945年毕业后,适逢抗降服利,蓝曼随部队进军东北。1946年起,他担当第四野战军坦克连队第一任辅导员。1946年长春失落守后,形势日见急急,坦克队边演习,边参加战斗。文质彬彬的蓝曼,成为在沙场上猛打猛冲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他第一次参战是攻打德惠县城。战斗打响后,蓝曼乘上第一辆坦克,冲在最前边。当坦克走上一座石桥时,轰的一声,履带被炸断了。蓝曼带领乘员躲开仇敌雨点般的子弹,爬出坦克,暗藏在桥下。当第二辆坦克靠近石桥时,蓝曼机灵地跳上去,连续向地堡群提高。他们绕路靠近了仇敌的地堡群,一炮一个地将固定火力点摧毁了。坦克每开一炮,端着望远镜的朱瑞司令员就愉快地叫一声“好”。
庆功会之后,蓝曼便将这次战斗情形写成了一篇战地通讯《枪毙敌堡》,刊登在《牡丹江日报》上,坦克部队参战这振奋民气的,极大地鼓舞了全战区的军民。这篇反响我军坦克初战的作品,是这位作家的处女作。后来,他随部参加了三下江南战斗,以及解放靠山屯、德惠与天津的战斗。天津解放后,蓝曼带领着自己的坦克营,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入城式。
新中国成立后,蓝曼调任师政治部宣扬科长;1951年春,任装甲兵司令部研究室翻译科长;1953年任坦克修理处长,同年改任《公民装甲兵》杂志社总编辑;1955年调度放军文艺社任《解放军战士》编辑部散文组组长;1965年调任公安部队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1966年调任二炮政治部宣扬部副部长;后任解放军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化部长(副军级)。
由于爱好文学,蓝曼在50年代初开始翻译苏俄墨客的作品。1951年他翻译的第一本诗集、苏联墨客马尔夏克的《五彩的书》由知识书店出版。随即他又译出了伊萨柯夫斯基的诗集《和平颂》,于1954年出版,深受读者喜好,短期内持续印了9次,印数达8.6万册。其后,他还翻译出版了《叶赛宁诗选》、《伊萨柯夫斯基诗选》、《谢甫琴柯诗选》、《蓝曼译诗集》、《鸽子》、《军官随笔》等诗集、故事集、散文集。
蓝曼又是一名军旅墨客,他的诗以文笔简洁清新、感情朴拙而著称,先后出版了《老舵手》、《绿野短笛》、《海阔山高》、《青龙湾》、《红岩灯火》、《悄悄思念》、《坦克奔驰》、《繁花集》(互助)、《森林抒怀》(互助)、《蓝曼诗选》等诗集。另著有散文诗《蔷薇集》、诗论《学诗浅谈》。
蓝曼在文坛享有较高的荣誉,1950年加入天津作协分会,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4年任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曾任湖畔诗社副社长,并以墨客的身份出访苏联与匈牙利,多次获奖。
我对蓝曼在长春的经历很感兴趣,便约他为我们副刊写一篇散文,回顾当年的战斗往事。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回到报社不久,我就接到他寄来的稿子。阅读之后,与我的设想相去甚远。他写的不是叙事散文,而是一篇抒怀散文诗,险些没有任何详细情节。提交给领导审核,部主任的见地是请作者修正。我把领导的见地写信反馈给蓝曼,之后他在5月16日的复信:“我已经觉得到,这篇文章使你难堪了。我认为,在本文中加点详细的事儿并不难,但那会限定了文章的视野,弄窄了文章的内含。我写这篇文章,原想以情为主,表现蕴藉,让读者读后有一点文章外的体味。这是我的想法。文章没有写好。现将文章做了点补充,恐尚不能使你们满意。如不适用,不必勉强。”
大约是不好意思再请作家修正吧,拖了几个月,部主任亲自操刀做了编削,然后揭橥了。我预感到作家肯定不满意,硬着头皮把样报寄给蓝曼。几天后收到他在9月7日写的复信:“前寄你的《眼睛》一稿,原是作为散文诗写的,经你们改过已失落去原有的形式。这样的文章揭橥无益,请将原稿退还给我吧!
”果真不出所料!
在生手眼里报刊编辑很风光,乃至可以主宰一篇稿件的死活,哪里知道编辑常常要受“夹板气”呢?
由于这个不愉快的插曲,往后我再也没敢向蓝曼约稿,估计他也不会给我写了吧!
2002年12月17日,蓝曼因病逝世,享年80岁。
蓝曼的纪实长诗《坦克奔驰》,以战士的措辞、战士的情绪,反响战斗的生活,刻画战士的形象。措辞普通诙谐,节奏短匆匆明快,表现出我军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不雅观主义精神。这部长诗,亦诗亦史,既有文学代价也有历史代价,这是我军文学史上最早以长诗形式歌颂我军机器化部队的开篇佳作。墨客虽然已去,但是他的作品必将长留人间,当代文学史也该当有一席之地。
据蓝曼的战友写的回顾录透露,蓝曼在黑龙江密山的东北坦克大队任职期间,文艺队一个女生爱上了他,她便是黑龙江省宁安籍的张薇华,俩人相爱后结成了一辈子的革命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