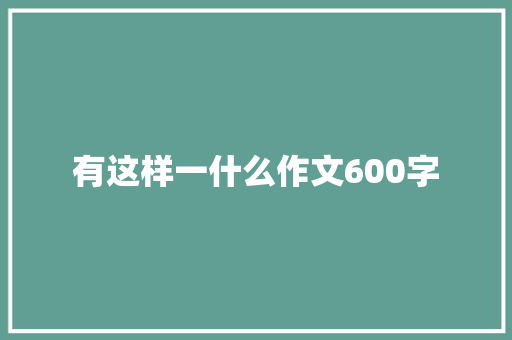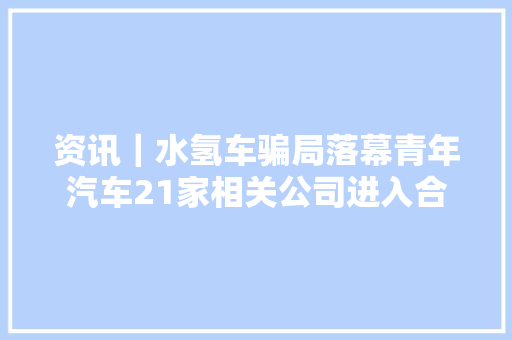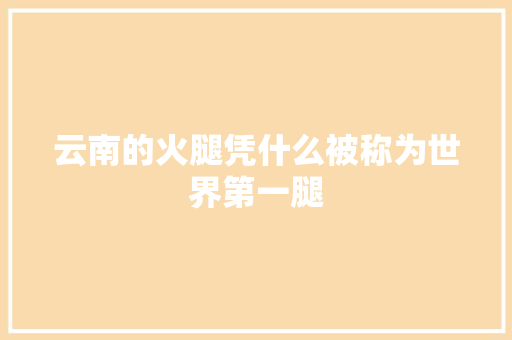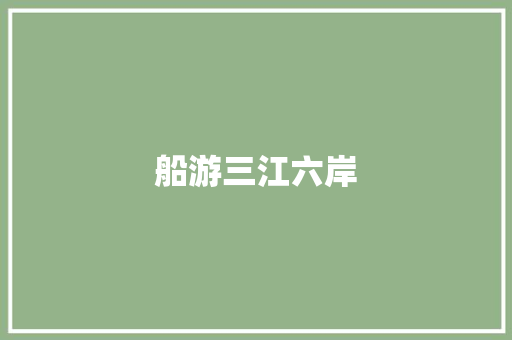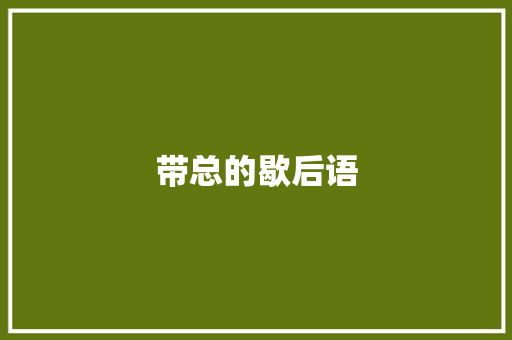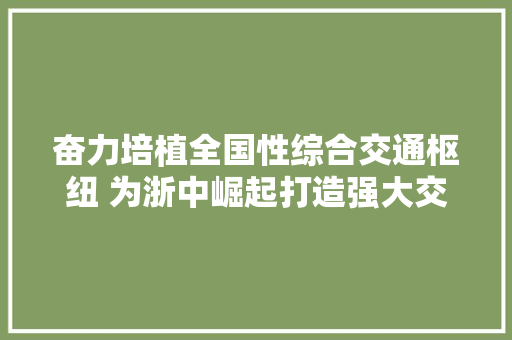从年轻时在火腿厂卖力气,到后来刻苦研讨成为火腿专家,43年只做火腿的赵增,其“国家火腿加工高等技师”身份背后,藏着老一代匠人朴素的情怀,与经久弥喷鼻香的人生故事。
手上的伤疤,是当年的学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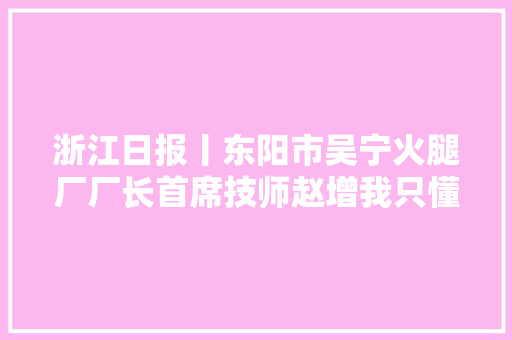
赵增最初与火腿结缘,是由于他爱吃肉。“听说火腿厂肉多,就义无反顾地去了。”赵增说,那是1979年,他高中毕业后找的第一份事情,进入国营东阳县火腿厂,当了一名火腿学徒工。
吃肉是大略了,牛肉干、腊肉、喷鼻香肠、肉松、猪油渣……年轻人饕餮,悄悄往嘴里塞几口,老师傅们即便看到了也不太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火腿厂的顶峰期,一年有数不清的火腿从东阳运到杭州、上海等地。险些一全体冬天,火腿厂里都是晾晒的火腿,一只只、一排排、一片片,仿佛“肉的森林”。
火腿晾晒是个力气活,每天早上7时开始,赵增就和伙伴们一起,把火腿从仓库抬出去晾晒。火腿24只一组,挂在一根长长的杆子上,一杆子火腿怎么也得有几百斤。
上午抬出去,下午又抬回仓库,每天来回100多趟,压得赵增肩膀生疼。不少伙伴撑不住辞职回家了,父母也劝赵增换个轻松点的事情,但赵增不同意。
跟师傅学削骨、学上盐,是赵增最花心思的地方。削骨的时候,如何握刀,哪里使劲,才能把骨头削得光滑?抹盐的时候,哪些地方要厚抹,哪些地方要薄抹?赵增的心里有一百个问号。
一开始,有的师傅不愿意教,“教会徒弟饿去世师傅,以前都是这么说的。”赵增说,他也不气馁,有事没事就给老师傅们磨磨刀,端端茶,乃至老师傅家里造屋子,他也赶去帮忙。
赵增的勤快,老师傅们看在眼里,小后生知礼数又好学,没有哪位师傅会不喜好的。逐渐地,师傅们接管了这个小徒弟。
赵增的双手,至今有不少或浅或深的伤疤,最长的一道,足足2厘米长,这些都是他当年的“学费”。刀修火腿,划伤难免,但最难忍的,是给火腿抹盐的时候,伤口一打仗盐,不仅痛,还不随意马虎愈合。
在不断的学习中,赵增度过了3年学徒生涯。
多走多跑,让他见多识广
赵增能吃苦,更爱研讨。当时火腿厂有十多种报纸、杂志,赵增常常看,还自费订了食品类的月刊,厂隔壁有个东阳县图书馆,赵增专门办了借书证,有空就去借一两本书来读。
报纸和书本,大大拓展了赵增的眼界。他看到有读者反响说,火腿看着像牛粪粘在上面,因此敬而远之。这让赵增知道,老底子的火腿卖相确实有问题,该当与时俱进。本日,市情上已经很少见到不加洗濯和精修,就直接售卖的火腿。
从学徒工到精良学员,再到技能好手,门市部主任,赵增一起走来,不仅完成了从技能人才到全能人才的华美转身,还报名读了函授大学,真正找到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1995年,赵增从国营火腿厂门市部主任的位置上辞职,办起了自己的火腿厂。当了老板后,赵增的脚步也没有闲下来,金华周边的同行,他基本全部切磋过,还跑到云南、四川、江苏、山东,乃至西班牙等地,到处学技能。
云南的诺邓火腿登上了央视“舌尖上的中国”,这让赵增坐不住了。“自古有名的金华火腿,竞争力去哪了?”赵增打“飞的”到昆明,转了好几趟车来到诺邓这个小村落落。“屋子便是我们这边的老屋子,经济发展一样平常,怎么就出了这么好的火腿。”赵增现场走、现场问、现场品尝,终极得出结论:一来,当地景象适宜火腿加工;二来,井盐的加工办法颇为独特;第三,质料好,猪喂养时用的饲料少。
质料好的另一个范例例子便是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猪吃的是橡果,以是肉的味道特殊。赵增在西班牙学习了好几天,研究火腿质料问题。“可惜因此游客身份去的,很多深层次的东西看不到,人家也不会见告我。”赵增说,未来如果有行业互换机会,他还乐意多出去学习。
多走多跑,让赵增见多识广。有一年,在江苏如皋稽核时,当地工厂正在修割腌制一批鲜腿,赵增一看,有点不对劲,他辅导工人把鲜腿一只只分开摊凉后,再把包裹腿肉的油膜用刀割破刮除,接着才抹头盐,摊凉再抹二道盐。
“这层油膜常日是不去的,就像一层塑料薄膜,起到保护肉的浸染,让盐的渗透变慢,让肉减少水分流失落,如果去掉了,肉接管盐分多了,水分流失落快,肉会凹陷,卖相变差,而且重量变轻,经济效益自然就差了……”赵增说,一开始大家都质疑他,以为他多此一举,摧残浪费蹂躏了好东西,后来创造,当地同样质料同等加工条件下,其余一家厂的腌制加工失落败了,丢失惨重,而赵增这边却安全无事。原来,赵增创造那批鲜腿在运输时闷太久了,以是才采纳去油膜等一系列方法“降温”,虽然利润降下来了,但至少保住了这批火腿。
功夫在手上,坚持在心间
都说火腿是韶光的赠送,一只鲜腿如何变成“珊瑚同肉软,琥珀并脂明”的火腿,赵增是这样做的:
先用刀刮去鲜腿上的毛,保留白蹄壳,再修劈骨头,整修成竹叶形,中骱的圆骨不得露出,边缘哀求弧中有直,将腿胚修割至面平皮洁。
一把盐,更是贯穿了全体腌制过程。用盐的讲求是赵增多年来从心口相传中习得的技能精髓,也是他多年操作履历的综合所得,用盐量必须按鲜腿公斤数打算,腌制韶光常日须要一个月乃至更久。
修腿、腌制后的下一步便是给这些粗胚进行修缮与洗濯。初出盐浴的火腿将进行名为“洗腿”的工序。火腿浸入净水中,用竹帚将余盐洗濯掉,用刀刮去残留,剥去油膜。进行捶打整体塑形,为下一步曝晒做足准备。火腿须要经由足够的晾晒,以晒干水分出油、发酵阴燥。
“做火腿三分靠技能、七分靠景象,温度对火腿品质有关键影响。”基于此,赵增对发酵房做了两次改造。第一次是加装空调,使传统发酵房变成能控温的二代发酵房,后来又改造成既有空调又有除湿机的三代发酵房,让火腿品质更有保障。
除了质料“一把盐”和功夫在手上的“两把刀”,赵增制腿,还有不少独特讲究。比如,他只做“冬腿”,意思是入冬往后才开始腌制,用天然的低温抑制霉菌。
他还承诺不加亚硝酸钠。亚硝酸钠是一种添加剂,除了防腐还能增色。但赵增对此颇为抗拒,他认为,只要技能到位,不加添加剂,火腿还是好看且能保存。
金华火腿全行业每年都会进行一次抽检,紧张靠火腿考验技师打签,他们会将毛竹签刺入火腿3个特定部位,迅速拔出嗅其喷鼻香味,就可判断整只腿的品质,过程看着有些酷炫。作为抽检师,赵增每年都要抽出大约一周的韶光,去金华火腿行业的一半厂家打签,五六秒一只,1个小时嗅大约1000只腿。
对品质的追求,让市场对赵增的火腿颇为认可。他的产品被金华火腿行业协会评为“质量最佳产品”,获浙江国际农业展览会金奖,他也被认定为金华市金华火腿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国家火腿加工高等技师、八婺工匠、浙江工匠……
“我只懂火腿,也只想做好火腿。”赵增说,入行至今43年,他就只做了这么一件事,也确实做成了。
匠民气语
别人都说干一行爱一行,我以为爱一行干一行,实在更幸福。
43年,我也算是个火腿老匠了。9年前,我儿子开始接班,他现在已是火腿高等工了。我跟他说,做人就跟制作火腿一样,你要给它上大盐,有时候会有些痛楚,但这样火腿才能喷鼻香。
现在爱吃火腿的年轻人少了,我有点担心,我们考试测验做过“豆瓣酱火腿”,它既有火腿喷鼻香,又有豆瓣酱的味儿,也做过低盐的“风冻腿”,市场反应不错,接下来还会不断创新。
未来,我也有一个自己的火腿梦,希望做一个完全的家当链,这样才能用更好的质料,做质量更好的火腿。
值班编辑:何贤君
值班主编:杨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