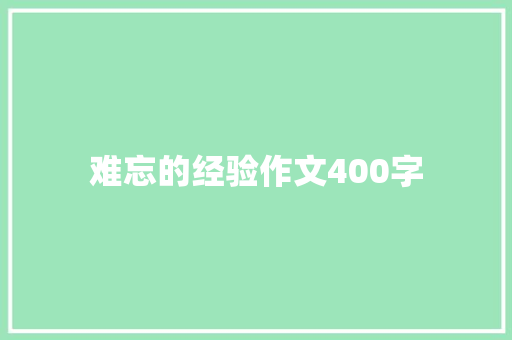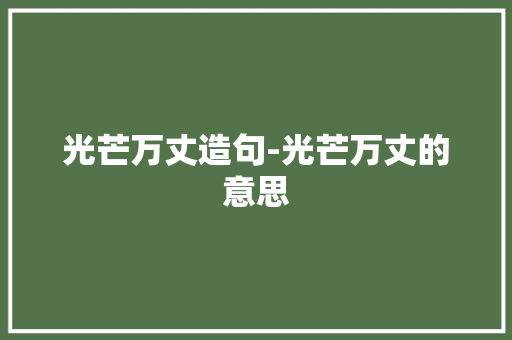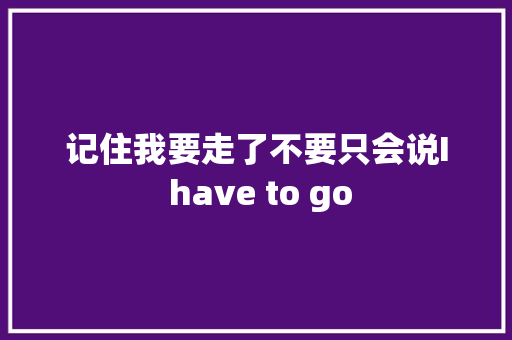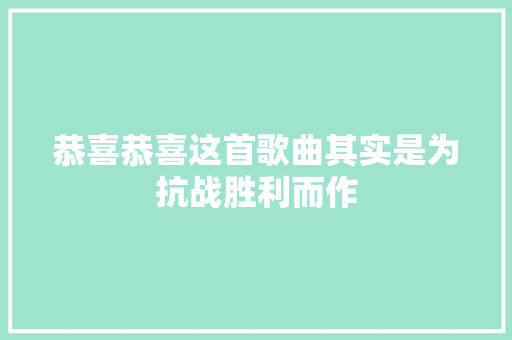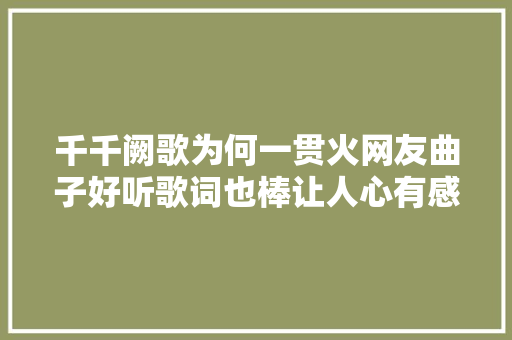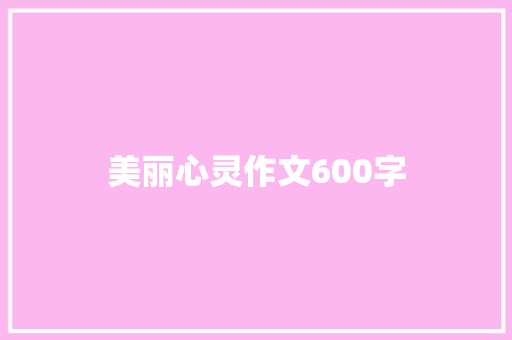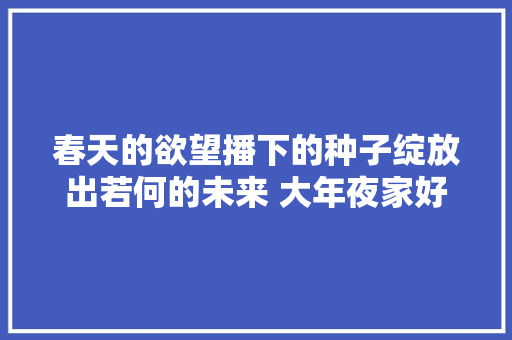陈舜臣写琉璃厂,写到了点子上。“……大概人们提及极具文化味的地方,每每会想象那是一个有大学或图书馆乃至是博物馆的地方。可琉璃厂一带并没有这些,自古以来就没有。人们想象的所谓有文化的地方都是作为政府项目建筑的公共文化举动步伐,可琉璃厂的发展却没有借助所谓国家财力。说得普通一点儿,琉璃厂是凭借民间之力创造的、极富文化氛围的地方。”(《琉璃厂的历史》)。把孔役夫旧书网比作“21世纪琉璃厂”,只因它和那条熙熙攘攘的街道确有几分气质上的契合。老夫子逛北京城,自带指南针,不知不觉往厂甸走,而赛博空间里的读书人,兜兜转转,总要回到“孔网”。
孔网的气质和它的创始人显然是有关系的。孙雨田师长西席在2002年创办孔网、又在2015年参与创办杂书馆,这两者都是各自“品类”中的分外之物:孔网是最不像电商网站的电商网站,它有个性化的商业逻辑和企业文化;杂书馆是最不像图书馆的图书馆,它打破了图书分类法搭建的严谨秩序,以“杂”而自居。孔网和杂书馆不能分开来看待,前者数字、后者纸本,前者商业、后者公益,表里归一,到底还要落在“文化”二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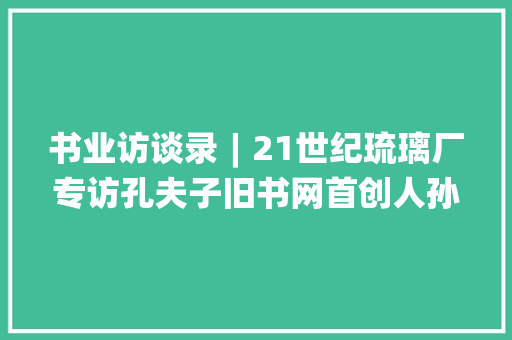
孔役夫旧书网创始人孙雨田师长西席
肖:孔役夫旧书网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样的?
孙:2002年我创办孔役夫旧书网,到2006年底、差不多到2007年新年的时候开始收费。中间大约5年的韶光没收过一分钱。孔网的商业模式很大略,便是租金和交易费。租金方面,开书摊是免费的、开书店的用度在100到600元之间,也不用交任何押金、担保金。现在入驻孔网的书店有1万3,书摊则达到10万多。在交易费方面,面向入驻门店的费率是5%。
从孔网现在的商业模式来讲,它对所有人是公正的,很多小摊摊主都能得到流量。淘宝的收费模式是向少部分人收更多的钱,投放广告卖得更多、卖得更多就连续投广告,不投广告的话,大部分人没有流量、挣不到钱。孔网不一样,它向所有人收一小部分的钱,大概每卖100块交5块钱。这种模式向所有人收费,但额度上比较温和。我们的收费采取均匀主义,官方不干涉商品搜索排序,完备按用户购买意图排序,以是搜索的排序是公正的。此外,孔网卖的是非脱销书,只要书足够好、具有独特性,谁都可以卖出去。
孔网的目标不是一个电子商务公司。任何一家公司都看重利润,但电商更看重规模,更看重GMV(成交总额)等关键指标。但实际上这个行业不会有太大的交易额,去年我们做到11个亿旁边,这已经算是很高的数字了。可是,哪怕再高也只是读书人的小市场。
孔网并没有想过成为一个纯商业化的公司,它和其他电商公司的商业逻辑不太一样。比如说,在我的逻辑里,匆匆销是有问题的商业观点,互联网通过补贴获取新用户,恐怕也不太合理。在所有的用户中,最宝贝的应该是老用户,只有他们才能为网站持续地贡献代价。很多公司不看重老用户,而是热衷于招揽新用户,来一个就给多少钱。这听起来很好,但要反思一下,商业是这样的吗?搞双十一、搞匆匆销,结果很可能是平台没挣到钱、卖家也亏本,由于这种大活动常常不收卖家佣金,还须要卖家冒死打折。不打折的话,用户也不傻,不会参加进来。这样一来,对用户也不好,他们很随意马虎买一堆不该买的东西。以是匆匆销充其量只是数据好看。有一些公司,基本上一年70%的销量是靠匆匆销出去的。我们从来不搞活动、不贬价,我也没做过市场营销。除了社交媒体方面,孔役夫旧书网基本上没有运营部、也没有市场部。很有趣的是,双十一的时候,别人贬价我不降,但活动期间我们的数据反而实现了50%的增长。
肖:不做电商公司,那孔网的目标是什么?
孙:孔网的目标是做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名片。我希望人们一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能想到孔役夫旧书网。一样平常人家里的藏书不会超过1000本,而且多数是《红楼梦》《三国演义》之类的经典书或者脱销书,普遍雷同。可是,当阅读的需求变得多样化,你看书就要看作者、看译者、看出版社、看版本,做到这个地步,可能才算真正的读书人。在中国,真正看书、读书的知识分子,基本都在孔网。
前面提到,孔网的商业模式与现在的互联网是扞格难入的,由于我们不融资。只管别人认为这种商业模式是异类,但我们还能保持着盈利。大前年我们有6个亿的交易额,前年8个亿,去年11个亿。这很难,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除了前面几家,其他人很少能有利润。在这样的情形下,第一要捉住用户,我只为2000万用户做事,不会做事太多人。即便有些人知道孔网的存在,但他们不来买书的话,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第二是资源。现在我们的杂书馆里有100多万册藏书,个中有80万件都是建国之前的文献资料。名人信件手稿大概有20万通,个中康有为、梁启超的信件、手稿都达到百件以上。
孔役夫旧书网主页
肖:您在2002年创办孔网、又在2015年参与创办杂书馆,现在杂书馆跟孔网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孙:杂书馆是由孔网、高晓松以及一批藏书家共同发起的建立的民间私人图书馆,孔网是杂书馆的运营者,馆藏图书还是属于藏书家的。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打通的。
现在杂书馆已经有了一个平台,还在持续的培植中。从运营模式的角度来讲,可以拿它和孔网做一个比拟:孔网供应资源的所有权,杂书馆供应资源的利用权。举个例子,很多学者写文章、做研究须要资料,又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相应的,不少藏书家专注藏书但又不利用。如果每个藏书家都把藏书放到杂书馆、放到我们的平台上,学者和藏家之间就可以对接起来。
如果我们未来能够进一步实现与国内外图书馆的数据联动,建立一个统一的资源平台,那专家学者们就不用四处觅而不得,直接在网上检索即可。对付藏家来讲,这种模式也有几个好处:第一,每个做收藏的人都希望展示自己的藏书,现在有了一个窗口,可以让你展示一辈子的心血;第二,有些人不想出售原书、但想卖复印件,对付这部分人,他们可以借助这个平台“以藏养藏”;第三,通过这种办法也有望丰富藏家们的收藏,当别人看到你的藏书之后,他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你的需求,会主动把干系的图书卖给你。可以说,杂书馆对付孔役夫旧书网来讲是一个补充。现在杂书馆还在逐步做、逐步发展。孔网我已经做了18年,再做个18年也没有什么。
杂书馆西文汉学馆一角
肖:现在孔网全体团队,包括杂书馆在内有多少人?
孙:我们的员工只有100多人,不算是很大的团队。孔网的流量还是挺大的,但技能产品部只有50人,他们都是高度专业化的。我们还有专门编藏书目录的部门,大约十几个人,全是科班出身。
只管团队小,但公司能留住人、大家都乐意干工作。这个团队的效率还可以,报酬也不错。我们加班多,但都会给出对应的报酬。这里有很多同事在上学的时候便是孔网的用户,毕业后又来到这里事情,以是他们特殊掩护孔网的利益,有时候比我更爱这家公司。
孔网能够活下来,内功很主要。我们须要站在更长远的韶光维度上去考虑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企业的发展就跟开车一样,终极取决于你能开多久。开快车去世亡概率高,180迈很随意马虎就没了,那我就开80迈乃至60迈。我们现在还年轻,可以开到七八十岁,还有很多年。中国亚马逊7月份不再发卖图书,当月我们的交易额涨了15%——企业活着才能不断等到机会。
肖:您刚刚提到亚马逊倒下了,但从旧书拍卖这些方面来看,这两年也有不少新的竞争对手?
孙:旧书市场是一个特殊垂直的行业,行业门槛还是很高的,大的企业看不上这一块,小的企业做不了。这么些年下来,能直接竞争的对手不多。实在这个市场特殊大,也特殊难做。做企业犹如开车,既然选择了80迈,就不要倾慕人家开180迈,心态要平衡。在中国市场上,很多公司只是昙花一现。C2C这个商业模式本身是一个奇葩的存在,按理说,每个行业都该当形本钱身的C2C平台,但是没有,基本上淘宝一家独大,其他很多公司都去世掉了。为什么孔役夫旧书网作为C2C平台还能活着,由于我们的商业模式完备不一样。
做互联网企业最难的地方在于,用户不会管你的团队是1000个人还是2个人,只管他们看到的产品好用不用。就算只有2个人,你也要做出跟别人一样的产品。既要踏踏实实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也得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实在我认为我们做得还远远不足。我更有钱了,我还是会全部砸在孔网里,把孔网做得更好。我拿着钱也没别的事干,末了老了也就捐了。很多人劝我把孔网卖了,也有很多投资人、上市公司跟我说要买。但卖完之夹帐里攥着钱干嘛呢,大概末了还是要再买一个孔网回来。我的想法特殊朴素,人生很长,可以逐步来,就想花这辈子的韶光只把一个事情干成。
肖:你认为旧书这个行业的独特之处在什么地方?
孙:孔网除了旧书、还有古玩杂项等方面的拍卖和发卖,实在都会碰着很多专业化的问题,办理这些问题须要商业聪慧,特殊要重视对包管交易机制的设计。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建立诚信很难,可一旦建立起来就非常稳固。以是很多卖家离不开孔网,在这里,封号是一个非常严明的事情。这么多年我都没听说过谁拿着钱跑了。也正由于这样,如果有轇轕,卖家和买家一样平常可以私下办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缘故原由,便是买书的每每比卖的精。
如果卖家和买家无法私下折衷,我们会参与来做专业的处理。孔网有专业职员鉴别书的真假和品相。干这行,我们是专业的。在书的品相方面,国家没有任何规定,以是孔网有很多规则是自己推出的,也得到了行业内的认可。我们有严格的品相标准,特殊细致,如果经由裁定,卖家不符合相应的哀求,就不能连续上架、就要赔钱。
除了旧书,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孔网卖新书,往后新书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像京东上排名第一的新华文轩,现在已经入驻孔网。很多出版人、出版品牌也开始在孔网上开店。目前孔网上的新书大概占1/5。这里面有个很大略的逻辑:所有买旧书的人也一定买新书。买旧书的人没有不买新书的,看在哪买便宜罢了。如果当当和京东不搞匆匆销,它们的新书价格并没有上风,纵然加上运费,孔网也要相对便宜一些。
肖: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行业的?
孙:这个行业确实是利国利民的,这两年我们做了很多比较故意义的事情,有些事情是别人干不了的。
第一,是参与了第26届北京国际图书展览会暨第17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去年恰好是新中国成立70年大庆,这一次的书展规模很大,而核心展区就只有三家公司——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发行集团和孔网。我们作为民营企业能进入核心展区十分难得。这次有一个专区用来呈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改革进程,涉及马克思思想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得老百姓推戴和爱戴等方面的内容。环绕这些议题,我们都拿出了实物证据,陈设了多种“第一套”,比如第一套毛泽东选集等等。展览的时候,包括中宣部黄坤明部长,北京市委宣扬部副部长赵卫东,北京市委宣扬部副部长、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王野霏等多位领导都到现场来参不雅观辅导。末了在受表彰的五六家单位中,只有我们是民营企业。
第二个比较故意义的事情是和潘家园联合举办的“万阅典藏”古旧书展览会。潘家园为这个活动供应免费的园地,并投入大力度做宣扬。我们则约请了全国大概1/3的旧书书商,北京本地的不必说,上海和江苏那边的书商全都来了,广东相对少一点、末了交易额大概达到2000多万,有很大的影响力。
我以为干任何事情,终极都在于你自己强不强,自强则万强。把事情干好,往后自然会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孔网每年的包裹量大概1600万,乍一听也没啥。可全国的包裹总量去年将近600亿,个中的大头是淘宝、京东和邮政,对付旧书这个的小众买卖来说,量级已经不小,没有必要妄自菲薄。
说这个行业利国利民,还有一个缘故原由。在这个旧书的生态链里,有许多二手书店、有许多卖家便是指望靠卖书养家的,他们没有什么其他赢利的渠道。有很多人发邮件、打电话来感谢我,说一个月能卖1000块钱的书,特殊感谢我。我本来以为1000块钱太少了,后来一想,人家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做孔网是兼职,除了上班一个月还能卖1000块,这一年算下来有个1万块旁边的收入,撤除本钱六、七千的利润还是有的,那很好啊。我们为几十万人供应了养家糊口的收入。既然那么多人靠这个行业用饭,那么办好孔网便是我们的任务。
我一贯认为,孔网不仅是一个交易平台,它有自己的行业义务。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免费供应外部查询的,即便已售的商品也是一样。如果这个公司骨子里是商业导向的话,绝对不应该把已售的东西也显示出来。我们将孔网的数据全部放开,为之付出了非常高的本钱。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便是一个公司的情怀。在骨子里面,我认为我们是一个行业性的平台,不能只看商业利益。实在很多人见告我,这些数据很主要、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供应付费做事,这些我是知道的。但我从来没干过这事。每个人都想学海底捞,海底捞的核心精髓是让利,大家都想学挣钱的部分、但不想学让利的那部分,那就没戏了。通过这些数据的开放,我们为大家供应了定价的标准。而这种做法也带来了回报,在旧书拍卖中,买家、卖家的数据实现了全透明,这种透明则带来了孔网拍卖市场的繁荣。
肖:卖家之外,您又如何看待孔网的用户群?
孙:买书的紧张是读书人,而读书人是一个泛用户群,由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读书人。它跟你的职位没紧要、跟你的社会地位也没紧要。正由于读书这个事情不是显性的,以是在任何时候要聚拢一帮读书人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很多买书、读书的人都是年轻人,老人逐步退下来了,年轻人起来了。现在总说年轻人不读书,实在年轻人比想象中的更热衷阅读,由于他们受的根本教诲比以前要好很多。像我们家还比较穷,小时候也没吃饱过饭,基本上没有太多这方面的追求。现在的孩子不一样,他们有独立的意识,有自己的品味和追求。
我们这一代人是从集体的环境里出来的,行动上、生理上都是偏集体化的,比如说单位上班、老板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但现在公司有很多年轻人放工之后就关机,单位里乃至还有一个人不用微信。社会的发展就在于多元化,我们要原谅多样化的行为,才可能不断地发展。现在全体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他们不再只追求有份事情、有碗饭吃。他们有自己代价不雅观,按自己的代价不雅观去干事。我以为这是至关主要的,我们做企业也该当这样,要顺着自己独特的代价不雅观一贯走下去,只要坚持,就会收成社会的正反馈。
以是我不会把孔网做成一个电子商务公司,而要把它做成一个文化公司。真正做文化是很苦的一件事情。杂书馆做了4年,接待超过21万人。有人质疑我们在作秀,我的回应是:你也可以做4年秀试试看。为了杂书馆,须要租用2000多平米的空间、每年投入300到400万的用度,4年下来,单单这一项就净亏1500万。但这个事情须要逐步来做,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培养更多的核心用户。
肖:孔役夫旧书网如何掩护和用户的关系?
孙:我希望孔网成为一个有感情、有温度的平台。
正如前面提到的,孔网的发展紧张有两个核心的抓手,用户和资源。未来一段韶光,我们想要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前段韶光,孔网APP上推出了“关注”功能,现在一天有1000多条动态。许多人通过动态发布自己淘书、卖书经历,乃至有人在里面写诗。我们想把它做成这个行业的朋友圈,打造一个读书人和卖书人的圈子。买新书的话,用户每每是哪家便宜哪家买,交易完后跟这些平台没有情绪上的维系。孔网的书比较特殊,这些书本是有感情的,卖书的店铺本身也是个性化的,每一个买家也有他们的故事。现在我要找鉴定专家给用户讲如何鉴别信札、找修书的师傅讲如何做文献保护与修复。只管这些事情看起来和商业不直接关联,但通过这些办法,孔网可以逐步地形成知识沉淀和文化氛围。真要说,这些事情和商业也是干系的,由于这些用户可能都会变成买家。
踏踏实实地做文化,不忽悠人,做得好了,自然会得到用户积极的反馈。互联网上骂我们的声音总体不多,但在孔网论坛上骂我们太正常了。论坛开了一年,我回了很多帖子。我一边回答一边这么想,用户离不开你才会骂你。我特殊看重用户的评分,看他们指出问题所在,然后逐步来改进。在APP Store上,满分评价是5分。孔网作为一个C2C的平台,和B2C的APP比较理论上没有什么上风,但我们三万多个评价,均匀下来和微信一样有4.9分,这便是用户感情的表示。
孔网APP界面
肖:末了我想理解下,孔网和学术圈的关系如何?
孙:海内有很多学者都跟我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北大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人大历史学院的孙家洲教授和清华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教授都来参加过我们的活动。除此之外,杂书馆有很多学者或干系团体来参不雅观、孔网的新书广场常常售卖学者的著作。
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没有太多韶光和精力与学术界展开进一步的互换与互助。我一贯在想,我们现在的实力还不足,等到实力再强一点,我希望能够通过某种办法为他们供应更多的帮助,乃至进入出版领域来做一些事情。
(访谈者系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副教授;赵庆喷鼻香、邝静雯、苏子晴、郑焰丹、秦倩滢、莫纯扬参与了本文的整理和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