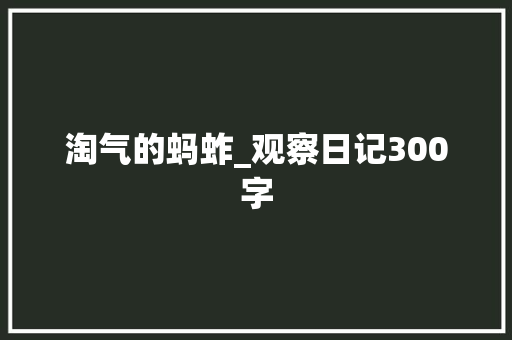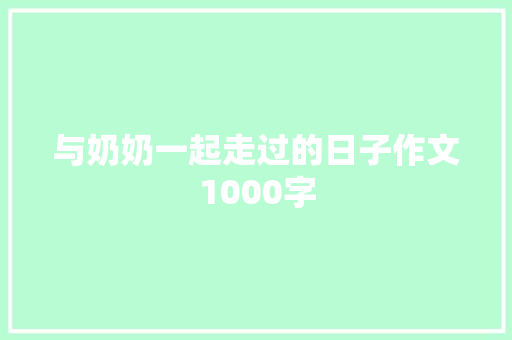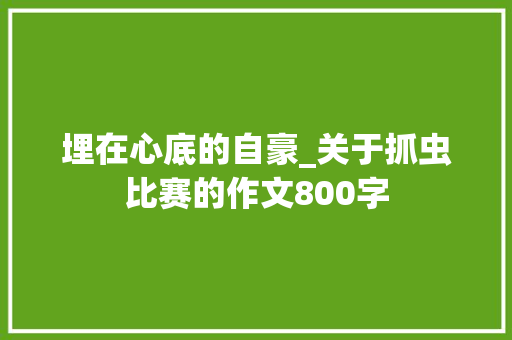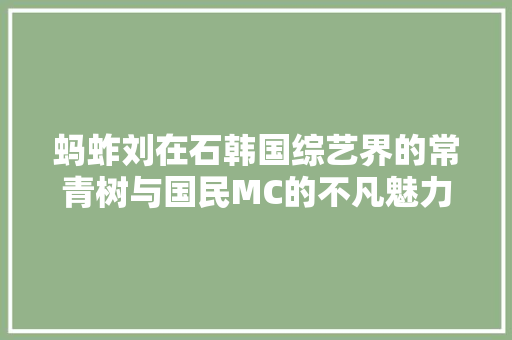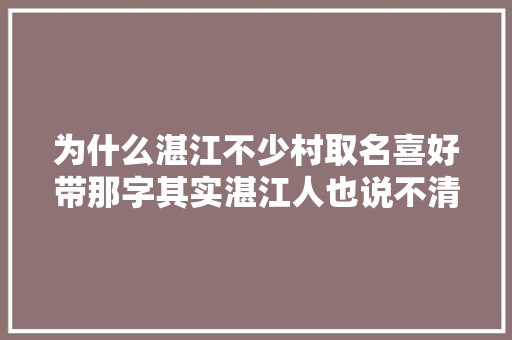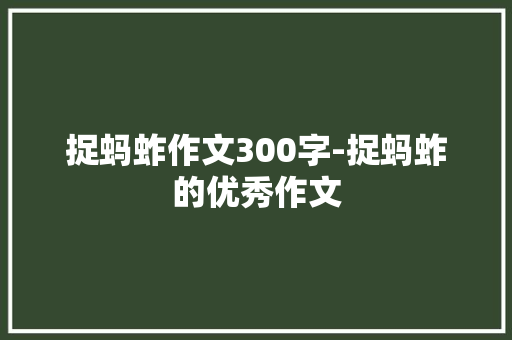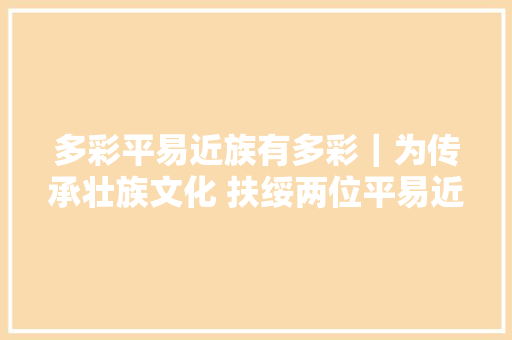——题 记(【法】法布尔著《昆虫记》)
我为卿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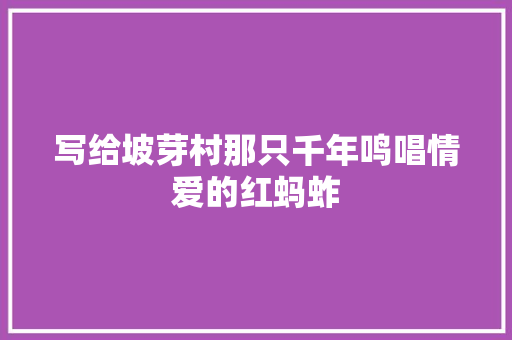
——写给坡芽村落那只千年鸣唱情爱的红蚂蚱
大凡昆虫,总有三对胸足,两对翅膀。或漫舞于苍穹天地之间,或振翅高飞于野外山林之际,或藏身暗藏于沼泽草丛之际,或低吟浅唱于山谷河流之畔……能飞会走,是介乎“飞禽”与“走兽”之间的“两栖生物”。
听说,蟋蟀、油葫芦、蝈蝈号称中国“三大鸣虫”。三大鸣虫中,玩得最好、最精彩、最有文化韵味确当数蟋蟀。蟋蟀又有“第一小提琴演奏者”的美誉。
(一)
在《坡芽歌书》中,有一首名为《油蚂蚱》的情歌。这首“蚂蚱歌”,让作为壮学人文学者,云南壮族作家的我,为之陶醉良久,乃至痴迷其间……
听说:歌书上画的蚂蚱捉住昆虫的特性,突出了长长的触角,大大的复眼和强壮的后腿。同时,昆虫的尾部画了一条尖尖的长尾巴,表示这是一条雌昆虫。其符号象征,在此其表示壮族少女,即歌中的“你”。
在此歌中,笔者认为:昆虫是少女的象征符号。昆虫的种类甚众,但“油”通“柔”, “柔”在壮语里是“俏丽”的意思。柔蚂蚱,是的是蝗虫中最俏丽的一种。“柔蚂蚱”,并非是王志芬书中所谓“油蚂蚱”。
笔者考证:这种“蚂蚱”,小巧玲珑,有小家碧玉的风范。头背鲜红,全身玄色,细皮嫩肉,优雅纯净,秀气俊秀。此歌用蚂蚱象征心仪已久的女性,表示出发自内心深处对女方的深情赞颂。“柔蚂蚱”的头背是鲜红的。而这一点红,和歌者所要赞颂的女性的红唇炎火相对应,《坡芽歌书》堪称熟谙《诗经》的“赋、比、兴”之道。
这首《蚂蚱歌》,用蚂蚱来比喻女性的面部面庞娇美,光荣红润。用荔枝色来比喻其面部洁白如月,面如满月。总体上形容此女的肤色白里透红,光滑好看。此歌赞颂女性的貌美嘴甜,从而层层递进,蕴藉弯曲,奥妙地打听该富宁A妹,家住何方,以便上门提亲求婚。
壮族人“以歌代言”,“倚歌择配”,“歌圩”便是一年一度的“赛歌大会”和“歌唱集市”,又称“风骚街”或“东方壮族情人节”。歌圩场上,初次相会的壮家青年男女,对歌开唱之际,最想知道对方的姓名和家住何方,因此,对歌之初,乃在试探,歌手用“一对一”问答的办法,逐步摸清对方的情形。“有心摘花怕有刺,丢个石头试水深。”从某种意义上讲,《蚂蚱歌》是一首初恋歌。
作为“歌唱的民族”——壮族,生命中不能没有歌唱,否则,就像“庄稼没有太阳,万物都不能成长”。《坡芽情歌》借一只昆虫蟋蟀进行反复咏叹,“与歌相伴”,壮家儿女的“歌海”人生,从此开启。正如【法】法布尔著《昆虫记》中所说的那样:“在我心里,那些迢遥的弘大星球啊,永久不会比草叶上一只小小的蟋蟀更能打动我。”
(二)
《坡芽歌书》《油蚂蚱》情歌中的昆虫“柔蚂蚱”,则是“俏丽蚂蚱”的壮语记音与汉译。
歌书上用抽象的线条,写意画的昆虫,夸年夜地突出并捉住鸣虫的特性,光鲜表现一对长长的触角,大大的复眼和强壮的后足。因此,与其说是一只蚂蚱,倒不如说是一只蟋蟀。由于,蛐蛐鸣,蚂蚱叫,都只是一个表情达意的象征性文化符号,让歌手莫要忘却这首情歌 “故意味的形式”——“图画笔墨”。
记不得是哪一年,我首次踏访富宁县剥隘镇“红饭花开”的俏丽村落庄——“坡芽村落”。当时,时任县委宣扬部副部长的刘冰山师弟指着老人厅墙上的81个坡芽歌书符号见告我:“师兄你想听哪首歌,就指那个符号,‘歌手’侬凤妹可以现场点唱。”我听罢,大呼传奇:“现场点唱,妙不可言!
这便是“歌仙”刘(僚)三姐的民族的神奇之处。不仅开口能唱,而且可以点歌现唱,全赖这一张画满九九八十一幅图的图画土布……”
在云岭壮乡,有一句壮族谚语:“会走路的人,都会舞蹈,会画画的人,都会刺绣,会说话的人,都会唱歌”。 每逢春回大地,壮乡便是一片“歌海”。正如民间文学大师钟敬文所言:“歌仙”—— 刘(僚)三姐,是壮族歌圩风尚孕育的儿女。有一首歌这样唱道:我们壮乡山歌多,山歌多过九条河。姑娘都是刘三姐,小伙赛过阿牛哥。
尤其是《坡芽歌书》画布的创造,更是给壮乡“歌海”,增长神奇的一种文化遗产,见证“铺满琴键的地皮”,只要轻轻一踏,就会“大地飞歌”,七彩音符,就象泄洪塌方一样,就象飞蝗成灾泛滥,饕餮庄稼一样平常,铺天盖地的扑来……
大慨记得当时的侬凤妹(后来的国家级非遗名录《坡芽情歌》项目传承人),身着玄色衣裤,胸挂白色珠链,腰系壮锦方格纹的花围腰,头戴壮族沙支系范例的紫赤色绣花头帕,方格织布巾上,点缀绣花图案,古朴蕴藉,素雅独特,犹如一束残酷的山花,她的照片一度成为壮族女性的衣饰形象代表。侬凤妹虽不懂汉语,也不识汉字,但并不妨碍她成为壮族歌神“姆六甲”。
《油蚂蚱》,壮语情歌从天籁传来。唱歌的人,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人”侬凤妹,她用富宁壮族沙支系的措辞,清唱起来:
(壮语原词对译汉语后是这样:)
妹很会说好,妈你是人哪(儿)
有你好象官,嘴粉蚂蚱荔枝。
手脚白如蕉心,你当妹人哪(儿)
告给哥知道,哥知道高下。
哥很想去返。
用汉语意译的歌词大意是:
妹妹你真会说话,是不是你阿妈教你的?
你一定出生在王侯将相家。你的嘴唇像油蚂蚱一样红润、像荔枝一样粉嫩,你的手啊白得就像芭蕉心。
你是哪家生的妹妹,你给哥哥讲句实话,是远是近让哥心中有数,也好下次去你家找你。
笔者认为,壮学专家刘冰山对《油蚂蚱》的文学解读,基本符合《坡芽歌书》的壮语意蕴。
壮族人天性浪漫,故任何时候都追求生活的丰富多彩。“歌伴人生”,是壮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唱歌是抒怀达意的最好媒介。
壮乡富宁每逢“陇端街”,每当夜幕降临,每遇外村落“勒包”(壮语:小伙子)“串姑娘”,坡芽村落的男女老少,便欢聚村落头寨尾,“以歌代言”,相互酬唱,你问我答,风趣诙谐,一片欢快……歌声中寄托着壮族公民的生活空想,也流淌着壮人光辉残酷的历史文化,表示着壮家儿女保持不懈、俭朴勤奋,吃苦刻苦、乐不雅观向上的民族性情,传承着骆越子孙以和为贵,崇尚自然,祭祖敬神,和谐人生的民族精神……
在《坡芽歌书》中的这只蚂蚱,实际上是用以表情达意的紧张物象为代表绘制而成,书写符号相对抽象而固定,且能唤起歌手对歌词的相同影象。每个人,只要见到这个图画,即可根据约定俗成的特定含义演唱整首山歌。换言之,第12首男唱,便是“蚂蚱”情歌。
从艺术上讲,用红蚂蚱的红,比喻“勒少”(壮语:姑娘)的嘴唇,用芭蕉心的白,比喻女方手指长的嫩白,紧张利用《诗经》中“比”的表现手腕。“蚂蚱”,成为情歌中美的意象和爱的符号。
从审美上剖析,壮语山歌中,常以王侯将相作比喻,赞颂人命运好,身份高,地位显,穿着好看,长相美,落落大方,举止派头。而壮人的审美意识,感化当地乡土物产。故赞颂女性的红唇,则是“红蚂蚱”,赞颂女人的肤色,则是“野芭蕉芯般又白又嫩。”独具“壮乡色彩”和“壮味”审美的乡土不雅观念。恰好应验一句箴言:“听得懂壮语苦情歌的人,会不由自主的让泪水把心灵淹没……”
(三)
当我再一次回眸《坡芽歌书》上的那只小小的昆虫,只见一对长长的触须,大大的复眼和强壮的后足。——这是一幅多么夸年夜抽象、童趣十足的简笔画。让我想起壮乡的民间歌谣:“蛐蛐蚂蚱多,蚂蚱多,(蚂蚱,壮语读音为:“梦天”。 )蚂螂(实为蜻蜓)蚂螂哥哥。”恍惚儿童时如纱窗般透明的豆蔻影象,又一次涌上心头……
“心想与妹唱几句,不知金口开不开?”由于这只蚱蜢,才有《油(柔)蚂蚱》这首“祖母的祖母传唱六代人”以上久远的探情歌。
壮人山歌,唱的比做的好听。作为“稻作民族”壮族人的爱情,不仅热烈、朴拙,而且坦直、坦白。但是,爱情宣言与直白,却要通过男女双方用壮语本地方言歌唱出来,尤其是女性歌手来传承与表达,必定是“绕山绕水”,“环顾旁边而言”,“悄悄静的爱情,羞答答的盛开”……这大概便是壮族人的浪漫天性使然。自由恋爱,情歌盟誓。虽然“骨子里激情亲切旷达”,但是“行为上蕴藉谦让”。属于“火山爆发型”,外表沉着,内心炽热……
对壮族传统情歌的套路而言,《油蚂蚱》是“初会歌”。这是初次见面,以歌交友的一种办法。内容一样平常是“问家住何处”,“谦恭赞颂”,虽属礼节性唱答,但都采取比兴的手腕和蕴藉的喻义,表达交友的诚意,以歌传情。在壮族传统的初恋歌中,大多以“穷哥苦妹”模式为歌咏题材,抒发同甘共苦,刚毅不渝的爱情,成为壮族的传统婚姻文化生理特色的生动写照。
多个比喻的意象,生动形象,让听者无人动容,乃至泪满衣裳……印证那句名言:“会壮语的人,听《坡芽歌书》会堕泪痛哭的。”以是,千万别让苦情歌燃烧滚烫的泪珠,烫伤你薄弱的心脏。
蚂蚱,大自然的歌者,稻田里的演奏家。每当它唱起求爱的情歌声时,它演唱的乐曲,就会格外地清新幽美,婉转动听。尤其是发出舒缓而悠长的叫声时,仿佛在声声呼唤它的心上人和它的配偶——另一伴,柔柔、短匆匆、缠绵悱恻,柔情似火之后,又发出一种酷似六弦琴与三角铃的旋律时,彷佛在倾诉衷肠。每逢听到雄虫的低吟浅唱,振翅高唱时,雌虫就会循声而至,共同完成传宗接代的“洞房花烛夜”……
坡芽歌书,这组幽美的壮乡爱情的密码,抒怀且浪漫,是有时得遇的美物,却引人深深奥深厚迷,我已经不但一次地陷入那些歌词所营造的情境……
从《坡芽歌书》2006年创造至今,每逢秋之始,一旦我在书桌窗前听见花园里的鸣虫唱歌,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坡芽歌书”女传人——侬凤妹亲手用神仙掌紫赤色果汁绘画的那只简洁、抽象、生动、真切的“油蚂蚱”,还有同名的这首歌,久久不能忘却其如“天籁之音”的美妙旋律……
我为卿狂!
由于,“俏丽村落庄”坡芽村落——《坡芽歌书》土布中的这只千年鸣唱的小小红蚂蚱,不仅常常会唱着情歌飞进我的心田,而且还时时会钻进我的梦乡……
文/龙符主编:刘飞副主编:邓凌编辑:小小吴审核:蓝淽 郭强 秋水法律顾问:冯在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