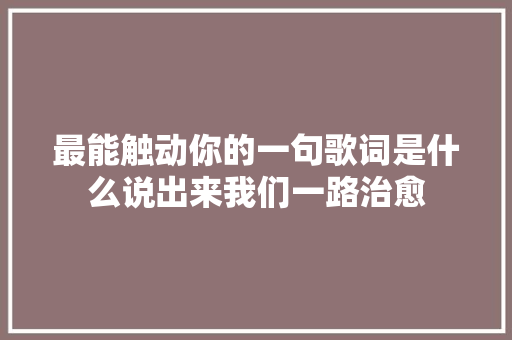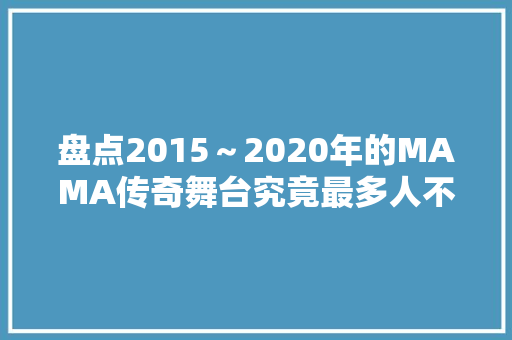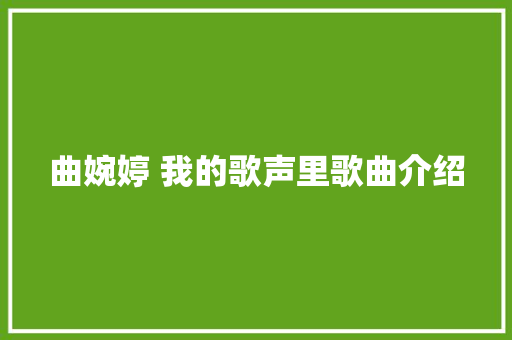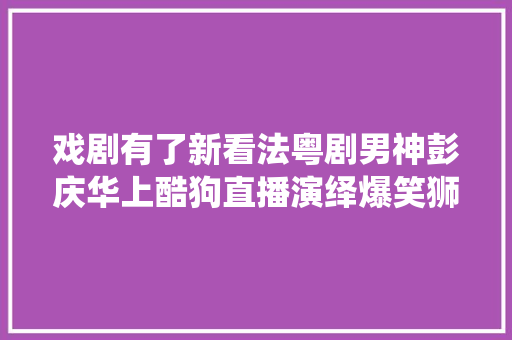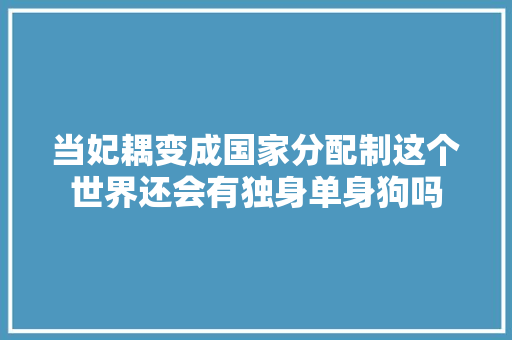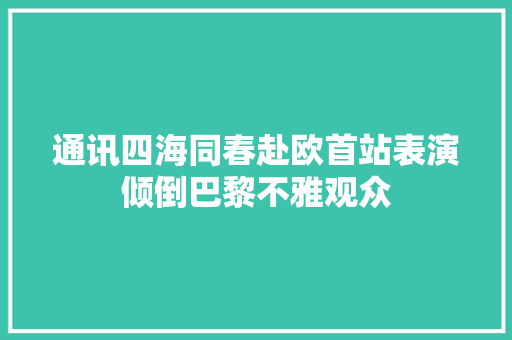之古人们提起大卫,总会说他是个说唱歌手,更熟习的人会说他是个墨客。而在5月6日的北京乐空间,大卫今年首次个人专场演出《在你身上,我战胜了这个时期》之后,无论多么挑剔的不雅观众都不得不承认,大卫是一名真正的艺术家。
人们从未在livehouse里见过这样的演出,不仅仅有乐队的演出,还有小品、Beat box、行为艺术、舞蹈,乃至还有二人转。5月6日晚十点,北京乐空间阴暗的灯光中人头涌动,他们当中有人专门重新疆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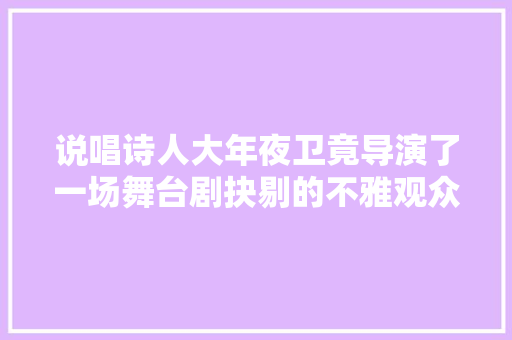
演出在大卫的个人记录片《大卫:孤独与联络》中酝酿,人们安静地不雅观看着。忽然灯光亮起声音寂静,一个长发半裸酷似耶稣的男人手里牵着一根铁链子走上台,铁链子的另一端拴着的便是大卫,依然是他标志性的黑西装黑礼帽,演出便是在这种极具象征意味的出场中开始。
将多种艺术形式结合在舞台演出中是大卫这次个人专场的最大看点,在第二首曲目《独舞之殇》中,开头一段踢踏舞solo演出把演出带入了第一个小高潮。
踢踏舞的强烈节奏之后,趋于平缓的舞台上,伴随着《独舞之殇》在台上的,是一张钢丝床,一个男人赤裸上身躺在床上,在享受着一个女人的推拿做事,大卫在演唱中走到床边,在被推拿的男人身旁念诵着歌词,帮着女人一起推拿。
在大卫前一场浸没式话剧演出中,伴随着象征着肉欲快感的推拿男女的是被铁链子拴着的耶稣,然而在这场演出中,换成了耶稣拴着大卫,大卫留在了推拿床边,与那迷恋肉欲的众人中,独舞之殇,“你甜美的就像是一颗梅子,我孤独的就像是一根儿锤子”。
台下的不雅观众被大卫的台风所传染,不同于很多乐队演出时总担心不雅观众不足嗨而用飙音量的办法试图带动感情,大卫并不喜好这种过于粗暴的办法,他细腻地在演出中精心铺设出节奏感,时而如狂欢节游行般的疯癫叫嚣,时而又是留白般的安静低语。
在一曲《我老了,我哭了,我恨你》之后,大卫要给不雅观众一点新的刺激,大家须要想起大卫同时也是一名癫狂的演员。去年大卫的单曲《一个大面儿的大腕儿在大圈儿里捡褴褛》在网上引起很多共鸣,人们预测他这首歌中详细指向的“大腕儿”会是谁,在当晚的舞台上,大卫用假发、皮裤、眼镜和“梦想”这个词揭晓了答案。
相声小品这样的措辞类节目原来该当是讽刺的艺术,但显然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相声小品却成了谄媚的艺术,那些并不可笑的过期网络段子妆点着一个个粉饰太平的故事。
大卫的演出从来只为创造而生,他乐于去让不雅观众体验诸多的“第一次”,将不同领域的艺术形式搭配到同一场演出中,来实验他们之间相通的灵感会碰撞出若何的火花。这一次,大卫带来的更是人们绝对意想不到的演出——东北二人转《鸡年大吉》。
这是livehouse历史上第一次涌现二人转,也是二人转第一次走进这种演出现场,或许,在很长很长的未来都会是唯一的一次。“只有在大卫的舞台上,这统统才显得那么自然不违和,也才会迸发出实验性的快感”,一位音乐媒体人在台下如此评价。
在这个民谣开满山的时期里,二人转这样生于大地的艺术却被视为低俗内容,那些附庸风雅的伪文艺青年们宁肯去听烂大街口水歌一样的所谓“民谣”,也不肯欣赏一下真正来自民间的音乐。大卫便是要把二人转带到自己的演出舞台上,跟Hip-Hop、踢踏舞、Beat box放在一起,让现场不雅观众体验一次真正多层次的演出。
一场小品和一场二人转演出,livehouse的演出中常见的是“牛逼”的叫嚣与尖叫声,却少见真正的诙谐感,不常听到愉快的笑声。大卫做到了,事实证明,来看大卫演出的不雅观众很具备欣赏跨界混搭风格的能力,对付民间戏曲也充满了好奇与激情亲切。
在二人转带来的热闹中,第一位特邀演出高朋出场了,他便是在前不久天下读书日的单向街朗读之夜上与大卫相见恨晚的音乐人、作家钟立风。当晚,钟立风用新创作的俄罗斯风情的曲子伴奏,与大卫共同演唱了《与爱情有关的十个短句》,钟立风自己又又演唱了《盲人与一位女子去渡海》。
在演出后,钟立风很激动在台上讲,他曾经一度想要放弃对音乐的追求,但是在大卫身上看到了创作的希望。在这些年里,钟立风一边进行着音乐创作,一边旅行写作,算不上高产,却是精心打磨自己的每一部作品。
在大卫身上,钟立风仿佛看到了自己二十年前刚来北京时候的锐气,已过不惑之年的他碰着对音乐与文学创作更加深刻新锐的大卫时,愉快的像个少年,大卫也紧接着把自己的那首《少年》送给了钟立风。
如果说第一位特邀演出高朋钟立风是提前宣扬不雅观众们期待的,那么第二位特邀演出高朋便是没有提前宣扬却被最熟习大卫的粉丝们预感一定会涌现的——崔健。
[video url=\公众https://v.qq.com/iframe/preview.html?vid=p05035l1e78&\"大众 title=\"大众\公众 cover=\"大众\"大众 tip=\公众视频地址必填, 封面图片在移动端会须要呈现\"大众]
崔健&大卫《混子》
在去年北京工人运动场崔健摇滚三十年演唱会上,大卫是崔健的特邀演出高朋,而在5月6日大卫的个人专场上,崔健同样作为特邀演出高朋走上了大卫的舞台。在此之前,崔健从未在这种小型livehouse里给独立音乐人当过演出高朋,这是一次被见证的历史。当晚,这两位彼此奉为心腹的忘年交演唱了一首《混子》,这首歌是两人共同的写照,送给彼此,也送给这个时期。
崔健的涌现带来了当晚最大的高潮,让台下的不雅观众完备陷入了痴狂中。只管一些虔诚粉丝已经有所预见,但看到崔健抱着吉他走上舞台,戴着他那顶红五角星的帽子,用低沉的声音先容起跟大卫的同台渊源时,尖叫声持续了许久。
如果说对一个时期的不同意不平服欠妥协算作是“混子”的话,那么舞台上的正是一个当年的“老混子”和一个现在的“小混子”,崔健在八九十年代对社会与艺术的改造在精神上继续到了大卫身上,这首两人同唱的《混子》便是一曲延续了三十年的人格宣言。
在对崔健的继续上,大卫延续的是激烈反抗的思想基调,却又保留着自己更加细腻的美学表达。大卫将崔健的反抗精神加以自我诗性的阐述,在艺术上有传承又不会勾留于过去,而是永久立足于这片地皮的当代。
在这个反抗精神被逐渐淡化的时期里,当年的热血青年很多变成了大腹便便的中年人,他们逐渐在现实的打压中失落去了对改变未来的期待与希望,有的干脆变得犬儒,只有在酒桌上对年轻人大声指教时才会眼睛里闪出一点光芒,如此的卑微可怜。可总有一些人,他们的热血是不变的,不会随着自己的年事改变,也不会随着外界的现实改变,他们只会把自己的精神保留住,连续通报下去。
在livehouse的舞台上,不知崔健是否会猛然间回顾起28年宿世人面前的演唱,想起长征和红布,想起自己音乐生涯的开端,只管那时还没有如此常见的livehouse园地与设备,可台下狂热激动的年轻面孔与他们对诗意与抗议的渴望却战胜了时期。
“在你身上,我战胜了这个时期”,这是大卫这次个人专场演出的名字,也是大卫对付自己创作与人格的寄托。这个时期对大卫这样的创作者并不友好,商业与消费充斥了文化艺术领域,成本和媒体替人们做出选择,挑选出那些煽情、低级、随意马虎产出和复制的作品,来添补人们的空闲韶光,让人们变得更加空虚。
把这个时期刺痛,让人们想起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便是大卫正在做的事情。他的作品时而激进,时而深情,他要让人们感想熏染到内心的振荡,去思考自己与这个时期的关系,自己与这个天下的关系,真正的艺术便是要让人产生这样的思考。
持续到凌晨一点半的演出,没有人提前退场,大家期待着这场演出能够不要结束,可以一贯演下去。大卫变幻迷离的舞台风格犹如把人们带入一场梦境中,梦中自有跌宕起伏的穿梭,时而优雅婉转,时而粗暴狂放。
大卫的演出不是让人理解的,是让人存心感想熏染的,那迷幻中无法解读的洒脱却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体验,人们无法明白自己为何不由自主去叫嚣、尖叫、堕泪和陷入沉思。
大卫不会停滞,还有下一场演出,下一首曲子、下一本诗集、下一部电影,大卫将自己的生命融入进他的艺术创作中。大卫是超越这个时期的,但也是属于这个时期的,如他诗中说自己如一把刀子插在这片地皮上,他注定要让这片地皮刺痛而改变。
尾声响起,大幕落下,演出结束。不雅观众久久不肯散去,凌晨两点的夜晚,纵然热闹如北新桥也有了生僻与落寞。这场演出会被每一个到场的不雅观众生平所铭记,那一晚,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用一场奇妙而激荡的舞台演出,打动了自己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