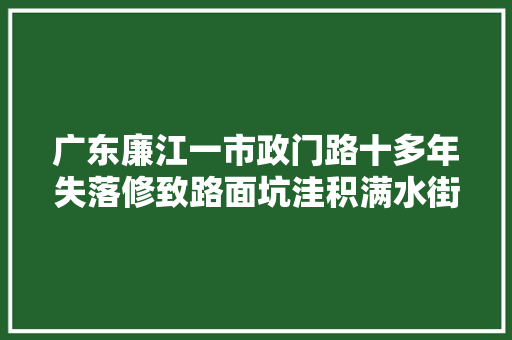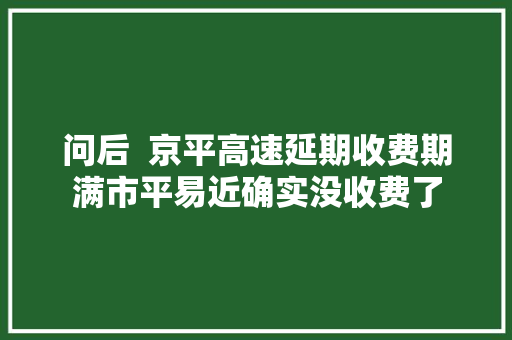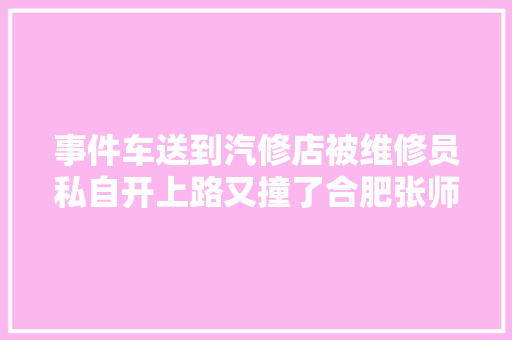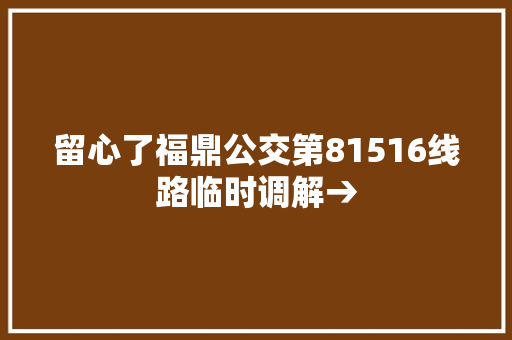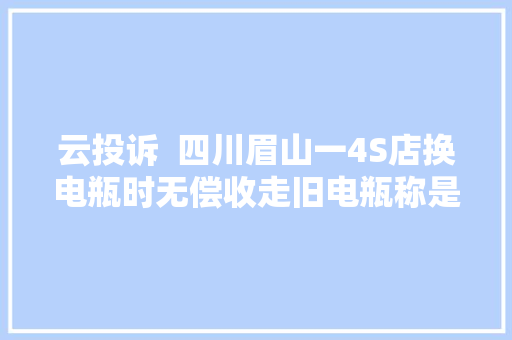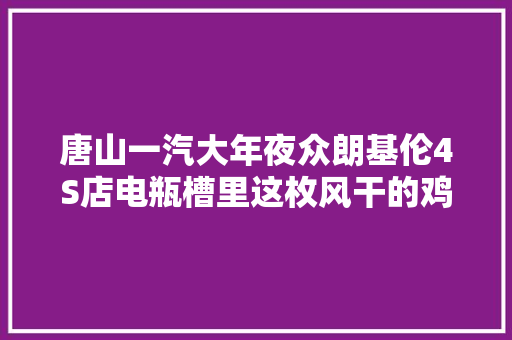杜欣欣/文
一

我记得人类学家玛丽·李基在东非奥杜瓦发掘时,将所有居住在赛伦盖蒂大草原上的人都称作邻居,而我得以结识李泽厚师长西席也是因美国西部地广人稀之故。
那是1996年夏季,经刘再复师长西席先容,我与夫君认识了李泽厚师长西席。当时李师长西席正在位于科罗拉多泉的科罗拉多学院任教。科罗拉多学院是一所私立的四年制文理学院,虽然不大,但名声不小,粱实秋曾在那里留学。我问过李师长西席:“一样平常人60岁都退休了,你却来美国闯天下,62岁开始在美国学校授课,你紧张吗?”李师长西席回答,最初是有点紧张。紧张是他从未正式讲过课,更没有用英文讲过。 “那你开始讲课时,最担心是什么?”“首先我担心的是学生听不懂我讲的。学生刚开始听我的课,确有因口音引起的问题,但很快就习气了。我将一个观点用不同的词汇阐明,以不同办法表述,学生如果听不懂其一,但能听懂其二,终极总能捉住一个。讲课紧张是要逻辑性强。”“李师长西席说:”我最怕的是听不懂学生的提问,后来也不怕了,由于学生的问题很大略。” 我问:“那你的英文一定很好吧?““我的英文只学到初中二年级。当时上的还是屯子中学。后来到北大上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俄文。一年后,我就能听四年级的俄语课了。但我比较守旧,决定还是去听三年级的课。”
除了俄语,李师长西席还学过德语,大概学习半年之后就能看原版书了。某年,他在威斯康星大学演讲,很多听讲的中国学生夸奖他英文好,但他说:“我的英文并不好,只是讲得流利不太在意语法。我以为学习措辞语感很主要。”他坦承:“我知道很多专业单词,但日常用语弗成。” 每个学期末,美国的大学都通过学生问卷对西席进行背对背评价,据李师长西席的系主任说,学生对他的评价很好,有两位还说他是自己最喜好的老师。他的课注册名额是25人,但能有27-28人注册,由此也能看出他开课是成功的。
在科罗拉多学院教书后,李师长西席决定学习开车。他说不会开车就不能行动。确实,科罗拉多泉市相称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面积,但当时居住人口不到30万,根本无法建立公共交通。当时很多人劝他年纪这么大了,不要学开车,可以依赖儿子接送。但他坚持要学,并拿到了驾照。我原以为李师长西席开车不过是搪塞高下班,从未想过他还能开长途行驶高速公路。
1997年夏天,我们约请他与再复师长西席一家来我家做客 ,行程大概4小时。那时没有GPS,他们决定开车跟随。由于我对道路不熟,选择了一条并不随意马虎行驶的山路。山道弯弯,好不容易驶上国道,却只看到刘师长西席的车。一起上,我都不敢开快,一贯把稳着后面的车是否跟上。三个多小时之后,我仍未看到李师长西席的车,只好停在路旁期待。一贯看不到他的车,无奈,只好连续向前。附近我家的高速公路出口,我溘然创造李师长西席的车停在路旁。原来他早到了。我说:“不是说好了跟我的车吗?”他回道:“你开得太慢了。”李夫人文君在一旁不做声,后来我听说他开车不看时速,一个劲向前开,文君对此很不满意(很多人称李夫人为师母,但李夫人坚持要我称她文君)。
2003年的美国独立节,我与李师长西席一家从博德出发去位于南科达州的拉斯摩总统山国家公园。去时,我和李师长西席的儿子李艾轮流开车,李师长西席只开了非常短的一段。回来时,李师长西席非要驾驶,但文君不肯望他开,小艾也不好意思谢绝爸爸的要求。我把稳到,李师长西席开车时,牢牢地握住方向盘盯着前方,险些不看速率表。小艾时时提醒:“爸,你开得太快了。”他开车确实令人紧张,文君胆小,又不会开车,更随意马虎反应过度。到了怀俄明州,李师长西席说了一声想去方便一下,径直就开下出口,偏偏那出口没有方便之处,行驶至小路尽头,他猛然煞车,彷佛还未完备意识到路已尽。我们纷纭下车,松了一口气。
二
李师长西席离开科泉迁往博德,与刘再复师长西席做了邻居。我与夫君到访李师长西席家,常常住宿于他的书房。他的书房里有三大架和一小架书,分类是哲学、历史、文学、医学、生理学、脑科学和神经科学。 个中最多的是哲学书:海德格尔、尼采、康德、叔本华等。书架上的很多书中都有折页和标红。我们睡的是一张充气床,很不舒畅,但我从未提起过。直到2013年,我们不再是唯一住宿他家的客人,他才得知那张床很不舒畅。他对我说:“你们太客气了,为何不早见告我?”于是那张充气床就被换成折叠沙发床,再被安置在客厅里,又加了一道屏风。李师长西席指着床和屏风对我说:“这是专门为你们添置的。”
那天晚上,我睡在屏风里。屏风外下几节楼梯,便是厨房和另一个客厅。我听着李师长西席带着计步器在那里走来走去。他长期失落眠,完备靠安眠药入睡,而我那时也失落眠十多年了。不知过了多久,李师长西席的脚步声逐渐消逝了。大概深夜三点,我听到他又起来了,在客厅和厨房之间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叹气:“还是睡不着啊。”越日清晨,我问他半夜起来的事,他却矢口否认:“没有这个事,一定是你在做梦。”那段韶光,我们常常谈论“如何能睡着觉”。李老师对安眠药颇有研究。虽然我吃了很多年的安眠药,但面对他的 “催眠还是安眠?”等问题,竟然答不出来。他问我每晚服用多少舒乐安定,我回说:“两片。”他问:“两片是什么意思?我问你多少毫克?”继而他就批评我:“你不严谨。”
我虽愚钝,但多年交往下来,也记住一些李师长西席对哲学家的评价。在某次发言中,他谈到西哲的排名,依次为康德,休谟,马克思,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笛卡尔,毕达哥拉斯,杜威,海德格尔。但另一次发言中,他说最推崇康德和柏拉图。他还说:“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讲年轻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什么都不满意,二是总以为自己最了不起。尼采能够知足这两个特点,以是他深受年轻人的喜好。在中国,海德格尔很有影响,由于他的哲学有激情,随意马虎被中国人喜好。”李师长西席曾提到中国哲学家的排名是:孔子,庄子,老子,荀子,孟子,韩非,王弼,慧能,朱熹,王阳明。有时他就某个哲学观点说上一两句,譬如“道德,一是来自上帝,二是来自社会须要。”我曾问他:“中国是否不存在真理问题?”他回答:“中国不存在真理(Truth)问题,不把真理问题排第一。”
除了哲学,李师长西席对社会学的一些课题很有兴趣,比如男女之间的差异、家庭关系等。他数次推举我读《脑内乾坤》(Brain Sex)。当得知我还没读,他就说:“你怎么还没读,那便是讲男女之间差别的。这本书能在女权运动飞腾的八十年代出来,不会完备没有道理,那里面说的征象和现实很同等,不过不知道科学根据如何。”提及男女关系,他一贯认为,夫妻之间除了爱,紧张是恩,恩典维系家庭。末了的实在是感情。“大家都想有爱其他人的自由,但又哀求对方对自己忠实。这当然是说已婚或已经建立长远关系的人的心态。”李泽厚师长西席几次和我提起要研究一下婴儿与父母同睡会对生理造成的影响,成年之后有无差异,并将此作为东西方文化差异来研究。他对女性的性生理十分好奇,我们有过比较深入的磋商。他说女性的性生理大大的繁芜,比如欲仙欲去世便是女人才有。他基本认为在享受性方面,中国女性还是比较被动,但险些每个女性都有做母亲的欲望。他喜好几个女演员,比如蒋雯丽,他认为她的眼睛特殊俊秀,很好奇她在真实生活中是不是这个样子。
李师长西席对自己的边幅也很把稳。一次他见告我,他不想照镜子,由于自己老了丑了。我听了大笑,“我以为只有女人才这么在乎自己的样子容貌,你,一个理性的哲学家居然有此动机。”他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吗?”并问我对他边幅的意见。我说:“你三十几岁不好看,太瘦。五十几岁时最精神,特殊是《明报月刊》上刊登那张照片。”听后,他也承认五十几岁时的自己最帅。 我们一起看过电影《色戒》,他认为李安很棒,指出一些特殊的镜头:“王佳芝第一次和易师长西席之后的那扇窗户,还有易师长西席作爱时的背影,王佳芝放走易之后,走到街上赫然看到橱窗里的模特以及末了三轮车上摇动的风车,还有钻戒放在桌上摇动。”我说梁朝伟演得很好,比如眼神刚开始是冷冰的,但后来看王时就带了怜爱。他说:“原来并没觉得他能演得这么好,这次算服了。”“但张爱玲被捧得太高了,乃至超过鲁迅。也不但夏志清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不喜好她,由于你们还有空想主义。”
李师长西席一贯订阅的英文杂志除了时报周刊类,还有艺术类。他常常抱怨随年事已高,英文开始退步,与此同时,他的医学藏书也扩充为一个书架,个中很多是英文版。他特殊向我推举默克的康健手册(Merck Manual)。我以“不想知道那么多让自己紧张”为由谢绝,他说:“你没有科学精神。”每次身体涌现问题,李师长西席都会仔细研究,对任何医疗康健的决定,他都要研究了很多资料之后,综合考虑才作出决定,极少只听一个年夜夫的建议。大概自2000年往后,李师长西席的书架上增加了很多当代史的回顾录。他将回顾录中的内容与当年自己听到的或经历过的对照,他说:“总想弄明白一些事,不能这么糊涂地去世了。”
李老师送过我一些他的著作。每次我问他问题,他就会说,这个问题我在哪本书提到了,你都没看。言语间颇有不满,我也心生惭愧。每次我对他说:“我看不懂你的文章。”他又说:“你不要去看我的书,只看你爱看的就好了,我的书不好看。”虽然李师长西席的书架上没有很多文学书,但他有时会商到文学。中国文学家中,他第一推崇是鲁迅。他不喜好周作人,讨厌胡兰成,以为钱钟书的《围城》是三流小说,只是英国名流的小噱头。我记得他曾评价钱钟书的学问是一地散钱,有了互联网后,其博学的意义减半。
李师长西席那代人和我们这一代都读过很多俄国文学。李师长西席喜好陀斯妥耶夫斯基,他见告我40年前读过《卡拉玛佐夫兄弟》,至今想起来还有震荡力。我们曾谈论过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李师长西席说:“好的作品是人物丰满,有故事性,但最主要的是措辞,用什么措辞写。个人化、个性化的措辞,在于把握措辞的能力,以是作者必须对措辞敏感。有些小说侧重于社会性如托翁,有些侧重于哲理性如陀氏。”他以为卡夫卡、乔伊斯的作品没什么故事,读来沉闷。有时,他会对我的写作读书提出意见:“你对当代人生活细节感兴趣很好。作家最好是做业余的,不能将此当饭吃。当然不用除那些天才,比如巴尔扎克。好作品和天才有关,也和阅历有关,但有阅历不一定能出好作品。但科学并不见得有天才,规律在那里迟早会找到,但是文学就不见得。”
关于文学作品中的噜苏,他认为不能通盘否定,比如红楼梦便是讲噜苏,托翁也如此,但由于有了情绪,以是读起来故意思。休谟也很噜苏,但因无情绪,很难读。写作题材是一个问题,但不能太绝对,比如齐白石画的题材大多是劳动人民所用的物件,但却与上层意见意义结合。他不止一次说过:“搞文学的人该当糊里糊涂,太理性的人不能弄笔墨,我没读过王小波的小说,我认为他太理性,不会写小说。”
李师长西席最不喜好看马戏杂技,他说从来不看杂技。 2012年圣诞节之际,我们和他一家去看电影《安娜·卡列尼娜》。看完电影,我们同等以为电影中的安娜不足俊秀,而在托尔斯泰的书中,安娜该当比吉蒂俊秀很多,她的俊秀不仅使吉蒂一见就自愧不如,而且使沃伦斯基初见时顿有电光雷火之感。回家的路上,我们还在议论着电影。他表示同情卡列宁,我说:“你同情卡列宁就解释你老了。”李师长西席说:“托尔斯泰提出一个什么是幸福的问题,吉蒂的生活还是安娜的生活?实在当时法国很多贵族家庭生活便是如此,丈夫不能知足妻子,妻子有了外遇,丈夫默认但不离婚。俄国社会崇尚法国,卡列宁肯定不吸引人,安娜不爱他也没什么可以责怪的,但安娜要冲破社会习俗,要把关系公开,还想离婚。”我又问:“安娜可不可以不去世。”李师长西席答:“一样平常人都会不去世,特殊是有了孩子,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孩子便是统统,有了孩子可以没有丈夫。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你(指作者)就不是这样的,但你也承认无论如何你也是妈妈。当妈妈是本能,本能就很难降服了,而人的第一本能便是生。”过了一阵,我又问了同样的问题,李老师说:“你也老了啊。”如果我说自己老了,他又会很不以为然地说:“我62岁才去科罗拉多学院教书,你还没到我那个年事呢。”
三
在落基山下,李师长西席常叹闲愁最苦啊闲愁最苦。每年夏秋,他会回中国。数月后,他回到科州,又总被那边的热闹折磨得精疲力竭,他叹:“这里太寂寞,那边又太热闹。”近年返回后,他累得连讲电话都没了力气。 我的一个年轻朋友是八十年代大学生,托我向李师长西席存问。 李师长西席连说感激她写了这么激情亲切的信来问候我。过了一下子,他又说:“八十年代写信来的人很多,有些信写得很激情亲切。”大概过了一周,他又问:”你那个朋友怎么会商起我?前几年,我在海内讲座,有人看到我的名字竟以为是李嘉诚的儿子。”
我不雅观察李师长西席不喜好与人交往,也很不喜好热闹。某次,金庸受邀来科州大学博德分校,约请人是李师长西席的好友再复,不少在美华裔文科学者前来,但李师长西席没有出席。又某次他碰着某有名画家,画家说:”我和再复是朋友,再复和你是朋友,以是我们也是朋友了。“李师长西席不语。画家要送他画和字,李师长西席不收。后来,针对那个画家谄媚于权势,他说:”哪朝哪代都有无耻文人。“
李师长西席一家只有三口人,我们常笑言他家也是三权分立:妻子文君统御厨房家事,儿子小艾统御汗滴(英文Handy的谐音)工程,老李统御形而上抽象领域。小艾处事严谨,设置的网络密码长达50个数字!
他凡事讲求操持,纵然父亲找他有关电脑的事儿,哪怕在墙上釘一个钉子,他都会说:“来日诰日(或后天)上午9点吧。”到时候,他一定会来处理。在车库里,小艾还谅解地放了几只修路用的红白塑料路障,以帮助老父停车。然而,李师长西席却不愿求儿子,他的中文电视、电脑等一干问题仍旧找我。李师长西席常说,我的妻儿从来没读过我的书,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兴趣爱好更是南辕北辙。李夫人文君是孤儿,自小在上海跟养母终年夜,后来考上北京的文工团成为舞蹈演员。与李师长西席老师结婚后,她带了母亲同住。文君说母亲在世时,她不会煮饭,母亲去世后,才学着烧菜。因李师长西席吃食挑剔,结果她会烧上海菜和湖南菜(李师长西席是湖南人),成了好厨师。每次我们到访,文君总会做些特殊的菜如火锅、春饼等。最初的几年,李师长西席总是邀刘师长西席一家过来用饭谈天。每每是文君烧菜,我打下手。她极爱干净,饭后的清理一样平常也由我做。
李师长西席喜好给妻子买礼物,特殊是小首饰。妻子试戴耳环,总问他怎么样,他也总会给出见地。午饭前,李老师坐在沙发上,文君像小孩似地蹲在他面前问他中午吃什么?我有次开玩笑说:“你对文君像对孩子。”他说:“她本来便是个孩子。”我创造实在文君也是把李师长西席当孩子哄的。李师长西席有时也会耍小孩脾气,在拉斯摩总统山国家公园,文君买了一个印第安人的手镯,她太瘦,手镯戴起来有些松,想去换,李师长西席说不用换,我开始打圆场要陪文君去换,结果他竟然掉头而去。
每次饭菜烧好了,文君自己却不怎么吃。以前有朋友曾总结烧好菜的窍门是“馋而不
李师长西席很能享受饮食之乐。夫君为了掌握胆固醇略高,常年在自助食堂用饭却能做到不碰一口红肉,李师长西席对此评价道:“我很理性,但只是在判断问题时比较理性,我怎么也无法做到像他那么理性。如果我像他那么理性,什么乐趣都没有了。”近年为了掌握饮食,吃晚饭时,李师长西席只能分到一小盘菜,由于他很馋,还要坐得阔别饭桌才能掌握自己。
除了好吃,李师长西席还好酒,险些每顿晚饭必有小酌。他家常年备着葡萄酒和烈酒。每次去那里,我都会陪他饮酒,吃着文君烹饪的佳肴,我们的话题每每漫无边际。我说的多是社会新闻,人情百态,他很喜好听。有时说着说着,他会嘲笑我:“女人便是话多。”我顶他:“你听了这么多还居然这样说我,真不厚道。”他听了大笑。
李师长西席非常反对文如其人的说法。他说文章都是做出来的,如果作者性情坦直,可能反响其人会多些,他认为这“如果”可以在1%-90%之间,要详细看。他强调个体差异。他谈到:“女人一样平常结婚之后都看重家庭生活,以丈夫孩子为中央,对其他的东西兴趣不大。但你(指作者)是一个例外,一贯没有损失好奇心。”我多次听他说:“严复曾说国人重博识,西人重新知。这便是很不同。中国人看重读书多的人,以读书多少来剖断有无学问,再以此来评价人。但读书多却无创新,不能算数。还是要有自己的东西,比如读书,紧张看这本书提出了什么问题,这问题是否得当,办理得怎么样。比如熊十力有创新,这个人很直率,夏天光着膀子,无论男女到他那里,他都是光膀子,吃菜自己一个人独吃,从来不让,还说这菜补脑筋,以是我就得自己吃。”我还记得他说过,“中国可能出歌德,但却出不了爱因斯坦。”虽然他几次再三强调新知 ,但他评价人还是常说有没有学问(一笑)。
如果刘再复师长西席在场,有关文学的话题就会比较多。李师长西席谈到:“郑孝胥的古诗词很好,但人们便是不喜好他,包括汪精卫。我很早就很不喜好周作人和郭沫若。”我说:”因人废诗,这在中国彷佛比较盛行,西方不大这样吧?”刘师长西席说:“是的。这是中国的传统。西方对付海森堡和海德格尔就宽容得多。”我问:“那这传统是好还是不好呢?大概我的问题很蠢,是不是非理性?”李师长西席答:“这问题不蠢。生活本身就不理性。中国是将行为笔墨和书面笔墨结合起来看,一个文人大节不好,终极也不能受到历史尊敬,当然经由很长的时空之后,如果特殊突出的还是会得到一些承认,比如董其昌的字等。但我一想到周作人穿日本军装的照片,我就怎么都不能欣赏他的散文。”
有时,我与李师长西席分享我读过的书。我和他谈起《Into the wild》(走入荒野)的主人公Alex,他说:“那是慢性自尽。如果是中国人,人们就会提及父母怎么办,既然父母生了你,拉扯大了,就不能走极度。”他又提到希腊靠航海贸易发展起来,中国是农耕社会,以是特殊在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说:“实在Alex可以去做隐士,但他不信教。”李师长西席说:“信教有多种,可以做隐士也可以去挣钱。生命本无意义,全靠自己去探求,佛陀最聪慧,知道人生下来便是苦,但已经生下来了,怎么办?”“刘再复不承认有忧郁症,实在西方很多人有忧郁症。”
我们多次谈及去世亡,李师长西席说,他赞许安乐去世,并多次谈论如何安乐去世。那时科州还没实施安乐去世合法化,我说你安乐去世是非法行为,他带着几分得意地说:“我有办法!
”然后小声说他积攒了不少安眠药,又补充道:“你不要见告文君。”
读完《Persepolis》(中译为《我在伊朗终年夜》),我和他谈论中国为何缺少侦查小说和漫画。李师长西席答:“这我早已把稳到了。没有侦查小说的缘故原由是中国人缺少推理逻辑思维。很多人写论文,写得措辞很好也激情,但便是逻辑漏洞很多,根本无法说服人。以前总要理论联系实际,我最反对,有些理论便是不能联系实际。”我说:“那便是说中国人特殊实用吧”“是的,便是我说的那个实用理性。这当然有不好一壁,那便是实用,但也有好的一壁,那便是反而随意马虎接管一些新的思想,由于有用。受这种传统思维影响,中国人在科学就没有什么创造,最多也是技能层面的。但这不即是说中国人没有能力做推理逻辑,而是受传统文化思考影响,比如中国人到了西方,还是有不少人做得不错。爱因斯坦曾说,中国没有实验,没有推理,但还有一些发明。中国没有数学公理。但日本人更差,险些没有推理逻辑能力,多是履历主义,他们将神秘主义和履历主义结合起来,出了一些东西,但他们没有多少发明创造,也没有像样的哲学家。哲学家便是提出问题,供应一个看待天下的视角,不同的视角看宇宙。”我问:“没有漫画的缘故原由是否由于中国人太看重威信。“他说:“有这方面的缘故原由,还有一方面便是中国人好面子,讲究的是人际之间的关系。”
我们也常谈到印度。李师长西席问我:“印度人是否善于抽象思维?比如发明了零,最近看到一篇宣布是这么说的,说打算机科学技能最适宜印度人,你和印度人打仗多,觉得如何?”他说他对印度人安于自己等级的印象特殊深刻。我去印度旅行前,李师长西席几次再三哀求我理解印度古代措辞留存情形。他说:“古笔墨,比如古埃及笔墨、巴比伦楔形笔墨都没有遗留下来,但是中文却流传下来。一样平常来说,措辞和语音有关系,中国字则没有,但却保存下来了。”
有一次,李师长西席和我评论辩论我的写作和读书。他说:“我记得几年前,你就发愁没有方向,如今还是如此。这不奇怪,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找到方向。比如你现在为了写家史要读近代史,但还是不足详细。现在书太多了,你没有方向地读,会摧残浪费蹂躏很多韶光。”他看我有些沮丧,又说:“你已经很不错了,除了上班还出了三本书,翻译了三本。你文章已经写得不错了,你还是好好写文章吧。”多年来,除了叹闲愁最苦,李师长西席总说心情不好。如果我说:“我也一样,总是updown,updown。”他就说:“我都是down。有些人以为我很生动,实在都是假象,你还有些朋友,我年轻时就不喜好听人谈天,交不到朋友,不过这几年有些不同,在北京用饭,热闹的我也喜好,有时桌上就我说话,说得很多,大概是老了就变了。”他还说自己
李师长西席很尊敬何兆武,数次提到何师长西席几近贤人。他说:“何师长西席大我九岁,可是每次我回京都是他来看我。2006年,何师长西席生病住院。我返国后,打电话给他,说该我去看他,他还是来看我。他以前从清华到皂君庙社科院宿舍便是骑车来,现在他坐车,但是我在东四附近的家,进不来车,他得走进来。他妻子大他10岁,后来患了10年迈年痴呆症,都是何师长西席照顾。五十年代,历史所出书,将他排在末了一名,排在李学勤等人之后,实在他资格学问远赶过那些人。他英德法文都是最好的,他不是右派,但是就这样陵暴他。八十年代,何师长西席翻译一本《德国的年夜难》,书压在商务印书馆15年才出版。他连问都不问,一样平常人都会去问。八十年代,他连屋子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社科院对他很不好,末了调到清华去了。
2012年,李师长西席返国后去看望了107岁的周有光。周老住在一栋大略单纯楼里,房间很小(他也不要搬大房间),屋子里有不少书,但整顿得挺整洁,并不像宣布说的那样乱。周老还可以在保姆搀扶下上三层楼,听力有些问题,但视力还好,听说是当年做白内障手术放入人工晶体很成功,周老说这辈子两次幸免大灾,一次是重庆轰炸,气浪将他推出十几米,一次是反右前从经济事情调去搞笔墨改革。后来从事经济事情的同事都被整得很惨,自尽的家破的。他说:“周老不愿接管采访,但还是喜好有人去看他。”
2007年2月7日晚,我给李泽厚师长西席打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疲倦无力,我问,“你病了吗?”他说,“我病了,5日那天清晨,溘然左半身抖动不已。大约持续一小时。包括牙齿高下斗殴,彷佛冻着了似的。后来朋友劝我去医院,我在那里住了两夜。”他又说,“年夜夫还让我住院检讨,但是我不干。后来和年夜夫吵起来,自己把管子拔了才出来的。”我知道他的倔劲儿又来了,无法相劝,只问他须要我做什么,是否问一下我那仁心仁术的表嫂丽岩年夜夫。他多次咨询我的表嫂,后来表嫂一家到科州,李师长西席特意请他们用饭。自那往后,李师长西席总说体会到什么叫行将就木、朝不保夕和一病不起。
2008年12月,由于北京太冷,他比操持提前从北京回来。回来后,李师长西席的心情很坏,基本不接电话。在中国时,朱厚泽陪他去贵州,但不过两年,朱厚泽就去世了,这个很令他吃惊,由于去贵州时,朱师长西席还非常康健。听到李慎之师长西席去世的,他也觉得很溘然,由于数月前,他还见过李慎之师长西席。
2012年,他从北京归来,一周之内疲倦得无法接听电话。自从他的几个熟人得了老年痴呆症,他也有患病,李师长西席常常为此很沮丧。 由于他的状况并未像自称的那么不好,他又沮丧了很多年,我也没把他的话太当回事。
2014年12月30日,李师长西席约我和夫君去他家。文君说他精神不好,很不爱讲话。到那里后,他精神看着还不错,但他说视力出了问题,不大能看书了。他一贯说看不清楚,但却看出我胖了一点(一笑)。虽然我们已经用过晚饭,还是坐下来陪他饮酒,吃些坚果。眼病使他更加沮丧,但他还在写作。李师长西席送我他的著作时,总说这是末了一本了。我笑道:“你已经说过多少次这是末了一本了。”
四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美的进程》在中国大陆热卖,李泽厚师长西席成为大众文化明星,但那时我已身在国外。1986年返国后,我忙于教书,以及外企兼职又要养育女儿,乃至从未有过空隙读一本李泽厚师长西席的书。然而,与很多好学上进的人一样,对付大学问家,我怀有天然的崇敬。可以说,认识他25年来,我一贯怀着崇敬的心情与他交往。我们之间相差24岁,他算是我的父辈,但是每次与李师长西席通话,都觉得他思维敏锐,声音洪亮,兴致总是很高,从未感到他老了。直到他76岁之后,我才溘然产生了记录的急迫感,这些交往点滴原来也只是为了记录留存。
2017年,我母亲患病,李师长西席夫妇曾前往医院看望。我母亲过世,他讯问了很多细节。自那之后,李师长西席身体日渐朽迈。我与他从十天半月见面,逐渐减少至一月一次。2020年疫情以来,李艾因担心传染,只能网购,但当地华人超市不能网购。我买菜前都会发微信问他欲购物品,他让文君写下须要物品拍照给我。文君一贯说李老师胃口很好,他家的采购量很大。我们买菜后送至他家门口,按一下门铃,文君每每会涌如今窗户上,向我们合掌存问。
大约一个月前,李老师曾微信我说他摔了,并扣问能否找我表嫂丽岩诊断。我回答没问题,他却顾虑重重,说好久没联系不好意思。我问他摔得可重?他说不严重,只是在做翘腿运动时,椅子挪动跌倒。文君10月27号曾致电给我,说李老师又一次摔了。我问可看过年夜夫,她说看过,并未伤着骨头,只是比较疼痛。文君还说,他吃太多的安眠药。大概是听惯了李师长西席常说自己行将就木,我也没太放在心上。之后,我再次微信给李师长西席扣问须要买什么菜,未获答复。又致电去,家中却无人接听。我虽有些担心,但总觉不会有事,也不好意思打扰。
2021年11月2日晚,我溘然接到李艾关照:我爸本日清晨过世。他说父亲是在睡梦中过世的,还说已经留下遗嘱,大脑冰冻保存,尸首火化,还说他们都不打算办丧事。这个实在太溘然,记得文君上次来电还说,希望疫情过后大家再聚会,可惜再无可能了。
(作者系本报专栏作家,现居美国科州。文中紧张内容记于2007年,全文改于2021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