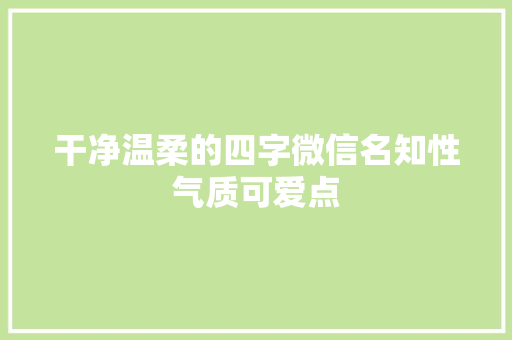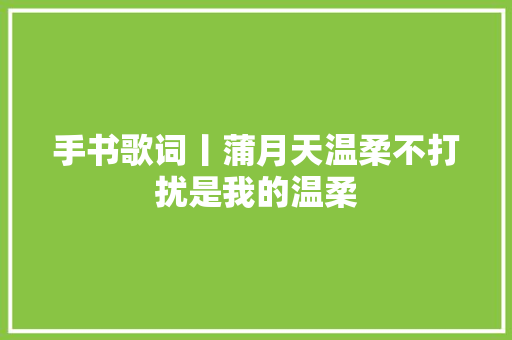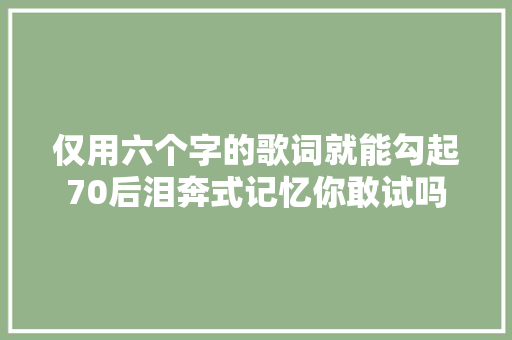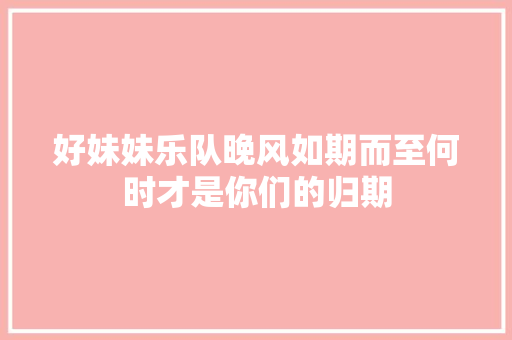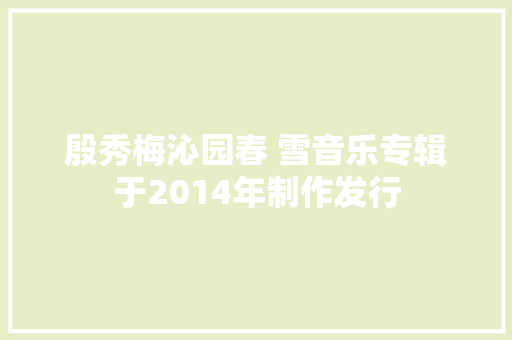坐看云起时
坐看云起时,秋之昙日屡目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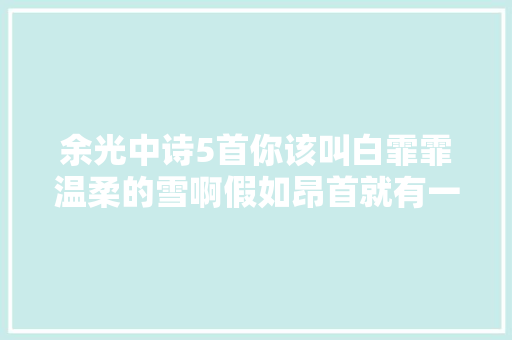
以白眼与青睐。我遂遥念阮籍
念他每行至第三世纪的穷途
辄恸哭如我,如我坐在
不知江南是什么的相思树下,看云起时
看云起时,善变的太空能作青白眼
看今之白我者,昔曾青我以晴朗
看云起时,谁在作青白眼
我并未恸哭,并未恸哭如魏人
我是行到水穷处,疑无路
遂坐看云起,测风的方向
云起时,统统在变,宇宙在作壁上观
不雅观昙的抱负如何成形,如何合,如何分
如何自无中生有,如何善遁
当我闭目看一只归鸟
如何泳入荡胸的层云
当梦跌碎在玻璃表面,自泰山
白霏霏
温顺的雪啊你什么也不肯说
嘤嘤婉婉谜样的打发
向右耳,向左耳
那样轻的手掌温顺的雪啊
那样小的唇
如果仰面,就有一千个吻
落在我脸上,俏丽的痒
你该叫白霏霏温顺的雪啊
只有女友有那样白的嘴唇
那样白的手
一开就落,那是什么样的树?
一吻就失落踪,什么样的嘴唇?
一抖就放手,什么样的手?
什么样的洁癣温顺的雪啊
一践就去世亡?
在爱斯基摩的冰圆顶下
仰脸,举臂,像一个孩子
且伸开馋了好久好久的嘴唇
只为舐一舐温顺的雪啊
小时的影象
山雨
雾愈聚愈浓就浓成了阵雨
人愈走愈深就走进米南宫里
路愈转愈暗就暗下来吧薄暮
墨点点墨点成的墨景
更多的雾从谷底蒸起
究竟,是山在雨里
或是雨在山里
一座小亭子怎么说得清?
听!
森森矗立,林阴的深处
一声鸟
把四壁空山啭成了一句偈
守夜人
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
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
已经,这是末了的武器
纵然围我三重
困我在黑黑无光的核心
缴械,那绝不可能
历史冷落的义冢里
任一座石门都捶禁绝许
空得恫人,空空,恫恫,的反应
从这一头到韶光的那一头
一盏灯,推得开几英尺的浑沌?
壮年往后,挥笔的姿态
是拔剑的勇士或是拄杖的伤兵?
是我扶它走或是它扶我提高?
我输它血或是它输我血轮?
都不能回答,只知道
寒气凛凛在吹我颈毛
末了的守夜人守末了一盏灯
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
做梦,我没有空
更没有甜睡的权利
荔枝
不必妃子在骊山上苦等
一匹汗马踢踏着尘凡
夺来南方带露的新鲜
也不必墨客贬官到岭外
把万里的劫难换一盘口福
七月的水果摊口福成堆
旗山的路畔花伞成排
伞下的农妇吆喝着过客
赤鳞鳞的虬珠诱我停车
今夏的丰收任我满载
未曾入口已经够能干
袒露的雪肤一入口,你想
该化作若何消暑的津甜
且慢,且慢,急色的老饕
先交给冰箱去秘密珍藏
等冷艳沁澈了清甘
洗手不干成更妙的仙品
使唇舌愉快而牙齿复苏
一宿之后再取出,你看
七八粒冻红托在白瓷盘里
东坡的三百颗无此冰凉
梵高和塞尚无此眼福
齐璜的画意怎忍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