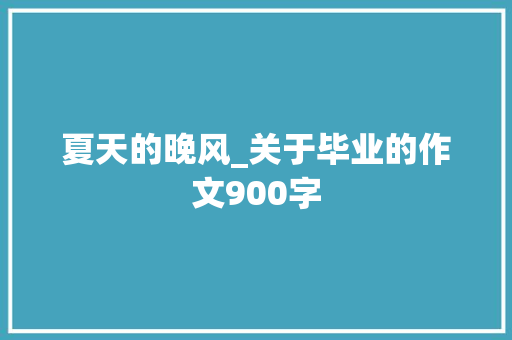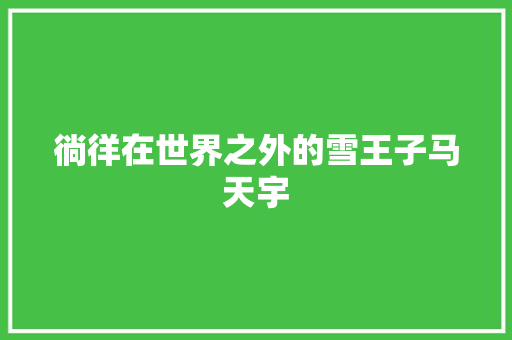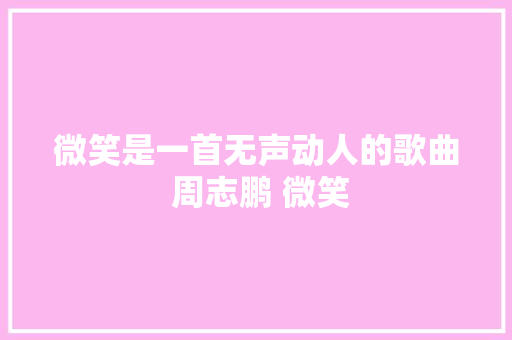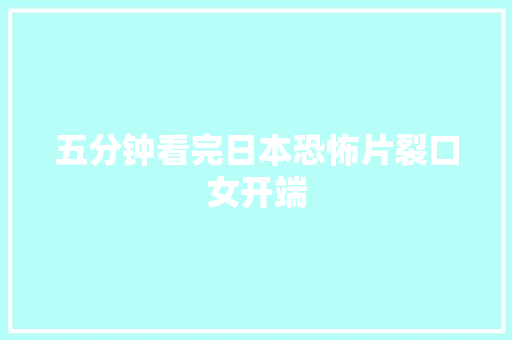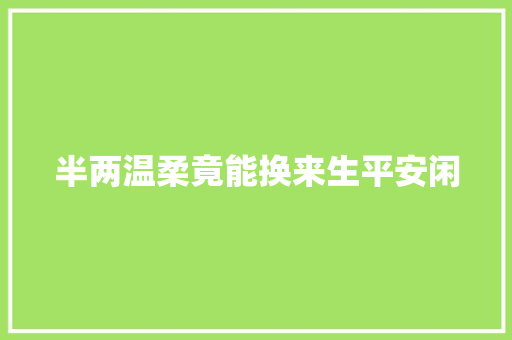檐下燕儿年年纪纷飞来又复去
岁月不觉又斑驳发肤多少很多多少纹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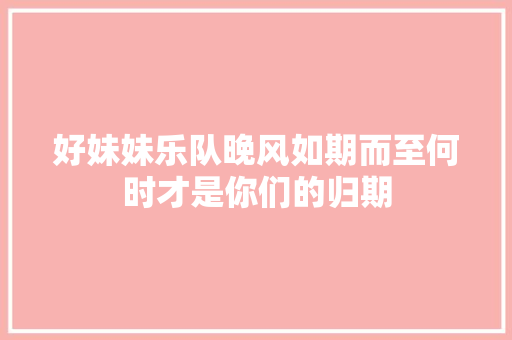
远远传来月色下谁在哼着旧戏
缠绵悱恻地消磨离人多少愁绪”
——《准期》
他们的歌并不像一样平常意义上的民谣,大略,纯粹,这是我初听好妹妹时的感想熏染。
逐渐的,我创造那是种少年感,他们唱着少年无所畏惧的快意,前路无垠的广阔和追逐所爱的执拗。
他们唱“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的感激”“你啊你,是清闲如风的少年”“那一年我二十一,那年你二十七”“许多人,交往来交往去,相聚又别离,让我拥抱你,在晴朗的景象”带着耳机听着大略的歌词,那么贴切,那么真实,后来才知道,我们实在不是在听好妹妹,而是他们唱的自己。
那年,我们有最美的身体,追星赶月也未以为怠倦,恋恋风尘,举手无悔枕山河入眠,爱上了那个残酷的温顺了我们青春的人,不须要调情,不用分场合,随时的一个眼神交汇便是灯火辉煌。
那年,那个青草味道的夏天,午后冗长的数学课,头顶风扇嗡嗡的吹乱了作业本,我们却不留神的趴在桌上闭着眼,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性,带着梦想,唇角飞扬。
“温顺的晚风
轻轻吹过 爱人的梦中
温顺的晚风
轻轻吹过 故乡的天空
温顺的晚风
轻轻吹过 城市的灯火”
——《晚风》
音乐有的时候不须要那么严明,不须要那么立意深刻,只要在孤单的时候给人以温暖,在受伤时给人以抚慰,在暴躁时给人以沉着。
就像他们的乐队名字, 逐步念出也能让民气底变得优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