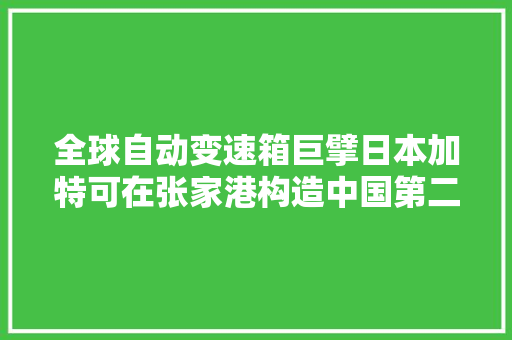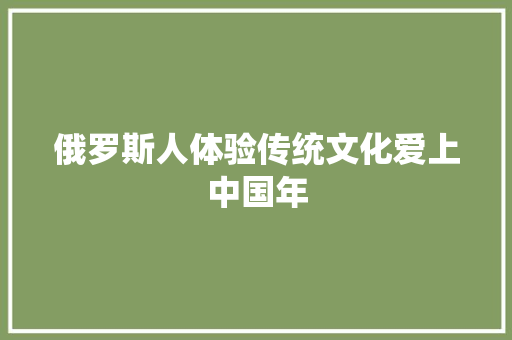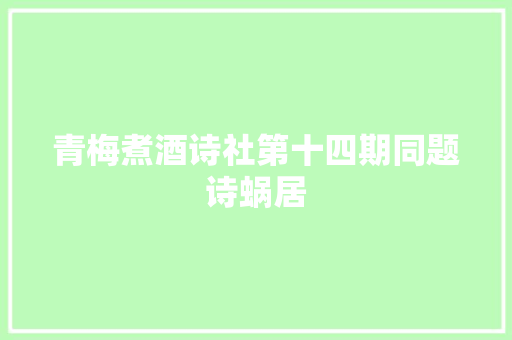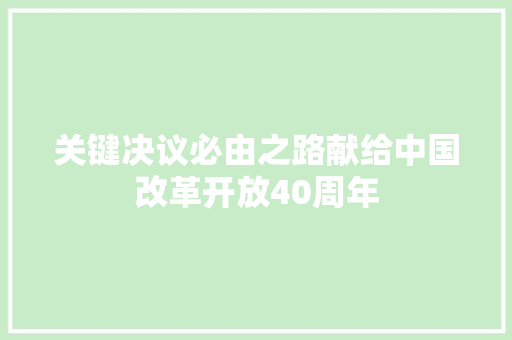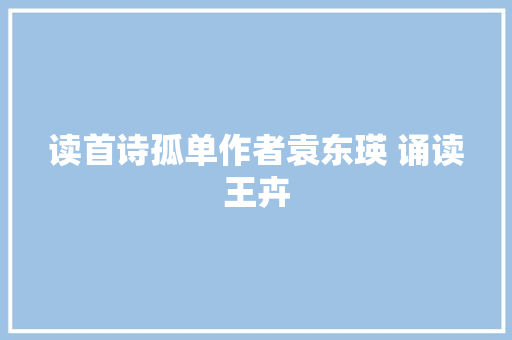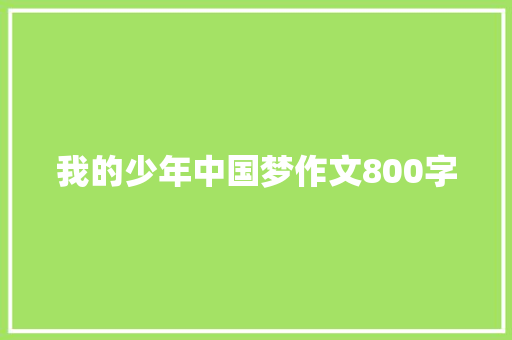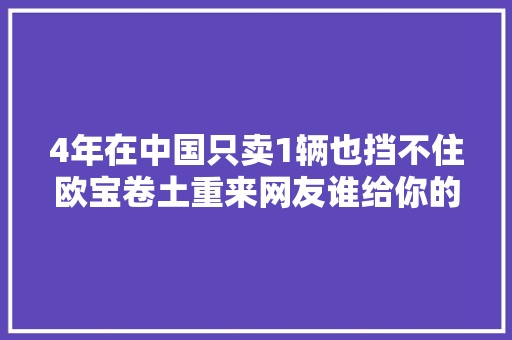作者:胡 平,系作家、学者,已出版书本30余种,著有《中国的眼珠》《千年沉重》《瓷上中国》等多部作品,曾获全国精良报告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
《景德气候: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胡平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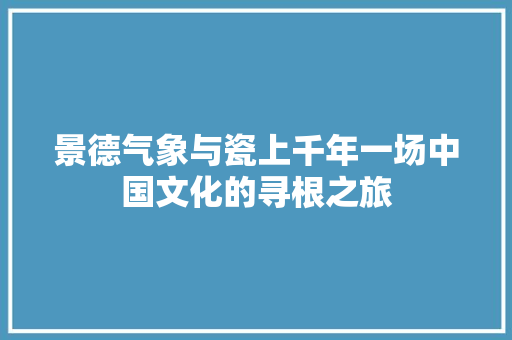
1楔子
自2013年深秋第一次来景德镇,迄今已经8年。
无数次地来往,少则住几天,多则待十几天、大半月。这回从去年6月始,在镇上东南角的三宝村落,客居一年多了。山居的日子,重读由我所著的《瓷上中国》。此书2019年被推举为“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向外洋推举的七十本好书”之一,再读却略有粗率之感,让我对这方水土感到歉意。
景德镇三宝瓷谷
在中国以丝、茶、瓷驰名天下的年代,景德镇这方水土贡献出了个中两种。
过着日日捧瓷喝茶烫到假牙的日子,对这方水土的不雅观察与思考逐步深入。我与这方水土上活动的人,尤其是被称为“景漂”的中外新景德镇人,也有了声气相投的联系。
我想,我该当再写一本书。此书,将不仅仅看重历史,也同样不雅观察现实;非专注陶瓷,而且专注于漫长过去与今日在景德镇留下深深足印的人们,尤其是他们的生命办法、生活办法,这些足以构成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再有,我想让本书的肌理成为思想的一片开阔草地,看似突兀却自然地跳出一只只令人熟习或陌生的“蚱蜢”,如伏尔泰、包豪斯、民艺运动、乾隆等等。
于是,刚刚问世的《景德气候: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便成了我这只长喙老雕在景德镇这株苍森大树上的又一长叩。
“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礼记·学记》),无疑,不叩则不鸣。地域文化魅力无穷的地方,总是书写饱满的地方,如肖洛霍夫之顿河,马尔克斯之南美,老舍之北平,莫言之高密。地域文化模糊,难以让人有解读、探索兴趣的地方,总是书写苍白的地方。
那么,景德镇,是否算是一座久别于书写的城市呢?它于当下,又具有若何的意义?瓷从何来?小小一片瓷器,何以成为“中国”,又如何承载中华文化的灵与美?我想,这是我在写作新书的过程中,须要逐步找寻的答案。
2唯中国有瓷,瓷源于玉
在距今万年旁边的新石器期间,我们先人的盛器,可能是一片芭蕉叶,一只贝壳,乃至是鸵鸟蛋壳。这些天然的盛器因陋就简,很未便利。有一天,他们在无意之中创造,被水浸湿后的黏土可塑,晒干后再用火烧,会变得坚硬而结实,陶器便应运而生,这是人类制造业漫长历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凡是有人类聚居的地方,险些没有哪个民族不会制陶,制陶应是文来日诰日然演绎的结果,却又是文明低级阶段的产品,存在诸多毛病,注定要逐渐被历史淘汰。
那么,陶器要蜕变为瓷器,取决于哪些条件呢?考古学界和陶瓷学界一样平常认为,得有三个条件在同一时空涌现:一是瓷土或高岭土的运用,它们构成瓷器的骨肉。二是窑炉温度达到1300℃。炉火温度亦是文明程度的一个侧影。西方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有一把衡量文明程度的大略的尺子,能达到1000℃旁边,大抵迈入冶炼铜锡的青铜时期的门槛,粗放型原始城市的涌现成为可能;1200℃至1300℃,可冶炼生铁,大批量的铁制工具、农具及兵器,用于生活、农耕与战役,谓铁器时期;而烧制瓷器,柴窑须要达到1300℃旁边。由于烧制温度高,瓷器在致密性、光洁性、硬度、防渗水性等方面,大大优于陶。三是釉的发明。釉是附着于陶瓷坯体表面的一种连续的玻璃质层,说白了,便是一身光润、平滑的衣裳。除了美容,还能增加制品的机器强度、热稳定性和介电强度,有便于拭洗、不被腥秽侵蚀等优点。
以上述“三合一”条件来看,地球上许多地方都创造有瓷土,然而不是每个地方都生产出了瓷器。窑炉超越1200℃这件事,在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的古代,中国人也不会比外国人多长一个脑袋。古巴比伦人烧出来的釉虽有缺憾,但那是公元前3000年,而中国人有“釉陶”,是在商朝(约前1600—前1046年),至少晚1400百年。然而,瓷器却没能问世于他国,由陶而瓷的路径上,不但古巴比伦人的运气有点儿背,西方不少具备“三合一”条件的国家,15世纪以来一贯“众里寻他千百度”,直至18世纪中叶,才能拥其入怀。300年流光虚掷,大约背在一个“玉”字上——不知且无感于天下有玉。
玉,是引领一代代中原民族的瓷人攻坚克难、玉汝于成的关键。
大约在8000年前,中原先民在磨制石器的时候创造了玉石,玉石质地周详温润,富于光泽。作为工具,玉杵、玉函、玉斧等,较之一样平常石器不易破碎,比起骨器、木器,也更趁手。此后,先民逐渐认识到,玉用尴尬刁难象,是暴殄天物了,其物理属性、审美代价,使它适用于祭神、通神。“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周礼》中便有以玉敬拜的记载。玉作装饰,有玉几、玉户、玉册、玉卮、玉铃、玉柱、玉屏、玉笈、玉律、玉案等,后来又因其稀缺耐久,发展为货币,成为中国泉币史上最早的系统性玉石货币体系——璧。玉带、玉佩、玉笏,则成为皇权及官员等级的标志。玉玺、玉座,更是帝王权力的最高象征。
从商代的原始瓷器到东汉的青瓷,这种发展是一种玉器效应。最早的瓷器皆青、白,便是多数玉的颜色。随着技能不断进步,宋代中期又烧制出影青瓷,青白釉色十分淡雅,釉面明澈洁丽,光荣温润如玉。迎光不雅观之,花纹内外皆可见,为特色,故称“影青”,也有“假玉器”之谓。
玉,宛如彷佛一道类似激光的强烈光束,引领中原一代代工匠,在攻坚克难中铸造出了瓷。
3瓷,何以为“中国”
瓷器与茶叶、丝绸,并列为古代中国三大外销商品,具备环球影响力,相称长一个历史期间内,堪称中华文化卓越地位在器物贸易层面的标志。英文里,瓷器和中国是一个拼法,即china。这一西方人对中国的命名法,被中国人照单全收。
于是,一个问题由此而来。在丝绸、茶叶、瓷器三者中,西方人以瓷器命名中国,这轻薄易脆的物件,难道挑得动中国文化这座丰饶而又厚重的大山?或者说,国人是否认同,比起更悠久、有名遐迩的丝绸、茶叶,与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以“中国”命名的这片辽阔江山,瓷器在物质层面、精神气候上,与“中国”存在更多契合?
瓷与中国齐名,承载着中国文化、哲学、审美、生活办法等丰沛内涵。恰如丝绸是2000年中国历史的一张名片,茶叶是500年中国历史的一张名片,瓷器则是1000年中国历史的一张名片。与丝绸、茶叶比起来,从大国到小邦、从欧洲到非洲,中国瓷器的千年存在,有遗存、遗址可验,有文籍、实物可证—
宋代赵汝适在《诸番志》一书里记载,菲律宾群岛的偏僻山区有海胆人,“人形而小,眼圆而黄,虬发露齿,巢于木颠”,他们三五成群,潜伏在树丛中,以暗箭射人,但只要将瓷碗摆在地上,他们就高兴地跳出来捡拾——“忻然跳呼而去”。菲律宾群岛较其他民族而言,较早利用瓷器,仪式、宴会都离不开瓷盘、瓷瓮等。十多年来,该国出土了大约4万件中国瓷器。
马来西亚吉隆坡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批中国明代瓷器,大部分出自景德镇,十六世纪时在柔佛州拉玛出土。马来西亚华裔作家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提到,“乃至本日,在柔佛河岸,也可以见到荒漠的村落落跟营幕的遗地,在玄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在吉隆坡国家博物馆,名字涌现最频繁的,不是满剌加国创始人拜里米苏拉,也非长期担当总理的马哈蒂尔,而是郑和。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位于今开罗南郊,在公园7—10世纪曾是埃及的政治、经济和制陶中央。唐宋时,埃及便从我国入口陶瓷,是中世纪伊斯兰天下与中国陶瓷贸易的主要枢纽。有学者对该遗址出土的60~70万片古瓷片进行清理、分类,确定1.27万余片为中国陶瓷碎片,包括晚唐邢窑白瓷、越窑青瓷,北宋广东窑系、景德镇窑白瓷及明清两代青花彩瓷等。
瓷器,为古老中国蒙上一层绮丽、美好的面纱,从公元16世纪末开始至18世纪,“东方热”“中国热”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着全体欧洲。
1580年葡萄牙都城里斯今年夜街上,已有6家出售中国瓷器的商店。本日,很多到葡萄牙的旅人会创造那里像一个瓷砖博物馆,无论飞机场、车站、地铁站、住宅的外墙,还是传统街道的地面,乃至路牌、门牌、店招牌、大厦名牌、景点示意图等,皆由瓷砖制成。
1603年,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报还一报》里有这样一句台词:“三便士旁边的盘子,虽然不是中国盘子,但也算是上好的了。”不经意间,莎翁透露出一个信息:此时的中国瓷器在英伦尚属奇异之物。到了17世纪末,英国各阶层已经饮茶成风。喝中国茶,用中国瓷器,成为国潮。英国当时还有个名词:Chinamania—中国瓷狂热症,剧作家莫里哀没少讽刺那些人。
法国上流社会中国陶瓷的“铁粉”很多,个中包括作家维克多·雨果。其《根西岛记事本六册》记载,在他称为“码头”的根西孤岛上,他先后买了48次中国瓷器,共花费3000多法郎。与此同时,他为一名女子朱丽叶买下一幢小楼,取名“高城瑶池”,在“瑶池”客厅的墙面上,挂满美不胜收的瓷器。他还将自己创作的57幅图案制成彩绘漆板装饰室内,图案中仕女、凤凰、仙鹤、麒麟、牡丹、兰草等中国符号与法兰西民族活泼风趣的表达融为一体,打造出一个华洋混搭的“幻境”。文化学者伏尔泰对中国文化也极力推崇,在他和浩瀚欧洲贤士的眼里,中国瓷器是古老中国的符码、文化中国的微缩,且不说青花艺术瓷,这种瓷墨分五彩的精准描述,化残酷于平淡的定性,若在高温釉下,色阶变幻,鲜妍奇诡,单说青花一样平常的陈设瓷、日用瓷—花瓶、笔筒、笔洗、茶具、餐具……曲水流觞、依依墟烟、豆架瓜棚、浣纱采莲、抱琴探友、雪窗读书、荷池涨满、黛瓦粉墙、男耕女织、老弈童戏、桃园结义、紫燕呢喃、远帆孤影,如此人间,宁静、平和,能不生羡?
雍正期间的粉彩
中国文明与技能文化结合得较为紧密的部分,像小雨一样浸染于异国的物质生活,终极渗入对方的思想不雅观念和话语体系。
瓷器(china)之以是能成为“中国”“China”,可作如是不雅观。
4瓷都千年,代表中国工匠的命运
一贯以来,都有一个说法,钧、汝、官、哥、定是有名于世的宋代五大名窑,与它们比起来,其时的景德镇只能算小老弟。我却一贯不解:若景德镇真是小老弟,为何真宗景德中,天子年号未给其他窑口所在地,何以单单给了重重关山之外的景德镇呢?
据1972年考古发掘,在景德镇市东南4000米的竟成镇湖田村落,有窑业遗存面积40余万平方米。湖田窑兴烧于五代,历宋、元,入明,有700余年,为宋代青白窑系代表窑场。20世纪80、90年代,湖田窑址又有部分发掘,出土大量青白瓷:餐具、茶具、酒具、文真、玩具、花器、宗教用品、扮装用品、枕头等,险些涉及社会生活所有方面。而湖田窑,只是当年景德镇一个窑口,浮梁县的湘湖镇、寿安镇、南市街也有窑口。
景德镇瓷器不惟为宫廷所重,也是民生所系、外销所倚。景德镇宋时的青白瓷在上海、广东、河北、福建、江西、江苏、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陕西、四川、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地均有出土。朝鲜半岛、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巴基斯坦,乃至非洲地区都有青白瓷遗存——在宋代的外销瓷中,青白瓷始终是一个紧张的品种。
可见赢得宋真宗天子年号的,不能是别处,只能是湖田40余万平方米和寿安(含南市街)10平方千米的丘陵、河谷。这里比法国传教士殷弘绪眼里的紧张在城区的镇,早700余年景为瓷业中央——制瓷作坊,蜂聚蚁囤;瓷器铺店,鳞次栉比;车马帆船,川流不息;商贾拱手,杯来杯倾;挑夫落汗,干后又湿……是它们,构成了当年的景德镇。
进入元代,青花瓷在景德镇创烧成功、成熟,在陶瓷史上具有划时期的意义:青花瓷一扫唐宋瓷器的单一颜色,以青白作地,衬托蓝色花纹,花纹呈现除刻、印、划、剔、贴、塑等外,彩绘成为主流。素雅与艳丽和谐统一,色调变革空间扩展,或盛饰淡抹,或写实写意,意境深远,清丽脱俗。
青花缠枝莲纹梅瓶
青花瓷的环球旅行,也是从元代的景德镇开始的。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太多史料与遗存可以佐证。景德镇的青花,若杜工部脸上酥酥的锦江夜雨,渗透进近代欧洲社会生活。至少在16、17世纪,大半个地球成了一个青花瓷流动的天下。
回顾中国的“环球史”,其序幕、发展、高潮、压轴,景德镇无不洞穿个中。放眼中国,有几座城市,如景德镇这样近600年里名动天下,影响西方从国王、伯爵到面包师、马车夫的餐饮习俗与艺术风趣?并在400年里决定着伦敦、巴黎银价的浮动?
景德镇瓷器,是东西方“哥伦布大交流”后中国经历1.0版“环球化”的最好注脚。
进入近代后,景德镇命运如何呢?
景德镇及其瓷器日益凋敝的年代,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锁国与守旧,中国文化在环球范围内走下神坛并日愈边缘化。仅剩的一点东西方互换里,China还是那个China,但无论是作“瓷器”义,还是“昌南”音译,都不是原来的China,此时的China已过客星稀。景德镇瓷器的命运,是近代中华民族命运的某种投射。中国的所有传统城镇中,景德镇最能代表中国传统工匠的宿命。
说是“千年窑火”,一代代消散了的工匠,却似葬在了一个无名的冢里,冢上唯有封建王朝一个个天子的年号:景德、永乐、成化、康乾……及他们投射在瓷器上的威信。由于“重道轻器”的传统,文人墨客除了有诗词惊叹器皿之美、工艺之绝外,多将陶瓷视为“君子不器”的工匠之作。除南宋蒋祈《陶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清代唐英《熏陶图说》与蓝浦《景德镇陶录》等文献之外,文籍里险些难寻陶瓷的踪影。当下书肆里关于景德镇的书本、报刊,网络上涉及陶瓷的笔墨,也少见将其提升到文化、历史与社会层面来核阅的书写。
及至20世纪90年代改制,“十大瓷厂”烟囱陆续熄火,海内、国外,真真假假的景瓷,在商铺生僻地缩在尘蒙的一角;同时,城市灰蒙蒙的,侘傺而破败。一些人以为景德镇弗成了,“广陵散不复传矣”。
且慢,还有几百斤铜呢,何况老祖宗给的这门手艺,绝非几百斤铜。这样说吧,景德镇像一个中年男人,遭受重击之后,有停顿,有迷惑,但不抱怨、不气馁,激活血脉里的手工艺基因,消逝几十年的手工业陶瓷作坊,大面积回归,逐步地却稳稳地走出命运的峡谷。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看似主不雅观的个体活动,却预示此城的文化意识一日一日在觉醒。
这座镇上的大多数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人群中,你至今不会创造他们有多么特殊,然而一旦进入指尖的天下,就变成执掌一物的国王。匠人精神,被景德镇足足打磨了千年,若地壤酝酿钻石,江河沉淀珍珠,是这座城市的基因。
当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要互联网,要金融街、陆家嘴,也要景德镇——貌似与“高科技”“金融”等光环无关,却代表着传统手工业至高无上之地的“景德镇”。
5瓷之要义,在于集中华文明之大美
在我们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泥土和地皮,一贯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生,与地皮、与泥土相依相偎,去世,也要回归地皮,和泥土融为一体。陶渊明有诗云:“去世去何所道,托体共山阿。”龚自珍有诗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瓷器,由猎猎的火焰中来,莫不便是我们先人穿越茫茫时空,对泥土、地皮的一种激情的拥抱?
瓷器,由缠绵的水里来,莫不便是我们先人对呵护人类生命的大自然,以别样的办法作永恒的崇拜?
彷佛天下上还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品,能够像瓷器一样,将物感与精神、生活,与审美结合得如此完美。
瓷器,集中华文明之大美。从瓷器中,可以看到玉器时期的玉器之洁,青铜时期的青铜之坚,石雕、木雕的朴拙之美,书法、绘画的变幻之美……我们这片古老的地皮上,所有器皿的美感、艺术和手腕,险些都融入了瓷器。
《易经》里说:“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瓷两者兼具,在光洁如玉的物质形体之外,还用一种隽永的诗性办法,将中国文化的精髓与气韵,深深地感化到中国人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中,让民族整体的命运在变幻不定的天下上拥有独特的气质和武断的存在感。
瓷上,还多少有些寥落的禅意,有空山新雨后般的清新,让被世事磨砺得日渐粗糙的心灵,再次探出含羞草一样平常的敏锐、灵动,让时下暴躁的人们,逐渐降去燥热,淡去短长。
在瓷千年洋洋洒洒的叙事中,将其他工艺、美术话语空间中局部穿行的历史意义、人文意义、审美意义,统统揽起来,就汇成了一条天高水阔、风帆正悬的大河。其画面、纹饰、色彩、光泽,穿越了光阴和空间,成为中华民族生活中一个永恒的精神原乡。
在东西方国家之间的信赖本钱越来越高,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越来越费劲的时下,什么样的文化形态,才是“真”的、“活”的、生动的中国文化?如何以中国文化的元精神、审美追求与生活办法,在环球说好令人理解、使人信服、让人温暖的中国故事?我想,答案可能在景德一镇可以探求到,正如当今,那些从西欧、日韩及天下各地赶来的洋“景漂”,来探寻中国手工艺的秘密一样平常。
“凤栖常近日,鹤梦不离云”。
若一艘大船,助推的人多了,有水来了,它就又扬帆起航了。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和出版社供应)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11日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