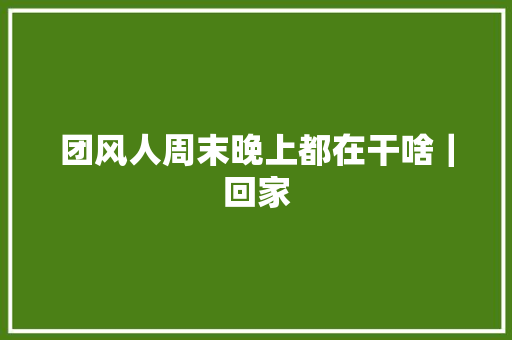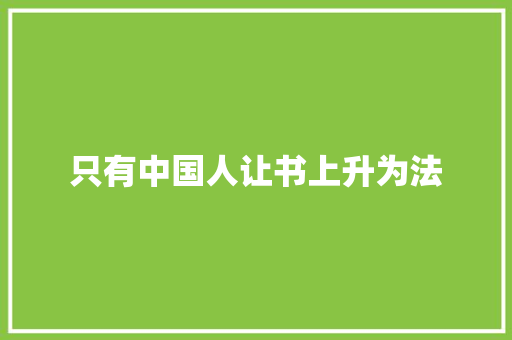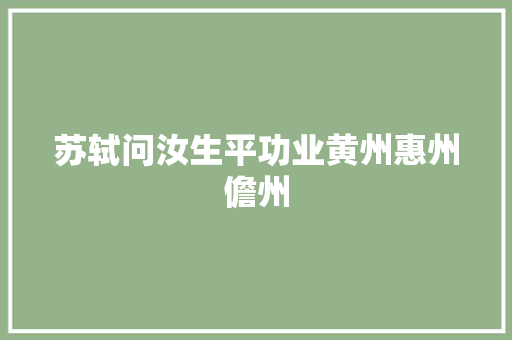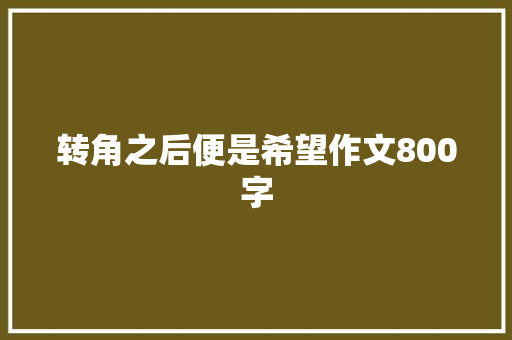沿着江安河、锦江、岷江、长江……就这样一起走,跟随流水,跟随作家的目光和车辙,去踏访那些被遗忘在草木深处的历史——这便是作家在我报“顺着水走”专栏的名字来由。
本日,我们为您带来“顺着水走”专栏的新一篇。这一次,作家调换了出行办法,乘坐高铁抵达苏东坡曾留下足迹与名篇前、后《赤壁赋》的黄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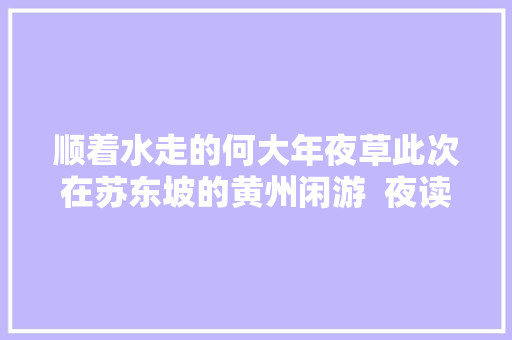
在苏东坡的黄州,闲游
文/何大草
刊于2024年8月1日文学报
一
黄冈,在苏东坡贬谪于此时,名为黄州。六月下旬,我乘坐高铁,经宜昌,去那儿闲游。
中午,定时到达黄冈高铁站。一钻出来,阳光当头泼下,像是滚烫的鲜开水。
站外的广场,正在大面积施工。人行通道用绿色的板壁隔出来,我随着人流,推着拉杆箱,顶着太阳,就在这没一寸树荫的通道中转来转去。终于,转了出去。
乘客排着长队打传统出租车,有顶灯的那种。瞥见前边好几台车都是女司机;我上的那台,自然也是。虽然车窗紧闭、开了空调,但女司机依然戴着墨镜、黑面纱,还穿了带帽的长袖防晒服,从始至终,我都没看清她的长相,更不知芳龄几何。但她人很豁达,语速极快,吐词又极清楚。更主要的是,车开得极利索,转弯时流畅、平稳。我诚恳地夸了一通,说,黄冈的姐好厉害,为“女司机”这个词争了光。她哈哈笑,说,“要活嘛。人家是在生活,我们是在活命。不然怎么办?”说得很惨,却像脱口秀,没一点惨味。
到酒店办了入住,但客房尚在整顿。我就去隔壁的快餐店,吃了一条烧鱼、一盘蔬菜、一碗饭,便宜、适口。这个时候,太阳满街,人蔫耷耷的,且又显出一种生僻和空旷,让人生出倦意,想昏沉沉睡一觉。
二
苏东坡45岁被贬谪到黄州,做一个挂职的闲官,过了四年多日子。仕途上一无建树,却写下了影响至为深远的前、后《赤壁赋》《赤壁怀古》《寒食帖》等等。
我一贯想来黄州,访一访东坡遗迹。本日终于来了,却也不急,进了客房,拉上厚窗帘,倒头睡觉。醒来已是下午3点过。出了酒店,打了网约车,先去看黄冈博物馆。
司机跟我年事相仿,头发花白,但更短、更硬扎,健谈,很是热心肠。他知道我喜好看博物馆,就推举了另一处小型博物馆(彷佛是家私人的),说里边有新挖出的好东西。我说还是先看大的吧,官方的毕竟大而全。他又问我,对苏东坡有没有兴趣呢?我说,正是为东坡而来的。他于是跟我大聊了一通苏东坡在黄州的掌故,把苏东坡称之为刺史,苏东坡跟和尚佛印交了朋友,佛印送了一块坡地,供其建房和耕种,这便是东坡。我听了哈哈笑。他也笑,更乐了。
他的话虽有错漏,甚或有点玄,却让我对他颇有好感。
博物馆很壮不雅观,像一座巨大的城堡,质量上乘,坚固、封闭,且门禁严格,我出示了身份证,人和包还得过安检,还要登记手机号码、来自何方,等等。但里边没开空调,且不见窗户,一进去,热得人发晕。空气中,还散发着彷佛装修刚完之后的刺鼻味。好在我带了把折扇,就一直地扇。
馆里只有几个参不雅观者。个中一位男士在给两位年轻女士年夜声讲授,谈笑风生,洪亮得全体博物馆都回荡着他的笑声。但这笑声并不让民气烦,由于,实在是太闷热、又太生僻了。
还有两个年轻母亲,带着儿女在馆里长知识。小朋友都热蔫了,却还懂事,在强打精神地走流程。
我是下午4点10分进的馆。门卫说,抓紧韶光,4点50就要清馆了。我摇着折扇,匆忙浏览一遍,逃掉了。印象深的,只有一点,便是墙上的文献资料见告我,黄州帮别号黄帮。我小时候,就常常听人说“黄帮”,起源居然在这儿。俗话说,湖广填四川,黄州话影响到成都话,这是自然的。但,可能在传播中倒了几个拐,意思已大为不同了。黄州帮的帮,有帮会之意。成都人说谁是黄帮,则是讥讽他生手,过不得硬。
手臂又痒又痛,我打车去买芦荟凝胶。请教司机,这几天是不是热得有点怪?他说,热得很正常,但还没有到最热,最热40几度。我又问,那最冷呢?他说,零下四五度,下雪,屋顶能铺厚厚一层白。我缄默半晌,说,苏东坡当年太难了。司机负责开车,
回酒店后,把手臂洗濯干净,抹上芦荟凝胶,觉得一阵清凉,舒畅了不少。歇到7点多钟,出去在隔壁快餐店吃了半块剁椒鱼头,喝了一大碗肉汤炖冬瓜。汤好喝,剁椒鱼头也很好吃,近于“巨口细鳞”,一大份才13元。
三
清晨六点多就醒了。可能是昨晚边写日记,边喝了浓茶,晚上醒了好多次,睡得很不深。去餐厅吃早饭,满耳朵都是清脆的童声,相称有生气。很多小学生在用自助餐,动作老练,吃得喜笑颜开。个中一个小男生,胖胖的,寸步不离地带着拉杆箱。箱子小小的,表面五颜六色,像是个玩具。我请教他,去哪儿玩过了吗?他答,参不雅观了“东坡纪念馆”。
赤鼻矶
9点过,我打网约车去东坡赤壁。司机比较沉闷,问三句话,答半句,留白多,靠你自己猜。市区不很繁华,但市声喧嚷,很有活力,车子行人自由清闲,听凭你按喇叭。终于穿过城区,驶入一条浓荫蔽日的小巷,算是到了郊野,安静了。司机却说,这儿才是老城区。随后,他停在一个四周无人的地方,说,售票处到了。示意我下车。我瞟了一眼,售票处门窗紧闭(且像紧闭了一百年),我下去干什么!
他问我咋办?我说,往前开啊。
两人无话,缄默又开了一段路,左手闪出一段逶迤的小山冈,冈上一溜古城墙。城墙下,有个小老头在摆摊算命,渺如一蚁。右边,视线展开,是公园的广场。这才算到了。
东坡赤壁,就在公园内。
所谓赤壁,原名赤鼻矶,意为:像红鼻子一样突出江水的赭红岩石。因苏东坡故意将它指认为“三国周郎赤壁”,从此以讹传讹,有名天下,误导众人至今。
我问售票员,路上那个售票处是咋回事?她说,那个是私人开的,不算数,早就关了。我听出背后彷佛有名堂,但也无心多问。门票40元,我扫微信支付前,顺口问了句,60岁有优惠不?她说,五折。我心头一喜,递上身份证,顺利捡回了20元。
公园内人很少,但有个人在大声放音乐(用手机或者收音机),吵得烦去世人。放眼望去,亭台楼阁,多数是仿古的,不算文物。即便有文物,恐怕也是明清的,跟苏东坡没紧要。
让人眼睛一亮的,是一口大池塘,荷花开得正盛,红颜粉嫩,让人怜之不足。
荷花大家都爱,但画出来的荷花,或者过于俗艳,或者不脱某种标榜。不好画。以我所见,只有周思聪的荷花兼有败落和出尘之美,能让人看了,缄默无语。可惜画荷时的周思聪,已经身患绝症,握笔都已困难了,可能算是她的“绝笔画”吧。但凡绝笔之作,都有一种不平凡的力量,不雅观之、读之,让民气口一震。
周思聪 荷花
苏东坡的“绝笔书”中写到:“某岭海万里不去世,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苏轼的人生,百转千回,终了之际,自己归结为命,彷佛有千言万语可说,但也不必再说了。这个时候,他六十六岁,距他离开黄州,已经十七年。
苏东坡在黄州,留下了很多故事、佳作,以及一个虚构的赤壁。
在苏东坡笔下,这个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我虽然晓得很夸年夜,但真的走到了,还是惊异这山坡:太小了!
太矮了!
还比不上本日的二十层电梯居民楼。
登上坡顶,看不见长江。止不住踮脚远眺:视线之内,依然全是房屋。视线尽头,是长长的林带,估计是长江大堤。向下俯瞰公园内,有一块长条形的水洼,系了条小船,造型平庸,呆头呆脑,可能是重现东坡夜游赤壁吧。失落望之余,不觉呵呵一笑。
我自然不甘心。出了公园,向左,登上了龙王山。
龙王山据称是黄州第一高山,顶峰海拔80余米,赤鼻矶只是它西侧的一部分。
山上植被茂盛,有如森林公园。几个老婆婆坐在路边快哉亭里闲谈。两个小学生趴在地上看书写字,妈妈站在一边骂骂咧咧训子。由于静,她们声音之响亮,险些振聋发聩。这幽与静,颇有点像成都的青城山,只是体量小了很多。但它有快哉亭、雪堂、望江亭,名称风雅,且与苏东坡有关。我大汗淋漓地爬到望江亭。望江?切实其实开玩笑,只看见了更多的房屋。请教一位当地师长西席,他说江还在西边。何以是在西边呢?我心里结下个悬念。
一位老婆婆主动见告我,长江改道了,要到江滩公园才能瞥见江。我查了下导航,间隔有十来公里呢。于是就先去了雪堂。
读过苏东坡《后赤壁赋》的人,都熟知他在黄州的住所,一在临皋、一在雪堂,中间有条著名的路,叫做黄泥之坂。
我在山道上拐了几个弯,看见一大片竹林,穿竹而过,就找到雪堂了。苏东坡生平爱竹,雪堂自然是被竹子簇拥的。
雪堂也在路边,有小桥隔开,过桥推开院门,多少的石头梯坎上,伫立一幢古式建筑,前后挂了牌匾,一个是“雪堂”,一个是“雪堂余韵”。建筑后边,是一大块开阔地。贴近院墙,又是一溜房屋,有招牌、横幅,写得清清楚楚:黄冈武当会馆,以武演道、以道显武,常年招生。门开着,里边供着像,我不敢贸然进去,只瞥见墙上四个字:尊师重道。大约该是武林宗师吧。
院里十分安静和干净。有个中年男子在扫地。有个憔悴老太太在打拳,行云流水,很是好看。还有个60多岁的先生长西席,白衣白裤,在伸展筋骨。我觉得他修为非凡,该当便是馆主了,就赔个小心,请教他这雪堂的来历。他也很和气,说东坡雪堂真正的故址,在附近几里外,如今是个派出所。而自己也是退休之后,才来这儿习武、养身的。师父嘛,他指了指,是那位扫地的男子。
师父进了一扇门,不见了。
院子里还有两扇上了锁的门,且有招牌:某某事情室,东坡草庐。后者像个小饭铺。地上倒立着一块牌子,上书:正宗木子店老米酒,麻城肉糕。以及电话号码。这些东西,可能已是往事了。
有个50岁高下的师长西席,圆脸面善,在我之后也进了雪堂。他说自己从杭州来,苏东坡做过“杭州知府”,以是特来看一看雪堂。我说我从四川来,是苏东坡的故乡人。彼此大笑,作揖而别。
四
下山后,觉得颇有饿意了,但还是硬撑着,登上古城墙,走了一长段。我晓得,这地方,这辈子都不会再来了。
城墙有个门洞,叫做汉川门。一位七十多岁的大爷在收钱:一人五元,两人也是五元,但十人是五十元。这章程何以这么订?大爷自己也不晓得。我微信支付,网络不好,良久,手机上才浮现出一个女士的头像。大爷说,瞥见这个头像就行了,解释钱已经到账了。我问,这个女士是老板吗?大爷不正面回答,只说:我是帮私人在收钱。
城墙上边,太阳烘烤着,热得很。很多古董、文物就摆放在墙上,也不遮风、遮阳、避雨雪,是否是真的?那还用说嘛。城墙里边,还有一个石刻作坊,立着石凿的毛主席、刘胡兰、雷锋等人的塑像。我转了十几分钟,下来时,遇见杭州来的师长西席扫码支付了五元钱,正要上去。我说没什么好看的。他说,来都来了嘛。
我肚子已饿得开叫了,但来一趟“大江东去”的出身地,连江水也没见到,实在意难平。就在导航上叫了网约车,去江滩公园。
城墙的阴影里,风大,凉爽,等车时我就空着肚子,看算命师长西席若何挣饭钱。一位男士,约五十出头,方脸、富态,坐在一把唯一的小凳上,由算命师长西席预言他的命。他的女儿,大约八九岁,还有个中年朋友,也站在一边看热闹。算命师长西席左手拿个发油的册子,右手五指伸开,在空气中划了几划,说那男士:你有能力、有魄力,人缘又好,不仅能当官,还能昔时夜官。
那男士哈哈大笑,说,什么官啊!
我便是个做生意的人。
算命师长西席倒也不窘,脸上浮出浅笑,静候对方付钱。
这时候,我叫的车来了。司机三十多岁,却很像个老江湖。他听说我去江滩公园看江,就嘿嘿一笑,说,江滩公园离长江还远得很。你要走着去江边,当心晒脱一层皮。我有点急了,说,难道黄州就看不见长江了?他说当然能。我就请教,看江最好的地方在哪儿?他说,汽(车)渡(船)码头。这码头的民用功能,已停了二十年了。江对面便是鄂州城。我问有多远?他说,江滩公园过去一公里多。我咬咬牙(肚子已快饿瘪了),说,那就去吧。
汽车沿着漫长的防护堤飞驰。我说,堤外便是长江吧?他听出我话里有狐疑,就耐心阐明,堤外是农田。二十多年前闹水灾,江水都漫上来了。后来才筑了这道堤坝,为了多一道防线。好吧,我信了。
汽渡码头到了,司机在树荫下等我。江水相称宽阔,但拍岸时并没有惊涛。相反,水声里有午间的慵
我勾留了几分钟,用手机拍了照片和短视频,也明白了一件事:黄冈在江北,鄂州在江南。而从东坡赤壁眺望长江,则的确是向西望。由于,长江在这儿拐了个90度的弯。以是,黄冈也可以说在江东。
回到酒店,我的棒球帽内圈、T恤衫后背,全让汗水打湿了。袒露的手臂,幸好有芦荟凝胶加持,还好,不算很痛很痒。这时候,肚子反倒不饿了。我喝了杯茶,缓行到隔壁的快餐店,吃了一条肥美的武昌鱼,加上米饭,共计21.5元。
下午阳光暴晒,我就躲在客房里开着空调睡觉,喝茶,养精神。还在手机上预订了黄冈到镇江、镇江到南京的高铁、南京飞成都的飞机,以及预订了镇江的酒店。该预订的,至此,都预订了。预订,老让我紧张,恐怕算错了日子、韶光、输错了信息,
等等。但也是一个有趣的寻衅。好歹,我算是搪塞过来了。
下午5点过,我步辇儿去万达广场喝了一杯瑞幸咖啡。户外空气依然热得很,街道、人、车,都萎靡了,连喇叭声都是无力的。阿弥陀佛,广场里有空调,依然人头攒动。我坐在一个角落,喝着咖啡,刷了会儿手机,读到原报馆同事发来的信息,一位老领导往生了,享年89岁。我想起这位老领导的样子,他个子比我高、身材比我魁梧,在同龄人中,算相称突出的,但他的为人,很是谦逊、虔诚。他跟我说过的一些话,以及说话的地方和蔼氛,此刻都历历在目。那已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阛阓的通道上,摆了些小摊,个中一个是手机贴膜的。我的华为手机膜已快脱落了,就去重新贴一张。贴膜小妹之礼貌而仪态大方,可以媲美空姐。她起立,接活,坐下,解开手机保护壳,用小刷子仔细清理,再用某种溶液洗干净表面,再把一张膜用细腻到极致的动作,稳稳地贴了上去。这全套动作做下来,你也可以认为,出色的银饰匠也不过如此了。末了,她还开具了一张收据,收费29.9元。
阛阓内还有肯德基,我意外创造有深海鳕鱼堡,就买了个双层的,加一杯芙蓉汤,共计30.5元,充当了晚餐。
回酒店的路上,在十字口水果铺买了串葡萄,约一斤,7.4元。做事员是位三十多岁的女士,我问她葡萄甜不甜?她摇头,笑道,我也没吃过。阁下有个买主见告我,这个葡萄不酸的。我心口倒是略酸了一下。
早早洗了澡,写日记,睡觉。来日诰日去看安国寺、承天寺。
五
安国寺、承天寺,跟苏东坡渊源很深。他刚到黄州时,过一两天,必去安国寺焚喷鼻香默坐,兼以沐浴修身。跟和尚的关系好,少不了吃茶、谈禅、聊八卦,以纾解心中之忧郁。承天寺呢,他写的《记承天寺夜游》,虽只有八十多个字,唯其短,连本日的小学生也能背诵:“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景象还是很热,但天色阴了下来,至少走在露天,没了暴晒之苦。上午九点多,我打了网约车,先去安国寺。车来了,司机和我相视一笑,便是前天载我去博物馆的老师傅。他问我,后来又去小博物馆没有呢?我笑道,大博物馆都快把我热去世了,哪还敢再去小博物馆送死。他于是嗟叹,还是文化投入不足啊,舍不得一点空调钱。
我觉得跟他是同龄人,一问,果真。他说自己1964出生(比我小两岁),是黄冈土著,退休了,闲不住,就出来跑跑网约车。我说,你肯定是个喜好读书的人。他说是啊,喜好读书,也喜好听书,苏东坡的掌故,还是很知道一些的。说着,他减速行驶,指着车窗外,给我逐一讲授。他说黄冈从前很小,到这儿,就已是郊野了。你看,这边是不是有点斜坡呢?佛印便是把这儿的几十亩地赠予给了苏东坡,让他种田,盖屋子,雪堂就在上边。
我朝窗外瞄了瞄,的确是有一条浅浅的坡道。但通上去,全是密密麻麻的屋子,比较简陋的居民区。雪堂?昨天我听说,是在本日的某个派出所。版本真是太多了。
老师傅又踩了下刹车,索性把车速降到跟人走路一样慢,手往挡风玻璃外挥了挥,说,这边从前是殡仪馆、火葬场。那边紧邻的,是一个国营的果园。从前,普通人家是吃不起水果的。恰好我们家有熟人在这果园里上班,时时会送些梨子苹果来。但果皮上有斑点,是去世人的灰尘飘上天,又落下来粘在水果表面的。我嘴再馋,也不敢咬一口。实在我家是很穷的,家中六个孩子,我排行老五。父亲去世早,全靠母亲摆摊子养活一家人。不过,穷是穷,我还是爱读书,听书,对古代的文化感兴趣。
我请教他,安国寺有什么好看的?
他说,好看的很多,数塔和一棵朴树最好看,有灵气。说着,他转了个话题,说从前寺外的街巷里,发廊、美容店多得很,方丈管不住,好多和尚都成了花和尚。而今不同了,新方丈有修为,有学问,也能找到钱,正在重振安国寺,很有一番新气候。
他的话,我昨天已经领教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点像野史。不过,野史才更有趣,何况他又那么激情亲切,并不图多赚我几元钱车费。于是,我边听,边回以激情亲切的点头。
安国寺
到了安国寺,他把我放在后门(也可能是侧门),互道谢谢,挥手作别。
寺里果真在大兴土木,到处挖坑、埋管、铺路。新建的殿宇,很是巍峨,富贵气逼人。但有刺鼻的、新装修的气味,让人不敢久留。倒是殿宇之间的空地上,成长着一畦畦玉米、瓜蔬,让人以为清新可喜。
通向大雄宝殿的石梯子上,立了块横牌,上书:“我在安国禅寺寻访东坡。”一头一尾,还标明了东、西方向。这是我在寺里看到的,唯一跟苏东坡有关联的实物。
我也看到了塔和树。原以为便是“塔和树”,结果不然,是塔顶上长了一棵朴树。也算一种奇不雅观吧。可惜,塔是明代的,树也只有百余岁,苏东坡无缘见到过。
六
我从正门(山门)走出安国寺,打网约车去承天寺。山门外有块广场,太阳隔着云层照下来,依然热得烤人。等了好一会,车来了,却是传统带顶灯的出租车。
司机表情冷硬,很酷的样子,全程无互换。到了目的地,他却破例笑了笑,说,记得确认收费的订单啊。我险些吃了一惊,很合营地笑道,好的。
下了车,却不见承天寺的影子。我创造自己站在大街的街沿上,正对一个比较派头的大门。一位先生长西席戴着口罩,推着自行车出来,前杠上坐了个可爱的小娃娃。我请教他,承天寺怎么走?先生长西席很激情亲切,他扬起左臂指示了下方向,用相称标准的普通话见告我:沿着我们单位的院墙,一贯走,不算远,一下子就到了。我连声道谢,顺便看了下门口的标牌,上边写有“国家电网”的字样。
大街上车水马龙。我沿着院墙,拐进了一条小道,首先瞥见的,是一大片湖面。湖名青砖湖,近岸有荷花,岸上有柳树,十二分古意。但还有一群中老年女士,间杂了两三位大爷,在放着音乐舞蹈,乐声震耳,略为绝望。不过,循小道再往里走,就寂静了许多。然后,溘然就瞥见了承天寺。
我听说承天寺早就没有了,只是在故址立了一块碑。立了碑也就可以了。可偏偏还新修了一座庙。一座庙,即便不如安国寺既壮且丽,至少,还是该有个山门、院落、大雄宝殿、藏经楼等等。然而,不是的。
我眼见的承天寺,小得就像一座地皮庙。在背后宿舍楼的映衬下,切实其实是寒碜。寺门紧闭,窗户安装了带格子的防盗栏。我凑近看,能模糊瞥见里边一张桌子,亮着三盏灯,墙上贴着彩印的菩萨像。
不过,虽说寒碜,倒是整顿得很干净。
干净就好。我从绝望中缓过气,继而觉得到喜感和有趣,还暗自窃笑了一小会儿。即便闲人苏东坡归来,可能也会抚须笑笑,再写一篇《记承天寺幻游》。
2024夏,追记
新媒体编辑:张滢莹
配图:摄图网、资料图
id : iwenxuebao
微信公号
新浪微博
@文艺速效丸
小红书
@41楼编辑部
小宇宙播客
2024文学报开启订阅
邮发代号3-22
周刊 / 整年定价:61.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