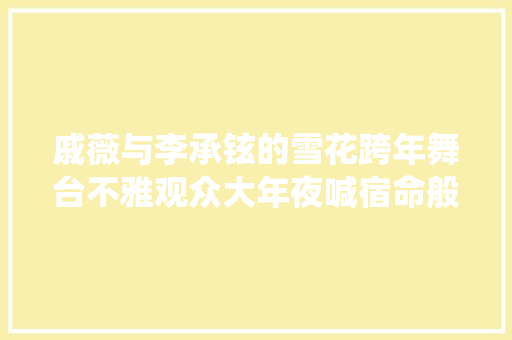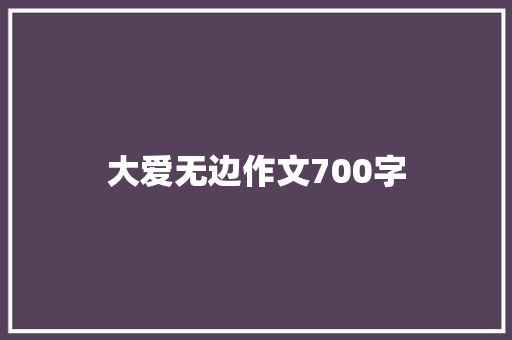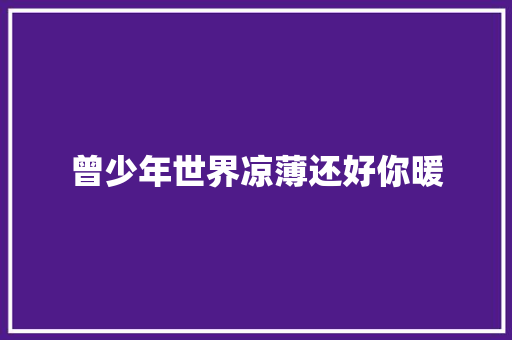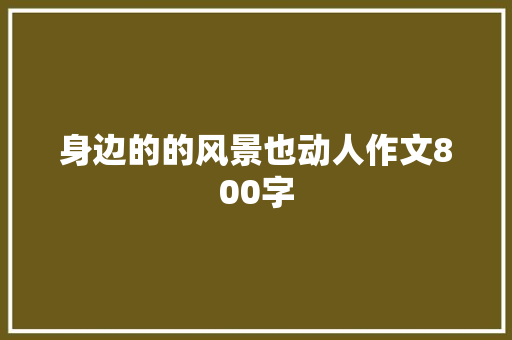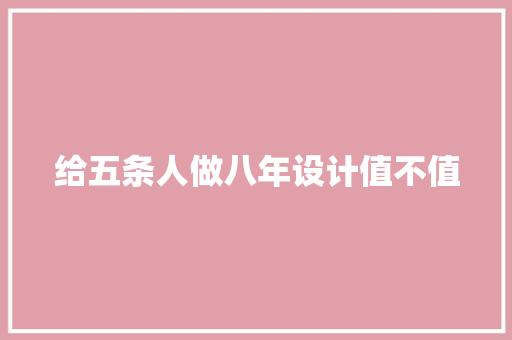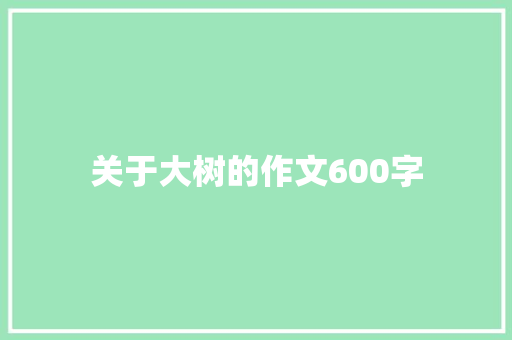只有中国人,让“书”上升为“法”
“书法”,原来是指“书之法”,即书写的方法——唐代书学家张怀瓘把它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用笔,第二识势,第三裹束。”周汝昌师长西席将其简化为:用笔、构造、风格。它侧重于写字的过程,而非指结果(书法作品)。“法书”,则是指向书写的结果,即那些由古代名家书写的、可以作为模范的范本,是对先贤墨迹的敬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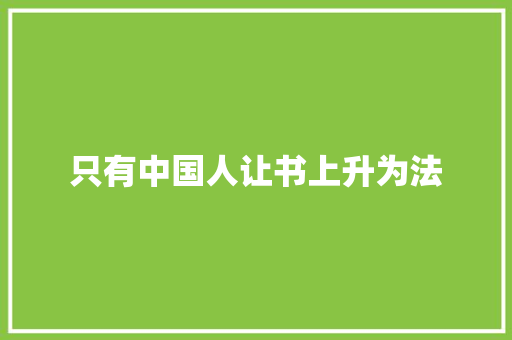
只有中国人,让“书”上升为“法”。西方人听说也有书法,我在欧洲的博物馆里,见到过印刷术传入之前的书本,全部是“手抄本”,书写工致俊秀,加以多少装饰,色彩艳丽,像“印刷”的一样,可见“工致”是西方人对付美的空想之一,连他们的园林,也要把发达多姿的草木修剪成标准的几何形状,仿佛想用艺术来证明他们的科学理性。周汝昌认为,西方人“‘最精美’的书法可以成为图案画”,但是与中国的书法比起来,实在是小儿科。这缘于“泰西笔尖是用硬物制造,没有弹力(俚语或叫‘软硬劲儿’),或有亦不多。中国笔尖是用兽毛制成,第一特点与哀求是弹力强”(周汝昌:《永字八法——书法艺术讲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与西方人以工致为美的“书法”比起来,中国法书更感性,也更自由。只管秦始皇(通过李斯)缔造了帝国的“标准字体”——小篆,但这一“标准”从来未曾限定书体演化的脚步。《泰山刻石》是小篆的极致,却不是中国法书的极致,中国法书没有极致,由于在一个极致之后,紧随着另一个极致,任何一个极致都有阶段性,江山代有秀士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使中国书法,从高潮涌向高潮,从胜利走向胜利,自由变革,好戏连台。工具方面的缘故原由,正是在于中国人利用的是一支有弹性的笔,这样的笔让笔墨有了弹性,点画勾连,浓郁枯淡,变革无尽,在李斯的铁画银钩之后,又有了王羲之的秀美洒脱、张旭的飞舞流动、欧阳询的法度庄严、苏轼的“石压蛤蟆”、黄庭坚的“树梢挂蛇”、宋徽宗“瘦金体”薄刃般的锋芒、徐渭犹如暗夜哭号般的幽咽抑扬……同样一支笔,带来的风格流变,险些是无限的,就像中国人的自然不雅观,可以“万类霜天竞自由”,亦如太极功夫,可以在闪展腾挪、无声无息中,产生雷霆万钧的力度。
我想起金庸在小说《神雕侠侣》里写到侠客朱子柳练就一身“书法武功”,与蒙古王子霍都决斗时,兵器竟只有一支羊毫。决斗的关键回合,他亮出的便是《石门颂》的功夫,让不雅观战的黄蓉不觉惊叹:“古人言道‘瘦硬方通神,这一起‘褒斜道石刻’当真是千古未有之奇不雅观。”以书法入武功,这发明权想必不在朱子柳,而应归于中国传统文化成绩极深的金庸。
《石门颂》的书写者王升,便是一个有“书法武功”的人。康有为说《石门颂》:“胆怯者不能写,力弱者不能写。”我胆怯,我力弱,但我不去世心,每次读《石门颂》拓本,都让人血脉偾张,被它鞭策着,急速要研墨临帖。但《石门颂》看上去大略,实际上非常难写。我们的笔触一落到纸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缘故原由很大略:我身上的功夫不足,一招一式,都学不到位。《石门颂》像一个圈套,不动声色地诱惑我们,让我们放松当心,一旦进入它的领地,急速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书法作为艺术,代价在于表达人的情绪、精神
对中国人来说,美,是对生活、生命的升华,但它们从来未曾分开生活,而是与日常生活相连、与内心情绪相连。从来没有一种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孤悬于生命欲求之外的美。本日陈设在博物馆里的名器,许多被奉为经典的法书,原来都是在生活的内部产生的,到后来,才被孤悬于殿堂之上。我们看秦碑汉简、晋人残纸,在上面书写的人,许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他们对美的追求却丝毫没有松懈。光阴掩去了他们的脸,他们的羊毫在暗中舞动,在近两千年之后,成为被我们伫望的经典。
故宫博物院收藏着大量的秦汉石本,在这些石本中,我独爱《石门颂》。由于那些碑石铭文,大多是出于公共目的书写的,记录着王朝的功业(如《石门颂》)、事宜(如《礼器碑》)、敬拜仪式(如《西岳庙碑》)、经文(如《熹平石经》),因而它的书写,必定是威信的、精英的、标准化的,也必定是浑圆的、饱满的、均衡的。个中,唯有《石门颂》是一个异数,由于它在端庄的背后,掺杂着调皮和搞怪,比如“高祖受命”的“命”字,那一竖拉得很长,让一个“命”字差不多占了三个字的高度。“高祖受命”这么严明的事,他居然写得如此“随意”。很多年后的宋代,苏东坡写《寒食帖》,把“但见乌衔纸”中“纸”(“帋”)字的一竖拉得很长很长,我想他说不定看到过《石门颂》的拓本。或许,是一纸《石门颂》拓片,鞭策了他的任性。
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大量的汉代简牍,这些简牍,便是一些书写在竹简、木简上的信札、日志、报表、账册、契据、经籍。与高大厚重的碑石铭文比较,它们更加亲切。这些汉代简牍(比如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大多是由普通人写的,一些身份微末的小吏,用笔墨记录下他们的事情,他们的字不会涌如今显赫的位置上,不会展览在众目睽睽之下,许多便是平凡的家书,它的读者只是远方的某一个人,乃至有许多家书,根本就无法抵达家人的手里。因此那些笔墨,更无拘束,没有演出性,更加随意、洒脱、残酷,也更合乎“书法”的本意,即:“书法”作为艺术,代价在于表达人的情绪、精神(舞蹈、音乐、文学等艺术门类莫不如此),而不是一种真空式的“纯艺术”。
在草木葱茏的古代,竹与木险些是最随意马虎得到的材料。因而在纸张发明以前,简书也成为最盛行的书写办法。汉简是写在竹简、木简上的笔墨。“把竹子剖开,一片一片的竹子用刀刮去上面的青皮,在火上烤一烤,烤出汗汁,用羊毫挺接在上面书写。写错了,用刀削去上面薄薄一层,下面的竹简还是可以用。”(蒋勋:《汉字书法之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烤竹子时,里面的水分渗出,彷佛竹子在出汗,以是叫“汗青”。文天祥说“留取赤心照汗青”,就源于这一工序,用竹简(“汗青”)比喻史册。竹子原来是青色,烤干后青色消逝,这道工序被称为“达成”。
面对这些简册(所谓的“册”,实在便是对一条一条的“简”捆绑串联起来的样子的象形描述),我险些可以觉得到羊毫在上面点画勾写时的流畅与轻快,没有碑书那样肃括宏深、力敌万钧的气势,却有着轻骑一样平常的灵动洒脱,让我骤然想起唐代卢纶的那句“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当笔墨的流动受到竹木纹理的隔断,便产生了一种滞涩感,更产生一种粗朴的美感。
实在简书也包含着一种“武功”——一种“轻功”,它不像飞檐那样沉重,具有一种庄严而凌厉的美,但它举重若轻,以轻敌重。它可以在荒野上疾行,也可以在飞檐上奔忙。轻功在身,它是自由的行者,没有什么能够限定它的脚步。
那些站立在书法艺术顶峰上的人,正是在这一肥沃的书写土壤里产生的,是这一浩大的、无名的书写群体的代表人物。我们看得见的是他们,看不见的,是他们背后那个弘大到无边无涯的书写群体。他们的书法老师,也是从前那些寂寂无名的书写者,以是清代金石学家、书法家杨守敬在《平碑记》里说,那些秦碑,那些汉简,“行笔真如野鹤闻鸣,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
北宋米芾《盛制帖》页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如果说那些“无名者”在汉简牍、晋残纸上写下的字迹代表着一种民间书法,有如“民歌”的嘶吼,不加润色,任性自然,带着生命中最朴拙的激情亲切、最真实的痛痒,那么,我在《故宫的书法风骚》一书里面写到的李斯、王羲之、李白、颜真卿、蔡襄、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人,则代表着知识群体对书法艺术的凝练与升华。唐朝画家张璪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我的理解是,所谓造化,不仅包括山水自然,也包括尘常人世,实在便是我们身处的全体天下,在经由心的熔铸之后,变成他们的艺术。书法是线条艺术,在书法者那里,线条不是线条,是天下,就像石涛在阐释自己的“一画论”时所说:“此一画收尽鸿蒙之外,即亿切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
北宋欧阳修《灼艾帖》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他们许多是影响到一个时期的巨人,但他们首先不因此书法家的身份被记住的。在我看来,不以“专业”书法家自居的他们,写下的每一片纸页,都要比本日的“专业”书法家更值得我们欣赏和铭记。书法是附着在他们的生命中,内置于他们的精神天下里的。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字迹的圈圈点点,横横斜斜,牵动着他们生命的回转、情绪的起伏。像张旭,肚子痛了,写下《肚痛帖》;像怀素,吃一条鱼,写下《食鱼帖》;像蔡襄,脚气犯了,不能行走,写下《脚气帖》;更不用说苏东坡,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寒食节,把他的委曲与愤懑、叫嚣与彷徨全部写进了《寒食帖》;李白《上阳台帖》、米芾《盛制帖》、辛弃疾《去国帖》、范成大《中流一壶帖》、文天祥《上宏斋帖》,无不是他们内心天下最真切的表达。当然也有颜真卿《祭侄文稿》《裴将军诗》这样洪钟大吕式的震荡民气之作,但它们也无不是泣血椎心之作,书写者坦直的性情、喷涌的激情和向去世而生的气概,透过笔端贯注到纸页上。
他们信笔随心,以是他们的法书浑然天成,不见营谋算计。书法,便是一个人同自己说话,是天下上最美的独语。一个人心底的话,不能被听见,却能被瞥见,这便是书法的神奇之处。我们看到的,不应只是它表面的美,不但是它起伏抑扬的笔法,而是它们所透射出的精神与情绪。
唐代李白《上阳台帖》(原件拍摄版,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他们之以是成为今人眼中的“千古风骚人物”,窍门在于他们的法书既是从生命中来,不与生命相分开,又不陷于生活的泥潭不能自拔。他们的法书,介于人神之间,闪烁着人性的光泽,又不失落神性的光辉。一如古中国的绘画,永久以45度角俯瞰人间(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离世俗很近,触手可及,又离天空很近,仿佛随时可以摆脱地心引力,飞天而去。所谓洒脱,意思是既是尘凡中人,又是尘凡外人。中国古代艺术家把“45度角哲学”保持到底,在我看来,这是艺术创造的最佳角度,也是中华艺术优胜于西方艺术的缘故原由所在。西方绘画要么像宗教画那样在天国漫游,要么彻底低落到人间,像文艺复兴往后的绘画那样以正凡人的身高为视点平视。
我们有时会忽略他们的书法家身份,第一,是由于他们在其他领域的光芒太过刺目耀眼(如李斯、李白、“唐宋八大家”、岳飞、辛弃疾、文天祥),遮蔽了他们在法书领域的光环。比如李白《上阳台帖》,卷后附宋徽宗用他著名的瘦金体写下的题跋:“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画洒脱,英气雄浑,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根据宋徽宗的说法,李白的字,“字画洒脱,英气雄浑”,与他的诗歌一样,“身在世外”,随意中出天趣,气候不输任何一位书法大家。黄庭坚也说:“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只不过他诗名太盛,粉饰了他的书法有名度,以是宋徽宗见了这张帖,才创造了自己的无知,原来李白的名声,并不仅仅从诗歌中取得。第二,是由于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还有亲笔书写的墨迹留到本日,更无从感想熏染他们遗留在那些纸页上的生命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该当感谢历代的收藏者,感谢本日的博物院、博物馆,让汉字书写的痕迹,没有被韶光抹去。有了这些纸页,他们的文化代价才能被准确地复原,他们的精神天下才能完全地重现,我们的汉字天下才更能显示出它的瑰丽妖娆。
人们常说“见字如面”,见到这些字,写字者本人也就鲜活地站在我们面前。他们早已随风而逝,但这些存世的法书见告我们,他们没有真的消散。他们在飞扬的笔画里活着,在伸展的线条里活着。逝去的是朝代,而他们,须臾未曾离开
天下三大行书
永乐九年的兰亭雅集,王羲之趁着酒兴,用鼠须笔和蚕茧纸一气呵成《兰亭序》,后被列为“天下行书第一”。“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笔墨开始时还是妖冶的,是被阳光和山风洗濯后的通透,是呼朋唤友、无事一身轻的轻松,但写着写着,调子却陡然一变,笔墨变得沉痛起来,真是一个醉酒忘情之人,笑着笑着,就失落声痛哭起来。那是由于对生命的追问到了深处,便是悲观。这种悲观,不再是对社稷江山的忧患,而是一种与生俱来又无法摆脱的孤独。《兰亭序》寥寥324字,却把一个东晋文人的繁芜心境一层一层地剥给我们看。于是,乐成了悲,俏丽成了悲惨。实际上,庄严繁华的背后,是永久的悲惨。打动人心的,是美,更是这份悲惨。
唐太宗之喜好《兰亭序》,一方面因其在书法史的演化中,创造了一种俊逸、雄浑、流美的新行书体,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平。赵孟頫称《兰亭序》是“新体之祖”,认为“右军手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效法”,但紧张还是由于它写出了这份绝美背后的悲惨。我想起扬之水评价生于会稽的元代词人王沂孙的话,在此也颇为适用:“他有本领写出一种凄艳的俏丽,他更有本领写出这俏丽的消亡。这才是生命的实质,这才是令人长久冲动的命运的无常。它小到每一个生命的个体,它大到由无数生命个体组成的大千天下。他又能用委曲、吞咽、沉郁的思笔,把感伤与悲惨雕琢得玲珑剔透。他影响于读者的有时竟不是同样的感伤,而是对感伤的欣赏。由于他把悲哀美化了,变成了艺术。”
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卷(唐代冯承素摹)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苏东坡《寒食帖》,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三”,因此广为人知。自元丰三年抵达黄州,苏东坡就被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压迫着,以至于在到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他在凄风苦雨、病痛交加中写下的《寒食帖》,至今让我们感到浑身发冷。时隔九个多世纪,我们依然从《寒食帖》里,目睹苏东坡居住的那个漏风漏雨的小屋:“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不仅苏东坡的人生千疮百孔,到处都是漏洞,连他居住的小屋都充满漏洞。风雨中的小屋,就像大海上的孤舟,在苍茫水云间无助地漂流,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
《寒食帖》里透露出的冷,不仅是萧瑟苦雨带来的冷,更是弥漫在贰心里的冷。官场上的苏东坡,从失落败走向失落败,从贬谪走向贬谪,生平浪迹天涯,这样的生平,就涵盖在这风雨、孤舟的意象里了。
在我看来,《寒食帖》是苏东坡书法的迁移转变之作,少了几分从前的流丽优雅,多了几分沧桑,但苏东坡晚年在海南写下的《渡海帖》(又称《致梦得秘校尺牍》),才是苏东坡的成熟之作。那是苏东坡渡海北归前,去澄迈探求好友马梦得,与马梦得失落之交臂后写下的一通尺牍,在那点画线条间随意无羁的笔法,已如入无人之境,达到唾弃统统障碍的纯熟境界,它“布满人生的沧桑,散发出灵魂彻悟的灵光”(赵权利:《苏轼》,河北教诲出版社,2004年版),是苏东坡晚年书法的代表之作。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不禁惊叹:“沉著高兴,乃似李北海。”这件宝贵的尺牍历经宋元明清,流入清宫内府,被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现在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四家小品》卷之一。
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二”的,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安史之乱”中,颜氏一门报效朝廷,去世于叛军刀锯者三十余口。公元758年,即《祭侄文稿》开头所说的“乾元元年”,颜真卿让颜泉明去河北探求颜氏一族的遗骨,颜泉明只找到了颜真卿的弟弟颜杲卿的一只脚和侄子颜季明的头颅,那,便是他们父子二人的全部遗骸了。悲愤之余,颜真卿写下了这纸《祭侄文稿》。
在《祭侄文稿》中,我看到了以前从颜字中从来未曾看到的速率感,似一只射出的响箭,直奔他选定的目标。虽然《祭侄文稿》不像明末连绵草(以傅山为代表)那样有连绵不断的笔势,但我觉得颜真卿从提笔蘸墨起,他的书写就没有停过。《祭侄文稿》是在极短的韶光内书写完毕,一气呵成的。
这是一篇椎心泣血的文稿,笔墨包含着一些极度悲痛的东西,如果我们的知觉系统还没有变得迟缓,那么它的字字句句,都会刺痛我们的心脏。在这种极度悲痛的使令下,颜真卿手中的笔,险些变成了一匹野马,在旷野上当仁不让地狂奔,所有的荆丛,所有的陷阱,全都不在乎了。他的每一次蘸墨,写下的字迹越来越长,枯笔、涂改也越来越多,以至于到了“父陷子去世,巢倾卵覆”之后,他连续书写了靠近六行,看得出他伤痛的心情已经不可遏制,这个段落也是全体《祭侄文稿》中书写最长的一次,虽然笔画越来越细,乃至在涂改处加写了一行小字,却包含着雷霆般的力道,虚如轻烟,实如巨山。
《祭侄文稿》里,有对青春与生命的怀悼,有对山河破碎的慨叹,有对战役狂徒的谩骂,它的感情,是那么繁芜,繁芜到了不许可颜真卿去考虑他书法的“美”,而只要二心坎情绪的倾泻。因此他书写了中国书法史上最繁芜的文本,不仅它的情绪繁芜,连写法都是繁芜的,仔细看去,里面不仅有行书,还有楷书和草书,是一个“跨界”的文本。纵然行书,也在电光火石间,展现出无穷的变革。有些笔画明显因此笔肚抹出,却无薄、扁、瘦、枯之弊,点画粗细变革悬殊,产生了干湿润燥的强烈比拟效果。
苏东坡喜好颜真卿的,正是他笔墨里透露出的大略、坦直、诚挚,说白了,便是不装。苏东坡少时也曾迷恋王羲之,如美国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者倪雅梅所说,苏东坡的书法风格,便是“建立在王羲之侧锋用笔的办法之上”,这一书写习气,他险些生平没有改变。但在晚年,苏东坡却把颜真卿视为儒家文人书法的鼻祖,反复临摹颜真卿的作品(个中,苏东坡临颜真卿《争座位帖》以拓本形式留存至今),乃至承认颜真卿的中锋用笔不仅是“一种正当的书法技巧”,它乃至可以被看作“道德端正的象征”(倪雅梅:《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江苏公民出版社,2018年版)。
《祭侄文稿》不是一件纯挚意义上的书法作品,我说它是“超书法”,是由于书法史空间太小,容不下它;颜真卿也不因此书法家的身份写下《祭侄文稿》的,《祭侄文稿》只是颜真卿平生功业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当安禄山反于范阳,颜真卿或许就以为,身为朝廷命臣,不挺身而出便是一件可耻的事。像初唐墨客那样沉浸于风月无边,已经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梦想,此时的他,必须去面对生与去世之间横亘的关隘。
我恍然瞥见颜真卿写完《祭侄文稿》,站直了身子,风满襟袖,须发皆动,有如风中的一棵老树。
(作者系散文家,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研究所所长)
(来源:光明日报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