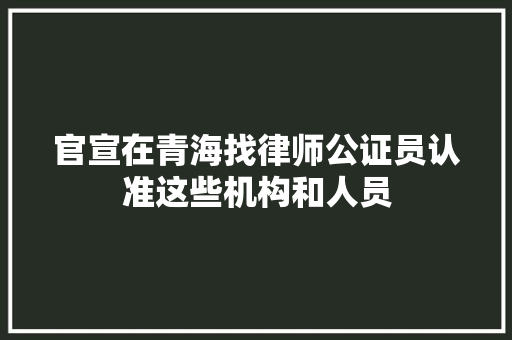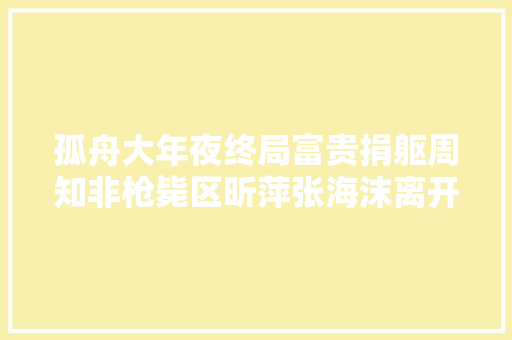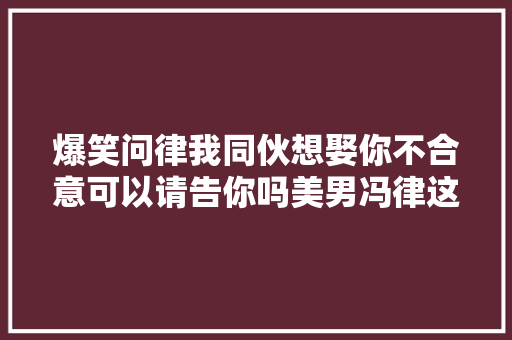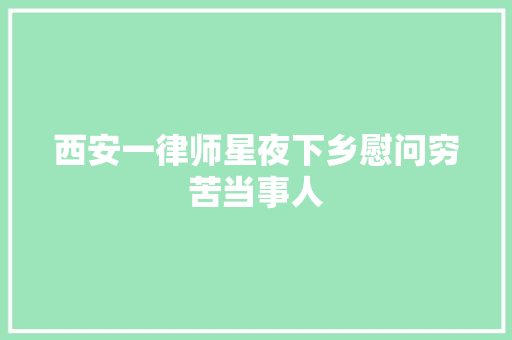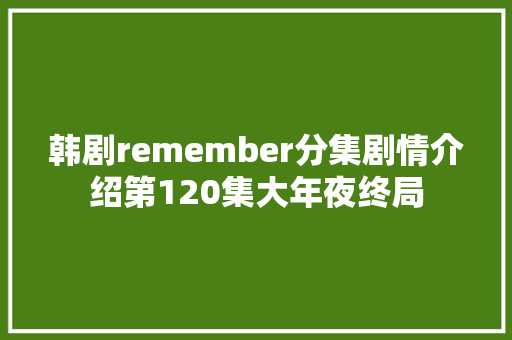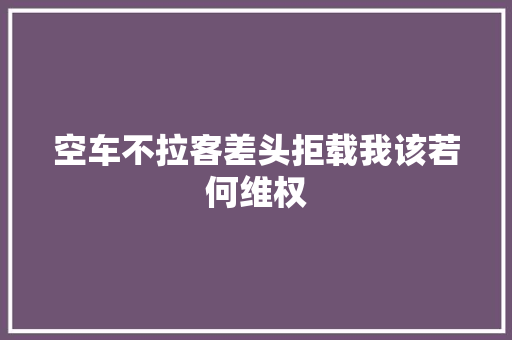胡杨林像针刺一样密匝地倒插在这片豫北黄地皮上,一早一晚聚起薄雾,阔拓的马路、小平楼都是崭新的,这些年内,大部分村落民陆续迁到了堤坝北岸,黄河即便再度涨水,也很难对清河集村落构成直接威胁。
从旧村落小径往北行进十几里路,就到了常卫云现在的家—一爿约20亩的桃林。入秋后,果树已全部凋零,地上铺满残枝落叶,天穹被用来防挡小鸟的网笼罩。

常卫云独自住在路中心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平房里,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孤零零地卧在房内唯一一张低塌的单人床里,头发散乱,浑身浮肿。身旁是坑洼的水泥地面和堆积如山的杂物,斜上方一只小小的天窗,灯时间暗,像一间单人囚室。
周遭实在太静了,没有鸟和兽,连一丝风也不闻。
常卫云现在的“家”在一片荒漠的桃园里
这个大略单纯搭建的平板间是政府给常卫云专门腾挪出来的“避难所”,除了儿子张海宾的好朋友阿鹏,平常不会有人来看她,亲戚乡亲们早已断绝往来。
常卫云反而以为清净和心安,阔别熟习的黄河水和杨树林,阔别可能“要她命”的人。
这天是传统“鬼节”,农历十月月朔,常卫云一大早醒来就以为头痛欲裂,浑身酸软无力。
11月10日,“张好峰父子反杀事宜” 被第十次坚持原判。“每次收到法院的讯断,我就要生一次重病。”她说。
一个人,一张床,一间简陋的屋子,所有的讯断书,便是常卫云现在生活的全部踪迹
她也不敢回原来的家,自从2009年7月3日过后,她再也没有踏进那个曾酿成惨祸的院子半步。不仅由于怕触景伤情,更怕暴露行踪,被许家的人创造。
那是一幢1998年建的两层独栋,附带100多平方米的院子,11年过去,院里落满了枯叶、断枝,两三米高的墨绿色大铁门上还残留当年被砸烂的伤痕,常卫云虚晃晃的躯体走过去,推开房门,破败的家具裹在尘埃中,一股腐气扑鼻而来。
常卫云颤颤巍巍地在门前一块空地前站稳,伸手指向地面:“当年便是在这里(打斗的)。”
行 凶11年前,2009年7月19日晚,河南新乡市清河集村落,31岁的许振军带着几个人来到张好峰家中,与张好峰、张海宾父子争执并打斗,许振军身中数刀去世亡。张家父子被判故意杀人罪,分别被判处去世刑和去世缓。
常卫云每次走进原来的家门都不自主地身体抖动
据眼见村落民的证词,闯入者年夜约五六个人,还有人翻墙进入张家,不少村落民都听到院内传出叫喊和厮杀声,漆黑一片中,详细的打斗细节,就连当事双方,都很难百分百确定复述。
而根据许振军朋友的交代,他们是3个人而非5个人,并且只有许振军一人下车去与张家父子打斗,其他人留在车上。
日前,法院采信的是另一种说法,称张海宾父子事先准备好了尖刀利刃,等待着有一天攻击和报复许。
张好峰的供词则是:当许等人踹门时,张家父子持棍棒躲在院内,混乱中挥舞棍棒,打伤了对方一行人。
据被告方代理状师常伯阳回顾,当张好峰得知许振军去世亡后,立马慌张起来,不才一次供词中,承认自己用镰刀致许振军去世亡,想一个人扛下罪名,保护儿子。
儿子张海宾,被法院讯断书形容为“犯罪手段残酷、性子恶劣,后果特殊严重”。
在张好峰妻子、张海宾母亲常卫云的泣诉里,“我儿只是想逃命啊,他有什么错?” 她说,当时混乱中,张海宾曾不顾统统逃出院子,奔忙几十米后,又被入室者追出连续殴打。
常卫云把这些年所有干系资料都藏在床板底下,每天都要翻出来研究
为了给父子二人翻案,在过去的11年内,常卫云日复一日到北京上访,据她自陈,整整10年来,她没有心思事情,睡在桥洞和车站,接火车站的自来水喝,吃快餐店里人们吃剩的饭菜,半个馒头可以吃一天。偶尔碰着好心的、状师,会帮助她一些生活开销。冬天,就用火车站的开水注满许多矿泉水瓶,在身体阁下围满一圈,再席地而卧。
这样的日子11年如一日,她已不在乎再来一个11年。
这10年来,只有两件事让她从北京一次次乘铁皮火车返乡:一是每个月都要来探望丈夫和儿子。“一个被关到开封,一个被关到新乡,探监都要让我跑两趟。”二是接管采访。直到去年9月,有首次哀求重访老屋院子,常卫云才再次推开了那扇尘封11年的大门。
这次熏风窗前去采访,她特地安排了儿子的好朋友接送,没见告当地政府。她说,前面几次,政府会招待媒体,一波来了一波又走,看到来了,许振军70多岁的父亲许洪振就在常卫云家附近慢跑,一边偷偷不雅观察。
有几次,儿子张海宾的同学小柱陪她去北京上访,两人住在车站旁20元一天的宾馆里,一张床。常卫云不敢睡着,由于乡里总有人打电话来提醒她,说许洪振一贯在尾随她。
常卫云回顾,这些年,光是在河南省内,许洪振的人就打过她8次,缝过针、住过院,许洪振等人却未曾受到过一次惩办。
按照当年村落民们接管采访时的说法,许振军一家是家喻户晓的“村落霸”,欺凌、打斗等已是家常便饭。
“天国纪念网”上对许振军背景的阐述
2010年3月,第一次正式开庭的庭审上,许洪振一家组织二十余人冲击法庭,围攻张好峰方代理状师高建涛,高建涛状师被打后住院数月,不得不发出《无法出庭奉告书》,宣告从此退出此案。
2011年1月,狱中的张海宾写下申说信:“模糊的东西我们终极都能看清,但要看清明显的东西,则要花费我们更长的韶光。我不能在明知道父亲的危险系数提高的情形下,把他一个人丢下。”
高建涛状师的《无法出庭奉告书》,图/受访人供应
同年10月,最高公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复核,撤销张好峰的去世刑讯断,父子二人皆变成去世缓,常日来讲即无期徒刑。
2012年12月10日,与过往一样,河南省高等公民法院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驳回重审。
而关于此案引起普遍争议的“正当防卫”,法院给出的驳回情由是:张氏父子得知许振军踹门时,手持棍棒藏在院内,许振军闯入后与之斗殴,由于许对其人身还未造成不法侵害,闯入的目的也还不明确,以是属于“故意伤人”。
2013年法院讯断书
“有人闯入我家门,我难道只能等着被打?”在常状师眼里,哪怕从人类的朴素认知出发,“故意伤人”也说不过去。
棍 棒许振军第一次闯入家门时,最初是常卫云替丈夫挨下的那些棍棒和拳脚的。
2009年7月2日一大凌晨,常卫云去镇上给儿子、儿媳房间买空调,好让儿媳安心养胎和坐月子。
旧院已经杂草丛生,破败不堪
她不知道,与此同时,丈夫张好峰和村落里9个村落民一块儿,正浩浩荡荡前往封丘县纪委,签下了举报前支书许洪振贪腐行为的联名信。
后来,在闯入张好峰家门之前,联名信上的其他8位村落民—许坤亮、张守芳、张思随、徐景周、刘万海、许振乾、刘万胜、许小峰,也陆续遭到许振军的上门打击报复。
据今年11月4日《红星新闻》的宣布,个中徐景周在当年的警方笔录中描述许振军闯进家门时的场景:“许振军一进门,就朝我头部打了一拳。”
越日晚上,许振军带着一行人冲进常卫云家院子,常卫云赫然看到,昨日那封举报信被许振军攥在手中。
这封信上没有常卫云的指模,常卫云记得,一个眼熟的小伙子还客客气气地对她说:“嫂,没你事。张好峰,你出来吧。”
大门被钝器砸坏的痕迹
常卫云很快创造对方拿着棍棒,要打人,于是连忙上前挡着几人,把他们往门外拦。推攘间,对方动起手来,许振军等人的拳脚、铁锨把和砖头,一股脑倾泻在她身上,常卫云使劲将对方往外推,血沿着她的额头流下来。
一楼的张好峰和女儿小朵闻声出来,也被打了几棍子。
那一晚“有月光”,以是常卫云能瞥见对方共7人,带着“7根大白棍,虎口这么粗”。
这次许振军他们很快离开,家里的钱只够拿给伤势最重的常卫云去医院,头骨骨折、浑身淤青血痕的她,在医院一住便是半个月。
没想到,16天后,许振军又带着几个人,再次气势汹汹闯进来。
常卫云2009年7月3日被打伤照片
7月19日晚上9时20分许,常卫云接到女儿小朵的电话,语气急得要哭:“妈,又有人上咱家来了!
”她听得见,许振军一行人正在跺跺地踹门。
当时,常卫云正在住院,身上带着半个月前被许振军等人打的伤,同时住在医院的还有即将临蓐的儿媳妇。
常卫云心急如焚,想跑回家,但双腿发软,几个邻居也打电话给她,让她“千万别回家”。
铁门上的门闩被闯入者硬生生打断
混乱的家里,惨案已不可逆转。张海宾在后来的供词里中陈述,双方打斗甚烈,他被当头一棒敲晕在地,他挣扎着爬起来,冲出家门想逃命,心里只想着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我不能去世在这里,不能让我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
离开医院后,等待着常卫云的,是再无返期的血屋,精神失落常的小朵,正在坐月子的媳妇和襁褓里的孙女。
家 人常卫云相信,女儿精神失落常不仅是由于受到惊吓,更是来自遗传。
还不到20岁,常卫云就嫁给了张好峰,丈夫脾气不好,爱打她,但常卫云总以为他“精神有问题”,以是“能理解他”。
过往,张好峰打完她后,她就坐在阁下一个劲儿哭,张好峰仄歪过去瘫在一旁,过了约半个小时才忽然回过神来,问常卫云:“你哭啥?咱俩吵架了?”
19日那次事发当晚,许振军被打去世后,张好峰、张海宾和小朵都被派出所拘押了,父子俩正在做笔录时,小朵一个人在走廊等着,忽然,许洪振带着一伙人又冲进派出所,看到女孩便立马冲上去,对她拳脚相加。
“肯定便是在那个时候受到过度惊吓(才精神失落常的)。”常卫云说。
越日,警方把女儿“还给了她”,小朵精神恍惚,身体僵硬,常卫云伸手去拉她,女儿却遽然吓一跳,猛地退后躲开。
失事时,女儿还不到20岁,这是老家中小朵的房间
带着精神失落常的女儿、虚弱的儿媳和襁褓里的孙女,常卫云本想去焦作投奔张好峰的一个远房叔叔,但没有找到人,倒是在路上偶遇了一对老夫妇。老夫妇好心收留了祖孙四人,还以每月100元的价钱租给她们一个单间,但实际上,住了3个月,不仅一分钱没收,还常常给她们买食品和水、婴儿用品等等。
那对老夫妇那时年夜约六七十岁,常卫云叫他们“寄父干娘”。
但这样的日子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不到1个月,儿媳就带着孙女不辞而别了,半个字都没给常卫云留下。
常卫云伤心欲绝,整日以泪洗面,3个月后的一天,女儿也忽然消逝了。
仅剩的亲人一个个离她而去,这下,常卫云真实地感到“天塌了”。
但“寄父干娘”还没放弃她。他们帮常卫云满天下找女儿,还去山上“烧纸”,听说这样可以唤离开的人回来。
没想到,几个月后,老夫妇托的朋友竟真在济源一个村落落的柴火堆里找到了小朵,他们把女孩带回来,常卫云把她锁进屋里,捱了半年后,找个人家把小朵嫁出去了。
常卫云没敢和女儿多联系,但她知道这个可怜的女孩也没几天好日子过,由于精神失落常,有身了又流产。“连孩子去世在自己肚子里都不知道。”
常卫云后来还考试测验回去找“寄父干娘”的踪迹,老屋子却早已被拆除,电话也再不能打通,生命低谷里碰着的恩人,就这样消逝无影了。
有人劝她再醮,谁劝她骂谁,逐渐地,也就没人再提,她的泣诉也蔫了下来:“老公我可以不要了,儿子你得还给我。”
2014年的一天,离开多年的儿媳忽然联系上常卫云,想让她带自己去监狱看望张海宾,常卫云这才重新和儿媳取得联系。
张海宾交给常卫云一封信,拜托母亲转交给媳妇,常卫云看了一眼,上面写着:“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太对不起你了。如果我出不来,你就再醮吧。”
但她一贯自己保存着儿子那封信,舍不得拿给儿媳,直到下个月再去看张海宾时被问及此事,她才不得不把信交出去。
那时候,儿子、丈夫已在狱中待了4年。
认 字在外流浪的年头,常卫云也碰着过骗子。
比如收了她2000元承诺撰文宣布后,转眼间人去“文”空的假。
常卫云能精准地记得十多年来碰着的每个人的名字,包括一壁之缘的每一个、在北京一块儿上诉申冤的大姐、举报未果的哪个官员、某个曾乐意帮助她的状师……
她从木抽屉里翻出一本半个巴掌大小的线装低廉甜头小本子,泛黄脱页的横格里,密密麻麻地记满了汉语拼音,和一撇一捺生硬拼凑出的许多人名、电话。
11年如一日地上访,常卫云知道了翻案须要认字、写字。
小学一年级都没毕业的她,自己剪裁了半个草纸本,重新开始学认拼音。满当当地写下“a”到“z”,下面写着大写“A、B、C”,但她不晓得它们是什么意思。接着,她逐渐认识了“法院”“状师”“正当防卫”等等字词,学会用完全的句子表达“我要上诉”。
十多年来,碰着的每个人,名字、电话号码,她都留着,每一句留言都一字不差记住,她把每一个当“恩人”,把每一个状师当“再生父母”。
她还知道翻案须要取证。
她在村落庄里挨家挨户问证词,找眼见,拿着当年唯一的小手机,把村落民的话都录下来,想办法找人刻录成光碟。
翻案还须要懂点法律。
她把关于“正当防卫”的法律条文险些都背熟了,翻烂了公安局的调查笔录、重审的法院讯断书,桌板底下压着约五厘米厚的装订材料,模糊的字里行间,常卫云在每一个疑点和关键处划波浪线,歪七扭八地写下自己的疑问。
狱中的儿子张海宾也没闲着,政府给张海宾买了许多法律方面的书,他一个人在狱中自学,反复研究法律材料。他寄出去的每一封申说信都会收到回执,常卫云去监狱探望时,儿子拿给她看,现在,光回执单就累积了半只手臂这么厚,常卫云比划着给熏风窗看。
翻案还须要学会上网,时候与外界保持联结。
她窝在自己的单人床里,靠一部没有WiFi的手机看新闻,她知道等待27年的宋小女,也知道就在这两天,隔壁的原阳县又发生了一起灭门血案。
这些年来,常卫云自己的3个弟弟、1个妹妹,张好峰的5个弟弟、1个妹妹,没有一人肯再主动联结她。“穷走大街没人问,你懂吧?”她用力苦笑了一声,张好峰的个中一个弟弟还是许洪振的半子,“(他)不跟我们站在一个态度上”。
2012年,常伯阳第一次在郑州的事务所见到了常卫云,那时的她既“焦虑”又“亢奋”,带着无助的希望,“她对翻案还是有一定信心的,但她完备是手足无措的状态,只知道‘靠你们了’,全体人都是懵的”。
继高状师被打退后,经朋友推举,常伯阳以公益状师的身份参与此案,他当时没有想到,这一仗,一打便是8年。
常状师认为,对付张好峰案,状师群体中对“正当防卫”的成立险些是没有异议的。不过,纵不雅观近几年我国平反的冤案、错案,要么是存在明显争议及证据的,要么是真凶现身。这些年来,尤其是自于欢案往后,“正当防卫”在法律界得到更多重视,但要运用于十几年前的旧案,依旧困难重重。
而且,在细节模糊、时隔久远的情形下,对全体法律系统而言,还存在着另一个顾虑:一旦翻案,就意味着大量其他类似旧案都必须重新提审,耗时耗力,而且,这分明意味着“以前的人错了”。
“谁来负这个任务?”常状师叹口气。
(文中阿鹏、小柱、小朵为化名)
作者 | 熏风窗 肖瑶
编辑 | 何子维
排版 | 翁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