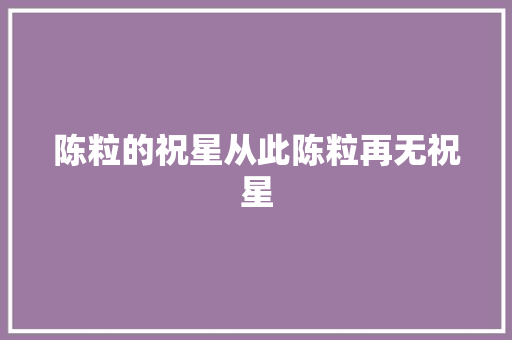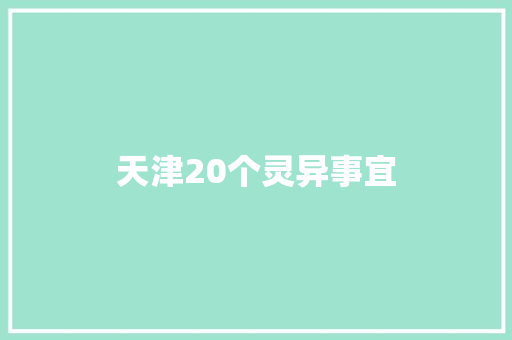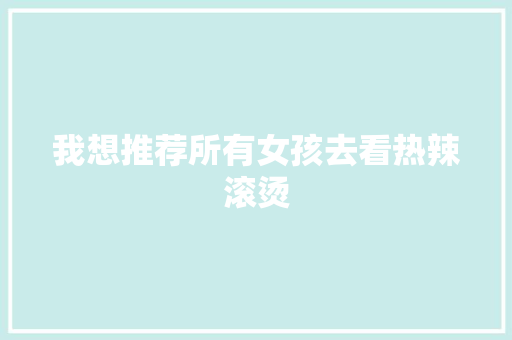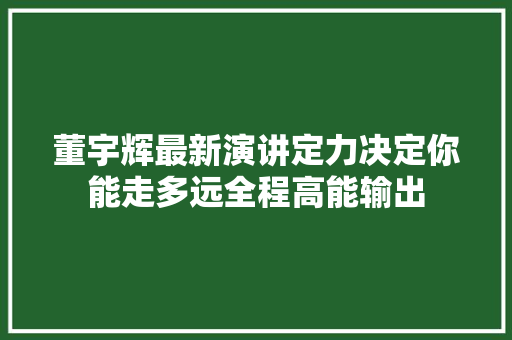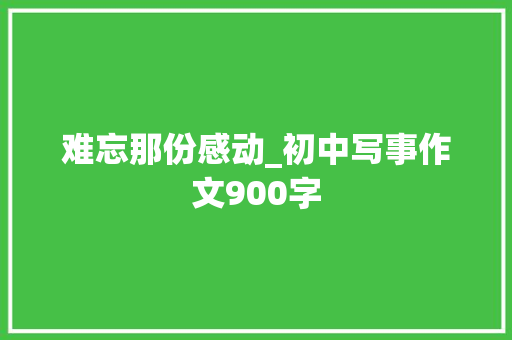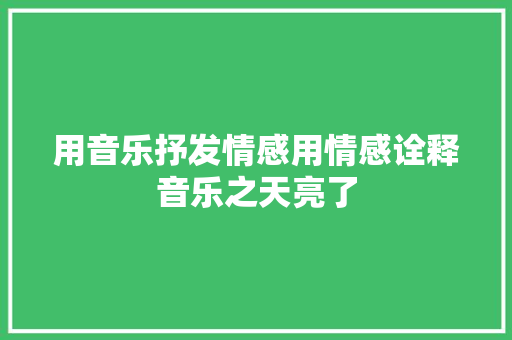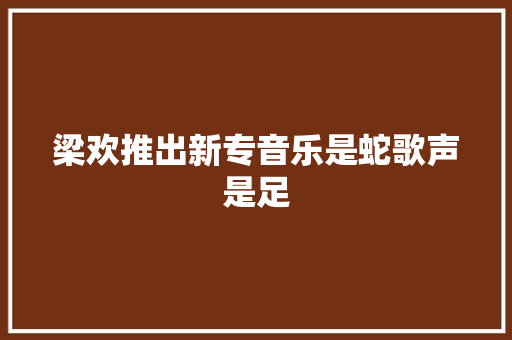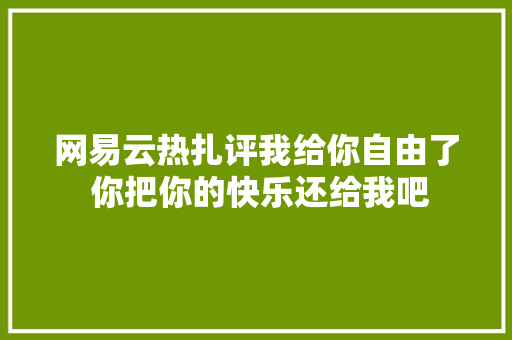“有声的文章与天上星图”——《空山横:讲演集,关于文学关于人》新书分享会现场,从左到右依次为杨庆祥、李敬泽、都靓(主理方供图)。
演讲或讲演,是一种与天下建立面对面的连接的办法。《空山横》是李敬泽演讲的初次结集,包括了15次真实的演讲以及1次想象的演讲,内容关于曹雪芹、鲁迅、杜甫、汪曾祺,也关于跑步、雨燕、鹅掌楸、超级AI,小到日常之物,大到天上星图,统统都与文学有关、与人有关。而《空山横》的书名,则与一首古诗有关,“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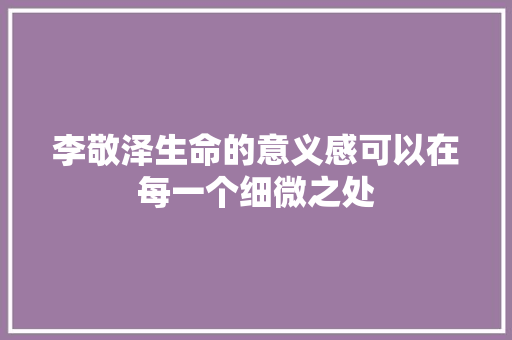
活动现场,杨庆祥从书名谈起,在他看来,书名的妙处,正好在“横”字上。“横”字怎么理解?“中国的笔墨是象形字,一横、空山。以是如果是底下一横,那便是地平线,是大地。如果上面一横,那便是天涯线,是天空。天、地,中间有山,山里面有人。这个人在哪里?不知道,这个人藏得很深,但是有时候他又探出头来,我以为这个特殊故意境,便是‘天、地、神、人’。 ”在这里,杨庆祥引用了海德格尔的不雅观点,全体和谐宇宙的构造的构图,便是“天、地、神、人‘四方’归于一体”,“他认为,当代人的困苦和焦虑就在于“天、地、神、人”里的“神”没有了,以是人就陷入了一个上不能接天,下不能接地的状态,人就会痛楚。”
对此,李敬泽坦言,自己起初并没有特殊想过“横”字是什么意思。一本讲演集,便是一个人对着一群人讲话。由于很害怕当着很多人讲话,李敬泽为自己想了一个办法,“我每次往这一站,我就想象我面对的是一座空山,你们都是空山中的树,一棵又一棵的树。我实际上是喜好‘空山’这两个字,以及‘空山’这样的一个情境。”“空山”直接套用了王维现成的词,但李敬泽为“空山”再加了一个字,变成了“一座空山横(héng)在面前”,但与此同时,这个书名也可以读作《空山横(hèng)》,“面对空山横(hèng)起来,不症结怕说话。”
杨庆祥说,自己曾经听过李敬泽很多演讲,在他看来,《空山横》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关键词,那便是“连接”——各种的连接,“他的连接迸发出思维与聪慧的火光。”事实上,李敬泽直言自己并不喜好提前将演讲的稿子准备好,“演讲这个过程,我自己不想把稿子准备好,便是想逼着自己,让自己保持着一种紧绷的、敏锐的、断港绝潢情急智生的状态。我以为这种状态使这件事不至于沦为乏味的‘发言’,它成了一件蕴含着‘意外’的事,我喜好这样的觉得。”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觉得呢?李敬泽说,这种觉得“正好不是说‘我有一个很有把握的东西,我要教给你,我要输出给你”,而是我站在这里,实在我对这个天下也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不愿定,也很没有把握,我乐意和你们一起来面对这个不愿定,咱们飞行起来、滑翔起来,看看终极落在哪里。”在李敬泽看来,事先准备的稿子,是一个“确定”的过程,而自己很喜好不愿定性,“我乃至喜好我自己脑筋的不愿定性。这种不愿定性意味着,我们随时乐意面对这个天下新的履历,面对想不到的问题,面对我们在惊惶失措中从这件事和其余一件风马牛不干系的事中创造的联系和连接。”
有什么方法能够对抗我们生活中的无意义感吗?面对这一提问,李敬泽给出的回答是,“我们之以是有时候评论辩论生活的无意义,常常是由于我们是被过多的意义感所满盈,有太多的意义感了,或者说有太多的伪意义。”在这里,李敬泽以现在年轻人很喜好的苏东坡为例,“苏东坡的生平,一方面他与自己的无意义感做斗争,《寒食帖》里‘去世灰吹不起’;另一方面他在任何一件小事上,在自己生命的每一个时候,都在为自己勘探和创造意义,他在天上的玉轮、地上的竹影、远方的亲人和一盘红烧肉之间去建立意义。”
李敬泽说,生命的意义感可以在每一个细微之处,那点意思、那点好、那点伤感和美感、那点内心的惬意,以及把所有这些联系起来,给自己的生命一个交代、一个言说、一个觉得,“咱们假定一下:如果人生没有烦恼,所有烦着我们的那些事全部取消掉,那人生可能真就没意思了。人生中所有故意思的事、美好的事实在也都是烦恼的事。”
而在杨庆祥看来,人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生存的烦恼、精神的困境和意义的困扰。他在这里引用了叔本华对此的比喻,“他说人生如钟摆,往左是烦恼,往右也是烦恼。然后你就一直地在烦恼和烦恼之间摇摆,由于你在烦恼和烦恼之间摇摆,你这个钟才走,你这个生命才走,以是烦恼是让我们走起来的一个过程。以是你要上发条,你要有烦恼,没有烦恼的人生没故意义,但是如果你这个发条上得太紧,把意义之链弄得特殊紧张,特殊单一,你可能会崩掉。以是有时候你要去跑步,你要去看鹅掌楸,你要去读苏东坡,你要去吃红烧肉,等等。”
以下内容节选自《空山横:讲演集,关于文学关于人》,较原文有删节修正。已得到出版社授权刊发。
《空山横:讲演集,关于文学关于人》,李敬泽 著,译林出版社2024年7月版。
听“空山”——一次想象的讲演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我们先从王维的一首诗提及,这首诗题为《鹿柴》。山本来无所谓空不空,山上有草木、飞禽、走兽、泉水和溪流,山怎么会空呢?但山便是空的,由于不见人。真的一个人也没有吗?也不是,至少还是有一个的,便是说出“空山不见人”的那个人。人不见人,山才是空的,天下才是空的。什么是空?便是无,只有一个“我”的天下空空荡荡。
空山里的这个人,纵目一望,放眼看去,他看不见人,他瞥见了无。但是,接下来,空山不空了,无中生出了有,由于“但闻人语响”。
“响”与“不响”是中国诗学和美学的根本布局
“响”便是有,便是不空,我们看不见人,但是听见了人的声音。这个“响”字真是用得好、用得响,一记铜锣一个二踢脚,一下子就热热闹闹、滚滚尘凡、一天下的繁花。前些天热播的电视剧《繁花》,里边的一个高频关键词是“不响”。在金宇澄的原著小说中,有人统计过,“不响”用了一千三百多次。还有人说,王家卫改电视剧,把《繁花》改得面孔全非,人也不是那些人了,事也不是那些事了。但实在,他捉住了“不响”,这便是小说《繁花》的灵魂。
“不响”的正面便是“响”,没有“响”哪来的“不响”啊?以是,看电视剧,一、二、三集看下来,就以为吵闹,像屋里飞来轰炸机,炸弹不要钱一样,我不得不调低音量,以免打扰邻居。王家卫是搞电影的,电影中一个至关主要的艺术和技能环节便是声音,他会不知道这个声音太吵太闹?他便是要吵闹,他便是要“响”,有了“响”,才会“不响”。 金宇澄的《繁花》、王家卫的《繁花》,每一个“不响”,都是闹市里一个静默的间隙,是不能说、不必说、不知从何提及,是“灯火阑珊处”,是“欲辩已忘言”,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是一个“空”、一个“无”。
反过来,“不响”又是八面埋伏,预示着、期待着“响”。“空山不见人”,是空、是静,不见人是不对的,“不响”令民气慌。陈子昂登幽州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也是一大“不响”,空山不见人、原野不见人、高处不见人,“百年多病独登台”,百年孤独啊。然后呢,陈子昂下得台来,便是蓟门桥,便是北京的三环路,“人语”轰然响起来,这是密欠亨风的人间、是鼓噪的俗世,把眼泪擦干,投入火热的沸腾的生活,拿起发话器高歌一声:“安妮——”
以是,《繁花》太响太聒噪。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唯一的办法便是关掉电视。晚清刘熙载的《艺概》里谈韩愈:“说理论事,涉于迁就,便是本领不济”,他认为韩愈的好处便是不迁就。从金宇澄到王家卫,写小说、搞电视剧,不可能不迁就,不可能不考虑我们作为读者、作为不雅观众的感想熏染,但有些事不能迁就,便是要坚持,比如便是要冒死“响”,然后“惊起却转头,有恨无人省”,在人间人语的大响入耳出了“不响”,于大热闹中间离出“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2023年,中国大众文化一个艺术的和审美的内在机枢,就在“响”和“不响”。年底,我们看了《繁花》,在大响中领会了“不响”。然后,让我们费力回顾一下,在年初,在电视剧《漫长的时令》中,范伟扮演的主人公叫什么名字呢?叫王响,王响在剧中最初是个话痨中年人。他儿子王阳,是个文学青年,王阳站在通往远方的铁轨上,向着他所爱的沈默念了一首诗——我现在忽然想起,沈默这个名字实在是“沉默”、是“不响”。这首诗是这样的:
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迢遥的事物将被震碎。
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吹个口哨吧,我说你来吹个斜斜的口哨……
现在,我们看到,王响的儿子对着“不响”的女子,念出了一首诗,在“不响”中召唤着“响”。“空山不见人”,那就打个响指吧,“迢遥的事物将被震碎”,这个人是要做漫威宇宙里的灭霸吗?但是,这期待着“共鸣”的响指并没有被感知、被回应,空山还是空山,而你必须把山里的人们、“面前的人们”召唤出来,你吹一个斜斜的口哨,像一枚尖利的箭,划破寂静、划破空无,把“人语”的“响”标记在天上,把人召唤到面前。
恰好这两部剧都是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往事。十多年前,在上海的一个会上,我曾经说过,90年代是一个文化上无人认领的年代。现在,在2023年,艺术家们终于来分头认领,他们的路径和方向如此不同,但是,纯属有时、不谋而合,他们都徘徊于“响”和“不响”之间。
这件事还不算完。前几天我去看了贾樟柯刚刚定剪的电影《一代风骚》,坐在放映厅里,默默地流了几滴老泪。原来,这也是一部关于“响”和“不响”的作品,逝去的韶光、流失落的生命,生命中不可追回、不可补救的不甘和悲慨,所有这统统,究竟便是我们在生命之响入耳出的那个坚硬的不响,或者是,我们在内心寂静的废墟入耳出的万物轰鸣。
《一代风骚》里,人物面对面的对话极少,能说出来的实在都是不得不说但也并不要紧的。看完了电影,我恰好在那天晚上遇见了刘震云,忽想起他在多年前写过《一句顶一万句》,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万句的“响”都是徒然,都是废话,我们所期待的,不过是从沉默中、从“不响”中打捞出来的那一句。或者说,一万句的“响”、一万句的重也不过被一句话轻轻地顶住,但顶得住的那一句又是什么呢?在座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以为,生命的要紧时候,那一句是很难找的?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写作文,动不动就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句话是个啥呢?现在我们终年夜了,把栏杆拍遍,把肠子都想瘦了,“汇”不出来啊,千言万语是四面八方千匹万匹的奔马,怎么可能“汇”成一匹马?《古诗十九首》的第一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一首诗下来,心心念念、絮絮叨叨,彷佛什么都说了,又彷佛什么都没说,末了只好是“弃置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算了,不说了,努力用饭,保重身体!
这算不算是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呢?可是这说出来的一句不便是一个深奥深厚广大的“不响”吗?
好吧,我本来并没有打算在这里评论辩论电视剧和电影和小说。我只是说,如果读过《鹿柴》,我们就知道,“响”和“不响”并非新事,也不是上海话。至少一千二百多年前,山西口音的王维就已经在谛听天地和生命的“响”与“不响”,这是中国诗学和美学的一个根本布局。
用你的声音探求和确认他者的声音
王维执着于“空山”这个意象,除了《鹿柴》的“空山不见人”,还有《山居秋暝》的“空山新雨后”。我们每个人,当“空山”这个词在心里浮现,如一只鸟在天上飞过,它是哪来的呢?你仔细地、耐心地想,很可能它就来自王维,这个词是王维在陕西蓝田辋川山中打出的一个“共鸣的响指”。
“空山不见人”,这是一幅画,视觉的天下寂静无声,然后,声音加入进来,听觉被声音打开,“但闻人语响”。在山里,什么样的人语才会“响”呢?如果是在远处,山林里同行的两个人在交谈,对站在这里望空山的这个人来说,这是不会“响”的,他又不是顺风耳,他听不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山里行走的履历,有时真是空山不见人啊,放眼望去,一个人也没有,你走着走着,忍不住冲破这空无,就要对着天、对着山喊一声“啊——”。你喊出去,听到的是自己的反应,你知道那是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声音填不满这个空,逐渐地就消逝了,像水化进了水里。但是大概就在远处,有一个人听到了,站住了,这真是“但闻人语响”了。
如果是我,我就要忍不住回一声“啊——”,这么“啊”过来“啊”过去,都“啊”成一个“阿来”了。——顺便说一句,阿来写过一部小说,就叫《空山》,我一贯认为那是阿来最好的小说,比《尘埃落定》更好。也有人嫌长、嫌慢,看不下去,那是由于他的山是满的、他的心是满的,是实心儿的,一点空也没有。阿来写《空山》时,是否想起过王维?他当然想过,我乃至断定,在写整部《空山》时,他最内在的声音便是来自王维,他把《空山》写得无限空、无尽有,这也是王维在《鹿柴》里所做的事。
扯远了,回到“但闻人语响”。这个“人语”不是一样平常意义上人的话语,不是人在说话,是人的声音,是人最本真的声音:伸开嘴,对着空山,喊一声“啊——”,我在这里,你在吗?你是谁?这个“你”便是自我之外的他者。在山里,在莽莽苍苍的大自然的旷野里,在无边无涯的沉默中,你的本能便是用你的声音探求和确认他者的声音。一个人在探求另一个人,不管他是谁,只要他是个人,你就以为山也不空了、天下也不空了。
这种原初的、本真的声音,有时便是一声“啊——”,到了《漫长的时令》里,那便是吹个口哨。我不会吹口哨,小时候走在夜晚的路上,远处忽然飞起一个尖利的口哨,真是又帅又泼皮啊。一个大孩子走着走着,忽然寂寞了,忽然一个口哨,对你发出召唤:我在这儿,你在哪儿?
在这样的时候,喊出一声“啊”的人,吹口哨的人,你便是在搭建一个舞台,一座空山或这个寂静的夜晚成为了你的戏院。我坚信,人类的舞台和戏剧,它的原初的、根本的动机是声音。戏首先是听戏,你站在山野里一个临时搭起的野台子下面,你坐在国家大剧院的后排,或者你身处希腊一座古老圆形戏院的高处,你很可能无法看清舞台上的人长什么样,但是这有什么要紧,舞台上的声音,必定会清晰地抵达你的耳朵。在一些古老的戏剧形式中,舞台上的人常常会戴着面具或绘上脸谱,个中一层隐晦的意思是,你看不见我,“空山不见人”;然后,请听我的声音,让我的声音找到你,在你的耳膜、颅腔、心房中回荡,你在这声音入耳到你自己的声音,既陌生又熟习,你被叫醒、被召唤,你意识到你的有、你的在。你知道,真正的戏剧发生了。
这实在是一个奇迹。一个人与他者、与陌生人、与熟习的陌生人的相遇,这实在是一个声音事宜。“响”是声音,但“大音希声”,“不响”或无声或沉默也是声音。当人们以声音建立连接时,天下才得以展开,戏剧才真正开始,生活才真正开始。人类形而上的超验体验普遍来自声音,在中原文明中,天意落为笔墨,但我坚信,在天意和天意的显现之间、在甲骨之形和甲骨之文之间,一定存有一个失落落的声音环节——然后,我们才能理解礼乐之“乐”,才能理解某种声音何以从根本上照亮了我们。
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那座空山,声音照亮了王维,他听到了人语之“响”,但他是王维啊, 一个绝顶闷骚的安静男子,他不可能扯开嗓子“啊”回去,他更不可能一个口哨打回去。他只是立在那里,悄悄地听,听着那声“啊”、那个口哨在空中消逝,然后,“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他瞥见夕阳照进了深林,他又瞥见这光照在青苔上。
整合/何也
编辑/张进
校正/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