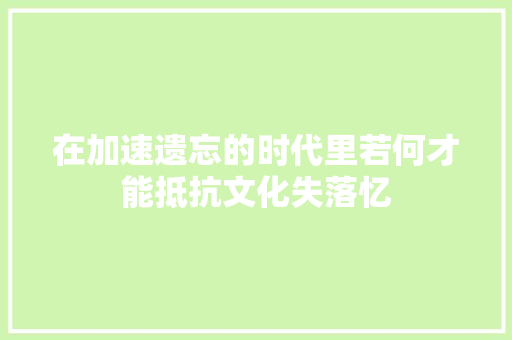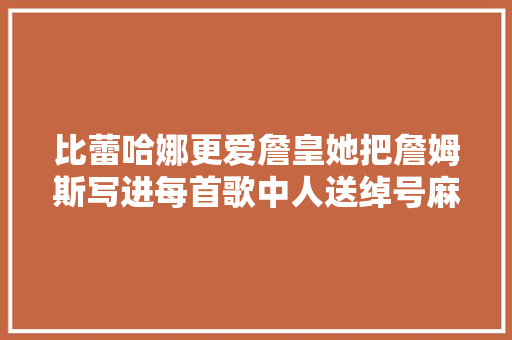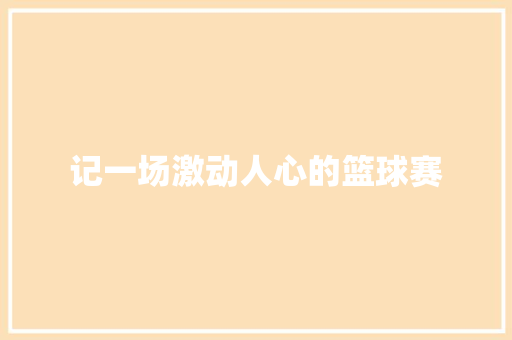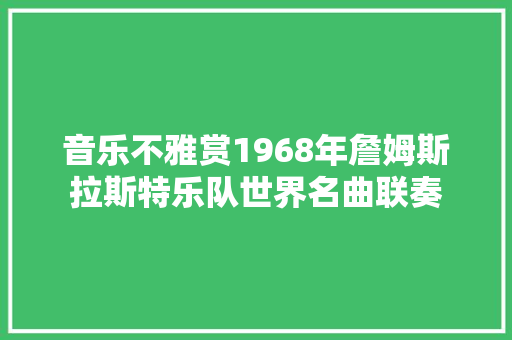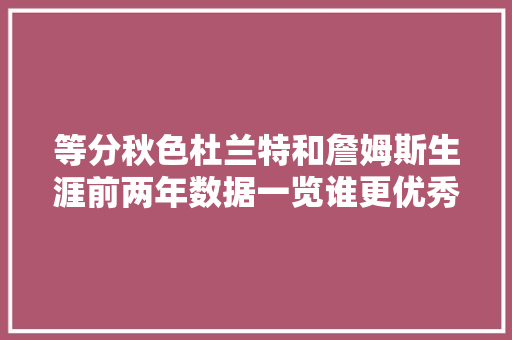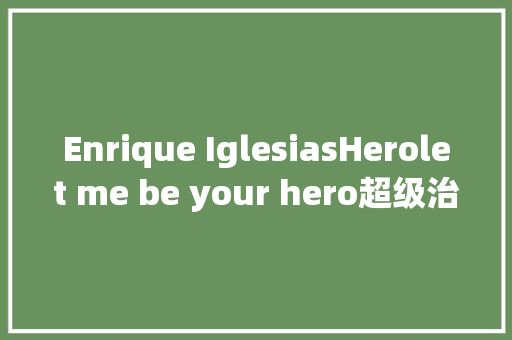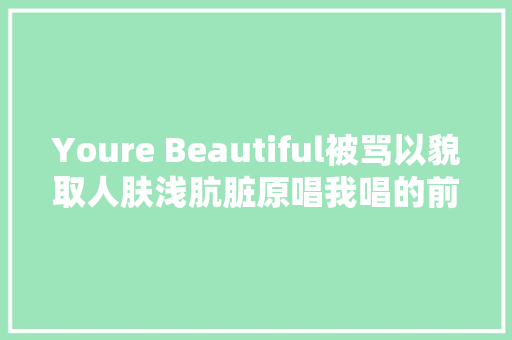【译者按】
1987年,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因胃癌去世,留下了尚未完成的遗作《记住这座屋子》(Remember This House)。2016年,导演劳伍·佩克(Raoul Peck)从这部未竟遗作得到灵感,通过记录片《我不是你的黑鬼》(I Am Not Your Negro),重新讲述了鲍德温和他眼中当年三位石友,也是三位精彩黑人领袖——梅德加·埃弗斯、马尔科姆·X和马丁·路德·金——的故事。实在,早在1968年,鲍德温在接管《时尚师长西席》杂志访谈谈论美国种族关系时,就以相称坦诚的办法,谈及了包括这三位在内的许多黑公民权运动家。在新冠肺炎依旧肆虐、美国种族关系日益紧张的2020年,鲍德温当年的这场访谈仍不失落实在际性。首先,这篇访谈在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之后,深入磋商了黑人作为被压迫族群的现状和历史根源,阐发了黑人社区对美国政治构造的不信赖,也深刻批驳了当时两党制的局限性。其次,虽然黑人在被殖民者劫掠出非洲来到美洲后的奴隶制度已经废除,但鲍德温重申了黑人依旧被俘被困的生存现状,工业化、郊区化的过程将他们像“多余人”一样抛出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生活,推向贫民区、监狱和精神医院等社会边缘。从某种意义上,他所说的黑人没有未来或“去世得更快”,都是这种被困被俘的延续和表示。此外,与六十年代相似,在和平抗议的同时,现在也涌现了一些砸店等暴力升级行为。不少美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六十年代,希望能通过当时的所行所思,试图去理解当下的一些行为。于是,鲍德温的1968年访谈,便成了主要的线索之一。作为译者,我们希望读到这篇译作的中文读者,不是把这篇文章当作阐明,而是一种开始,通过鲍德温的讲述、作品和经历去探究美国种族关系的繁芜性、延续性、断裂性。

詹姆斯·鲍德温
我们还能镇静下来吗?
詹姆斯·鲍德温:这取决于很多成分。对我来说,一个非常严明的问题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是否对他们的黑人同胞的真实生活有足够的理解,从而理解他们为什么走上街头。我知道,就此刻而言,他们可能还不足理解,从他们对付公民骚乱(civil disorder)的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我或任何其他黑人都绝不吃惊地看到骚乱的根源是白人的种族主义。但显然,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许多其他人,都对此感到巨大的震荡。那么现在你问我,是否有可能镇静下来。我认为,总统没有将骚乱报告的内容如实奉告公众年夜众,是一个缺点。实际上,我认为他和全体政府应对这种巨大的摧残浪费蹂躏和毁坏负紧张任务。他和副总统有任务向美国公民阐明那份报告,以及美国公民接下来该当如何看待这份报告。可是现在!
我们乃至还没有开始考虑这份报告,已经太晚、太晚了。之以是会有爆发、骚乱、暴力抵抗——无论你如何称呼它,缘故原由是这种结束的状态带来的绝望,看着你的父亲、你的兄弟、你的叔叔、你的表亲——无论是多么年长还是多么年轻的黑人——没有未来,这种绝对的结束状态。夏天到来,父亲和儿子都走上了街头——他们在屋里呆不下去了。我出生在那些屋子里,我知道。这不是他们的错。
1968年4月,美国华盛顿,军队坚持秩序。美国民运领袖马丁·路德·金在演讲中遇刺,触发了全国范围的黑人暴乱。
从短期效应来看,联邦政府此刻该当做些什么来平息事态?
詹姆斯·鲍德温:联邦政府是什么意思?在所有黑人看来,联邦政府已经成为一个神话。当你说联邦政府时,你指的是华盛顿,那意味着你指的是很多人。你指的是伊斯特兰参议员和华盛顿的许多人,他们出于冷漠,无知或恐怖而根本不打算采纳任何行动。你说的是有权力的那些人,他们只想保住手中的权力。他们所能想到的只是夏天的拍浮池,以及一些大略地掩护和平和公共财产的被造出来的事情岗位。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理解问题的真正根源,真正的危险是什么。据我所知,他们没有做任何努力来向美国人阐明,走上街头的黑人们是想要保护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而想要有能力保护这些,他就必须得到自主权,有自己的学校,并且警察军队必须进行彻底的整改。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如果美国黑人要在这个国家成为一个自由的人,那么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必须放弃一些东西。如果他们不主动放弃,他们只会被动地失落去。
【詹姆斯·伊斯特兰 James Eastland,民主党密西西比州参议员,1943年当选参议员后任职直至1978年12月27日辞职。在民权运动时期,伊斯特兰被视为南方抵抗种族领悟的代表人物,他常日将黑人称为“劣等种族”。他被称为“白人南方的声音”和“密西西比政治教父”。】
你说现有的事情岗位只是一些被造出来的事情岗位。我们须要若何的就业操持?
詹姆斯·鲍德温:由于美国使得一些人成为多余人口,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你知道的,它不仅使得一些人无法就业,也使得一些人不愿意再在这个体制中事情。我认为,就业操持首先该当真正寻衅美国的各行各业,和美国的所有行业工会。举例来说,你现在在好莱坞。据我所知,在好莱坞的任何一个行业工会中都没有黑人:没有黑人场务,没有黑人事情职员,全体好莱坞没有黑人在那个级别或更高等别事情。还有一些著名的黑人,他们为这个体系事情,而这个体系则将黑人打消在工会之外。现在行业工会中没有任何黑人,这并不是什么上帝的旨意,这不是什么在山顶上被神意规定的东西;这是美国人故意为之的结果。他们不肯望行业工会由于黑人而分裂,由于他们害怕黑人在经济市场上与他们竞争。当然,他们就使得黑人的处境远比竞争者更糟。如果不愿意谈论这个体系和坚持这个体系的东西,你就无法谈论就业操持。伊士曼柯达(Eastman Kodak),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在这个国家真正拥有力量的所有人。他们须要作出决定来开放他们的工厂、他们的行业工会,让我们开始事情。
那他们就须要为这些人开拓一些在职培训的项目……
詹姆斯·鲍德温:是的,顺便说一句,我认识很多现在在街上的黑人,他们比许多手握大权制订北美南美政策的家伙要聪明得多。你知道,这个国家说在职培训课程的时候,他们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教给黑人职业技能,只管这是个中一部分。他们担心的是,当黑人进入工厂、进入工会,当黑人进入美国系统编制内的时候,他将会改变这些系统编制。由于在这个国家,没有黑人能以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标准而生活。因此,他们四处挑挑拣拣,选出来几个黑人,然后把他们整顿干净俊秀,送到什么地方的什么大学里去,然后希望他们将来能回到街上去让其他黑人镇静。他们做不到。在这个国家要生存下去,代价仍旧是成为一个白人。而越来越多的人谢绝成为白人。这便是在职培训的最根本的含义。它的意思是他们想让你顺应现状。此外,让我们实话实说吧,美国白人不肯望自己身边有任何有自主权的黑人男性。
在职培训操持中,美国白人的事情体系须要工人受过演习,每天定时早上八点三十分上班,一贯事情到下午五点。
詹姆斯·鲍德温:是的,我认识很多人都这样事情了很多年。我们不必经由培训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乃至不须要勉励他们这样做。
你是否认为,由于很多黑人没有发展前景,因此他们失落去了固定事情的意愿?
詹姆斯·鲍德温:我们正在说的便是这个。不过我认为,还有比这个更深的层次。不仅如此。在这个国家,年轻人,不仅是黑人年轻人,普遍抱有一种深深的疑惑,以为统统都不值得。你知道,如果你看看你父亲的生平,就像我看着我父亲的生平,而他在更年轻的时候看着他的父亲。他父亲每天从八点事情到五点,末了空空如也。他什么也保护不了。他什么都没有。他勤勤恳恳事情了一辈子,末了寿终正寝时,他仍旧空空如也,他的孩子也空空如也。但是,更糟糕的是,人们开始从这种现状中得出结论:在这个国家——以这个国家自身的表现为判断依据——黑人便是空空如也。另一方面,我们很随意马虎看到那些小有造诣的白人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也不是什么美好的图景。我的意思是,我在质疑这个国家所流传宣传的最根本的代价不雅观。
以是,你呼吁的是政府和工业界的想法上的彻底改变。
詹姆斯·鲍德温:是的。
而鉴于他们的惰性和……
詹姆斯·鲍德温:恐怖。
……和恐怖,和其他各类东西,这样的改变彷佛是……
詹姆斯·鲍德温:……彷佛是不可能的。
肯定会是非常缓慢的。一个行业工会不可能立即洞开大门,从黑人社群中加入几百名会员。那么我的问题是……
詹姆斯·鲍德温:你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以是“清洁工”这类事情岗位,没有用吗?
詹姆斯·鲍德温:不,我来见告你会发生什么。今年夏天会重复去年夏天和前年夏天。你投一些钱在黑人贫民区(ghetto),这些钱终极将落入各种投资家的手中。十几美元小钱本来就无法改变什么。有几个人可能能从中捞到一笔,其他人将会在原地不动。
但是这种项目能否赢得韶光;让我们有韶光去进行更长期的改变?
詹姆斯·鲍德温:如果你至心想要改变的话,是可以的。但问题是你们是否至心想要改变。这个国家的黑人已经创造你们至心想要毁灭我们。
但是如果工业界和政府负责准备事情培训项目,如果工会向黑人开放呢?
詹姆斯·鲍德温:这么说吧,这个国家的劳工运动一贯以来都正好是建立在黑人和白人劳工的分隔之上。这也不是上帝的旨意。劳工工会与老板们一起将黑人塑造为白人工人面临的威胁。白人工人从未面临过任何真正的威胁。白人与黑人从未有过任何真正的缔盟。这都被政府、工业、工会联手阻挡了。
如果一个工会想要表明它负责地想要改变这种不平等,它要做的第一步是什么?领导层该当做什么?
詹姆斯·鲍德温:教诲他们的成员。发布宣言。惩罚任何反对的工会成员。
工业界有什么短期内能做的事情?
詹姆斯·鲍德温:我不愿定这些问题是该当我来回答的。不过我可以尽我所能回答一下。工业界能做什么?你知道,就和工会一样。劳工工会对黑人的接管只限于某个层级,他们永久不会超越那一层。他们如果不被困在低层,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大概很多。工业大概会雇我建造一座城市或者开飞机,但是它永久不会视我为一位普通的工人。这个规律当然也有例外,随处都可以找到这些例外。但是目前的规律便是如此,而例外实际上只是证明了规律的存在。
如果工业参与一起建造低收入家庭住房,你以为会有帮助吗?
詹姆斯·鲍德温:不。我以为我们已经有了太多、太多的低收入住房变成了高层贫民窟。
那如果它们不是高层贫民窟呢?
詹姆斯·鲍德温:比如说,在纽约哈勒姆区(Harlem),我不肯望再有新的建筑项目了。我希望人们去打击房地家当的政治游说,由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办理黑人居住贫民区的问题。
那在工业迁出城外的场合排场下,在郊区工业区新建造低收入住房,怎么样呢?
詹姆斯·鲍德温:这取决于美国人怎么想,对吧?他们之以是搬出市区去郊野住,便是为了逃离我们黑人。
那么工业界有一些人操持建立一些工厂和商店,让黑人贫民区的居民来运营?这是个好办法吗?
詹姆斯·鲍德温:这些工厂要制造什么呢?
计件事情,大工厂分包出来的小部件。
詹姆斯·鲍德温:这个主张本身很故意义,但问题是如果你要实现这一点,你必须首先办理黑人居住贫民区的问题。从房屋本身的情形来讲,这些房屋实实在在是不适宜居住的。如果不是打算真正地解放哈勒姆区的话,没有人会真的去哈勒姆区建一座工厂的。
那么,比如说,纽约州正打算在哈勒姆区建一座政府办公楼。
詹姆斯·鲍德温:在哈勒姆区。我还知道他们打算建在哪里。我知道这样说可能会有点像阴谋论,但我也知道为什么要建在那里。他们打算建在黑公民族主义书店(Black Nationalist Bookstore)现在的地址,而这样做的缘故原由之一,我相信,是由于黑公民族主义书店是一个对他们非常危险的聚拢地——125街和第七大道。在非洲的话,这就相称于是一棵会面树(palaver tree)。这是黑人会面交谈的地方。所有的不满感情不一定从这里开始,但会在这里聚拢。
【会面树(Palaver Tree)是许多非洲社区的指定地点(最初是大树,例如猴面包树),该社区聚拢在一起以和平和培植性的办法谈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时,会面树也可能变成演出和讲故事的舞台。】
你不以为这个主张很屈曲吗?即便没有了这个书店,人们还是可以再挑一个地方会面交谈?
詹姆斯·鲍德温:是的,但是美国白人,一旦涉及到黑人问题,已经展示出了他们绝对的、没有底线的屈曲。
让我们来谈谈普通的公民吧,一位白人男性住在89街和河边大道(Riverside Drive)路口,他该当做什么?
詹姆斯·鲍德温:这要看他怎么想。如果他想要拯救自己的国家,他该当与自己的邻居和自己的孩子发言。并且,他不应该和我谈。
他该当给自己的邻居说什么呢?
詹姆斯·鲍德温:说如果在这个国家里我倒下了——我,黑人——他也会倒下。
有什么行动是他可以参与的吗?对地方政府施压?
詹姆斯·鲍德温:对他的房东施压,对地方政府施压,对他能施压的任何地方施压。必须要向房地产商政策游说的力量施压。对教诲系统施压。让他们变动教科书,让他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能学习到我们共同的历史的原形。教诲系统现在完备由盈利的动机而运转,而没有别的准则。
那些自己从城市中逃离到郊区,而将黑人困在城市中央的白人呢?他现在该当做什么?
詹姆斯·鲍德温:如果他想拯救自己的城市,大概他该当考虑搬回去。那也是他的城市。或者只是问问自己为什么离开。我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他有一点钱,有某种想象中的未来,有一两辆车,你知道的,干净体面的孩子,干净体面的妻子,他想要保护所有这些。但他不明白,在考试测验保护它的过程中,他将毁灭这统统。
针对穷苦的项目呢?那会有帮助吗?
詹姆斯·鲍德温:你开玩笑吗?这个国家还从未真正面对过穷苦问题。我这辈子都没有见到过。消灭穷苦是一个玩笑。
你会如何改进它呢?
詹姆斯·鲍德温:先真正开始再说。
如何开始?
詹姆斯·鲍德温:是这样的,唯一的办理办法只有去打击某些人的权力。若非如此,则不可能做到。举例来说,钢铁公司的权力,既可以造诣一个城市,也可以毁灭一个城市。它们这样做过,它们现在也还在这样做。大家都知道。除非你乐意针对那些人并限定他们的利润,否则你就无法消灭穷苦。
只是限定工业的利润就够了吗?还是也须要限定政客的权力?
詹姆斯·鲍德温:但是政客们并没有为公民做事;他们做事于我刚说我们必须打击的人。这便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的现状。这便是为什么现在的政治机制如此弘大、如此繁芜,彷佛没有人能够掌握它。它完备不相应美国人社群的需求,完备不相应。我不仅在说黑人,我的意思是知足全体美国人的需求。
你的意思是说,它只回应工业的需求?
詹姆斯·鲍德温:它只回应它自以为是自己赖以生存的东西。
你以为我们该当做什么来改进警察与黑人社群的关系?
詹姆斯·鲍德温:你必须教诲他们。我并不是和警察有什么辩论。我能看出来他们的处境不佳。他们无可救药地无知并且非常害怕。他们就像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一样,相信自己在电视上看到的统统。他们受到所有人的尊重,这意味着他们是周六晚上的犯人(Sunday night sinners)。这样的警察是这个国家应得的,绝不料外,如果警察在他以为陌生的地方看到一个黑人,他当然会拦下他——而你知道,这个黑人当然会愤怒。然后可能有人会去世。但这是在这个国家培养出来的无知的结果之一。哈勒姆区街上的那些人,那些白人警察;他们都吓坏了,他们该当感到害怕。但年轻黑人男性便是这样去世去的,由于警察感到害怕。这不是警察的错;这是国家的错。
【俚语:Saturday night sinners, Sunday morning saints,周六夜晚罪过,周日清晨贤人,周日早上是基督教进见礼拜后悔罪过的时候,因此是道德上虚伪的人】
在最近的一次公民骚乱中,与去年夏天警察和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大肆射击比较,警察彷佛采纳了更为宽容的态度,而且更少开枪来制止抢劫者。
詹姆斯·鲍德温:不好意思,这个事情还没结束,而且,我不相信我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我反对用“抢劫者”这个词,由于我想知道是谁在抢劫谁。
那对付一个砸烂电视机商店的窗户,想要什么就拿什么的人,你会用什么词?
詹姆斯·鲍德温: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对付那个让一个黑人走到本日这一步的人,那个从黑人成长事情的贫民区拿走全部的钱的人,你对这样的人会用什么词呢?谁在抢劫谁?抢电视机吗?他不是真的想要一台电视机。他是在表达:去你的吧。这是对付电视机代价的判断。他不是要一台电视机。他是想让你知道他的存在。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大众媒体——电视台以及所有紧张新闻社——都在不断利用“抢劫者”这个词。在电视上,你总是看到一个黑人伸手进一个商店之类的图像。因此,美国"大众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野蛮人正在试图从我们身上抢劫统统,而没有人负责地试图找到问题所在。毕竟,你责怪的是一群被困的人,他们早已被剥夺了统统,现在责怪他们抢劫,我以为这令人恶心。
那对付偷袭手、爆炸分子、和抢劫者,你会把他们差异来看吗?
詹姆斯·鲍德温:我总是听人说抗议者里面有偷袭手,可是你看一下去世亡数字。
诚然,白人去世亡数字非常少。但是也还是有。
詹姆斯·鲍德温:我知道骚乱中去世的是谁。
虽然这么说,也还是有几个白人去世了。
詹姆斯·鲍德温:几个,没错,可是你知道多少黑人去世了吗?
多很多。但这便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谈论如何镇静下来。
詹姆斯·鲍德温:该当镇静一点的不是黑人,由于他们不会镇静下来的。
可是他们不是受伤最多的吗?
詹姆斯·鲍德温:这要取决于你怎么看了。我不愿定我们是不是受伤最多的。或者实话说,我可以确定地说,我们不是。我们是去世得最快的。
但是,我提出的问题是,偷袭手是否可以算是真正的革命者?爆炸分子是否是由于极大的挫败感,以是试图摧毁那些他们的不满的象征物?抢劫者,只是蠢蠢欲动的物质希望的受害者?
詹姆斯·鲍德温:我不得不问你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你究竟如何可能开始对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社群的人进行分类?我完备不同意你的分类。那些人之以是会上街,是出于一样的缘故原由。
我们的问题是否部分在于我们在炫耀所谓的美好生活,拍浮池、汽车、郊区生活等等,而我们在一群被社会剥夺了这些东西的人群面前炫富?
詹姆斯·鲍德温:没有人谈论过一个女人或男人在市中央事情后回到郊区的家里是什么觉得。这太明显了,切实其实不需我细说下去。我们的国家里面还有一个国家,一个被困的国家。是的,你们确实在炫耀。你评论辩论我们,彷佛我们不存在一样。真正的痛楚和真正的危险是白人一贯都在以这种办法对待黑人。你们一贯都这样对待桑波(Sambo,对付黑人或者黑人与北美原住民混血儿的蔑称)。我们一贯是你们的桑波——–你知道我们没有感情、没有耳朵、没有眼睛。我们骗了你们撒谎一百多年了,你们乃至还不知道。我们骗你们是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我们已经开始鄙视你们。我们不恨你们。我们已经开始鄙视你们。这是由于我们没有能力去关心我们的处境,而你们也不关心我们的处境。你们乃至都不关心自己的孩子会若何。由于我们也必须与你们的孩子打交道。我们不在乎你们会若何。你们自己决定。生存或去世亡,由于这些年来你们自己一贯在作出这样的生活办法的选择。
那一些黑人机构所扮演的角色呢?就社会进步的可能性而言,教会在黑人社群中仍旧故意义吗?
詹姆斯·鲍德温:你必须考虑到,我们有黑人教会这本身便是对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控诉。本来不应该有黑人教会的。但是有了。我们已经利用了教会。你知道,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对付教会的利用最出色。那是他的平台。教会一贯是我们唯一的平台。但正如马丁·路德·金本人创造的那样,北方哪里都找不到黑人教会了,它只存在于南方,由于南方的黑人社群和北方是完备不同的。南方还有黑人大家庭,至少曾经还有。北部基本上没有黑人大家庭,一旦没有大家庭,便没有教会。这意味着没有了平台。在芝加哥和底特律,都没有黑人教会可以利用。只有在亚特兰大和蒙哥马利那些地方才可以。而现在,由于马丁·路德·金去世了——以前并没有这样,但在他去世后就很明显了——这个平台不再有用,由于人们谢绝了全体基督教会。
马丁·路德·金
他们也谢绝了基督教本身吗?
詹姆斯·鲍德温:不像你们那么激烈地谢绝。
以是北方的黑人教会已经去世亡了吗?
詹姆斯·鲍德温:让我换个说法。它不再吸引年轻人了。任何组织一旦不再吸引年轻人,它的社会功用就至少可以质疑。这么说还是说轻了。
那么,亚当·克莱顿·鲍威尔(Adam Clayton Powell)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小亚当·克莱顿·鲍威尔(1908年11月29日至1972年4月4日)是浸信会牧师和美国政治家,从1945年至1971年任代表纽约市哈勒姆区的众议员。他是第一个代表纽约当选为国会议员的非裔美国人。鲍威尔留任近三十年,担当民权和社会问题的国家发言人。他还敦促美国总统支持非洲和亚洲的反殖民斗争后独立的新国家。在本采访进行的1968年,鲍威尔因挪用公款和其他个人行为而被指控,国会为此举行了听证会。】
詹姆斯·鲍德温:人们不把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视为牧师,他被视为政治家。实际上,他被认为是其余一个受害者。无法忍受亚当的人现在绝对、绝对不会攻击他。亚当被指控的罪过——先要说的是,哈勒姆区的人比其他所有人都更理解他的罪过。这是一回事。另一方面来说,只要你不弹劾伊斯特兰参议员,统统都是虚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为他而战,而是为我们自己而战。
那么,黑人社区中一些其他领袖呢?
詹姆斯·鲍德温:目前,黑人领袖中有那些真正的领袖,你从没听说过而已。罗伊不是领袖,惠特尼也不是领袖。
【罗伊·威尔金斯(Roy Ottoway Wilkins),民权运动中主要的社会活动家,从1930年代生动至1970年代,从1955年至1977年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中主要职位。】
【惠特尼·杨(Whitney Moore Young Jr. , July 31, 1921 – March 11, 1971),民权运动领袖之一。 他致力于打击就业歧视,并将美国城市同盟(National Urban League)从被动跟随民权运动转变为主动争取黑人在教诲、就业、住房、康健和福利等方面机会平等的法律权利的组织。】
佛罗伊德·麦克西克呢?
詹姆斯·鲍德温:佛罗伊德也不是领袖,但他更贴近时期的节奏和脉搏。首先,领袖是相称罕见的。本国的大众媒体不能打造出一位领袖。如果一个人是领袖,那么就算他面对各种反对,乃至包括来自黑人的反对,他还是一位领袖。领袖之以是成为领袖,是由于他便是他,是由于他热爱他的公民,他热爱这个国家。
【佛罗伊德·麦克西克(Floyd Bixler McKissick,March 9, 1922 – April 28, 1991),美国状师、民权运动活动家。1966年,他成为种族平等大会(CORE, the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的领导者,并将其变得更为激进。】
斯多克力·卡迈克尔?
詹姆斯·鲍德温:在我看来,斯多克力或许太年轻了点。你看,我比斯多克力差不多年长二十岁。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对许多人而言,斯多克力是一位领袖。他的意义乃至要超越了领袖,对许多人而言,他是一个象征。许多感到自己被精神阉割的年轻黑人男性追随斯多克力,那是由于他与权力阉割作斗争。我理解他们,他们是对的。我可能时时时会与斯多克力产生不合,但我是站在他这边的。他所说的实质上便是真的,这也是为何人们会因斯多克力而感到紧张,由于他们无法否认他的说法。对美国白人而言,他所作所为令他们切齿腐心,由于据他所说,我们在这里毫无希望。这些白人永久也不会做些有用的事,由于他们办不到。而且,既然我们现在在谈论斯多克力的问题,我想指出一件事。斯多克力从来没说过他仇恨白人。我恰好认识他,我知道他并不恨白人。他所坚持的是黑人自主权,而这种坚持另所有人如临大敌。他所流传宣传的便是这个。他认为,这个国家的黑人与全天下所有被奴役的人都紧密相连,这一点吓到了美国的白人。
【库瓦美·图雷(Kwame Ture,原名斯多克力·卡迈克尔(Stokely Standiford Churchill Carmichael, June 29, 1941 – November 15, 1998)是特立尼达人,美国民权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也是环球泛非运动的活动家。他建立了黑人权力运动( Black Power movement),后来成为黑豹党的“名誉总理”(Black Panther Party ),再后来成为全非洲公民革命党( All-Afric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A-APRP))的领导者。】
斯多克力·卡迈克尔
而且,他很清楚地说过,他说的也都是真的,这个国家源于革命,但现在已经在世界各地,耗费了无数亿美元和成千上万的生命,用来反对革命。他说的是,这个国家的黑人不应该再指望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我看来,往好里说,约翰逊总统就一个非常不值得信赖的大老爹(这么说还算给他面子了,这是我的意见)。但对其他黑人来说,和那些受着和我们所受的一样的压迫的人,压迫我们的体系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领导的。 若不是这里有如此多黑人,那么,美国决定去“解放”南非便是一件完备可以想象的事了。难道不是吗?美国试图驱逐共产主义的各类恶行,南非所有的自由战士会把南非变成另一个越南。你自己在越南干了什么,谁都骗不了。至少黑人不会上你确当。你流传宣传不是为了西方天下所谓的自我的物质利益而战。而物质利益就意味着我的苦工。我的锡、钻石、糖都被你偷走。这便是你的目的;这意味着我该当用永久为你打工。
我才不会。
天下上的人们被迢遥的间隔阻隔,也被如此多的其他事物阻隔,但人们还是该当开始思考我们的共同之处——这便是斯多克力想表达的想法。斯多克力想说的是我们的共同点,我们的共同点便是要把背上的人甩下来。对美国人而言,这个想法很危险、很骇人,由于它确实是真的。
你以为有一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理解吗?
詹姆斯·鲍德温:美国人不是帝国主义者。在他们眼中,他们便是年夜大好人。他们不过便是普通人。
不过我们指的是一种帝国主义……
詹姆斯·鲍德温:我们说的是帝国主义的终极形式,你知道的——西方帝国主义——这个天下会见识到的。
不过,对付黑人中的下层阶级,他们缺少足够的教诲,你以为他们理解你所描述的这种帝国主义的特点吗?
詹姆斯·鲍德温:我们比你以为的要理解多了,我们也从越南的来信中理解这些事情。
有任何白人可以……?
詹姆斯·鲍德温:哦对了,白色不是一种颜色——这是一种态度。你以为自己有多白,你就有多白。这是你的选择。
那么,玄色也是一种心态吗?
詹姆斯·鲍德温:不是,玄色是一种人的处境。
白人社区中谁能和黑人社区对话,并且被接管呢?
詹姆斯·鲍德温:谁都可以,只要他不以为自己是个白人。
在总统候选人中,你以为谁是出于美意,谁能被接管呢?理查德·尼克松?
詹姆斯·鲍德温:你肯定在开玩笑吧。
尼尔森·洛克菲勒?
詹姆斯·鲍德温:有可能,这取决于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我不会说他的不是。
罗伯特·肯尼迪呢?
詹姆斯·鲍德温:确实,罗伯特·肯尼迪呢!
鲍比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关于鲍比·肯尼迪最棒的评论是艾尔·卡洛维说的——我不是回避话题。Esquire刚刊登过卡洛维关于灵魂乐(Soul,1950年代发源自美国的一种结合了节奏蓝调和福音音乐的音乐流派)的相称奇特的谈论。艾尔说,如果我们可以研究并学习灵魂乐,他(鲍比)一定能够学会。他确实会学习也能学会,但灵魂乐无法被研究或学会。我只在一个相称公开的场合与鲍比有过打仗,以是我说的统统都是预测。他非常聪明,所有自由派人士都会加入他的行列。他有可能会成为总统。他险些就会成为总统。我能说什么呢?任天由命吧。我自己是不会加入那个行列的。我认为他非常精明,但我以为他很酷。好吧,我以为他可能非常危险。
【艾尔·卡洛维(Al Calloway),非裔美国文化杂志The Probe的出版者。】
【指1963年5月24日的鲍德温-肯尼迪会面,是一次旨在改进美国种族关系的考试测验。时任总审查长罗伯特·肯尼迪约请詹姆斯·鲍德温和一大批文化领袖,一起在纽约市肯尼迪的公寓里开会。会议不欢而散,没有达成共识。黑人代表团普遍认为,肯尼迪对美国的种族主义并不理解。终极,会议显示了种族场合排场的紧迫性,是肯尼迪对民权运动态度的积极迁移转变点。】
他很吸引人。他说的话都是恰到好处的,你知道吧,但并不是都在对的时候。我能看到他的那种魅力;毕竟,他是约翰·肯尼迪的弟弟。但是,我有其它的态度。我必须要尽我所能, 保持头脑复苏,不只只看到当下的事宜或人物。我不能把自己的性命请托给鲍比这个人。
你理解尤金·麦卡锡吗?
詹姆斯·鲍德温:不理解。我没法谈论他。不过我得说,对任何政客,我已经良久良久没有任何尊敬之情了。我也不得不提一下,这是我在过去四十三年,看遍了这个国家政治光谱得出的结论。我还想说的是,如果我支持某个人,不管那意味着什么,我不想见告黑人他们该当给谁投票,由于我不想那些黑人创造他们被背叛时,反过分来宰了我。
休伯特·汉弗莱呢?
詹姆斯·鲍德温:别提了。
你能阐明一下吗?
詹姆斯·鲍德温:不,还是别提了。只要看看他当副总统之后的作为就行了……这个武断的自由派。
你以为除了单单反对系统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角度去理解这些骚乱呢?从故意识或无意识的角度来看,它们还有可能是用流血的办法来净化我们的文化吗?
詹姆斯·鲍德温:好吧,我以为这个得提到托马斯·杰佛逊了,他说过:“每当我想到上帝是公道的,我都会为我的国家抖动。”
他也说过自由之树由血液灌溉而成吧……
詹姆斯·鲍德温:[由]暴君的血液[灌溉而成]。我们把它叫作暴动,是由于他们是黑人。如果他们是白人,我们就不会把这些叫作暴动了。
马丁·路德·金之去世代表了什么?
詹姆斯·鲍德温:[这代表了]这个国家现在徘徊的深渊边缘。这是一个非常繁芜的问题,答案也必须是非常繁芜的。这对黑人贫民窟意味着什么,对这个国家的黑人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杀去世了试图拯救你的马丁,而你将面对来自黑人的巨大反对力量,由于你选择了利用暴力。如果你可以射杀马丁,那你就可以射杀我们所有人。你的历史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你不会这样做,或者说,历史中没有任何阻挡你这样做的事情。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那将是败局已定的前兆,而你唯一的安慰只是知道败局已定。你会看到,由于没有人会再相信你所说的任何一句话,我不会再相信,这个国家也没有多少黑人能够再相信那些话了。我完备不相信这个国家的公民的道德。我不认为你做的事情是你认为是对的事情。我认为你可能会被迫这样做,由于这将是权宜之计。这个情由就足够了。
我认为,马丁·路德·金的去世对华盛顿的那些人来说都没有太大意义。我认为,他们根本不理解发生了什么。像州长华莱士和马多克斯师长西席这样的人当然不会理解。我会非常疑惑里根是否真的理解。当然,这便是问题所在,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机构有关。但是,对这个国家的黑人来说,这意味着你宣战了。你已经宣战了。[这意味着]你确实打算屠杀我们,你打算把我们关进集中营。毕竟,马丁的暗杀——无论是由一个人还是由一名国家骑兵完成的(后者是有可能的);抑或者这是个阴谋,这也是可能的。毕竟我也是一个相称有名的人,一个人也不会随便四处走动——政府对马丁的一举一动都了若指掌——就这次暗杀而言,我认为美国公民及其所有代表都有罪。
【莱斯特·加菲尔德·马多克斯(Lester Garfield Maddox Sr.)(1915年9月30日至2003年6月25日)是一位美国政客,从1967年至1971年担当美国佐治亚州第75任州长。 他曾于亚特兰大运营一家餐馆,谢绝为黑人顾客供应做事,违反了1964年的《民权法》,而作为武断的种族隔离制度推戴者而成名。后来他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担当州长期间担当副州长。】
对我来说,先是梅德加,接着是马尔科姆·X,然后便是马丁。这些故事都一样。在梅德加去世后,他们在密西西比州逮捕了某个疯子。但是,我和梅德加一起,都在密西西比州,你不须要密西西比的一个疯子去杀去世梅德加·艾佛斯。不管拜伦·德·拉·贝克维那人,他就从养老院的后门溜了出来,然后人们再也没听说过他了。我乃至不会谈论马尔科姆经历了什么,也不想说他的去世都有什么后果。现在马丁去世了。你知道,每一次,包括总统被行刺时,每个人都坚持认为,那是一个独狼式疯子的所作所为。没有人能承认这种猖獗是故意造成。现在,斯多克力立时要被枪决了。无论谁拉动扳机,都不是那个买子弹的人。鞭策暴动的是公民和他们的代表,不是斯多克力,不是马丁,不是马尔科姆,不是梅德加。然后,你将如此这般连续下去,直到创造自己无法转头,事实上,你可能已经在那儿了。因此,如果马丁的去世唤起了一个国家的良心,那么那将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道德胜利,但这种情形很有可能不会实现。
【梅德加·威利·埃弗斯(Medgar Wiley Evers)(1925年7月2日至1963年6月12日)是密西西比州的美国民权活动家,国家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实务秘书,以及曾在美国陆军服役的第二次天下大战退伍军人。他致力于推翻密西西频年夜学的种族隔离,结束公共举动步伐的隔离,并为非裔美国人扩大机会,包括投票权。埃弗斯在1963年被密西西比州杰克逊(Jackson)的白人公民委员会成员拜伦·德拉贝克威(Byron De La Beckwith)暗杀。】
某些人说,白人美国人立即将马丁·路德·金树立为贤人典范,是一种糟糕的躲避……
詹姆斯·鲍德温:这是他们罪过的证据,也是他们脱罪的证据。他们不知道的是,每杀去世一个马丁,就会有十个马丁涌现。你已经开始怀念马尔科姆了,希望他还在人间。由于马尔科姆是唯一一个能帮助黑人贫民区孩子的人。他是唯一一个。
我刚刚想说,我们这些白人……
詹姆斯·鲍德温:……希望马尔科姆还在人间?不过,你们这些白人,不管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你们还是创造了迫使他去世亡的环境。
我们创造了一种政治暗杀能够被接管的环境……
詹姆斯·鲍德温:……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去世亡,包括梅德加和马丁的去世亡。或许,这也会使得其它去世亡不可避免,包括我的去世亡。而这所有统统都因此自由的名义。
你认为“平息事态”意味着接管一种文化中的文化吗,意味着接管黑人文化的独立存在吗?
詹姆斯·鲍德温:你是说白人平息事态?
是的。
詹姆斯·鲍德温:当白人说平息事态,这背后的意思很大略。黑人的力量让他们感到害怕。白人的力量不会让他们害怕。斯多克力不是要把一个国家炸掉,使它不复存在。他也不是要威吓你们的孩子。白人的力量正在做那些事。白人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历史和现实情形,但他们不会承认的。除非奇迹发生,不然他们不会承认的。纯挚的美意也是没用的。一个人必须面对现实,那便是我们在做天下警察——我们这些美国人,由于某些显而易见的缘故原由,正在做着天下警察。当你们说着自由天下的时候,我们就像南非那些黑人矿工,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到底在保护谁。
是否有一些行之有效的黑人机构……
詹姆斯·鲍德温:为什么一个白人国家要指望黑人机构去救国?
好吧,为了开始一段对话,为了找到下一步……
詹姆斯·鲍德温:这就取决于你们了。
但是,难道美国的白人不须要来自某些[地方]的辅导吗?
詹姆斯·鲍德温:……[来自]任何黑人贫民区街头[的辅导吧]。
但是,在任何黑人贫民区的街头,你能学到[什么]……
詹姆斯·鲍德温:问问任何一个黑人瘾君子,到底是什么让他变成了一个瘾君子。
不过,我想问我们能与什么项目互助呢?
詹姆斯·鲍德温:你说的便是一种能够帮助你减轻包袱,但又不让你丢失任何东西的项目。
好吧,如果我们乐意费钱……
詹姆斯·鲍德温:我不是谈钱的问题。
但如果我们能互换各自的见地……
詹姆斯·鲍德温:好吧,首先,你必须和你自己的思想互换,和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互换。这也是你的国家。自从1957年我回到美国之后,我读了很多关于好白人的故事。但也正是这个国家中的这些年夜大好人逼着黑人们走上了街头。
约翰·林赛市长走上了街头,你以为这样的例子管用吗?
詹姆斯·鲍德温:我喜好约翰·林赛。或许,便是由于他走上了街头。或者,我也由于同样的缘故原由喜好约翰·肯尼迪,你知道吧,虽然我也有所保留。他至少比较跟得上时期。
【约翰·林赛 John Vliet Lindsay(921年11月24日至2000年12月19日)是美国政治家、状师和电视主持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林赛曾任是美国国会议员、纽约市市长、美国总统候选人。他还是《早安美国》的常任高朋主持人。】
我们该当有一个若何的总统?黑人总统会改进现状吗?
詹姆斯·鲍德温:首先,你须要一个人乐意冲破所谓的两党制。在华盛顿进军的那天,约翰·刘易斯是对的,当时,他说我们不能加入共和党——看看那是谁组成的。我们也不能加入民主党——看看谁参加了民主党。我们的党派在哪里?我们须要的是一个可以凝聚这个国家力量的人,既有黑人的力量又有白人的力量,我们须要有一个能够知足公民需求的政党。民主党做不到。只要伊斯兰特参议员在党内,就弗成。我对他指名道姓,但这只是浩瀚名字中的一个。只要尼克松还在共和党里,我就绝不会投票给共和党。我再次指出,你须要一个相信这个国家的人去开始改变它。既然我们还在谈论这个话题,顺便说一句,我们该当停滞保护所有得克萨斯州石油大亨,这些财主是任何文明见过的最大威胁之一。他们完备没有头脑,但是有数不尽的钱,还有无穷的力量,不可思议的力量。当这种无知的人节制了权力,没有什么比这种力量更危险的了。而且,这是在联邦政府的赞许下完成的。
【约翰·罗伯特·刘易斯(John Robert Lewis)(生于1940年2月21日)是美国政治家和民权领袖。他是民主党员,是佐治亚州的国会代表,自1987年以来一贯担当众议院议员。作为当时的学生非暴力折衷委员会(SNCC)的主席,刘易斯是组织1963年“华盛顿进军”的“六大”领导人之一,在民权运动及废除种族隔离的行动中发挥了许多关键浸染。“为事情和自由向华盛顿进军”,发生于1963年8月28日,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人权政治集会,目的在于争取非裔美国人的民权和经济权利。集会中,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揭橥了旨在推动族际和谐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黑人有任何天然盟友吗?
詹姆斯·鲍德温:我们都被同一帮人踩在脚底下。这个我之前就见告你了。我们都被踩在同一个脚底下。这便是为什么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到哈勒姆区的时候,每个人都惊呆了。他们以为黑鬼便是傻蛋,正如朗斯顿·休斯所说。[黑人被认为是]傻瓜中的二等公民。
【詹姆斯·默瑟·朗斯顿·休斯(James Mercer Langston Hughes,1901年2月1日 – 1967年5月22日)是美国墨客、社会活动家、小说家、剧作家和专栏作家。休斯是当时称为爵士诗歌的文学艺术形式的最早创新者之一,是哈勒姆区文艺复兴的著名领袖。】
你以为美国黑人在美利坚合众国之外有其他被压迫的天然盟友吗?
詹姆斯·鲍德温:有的,从古巴……到安哥拉。不要以为美国政府对此一无所知。这个满心要解放我们确当局,打定主意要让我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对话。
在《下一次将是烈火》中,你问道黑人是否想要融入一个正在燃烧的屋子。你提到,跟白人比较,他们没有那些相同的物质目标,你现在还是那么以为吗?
詹姆斯·鲍德温:我认为,斯多克力是对的,他说过,领悟便是最新一种用来替代白人至上主义的委婉说法。不,我不想要融入这个屋子,也不想融入任何其他人的屋子,尤其不想融入这个正在燃烧的屋子。我不想变成……像你们一样。你们,白人。我宁肯去世,也不要变成这个国家大多数白人那样。我们追求的是其余的东西,那也正是马丁和这个[黑人]群体追求的。你知道,我只想让你别打扰我。别打扰我就行!
然后,我们就会自己管好自己的。而且最主要的是,离我的孩子远点。
你以为是否有必要让本地社区来管理学校?
詹姆斯·鲍德温:学校和警察。
为什么是警察?
詹姆斯·鲍德温:看,这么说吧,我们住在[纽约的]哈勒姆区,或者住在[洛杉矶的]瓦特区。警察戴着警帽,枪套里装着枪,到了我们这里。他不知道我这一天怎么过的,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喝醉。他对我一无所知。他实在怕我怕得要去世。那么,他他妈的在这儿能干嘛?他能做的只有朝我开枪。他便是一个拿着薪水管集中营的人。我们能比你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社区,管得好得多。由于你们管不好。你们生来不是干这个的。如果这里民气乱如麻,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心烦。有些人,一些警察、领导人、市长之类的人,让黑人们滚回家,他们的反应是精确的:他们说:你给我滚回家——亲爱的,这里便是我们的家。我们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这便是我们试图去传达的信息;我们不须要你们来照顾我们。拜托,我们再也承担不了你们的照顾了!
看看你们都干了什么,看看对我们[干了什么]。说是照顾我们,看看你们都对自己干了什么。不,我认为这个国家的黑人该当管理自己的学校和警察。由于你们做不到。你们能做的便是上坦克和催泪弹——如果事态太过紧张,那就出动国民警卫队。你们还以为自己可以一边打内战,一边在世界各地打仗。
纽约市曾经有过一个规定,警察不能住在自己所管的辖区。但你说的是该当让他住在这个地方。
詹姆斯·鲍德温:是的,我便是这么说的。
你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什么希望吗?
詹姆斯·鲍德温:我有很大的决心。我充满希望。 我认为最有希望的事情便是正视当下的情形。 人们责怪我是个末日贩子。 我不是一个末日贩子。 如果不正视当下情形,你就无法改变它。 你必须正视它。 在某些时候,情形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 如果我们不正视,我们就无法[改变它]。 如果我们不改变它,我们只能去去世。 我们都要灭亡,每一个人都会去世。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是一张巨额账单,要付出艰巨的代价。 但是,我们已经积累了很永劫光了。 现在,账单来了,你和你的子孙要买单了,全天下的人也要你们买单。当你们的总统代表你们,跟我担保,说不会再容忍任何暴力,你可能以为那会吓到我。人们不会被吓到,当他们听到这些话,他们会生气。而且,你怕去世,可我不怕。
以是,要平息事态,有一个成分是很确定的,那便是国民警卫队……
詹姆斯·鲍德温:我不是那个须要被平息的人。
但可以说国民警卫队、警察、催泪弹这些方法并不能办理问题。
詹姆斯·鲍德温:我建议,每个城市的市长和这个国家的总统都换个策略,上电视去向白人讲话。见告他们,他们须要镇静。
在最近一些骚动中,有些黑人领袖让其他黑人不要上街,为什么?
詹姆斯·鲍德温:为了不让他们丧命街头。这不是在帮你们。除了美国公民以外,没人希望这一代人去送死。
那么,你以为我们须要对很多事情卖力吗?
詹姆斯·鲍德温:我不是要指控你们,你知道的。那不是重点。但你们要正视许许多多事情。我不会倾慕任何生活在这个世纪的白人,我可不想面对你们所面对的。如果你们不面对这件事,那对你们而言,便是死活攸关的事了。如果有人以为这是桑波的性命问题,那这些人都被骗了。这不是桑波的死活问题,也不可能是他们的问题,由于他们已经被屠杀太久了。这是你们的死活决议。你可能以为,我的去世亡、缩小或消逝能拯救你们,但不会的。这不会拯救你们。现在唯一能够救你的,只有你自己正视自己的历史……那不是你的过去,而是你确当下。没人在乎过去发生了什么,他们也在乎不起。但是,你们的历史将你带到了这一刻,你们只能通过以历史的名义,以神的名义,以措辞的名义看自己的所作所为,开始改变自己。现在的问题彷佛是我比你要看得更清楚,虽然我一贯在你们的历史之外,而且与其说是受害者,不如说是打消在你们的历史之外。这是由于我不能让你愚弄我。如果我让你骗我,那我就会去世。不过,我已经骗了你良久了。这便是为什么你们一贯问,黑人想要什么?这是你自己错觉的总和,所有自我欺骗的汇总。你们很清楚我到底要什么!
以是,当我们向你提出这个问题:如何平息事态?我们在问的实在是同一个老问题:黑人想要什么?
詹姆斯·鲍德温:是的。你在叫我帮忙拯救它。
拯救我们自己?
詹姆斯·鲍德温:是的。但是你们得自己来。
严格来说,从你的角度看,你会和一个准备摧毁一个城镇的愤怒的黑人去对话吗?
詹姆斯·鲍德温:我只认识愤怒的黑人。你的意思是,我怎么跟一个比我小二十岁的人对话?
对。
詹姆斯·鲍德温:那会很难。我试过了,也正在考试测验,实在一贯都在考试测验。真的,我所能做的便是见告他,我和你在一起,不管那是什么意思。让我来见告你,我不能见告他什么。我不能见告他,让他屈从,让他自己被屠杀。我不能见告他,他不应该武装自己,由于白人们都全副武装。我不能见告他,他不应该让任何人去强奸他的姊妹、妻子或母亲。由于那便是问题所在。我还会试着见告他,如果你打算宰了警察——由于这事可能会发生——试着不要去恨警察,这是为了你自己的灵魂能够得到拯救,而不是为了其他任何缘故原由。但是,让我们试着变得更好,让我们试着——不管我们须要付出什么代价——变得比他们更好。我们不须要去仇恨他们,只管我们必须得到自由。仇恨他们便是摧残浪费蹂躏韶光。
(访谈原载于《时尚师长西席》(Esquire Magazine)1968年7月刊,于2017年8月2日在该杂志重刊。)
(译者先容:王菁,社会文化人类学,上海纽约大学“环球视野下的社会”博后;马景超,女性主义哲学,维拉诺瓦大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