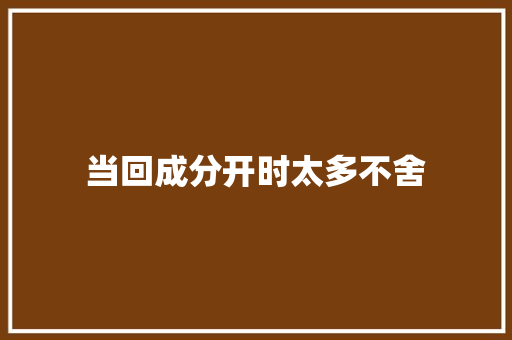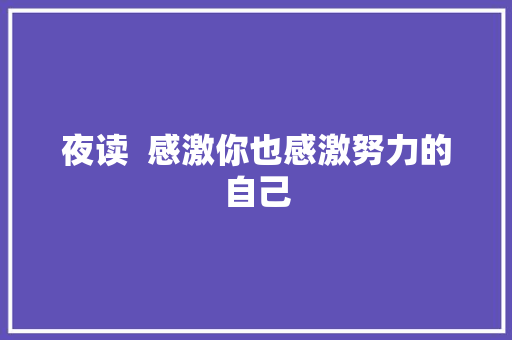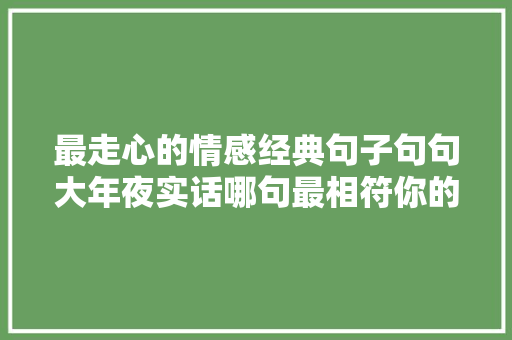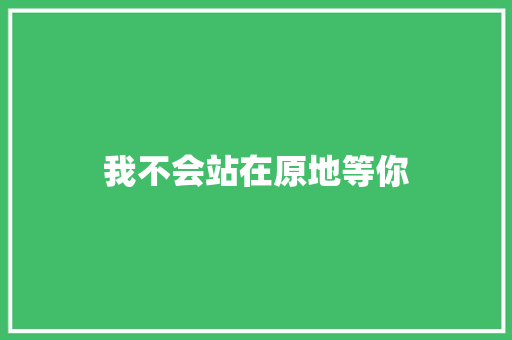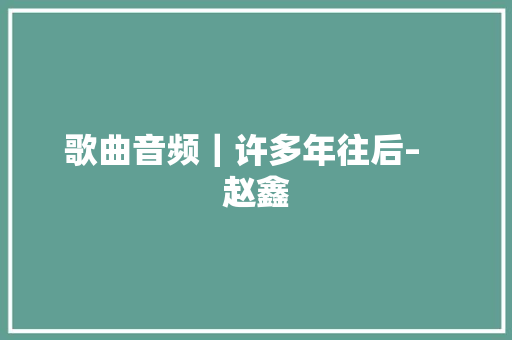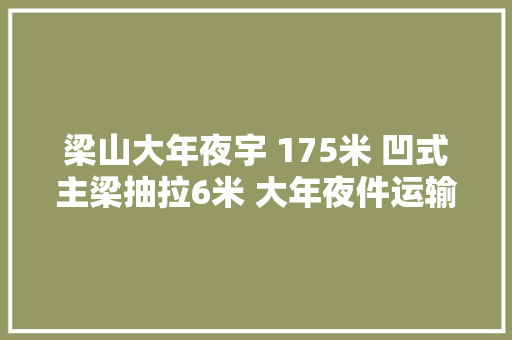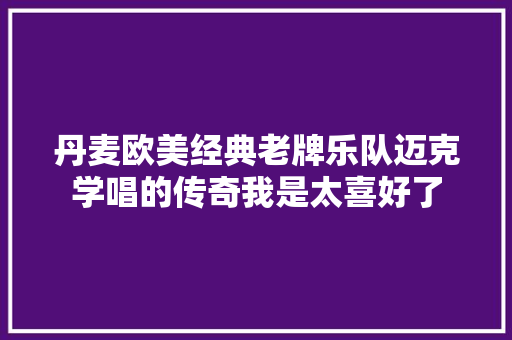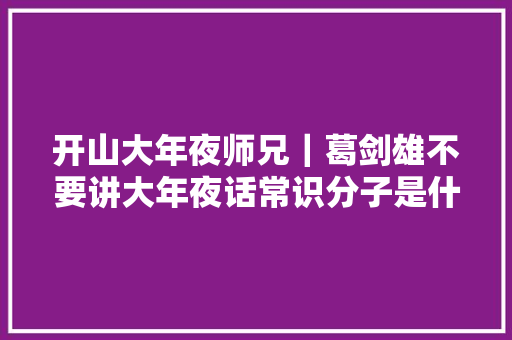我在兵部大院的单身光阴
作者:铁道兵战友网 危文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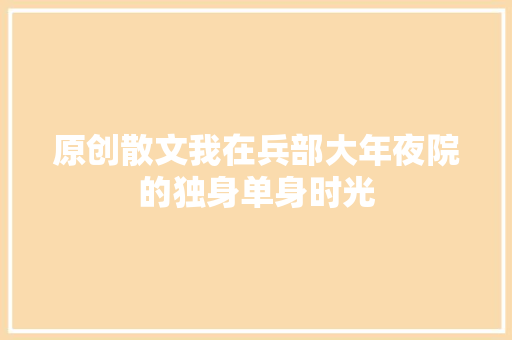
光阴苒任,岁月悠悠。从我转业离开兵部大院至今虽快四十年了,但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情一景至今仍影象犹新,尤其是那段快乐而温馨的单身光阴,更是回味无穷。
1977年秋,我从天山深处的铁道兵第二指挥部调到《铁道兵》报社,走进了神往已久的兵部机关大院。当时,正值报社新老交替,陆续从基层部队调进了十来个年轻的编辑,个中大多是虽已结婚但家属仍在外地的准单身,也有像我这样名副实在的未婚单身汉。刚开始,我们大都被安排在大院最南真个单身筒子楼三楼居住,两人一间的宿舍,约十平方米旁边,仅能放下两张单人床和大略的生活用品,虽显得有些拥挤,但对付我们这些来自基层部队的同道来说,已感到非常知足。记得当时与我们同住三楼的还有政治部秘书处、宣扬部、文化部、群工部等单位的单身战友,只管大家分別在不同部门事情,但由于都是年轻人,且大都来自于基层,有许多共同措辞,以是相处得十分融洽,逐步形成了一个亲如兄弟的单身群。
与兵报战友在机关办公大楼顶合影
那时,兵部大院绝大多数干部都携家带口,生活在大院西区的家属楼,而单身必竟是少数。因而,每天紧张事情之后,办公室人去楼空,只剩下我们这些单身汉,难免不免感到寂寞无聊。加上那时部队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电视还不遍及,且频道较少,机关除有时在广场和礼堂放放电影外,其它文体活动并不多。因而每天晚饭后,结伴闲步就成为我们的保留“节目 ”。
兵部大院紧挨着玉泉路,当时在北京算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大院西边全是大片的农田和菜地,记得机关还组织我们帮助附近生产队收割过水稻。以是,平时只要景象晴好,我们便在落日的余辉下,三五成群地溜达于田间小道,呼吸着殽杂各种农作物淡淡暗香的空气,有说有笑地互换着各种信息,偶而还与在田间劳作的村落民们唠上几句,这样既磨炼身体,又愉悦身心,成为我们一天中最惬意的光阴。有时,我们也沿着永定路和玉泉路边的林荫小道,穿行在熙攘的人群之中,感想熏染着薄暮时街头的美景;有时实在不想出大院,就爬上机关办公大楼的顶层平台闲步不雅观景,或坐在办公楼前毛主席雕像台阶上谈天逗乐,也别有一番韵味。
一样平常来说,单身最感孤寂难耐的算是星期天或节假日了,但这也正好是我们最为宝贵的学习韶光。由于只有在安歇日,我们既少有事情的牵扰,更无家务锁事的拖累,完备可以静下心来看书学习。因而一到安歇日,我除了大略打理好个人事务外,大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或宿舍里,较为系统地学习新闻、文史、哲学 、逻辑学等方面的知识,既有利于提升个人素养,又丁宁了寂寞的光阴。有时也给自己放松一下,利用安歇日补补觉、走走街,或约上一两个战友,花上一角钱到机关澡堂去泡个澡,在热气腾腾的水雾中相互搓搓背,也算是高等享受了。当然,有时我们也不甘寂寞,自寻乐趣,如打打乒乓球 、下下象棋,或结伴到郊野去垂钓、爬山等,尽可能地增长生活情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天高气爽的假日,我们报社和宣扬部共六七个单身战友,换上便装,骑上自行车,浩浩荡荡地前往西郊八大处爬山赏景,并用自备的食品和饮料在山坡林间举行了“丰硕”的午餐,大家又唱又跳,尽情尽兴,仿佛回到了童年。可在傍晚返回时,我骑的自行车在半道上爆了胎,由于入夜又找不到修车的地方,无奈之下,其它几位战友只好陪我推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大院,其实让我冲动了好一阵。
不过,对我们这些单身来说,也常享受到一些“分外”的报酬。比如,那机遇关常常组织职员参加一些集会、游园、参不雅观等活动,并安排专车接送。每次报社分到名额后,领导和同事们总是优先考虑我们这些单身汉。正因如此,才使我有机会参加过在公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联欢和在天安门广场的焰火晚会,与中心领导一起欢度佳节 ;也参加过在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大型游园活动 ,亲自感想熏染节日的欢快气氛;我还多次到中国美术馆、北京展览馆 、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参不雅观一些国内外的美术、拍照及其它艺术展,体验着美的享受;那时总政、总后及其它军兵种文艺团体的演出比较多,也让我们免费欣赏到了许多高水平的歌舞、话剧、曲艺等文艺节目,真是大饱眼福。除此之外,有时我们也作为铁道兵机关的代表,参加一些主要的政治活动。比如我曾多次到公民大会堂参加中心和总政举办的专题报告会,及时理解和节制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又如,我曾作为旁听代表,参加过由邓小平同道主持的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的闭幕会,虽只有半个多少时,但令我激动不已;我还参加过中心在公民大会堂为彭德怀、陶铸同道举行的伤悼会,以及为宋庆龄名誉主席举行的哀悼活动。等等这些,都让我印象深刻,倍感荣幸。
与机关单身战友在北京八大处合影
当然,提到单身生活,不得不说到“吃”。我在机关时,大院共有两个食堂,政治部和后勤部共用的第二食堂,就在筒子楼的对面,紧张为单身供餐,也为家属区供应米饭、馒头等主食。那时,我们单身每人都有固定的就餐桌位,每歺须提前预约点菜,并凭预约登记表打菜打饭,月尾统一结帐,直接从人为里扣款。那是个物资供应还比紧短缺的年代,但食堂尽力为我们丰富花色品种,担保饭菜质量,而且只要肯费钱,我们常常可以吃到油炸带鱼、肉沫鸡蛋 、粉蒸肉之类的特色菜,每逢周六,还有各种卤菜供应。特殊是有一种肉沫烙饼,吃着优柔劲道,满口生喷鼻香,我老伴来京探亲时吃过后,连连称好,至今还时常念叨。只管如此,每天吃食堂也有乏味的时候,以是我们也常聚在一起开“小灶”,每逢有家属来队探亲,便成为我们聚餐的“据点”。酷热的夏天,我们去永定路灌回几暖水瓶生啤,就着三五盘凉菜开怀畅饮,既解馋又消暑;寒冷的冬季,我们便炖上一锅猪肉加白菜和豆腐的“大杂烩”,一起来上几口“二锅头”,顿觉浑身热乎。每每推杯换盏之际,大家总是兴致勃勃,有说有笑,乐乐呵呵,战友之情溢于言表。尤其是编辑老田,每当酒酣之际,就会借着酒兴,用隧道的桐城乡音叙说其家世和经历,其抑扬抑扬、绘声绘色,绝不亚于一场精彩的评书演出,令人捧腹不止。
值得一提的是,单身战友之间,无论级别高低,年事大小,都能平等相待,以诚相处。如我的老首长、编辑一科科长陈达仕,当时已是四十多岁的正团职干部,但由于他与爱人两地分居,仍和我们一样挤在单身宿舍,没有丝毫分外,令我十分钦佩。当然,单身战友间有时也免不了个小误会或小抵牾,但只要相互沟通沟通也就云开雾散了。而更多的时候是彼此的关心帮助。那时,机关的住房十分紧张,每碰着有家属来队探亲时,同宿舍的战友都会主动倒出地方,然后自己到处“打游击”,有时实在找不到住处,就在办公室打地铺,也亳无埋怨。有时,单身战友之间也有相互调侃 、开开玩笑,乃至搞恶作剧的时候,以增长一些生活乐趣。一次,有个编辑的爱人来信见告他,打算近期来大院探亲,但沒确定详细日期,他便每天盼着接站的电报。我们几个好事者知道后,便用一张旧电报纸,以他爱人的名义如法炮制了一封假电报。那个编辑盼妻心切,也没仔细辨认,便信以为真,喜滋滋地整顿了房间,第二天又起个大早到集市买回了鸡,并准备吃过午饭后就去火车站接人。我们一看事情闹得有点过了,便立即把原形见告了他。这位编辑虽有些生气,但也很大度,晚上把鸡炖了,让大伙一起改进了生活。事后,不知是谁编了首打油诗 : “半夜三更起,买回一只鸡 ,老婆没吃着,战友打牙祭”。这个编辑的爰人来队后,照样以事把我们一个个数落了一通。
就这样,我们以亲如兄弟的战友之情,一起度过了几年故意义的单身日子。后来,随着一些战友家属的陆续随军,以及有的未婚战友相继在京成家,使单身群的人越来越少;再后来,单身筒子楼逐渐被随军家属作为临时住所而“蚕食”,单身的“地盘”也越来越小,使得我们感到了些许的失落落和孤寂。直至铁道兵奉命撤转,我转业随处所事情,也结束了为期五年多的单身生活。每每想起这段刻骨铭心的青春岁月,就心生留念,感慨万分。
写于2017年11月修正于2020年5月
编辑:朗朗乾坤 圆圆 2020.5.26
来源:新华号 威武铁道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