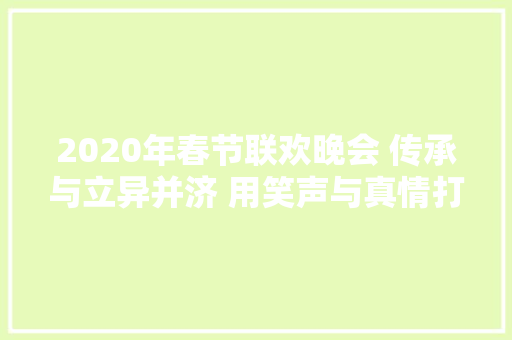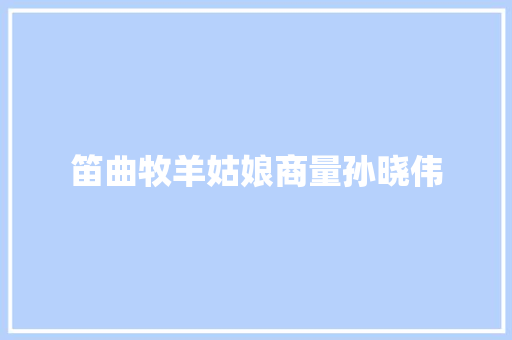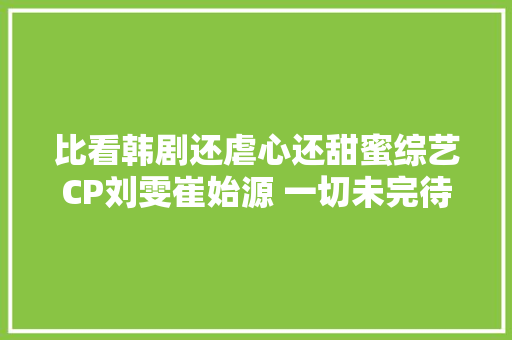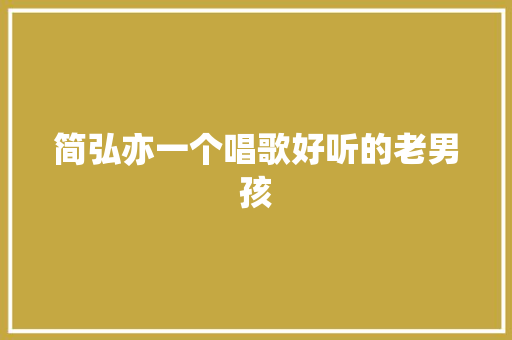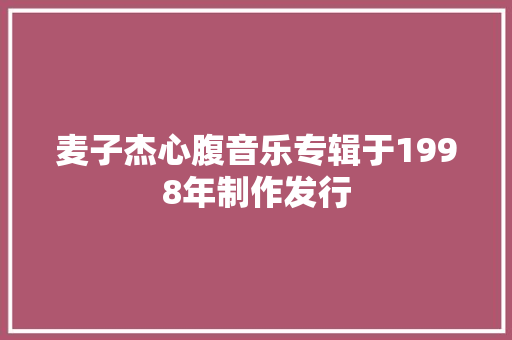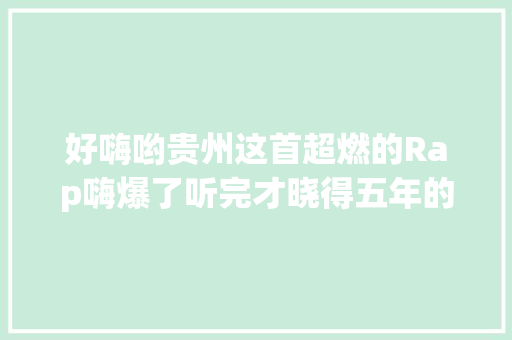想拍“深红国王”(King Crimson)的大导演很多,罗伯特·弗里普(Robert Fripp)都婉拒了。末了他选择了一点也不熟习这支乐队的托比·阿米斯(Toby Amies),希望这位独立影人能带着新视角靠近“深红国王”,少讲点陈年纪迹,多表现这支乐队作为一个群体的演进过程。如果阿米斯够厉害,弗里普希望这部记录片能照亮他的盲区,见告他:“深红国王”是什么?毕竟当局者迷。
成立于1969年的“深红国王”是前卫摇滚领域的提坦神,时期更迭后未被流放到地底不见天日。罗伯特·弗里普是唯一一个从乐队初创效力至今的成员,因此外界很随意马虎以为,“深红国王是罗伯特·弗里普的乐队”。这是对这支谜团般龟龄乐队最大略的阐明。实在不然。“深红国王是干事的一种办法,不是一种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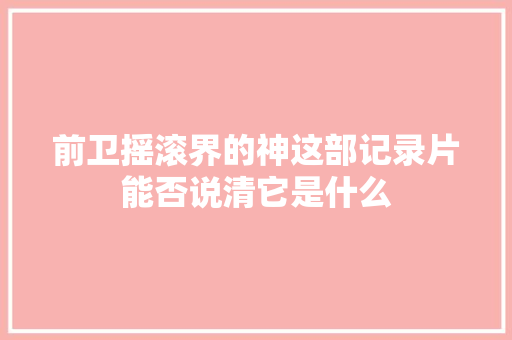
King Crimson (来源: Michael Ochs Archives)
托比·阿米斯的成片《In the Court of the Crimson King》刚刚在西南偏南电影节(SXSW)首映。对古老提坦神感兴趣的歌迷,现在可以离他们近一点。不虞外,弗里普形容的“干事办法”,是很多乐队成员的噩梦。他们或者痛恨它,或者无法理解,或因做不到而退却,或者被阴郁的力量吓退。贝司手崔·甘恩(Trey Gunn)把乐队生涯比作“一种长期传染,你的身体没有生病,但总以为周身不适”。前任成员艾德里安·布洛(Adrian Belew)在乐队期间大量脱发,“彷佛暴露在显微镜下而承受极大的压力”。上世纪70年代曾短暂入伙两小时的梅尔·科林斯(Mel Collins),记得那两个小季候他身心受创。“只要犯一个小错,天下末日就来了。”他很有勇气,第二次入伙从十年前持续至今,证明人的勇气也可能随年事增长。
罗伯特·弗里普 1973年
记录片中的罗伯特·弗里普
罗伯特·弗里普本人是吉他手。外界的印象:他是手持三叉戟(吉他)的狂暴海神,统治海洋的暴君。是也不是。“乐队成立的前44年,我很可怜。2013年开始,乐队阵容里才没有一个恨我的人。”但至少弗里普本人一贯强调,“深红国王是一个凑集体”。证据是:所有乐队赚到的钱都由成员平分,包括自己。他的任务只是把最有趣的人调集到一座录音棚,给他们一个key,见告他们你们有绝对的自由。然而自由太多使人焦虑,成员们均受到这种内心煎熬。
另一个焦虑来源是弗里普对成员“谛听”的极高哀求。如果有成员以为自己比别人更主要或者更有才华,弗里普会严厉地使他打消这个动机。他推崇“即兴的道德”,哀求成员存心听别人,多过把别人拖进自己的声场。上世纪七十年代多位成员被滥用毒品毁掉时,弗里普的愤怒可想而知。他讨厌纪律被忽略,听觉与回应之间的联系被损毁。他为自己的公司取名“纪律”(Discipline),把纪律视作人生信条。很多人只看到这个词严苛,弗里普却瞥见它光彩和肃静的一壁。“它意味着当你说你想做什么,你就可以指望自己真能做成。”
罗伯特·弗里普和“深红国王”的其他成员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相互对抗。第一张录音室专辑《In the Court of the Crimson King》揭橥前四个月,“深红国王”已经得到“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的约请,担当海德公园演唱会的开场高朋。媒体对他们的表现不吝赞颂。《滚石杂志》称其为“不可思议的精品”。
专辑《In the Court of the Crimson King》
那次亮相后的一年内,乐队成员半数离队,包括创始成员伊恩·麦克唐纳(Ian McDonald,今年仲春刚离世)和迈克尔·盖尔斯(Michael Giles)。麦克唐纳德情由是:无法接管自己向不雅观众贯注灌注阴郁。然而对不雅观众来说,正是“深红国王”彭湃的黑潮使人入迷。当采访弗里普的《卫报》作者提到听1970年单曲《Cirkus》时的恐怖,弗里普很满意:“这便是深红国王藏在房间里的觉得。”他知道,“人生很丰富,音乐是生活的反响,该当犹如真正的生活一样跌宕起伏”。
就像其他即兴群体,这支乐队的成员来去频繁。前三张专辑中没有任何成员的照片。那段期间他们从不巡演。乐迷好奇他们的样貌和身份,是人类还是外星人?弗里普说,这是他的刻意为之。“我希望我们奏出无法被眼睛瞥见的音乐。由于,空想化的情形是,音乐和演奏者无关。”
如人所想,弗里普相信音乐有神秘的力量。他说:“你有音符,你有音乐,但在它们之上还有其它。”他阐明寂静和音乐的关系:“寂静潜入音乐,这种包含着寂静的音乐又会流入乐手的手中,流淌出来。”他相信音乐能给人超验的时候,“就像一个人闭上双眼,他的爱人走进房间,就算什么都看不见,他也知道那个人就在那里”。
影片中,一位被弗里普称为“前卫修女”的中年女士把听“深红国王”当作“星期仪式”。导演托比·阿米斯特意在影片中保留了一段三分钟的沉思。当时的情景是,弗里普正在回顾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和已故哲学家JG. 班奈特(JG Bennett)的交往。他在追溯一段主要的对话时陷入沉思,阿米斯没有剪掉那三分钟的入迷。《卫报》的作者问弗里普当时在想什么?“我去了另一个地方,一个罗伯特·弗里普所在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罗伯特在场,所有人都在场。”他说:“如果我看上去非常严格,常常遁入自己的天下,那是由于问题不在于我。各处都是问题。”
弗里普把这种超验的体验视作只有少数人才能到达的田地(确实是)。在近年稳定的乐队阵容中,弗里普认为只有一个人:鼓手、键盘手比尔·莱富林(Bill Rieflin)才能抵达。影片的拍摄过程中,莱富林被诊断为结肠癌晚期。他对着镜头说出寻思熟虑后对待去世亡的态度。弗里普说:“比尔完备接管了这种结果。去世亡将成为他摆脱今生的办法。当他离开时,他会事了拂衣去,走得没有挂碍。”
记录片里的现任乐队成员上台前
一代代的乐手穿过“深红国王”。从影片的采访中,可以瞥见利用同一种乐器的几代乐手重叠在一起。老一辈的很清楚年轻人的感想熏染,“他们(老人)就像希腊戏剧中的合唱队,对正在发生的故事做出陈述和评价”。
影片中有那么多的声音,可罗伯特·弗里普的妻子托娅·薇尔考克斯(Toyah Willcox)认为还有缺憾,有点失落望。她以为,电影里一点都没展现出弗里普有趣的一壁,可导演明明拍了隔离期间他们在周日午餐上翻唱盛行歌曲的欢快情景。
弗里普本人对影片还是很满意的。“托比为我展示了深红国王的某一壁,我以为这一壁很动人,信息量也充足。他没有做到的是,见告我深红国王到底是什么。”真想知道,只能把自己完备地浸入音乐,感知“深红国王作为一股力量的存在”。
任务编辑:梁佳
校正: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