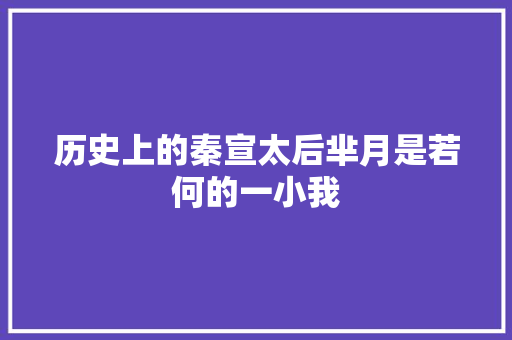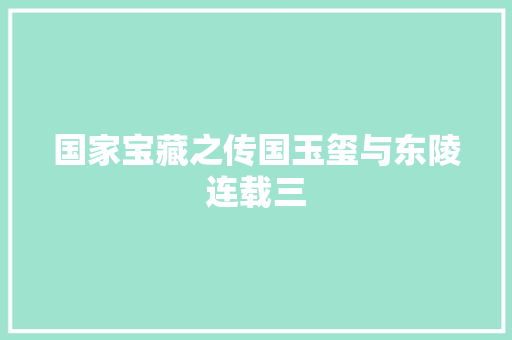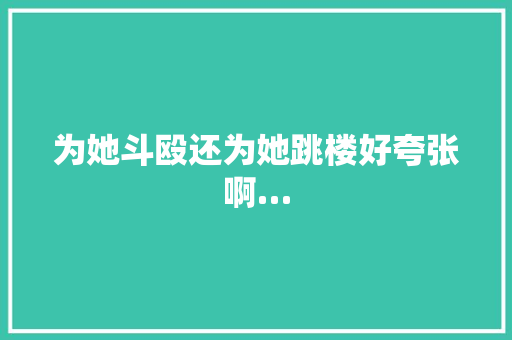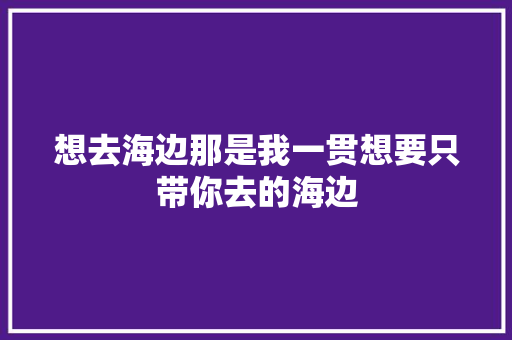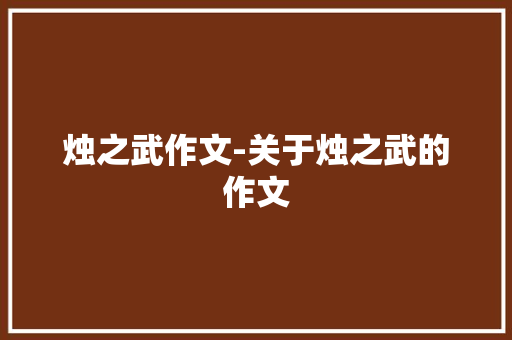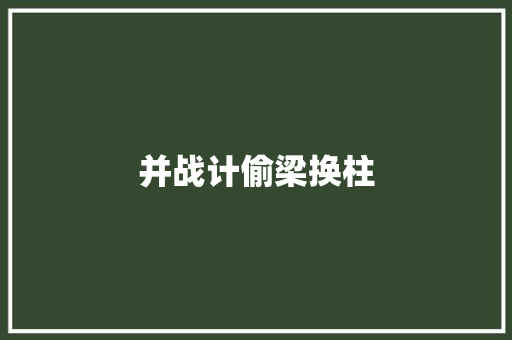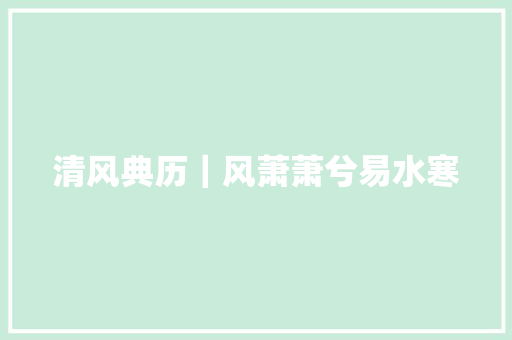从南门到北门的间隔并不远,这么近的路,这么轻的事情,政府竟然乐意花费十金,围不雅观的人都以为不可思议,他们议论纷纭,无人上前,奖赏迅速升至五十金,还是同样的任务。
有人站了出来,出乎所有人猜想,当他完成任务后,竟然真的拿到了赏金,一个言而有信法度严明确当局形象,通过这样一次社会实验很快树立起来,这成了一个大国崛起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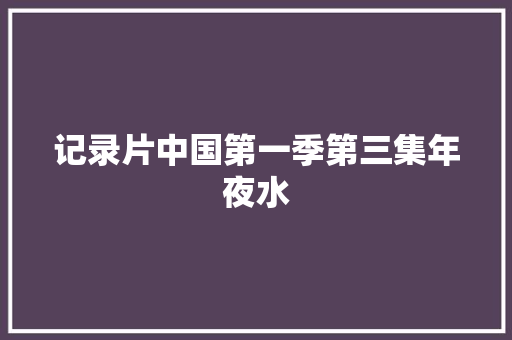
93年后的盛夏,一个名叫荀况的儒家学者来到秦国,此时,秦国已成战国七雄之首,但“儒者不入秦”的法则依然被默认,荀况,是数百年来第一位进入秦国的大儒,儒家学者视他为异类,而荀况不顾声名也要探究的,是天下人共同的疑问。
公元前278年,秦军伐楚,占郢都,烧夷陵,楚国国破,这一天,天空中飞来悲雀无数,遮天蔽日,凄鸣不止,残破的大地上,丢魂失魄的人们脑中只有一个动机,跑!
跑向哪里,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战国末期,经历多年混战,曾经的战国七雄强弱正逐渐揭晓,以公元前284年燕国联合秦赵魏韩险些灭齐为标志,昔日秦齐两大强国间的均衡被冲破,秦国从此一家独大。
面对强秦,七国中领土面积最大的楚国决定放手一搏,却被秦国的60万大军攻入了都城,郢都被破,无数楚国人流落失落所。
这一天,仓皇奔逃的人群中,夹裹着一个怠倦的中年人,他便是荀况,恰好在楚国游学的他,与百姓一同遭遇了战乱,此时此刻,孱弱的荀况和所有人一样,心中只有一个动机,活下来。
荀况是赵国人,年少时便学习了《春秋》等儒家经典,在百家争鸣的彭湃思潮中,他选择孔子作为精神导师,来到楚国前,荀况已在齐国的稷放学宫求学授课十余年,正是由于燕秦赵魏韩五国的联手伐齐,稷放学宫被迫停摆,无奈之下,荀况选择南下楚国。
然而,不息的战事跬步不离,统统犹如六年前那场大战的重现,到处都是离乱、伤痛,红色漫无边际。
眼睁睁看着楚国,这个立足南方数百年的大国被秦国重创,所有人都无能为力,作为一名稷放学者,荀况非常理解当时各个学派的学说,但它们都不敷以阐明面前的这些无助与祈求,这些血与火、爱与恨、善与恶。
荀况深受刺激,他反复拷问自己,这统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他一个手无寸铁的诗人,又能为结束这统统做点什么?
亡命的路上,荀况决定重回稷放学宫,阅历和判断见告他,思想依然是最有力,也是他唯一拥有的武器!
和多数恪守传统的士人不同,荀况一贯有着更开阔的肚量胸襟与视野,他并不排斥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也不偏信儒学先辈的不雅观点,荀况与孟子的性善之说针锋相对,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不同于禽兽,不在于人之性,而在于人之行。
人并不是由于本性中无法避开道德才有道德,而是由于人知道该当具备道德以是才努力向善,因此,他重视制度,强调规则。
要结束世间纷乱,只能靠人的努力,而不是寄希望于定命循环,他的想法在当时是很激进的,以至于很多人质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儒者?
而荀况,现在有了一个更加激进的想法,他想探求儒家与其他学派兼容会通的可能性。
重新回到齐国后,荀况很快参与到规复稷放学宫的事情中,他把楚国文化和游楚心得分享给学生们,同时,他也昼夜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曾困扰过孔子孟子等数代儒家学者,那便是,若何才能让儒学为现实政治所收受接管?
而此时的变局,在这个难题上又附加了一个新的参照,秦国,这个西部小国,为何能以变法崛起而令别的六国闻风丧胆。
荀况决定亲自去秦国看一看。
秦,起身于周王朝最西真个偏远之地,在贫瘠的自然环境与周边各部落的环伺中困难求生,终因养马有功被周王封为附庸,逐渐发展为诸侯国,而现在,秦国铁骑已经遍布各国,攻城掠地,势不可挡。
在世人眼里,以法家治国的秦,仍旧是一个谢绝礼制,未经开化的虎狼之国,也因此有了“儒者不入秦”的说法。
虽然如此,但荀况还是决然地震身了,沿泰山北麓济水南岸提高,一起西行,风尘漫漫,过了函谷关,便是秦国的领地。
踏上这片强大而陌生的国土,荀况心绪繁芜,数十年间,各国无论是王侯公卿还是普通百姓,没有人能忽略秦国的存在,也没有人能躲过它的巨大阴影,然而,荀况创造,那些在战役中被降服的人随后成为秦国子民,他们并没有恨意,反而对秦国抱有认同乃至交感,在这里,地皮私有性子下的男耕女织得到鼓励,战功爵位也不再是贵族的特权,而是大家可以争取的社会身份。
荀况不雅观察了一起,他真实地感想熏染到了“法”的力量,百姓淳厚畏法,官员恭俭忠信,政府的行政效率之高,超乎想象,秦国的法度,就像他们崇尚的玄色一样,镇静、理性、不容置疑,这统统的源头就在九十三年前那个徙木立信的地方,幕后主导者,是一个名叫商鞅的人。
从一根木头开始,秦国立起政府的威信,荀况深刻感想熏染到了隐蔽在法家思想背后的中心集权对付一个国家的主要性。
秦国的国君和丞相接见了荀况,荀况绝不惜啬地赞颂秦国海内安然有序,同时叹服秦国能够在诸国中胜出,不是幸运,不是有时,而是一定,但荀况也开门见山,批评秦国只重法制,在严刑约束与利益诱惑面前,民众成了只知耕战的工具,国家成了一部高速运转的战役机器。
荀况发起,要重视道德教养的力量,不要一味信奉武力,但是,犹豫满志的秦国君臣根本没有将儒家放在眼里,秦王更是直言,儒者无益于治国。
面前金黄的原野犹如一席盛宴,荀况心知,对这个意欲称霸天下的国家来说,自己只是一个局外人。
法和儒,真的方枘圆凿吗?荀况有些不甘!
酝酿已久的美好设计以及支撑着他来到秦国的信念和勇气忽然间消逝了,秦国,此刻就像它所秉持的法一样,冰冷无情。
就在荀况离开秦国不久,秦赵两国会百万大军于山西长平,时人这样形容这场战役,“长平之下,血流成川,沸声若雷”,终极,秦军以二十万伤亡的代价打败赵军,并将四十万赵国降军全部活埋。
荀况明白,秦国的政治制度,再一次彰显了它的强大威力,同时他也更加清楚,那里,不是他能够实现政治主见的国家。
公元前255年,年近花甲的荀况再次来到楚国,并在楚国丞相的提拔下出任兰陵县令。
间隔兰陵西南数百里外的楚国上蔡,生活着一个默默无闻的郡小吏,他叫李斯。
出身布衣,写得一手俊秀的羊毫字,在郡里做的事情是基层文书,平日里为数不多的娱乐便是带着儿子牵着黄狗去城外打野兔,他就这样活到了30岁,享受着一个普通人所能拥有的全部安稳与快乐,也承受着一个普通人不得不笑纳的平凡与卑微。
空虚的生活就像石子被抛上天空,飘渺得不知会落向何方,但,大概他生来便是属于天空的,只是须要一个机会。
终于有一天,李斯决定,不再过假装快乐的生活,他要做一个有为的士人,拜师求学,便是改变人生的第一步。
在离上蔡不到二百里的一个小村落,一个叫韩非的人刚刚游学归来,正准备再次出发。
他是韩国王室公子,拥有李斯不可企及的出发点,但,他同样烦懑活,韩国是战国七雄中国力最弱的,而且,韩国挡住了秦国东出的门户,秦国险些年年向东方发动攻势,韩国屡战屡败,为躲避战乱,韩非只好到这个离韩楚边疆不远的小村落避难。
与李斯不同的是,韩非日思夜想的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如何让韩国由弱变强,摆脱亡国危急,他动身前往兰陵,希望找到救国之方。
就这样,李斯和韩非,两个出身完备不同的年轻人不谋而合地拜到荀况门下,荀况知道,李斯和韩非都是难得一见的青年才俊,他常常与这两个徒弟纵情山野,把多年的思考讲给他们听。
曾经,贤人制订礼乐,并以此管理国家,但礼乐教养奏效韶光过于漫长,而且,一旦人们违礼,则无从约束。
以政府逼迫力为后盾的“法”,恰好可以填补“礼”的这一不敷,平治天下,必须礼义与刑法并重,于是,荀况援“法”入“礼”,取儒法理念各自的上风,提出礼法互补的治国模式。
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就像兰陵盛产的美酒一样,荀况的思想经由发酵沉淀,日渐成熟,此时,他已进入晚年,他想把自己的治国蓝图和政治空想请托给最看重的两个弟子。
但无论是李斯还是韩非,他们求学都带有明确的现实诉求,对付老师的治国之道,他们有各自的意见,荀况虽然提倡礼乐与刑法并举,但他始终坚持儒家才是最根本的办理之道,应以礼乐为本,刑法为辅。
李斯则以秦国为例,提出相反的见地,他说,秦国四代胜出,在四海之内兵力最强,他们所依赖的并不是仁义,而只是根据面前的现实去做,对付李斯来说,秦国的政治便是治国的最好榜样。
荀况一向鼓励学生揭橥不雅观点,但李斯的辞吐却遭到他的激烈回嘴,他告诫李斯,看问题要看到根本,不要只看到表面,虽然看上去秦军战无不胜,但实在,已是与全天下为敌的末世之兵,正是由于这个时期大家都舍本逐末,以是世道才会如此混乱。
荀况是深刻的,未来的历史将验证这一点。
韩非说话不多,思想却是静水流深,只管接管了荀况的很多不雅观念,但韩非也敏锐地认识到儒学的弱点。
他认为,儒家以孝言治,但百姓却很少能肚量胸襟大义,以是仁政行不通,儒家有德无势,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治国不能依赖明君贤臣,而必须在庸君庸臣的根本上来进行制度设计。
迫切想要挽救国家危亡的韩非,最崇拜的人不是老师荀况,而因此一人之力旋转了秦国命运的商鞅。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逐渐以法治代替礼治,以战功代替世禄,以中心集权代替领主分治,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升。
韩非总结商鞅、申不害、慎到这三位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主见君王该当用“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管理国家,并且明确提出“法不阿贵”,在律法面前不分贵贱,有权有势的人也要受到同样约束。
李斯佩服韩非的学识才华,韩非则欣赏李斯的乐不雅观果决,而且,他们对法家有着惊人的同等认同,他们都认为,思想要做事于政治必须顺应时期须要。
思想者以思想缔盟,在评点江山的激扬岁月里,二人结下了兄弟般的情意。
韩非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不能两成,既然认定了“法”的道路,那就要专注地纯粹地走下去,用超乎凡人的定力和坚不可摧的信念走下去。
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同门师兄李斯有着不言而喻的默契。
世事之困难,有如涉水前行,李斯和韩非都不愿定自己会走向何方,何处是激流涌动,何方是暗礁险滩,但在兰陵共同度过的日子,让他们内心多了一份无言的笃定,他们相互理解,互为心腹,有时他们以为可以一贯结伴而行,共同实现胸中凌云之志。
虽然,两个学生都背弃了荀况的儒家根基,但活着界大势的判断上,师徒三人却有着同等的结论。
数百年的混战局势,即将结束。
李斯自认为学识不如韩非,而且,韩非所追寻的是世间至理,李斯则看重学甚至用,他更想通过这种办法改变命运,李斯自傲会走出一条与同学和老师不一样的路,由于他有勇气赌上自己的人生。
公元前256年,秦国军队攻破周王城洛阳,周朝的末了一位天子被废,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宝器被搬到秦都咸阳,很明显,决出终极胜负的日子越来越附近。
李斯仿佛听到来自西边的无声召唤,他神往那片地皮。
那一天,兰陵的景象很好,是一个适宜远行的日子。
最喜好的两个学生就要走了,荀况的心情五味杂陈,他知道,此一去,师徒间便是永别。
李斯和韩非,分别要去往不同的地方,李斯虽然是楚国人,但他深知,天下的未来和自己的未来都在秦国,他说,机不可失落,时不再来,现在秦王要吞并天下,称帝而治,正是布衣游士显技艺之际,以是,他选择去秦国。
“来日,韩秦开战,愿兄不在秦军之中!
”
韩非选择回到韩国,先人基业是他生平都无法背弃的,韩非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倾慕李斯,他虽然贫贱,确是自由的,他没有任何羁绊,只为自己而活。
人各有志,荀况从来都是一个宽容的老师,他生平见证过许多大事,但此时,就连他也无法判断,这两个学生,谁的选择是精确的,荀况遗憾自己,不一定能看到结局,只管他对结局无比期待!
李斯沿着荀况当年的脚步,西行踏上秦的地皮,未来的他们,会在哪里相见?
并肩走过求学岁月的两个人,就这样,背负着各自的义务和欲望,走向各自的命运,也走进了战国末期风云变幻的历史年夜水中。
来到秦国后的李斯,并没有等待良久,他积极地向秦国的权臣自我推举,以期进入官场,并捉住统统机会,让自己的才华被把稳到,没有人知道,他的野心比才华还要大。
有一天,他收到秦王嬴政召见的。
历史为李斯准备了一个秦国,也为秦国准备了一个李斯,现在,他们正式相见了。
十三岁登上王位的嬴政,很早就有了统一天下的想法,他之前的数代秦王,业已为他打下雄厚的根本,李斯涌现的机遇刚刚好,他献上了吞并六国的构想,“阴潜谋士,重金收买六国大臣,不为秦所用者,利剑杀之,然后军事进攻”。
嬴政确定,面前这个外表平平的读书人,能够帮助他实现梦想,从此,李斯得到提拔重用,随着秦国的不断扩展,十年间,李斯的地位平步青云。
同样的十年,韩非的生活,则是苦闷而压抑的。
他回到韩国时,韩国国土仅剩下都城及附近的十多座城邑,是七国中面积最小、军事力量最弱的国家。
韩国位于秦军东出函谷关后的必经之地,因此,一贯处于强秦铁蹄的威胁下,为求自保,他已向秦国称臣纳贡多年,出身王室的韩非忧心不已,他多次上书国君,陈述富国强兵的方略,却始终不被采取。
每一个时期都有它辜负的人,滚滚年夜水中,个人命运微不足道,但对救国无门的韩非来说,被辜负的确是全部的天赋、才智和羞辱之心。
韩非不甘心平生所学就这样埋于暗椟,于是,他将政治见地付诸笔端,写下了集法家思想大成的《孤愤》《五蠹》等十余万字的著作,被后人辑为《韩非子》一书。
韩非早已清晰地看到,这个时期与以往显著不同,如果还用先王之政治该当世之民,那就像是守株待兔。
韩非不雅观察锐利,下笔彭湃,对世事鞭辟入里,读到他文章的人,无不惊叹拜服。
然而,只有他的祖国,韩国,仿佛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些宝贵的见地,浮云般逝去的年华里,陪伴韩非的只有他的笔和从不在人前出鞘的剑。
虽然不被韩国重用,但他不会放弃,他感到自己的血,仍在沸腾,心仍在跳动。
公元前233年的一天,已经身居高位的李斯来到咸阳城外,他要亲自去欢迎一位客人。
来人正是他的同门师弟,韩非,兰陵一别,两人已有十四年未曾见面,点名要韩非前来秦国的人是秦王嬴政,他无意间读到被传入秦国的《孤愤》《五蠹》,抚掌感叹道,如果能和此人畅谈一番,去世而无憾!
李斯见告秦王,作者韩非,是我曾经的同学,于是,始终不被重视的韩非就这样被韩王送到了秦国。
李斯认为,他或许终于可以跟韩非携手,共同辅佐秦王,首创前无古人的功业,但,统统都不复当年,他们彼此间的地位彻底翻转了,李斯从昔日的一名小吏变成天下最有权力的秦王身边最有权力的重臣,而韩非,则从王室贵公子变成死活握于他人手中的一枚外交棋子,是韩国用来谄媚秦国的一个人质。
李斯在瞬间溘然觉醒,梦一样平常的兰陵光阴再也回不去了。
韩非很快被嬴政召见,嬴政正在酝酿发动攻灭六国的战役,他准备采纳李斯的建议,先肃清最近的障碍韩国,同时对其它国家形成震慑,此事已成定局,嬴政信心满满,他希望从这位法家年夜师身上得到一些做帝王的学问。
但韩非却偏偏逆向而行,他献上《存韩》一书,哀求保全韩国,这显然不是嬴政想要的策论。
李斯明白,纵使遭受了那么多冷遇,韩非心里永久无法割舍故国,以是,他们注定只能成为仇敌,李斯深知,韩非以及他的存韩论与自己的主见恰好背道而驰,他建议杀了韩非。
嬴政有些犹豫,他敕令先将韩非囚禁起来再做决定。
失落去自由的韩非,没有等来可能的一线活气,他等来的是师兄李斯以及李斯送来的鸩酒,李斯不会容忍任何障碍阻挡秦国阻挡自己。
韩非已经做了所有该做的事,只管他的疾呼无人谛听,只管祖国弃他如敝履,这一刻,它更像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者,而非镇静实用的法家。
命运如此弄人,最赏识他的人是祖国最大的仇敌,最理解他的人,是面前要置自己于去世地的故人故友,在生命的末了瞬间,韩非彷佛更能理解李斯,或许李斯才是对的,他才是那个更专注更纯粹的铁腕法家。
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聊以抚慰,那大概便是,他和李斯之间的默契了,韩非猜想,面前这个最好的朋友和最强的对手将会把自己的学说发挥到淋漓尽致。
韩非去世后的第三年,秦国攻陷韩国。
自灭韩开始,秦国开启统一六国的征伐。
公元前228年,秦军俘虏赵王,盘踞赵国全境,赵公子逃到代郡。
公元前225年,秦军包围魏都大梁三个月,城破,魏国灭亡。
公元前223年,秦军盘踞楚都寿春,俘虏楚王,楚国灭亡。
公元前222年,秦军攻取燕国的辽东,燕国灭亡,进而进攻代郡,肃清赵的残余势力,赵国灭亡。
公元前221年,秦军攻进齐都临淄,齐王屈膝降服佩服,齐国灭亡。
自此,天下皆归秦国,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发布闭幕。
一个时期的帷幕连忙落下,一个新的时期迅即来临。
嬴政用十年的韶光完成统一大业,数代人苦苦追寻而不得的空想彷佛正在实现,人们放下刀枪,从沙场上走下来,奔赴荒漠已久的家园,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分封制度就此开始沉寂,由分封制衍生的世袭贵族阶层也随之被冲破。
当天下再次成为一家,原来寄托于各诸侯的臣民被纳入一个新的统一的国家组织,他们被授予平等的法律地位,并以户籍的形式牢牢与地皮捆绑在一起。
个体的力量空前壮大,国家和公民开始了崭新的关系,曾经散落四方的民气逐渐归拢一处,这将是一个完备迥异于过往的新国家,无限可能在孕育。
当然,统统都还须要韶光,更须要聪慧!
统一六国这年,秦帝国挑选天下最好的工匠打造了一枚国玺,嬴政选择来自西部的和田玉,让工匠刻上李斯用小篆书写的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他期待秦帝国能和这块玉玺一道,传给一代又一代子孙。
此刻,那些芸芸众生、贩夫走卒都在不雅观望,李斯可能会想起初生荀况当年说过的话,吞并别国是随意马虎做到的,但巩固凝聚它确是很难的!
是的,这个看上去已经统一的国家,如何才能长治久安、世代相传?